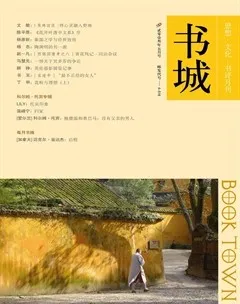“最不正經(jīng)的女人”
| 1 |∣在悉尼、墨爾本或舊金山、溫哥華這樣多元文化的移民都市居住,你有機會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跟在紐約或倫敦那些超級國際都市里的金融家律師政客們不同,他們成為世界公民是因為他們的靈魂 (global soul)而不是他們的資本(global capital)。因為對另類生活的好奇,他們從世界的一端漂到另一端,尋找能夠讓他們有感覺的生活, 或者前世似曾相識的家。而因為這些人的存在,你會覺得這座城市的空氣有所不同,充滿靈感、想象、激情和冒險。
澳洲女作家琳達(Linda Jaivin)就是一個這樣的世界公民,她出生在美國東北部的康州。在白人新教中心的新英格蘭,這個祖先是俄國移民的猶太人自幼就覺得自己與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于是年紀輕輕就跑到東方闖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在臺灣學習中文,然后到香港做《亞洲周刊》的記者,往來于兩岸三地,目睹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許多歷史時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港臺三地的文化圈子里,琳達是以“集合”地下藝術家搖滾音樂家和外國記者的派對著稱。當年,可能唯一比她更有名的外國人就是她的前夫,現(xiàn)在是澳洲國立大學著名漢學家的白杰明(Geremie Barme)。白杰明也是澳洲上世紀七十年代最早到中國的留學生之一,他那一口能跟北京人媲美的中國話,還有比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犀利尖銳又嬉笑怒罵的文章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報刊上名噪一時。如今的大山(Mark Rowswell)、大龍(Johan Bjorksten)一類的老外名流與當年的白杰明不是一個層次,因為他們耳濡目染的是世紀之交的市井文化、娛樂文化和商業(yè)文化,最后都退化成了來中國摟錢的老外。而白杰明,那才是只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能產(chǎn)生的文化精英, 他引以為師為友的是楊憲益夫婦、吳祖光夫婦、錢鍾書夫婦和黃苗子夫婦那些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琳達終于落腳在悉尼,這個邊緣世界的中心,這個為墨爾本人所不屑的“膚淺的、享樂主義的悉尼”。這些年,說著一口好中文的她在主攻小說寫作的余暇,也還翻譯介紹中國的文學藝術,像王朔的小說,像《霸王別姬》、《英雄》等電影的英文字幕,都出自她手。她也還時不時到中國,也許在三里屯的“書蟲”咖啡屋,你會與她不期而遇。
這個有著一頭火紅色頭發(fā)的女人,她的中文名字叫賈培琳。
| 2 |∣琳達的小說處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吃我》(Eat Me),一本不厚但在澳大利亞印了十余次的情色小說。今年又被在澳洲和新西蘭頗有盛譽的文本出版社(TEXT Publishing Company)選中重印, 成為該出版社的“文本經(jīng)典”(Text Classics)叢書系列之一。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四位三十出頭的悉尼白領麗人。朱利亞是攝影師,香桃是時尚雜志的編輯,海倫在大學里做婦女研究的教授,而費利帕是個作家,正在寫一部情色小說。這幾位都住在內(nèi)城(inner city),還是閨蜜,時不時一起泡咖啡館、聚餐什么的,有時不期而遇在朋友們的聚會上,交換她們的情色冒險。這樣說起來有點像《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里的那四個曼哈頓女人,不過雖然《欲望都市》可能更有名,《吃我》可是在一九九五年就出版了,比《欲望都市》早兩年。澳洲作家琳達當然沒有紐約專欄作家Candace Bushnell那樣占天時地利的優(yōu)勢,但從小說的挑戰(zhàn)性觀念和語言上比較,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我看來,《欲望都市》本來就是美國新教主流遮遮掩掩“禁欲文化”的產(chǎn)物,再經(jīng)過HBO附和大眾趣味的改造,早就變成了都市女性的購物指南和新型的“良友”畫報,倒是《吃我》,還保持著一塊天然去雕琢的璞玉的坦率真實,是經(jīng)過第二波女性運動后成長起來的都市自由女性大膽奔放、恣意而為的情色宣言。
書的開章就是午夜超市的一角,一個大膽放肆的熟女正自得其樂地往嘴中和陰道里交替放著各種各樣的水果,無花果、草莓、葡萄,水果的汁液和女人的愛液混合在一起,女性欲望的氣味充斥在水果蔬菜區(qū),向已經(jīng)要沉睡的午夜超市的其他角落蔓延。而在那里,一個為超市所雇的男偵探早忘了他的職責,沉浸在偷窺引起的快感和罪感之間。終于他也成了女人獵取快樂的一部分,臣服在她的裙下,接受她“吃我”的命令。
這刺激惹火的場面其實是費利帕正在撰寫的小說的一個場景,但也可以說是琳達《吃我》這部小說的一個主題隱喻。成熟自信的女性對性愛的欲望和享受—不止是來自異性—就像品嘗生活中最可口的水果點心或者各式大餐,是她們膨脹的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也是她們與這個世界發(fā)生最親密的關系的一種方式。
對于那些對悉尼人文地理感興趣的人,《吃我》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就是它可以充當一幅城市歷史風俗畫,通過書中特定的女性的眼睛,日常的生活情景帶上了享樂的性感的色彩和趣味。琳達筆下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悉尼內(nèi)城,諸如Pitts Point、 Darlington、Woolloomooloo、Glebe、Surrey Hill和Newtown,是這些女性主義者冒險的樂園,是她們獵取快樂的狩獵場。顯然,那時的Newtown還是城市“下只角”,是還沒成功的藝術家或說流浪漢游手好閑和不務正業(yè)的另類大本營,雖然破舊擁擠骯臟,但是散發(fā)著一種頹廢的誘惑和扭曲的靈感,就像那個神秘的流氓詩人Bram對二十出頭的女大學生香桃的蠱惑一樣。
今天的Newton已經(jīng)和溫哥華的Yaletown、Kitsilano或灣區(qū)的Oakland, 從嬉皮的公社實驗田變成了新雅皮用來炫耀的可增值的投資資產(chǎn)。這里臨近市中心,悉尼大學和科技大學則符合以研究生和教授為頭領的城市白領昂貴的品位,因此房價和租金二十年間翻了幾番,街上的景物人物也早已物是人非。那些已逝的二○○○年奧運會前的悉尼則只有通過琳達活潑生動的筆觸來體會觸摸了。維多利亞街上的Da Vida咖啡館,剛流行的英國樂隊Portishhead的音樂,Paddington 排屋周日花園酒會,它們通過琳達感性的眼睛和細膩的文筆,再一次生動活泛起來,向我展示昔日的流光溢彩和芳香氣味。
| 3 |∣寫情色小說的琳達也許是有意讓悉尼的聲色犬馬來幫助她遺忘剛剛過去的一段歷史。這有點像她的職業(yè)轉(zhuǎn)換,從一個以時事為焦點的新聞記者突然轉(zhuǎn)向了幻想世界,那種轉(zhuǎn)身的突然與決絕讓人不禁揣測后面沒說出來的故事。
三十年后回頭再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臺灣和八十年代的大陸是海峽兩岸的文藝復興和文化啟蒙的時代,那是改革開放還未被商業(yè)化浸染的依然有夢想的時代。而這一時代的精神和兩地的某種精神聯(lián)系,被琳達這來自美國的不安分的靈魂敏感而細膩地感受捕捉到。在她一九八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移居澳洲后,她嘗試用寫作來祭奠那段歷史。希望借助語言,借助紙和筆,給往日那些隨風飄揚的思想與刻骨銘心的經(jīng)驗一個棲息之所。
《猴子與龍》(The Monkey and the Dragon)就是琳達對已逝歷史的一份深情的懷念。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西方“中國熱”時出的大量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和歷史見證相比,二○○一年出版的《猴子與龍》是我所讀過的寫二十世紀八十年中國的文化氣質(zhì)和精神狀態(tài)(包括兩岸三地)最好的一本書。

準確地說,《猴子與龍》是寫臺灣歌手侯德健在大陸的奇遇,他不安分的人生的一段最有色彩和反諷意味的插曲。因此,琳達的歷史寫作是以感性的個人史出現(xiàn),帶著歷史中個人的獨特性和矛盾性這一人文關懷。而這段插曲所折射的兩岸三地的文化和社會變遷,則更飽含豐富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內(nèi)容。侯德健是那個時代不多的橫穿海峽,用流行音樂改變兩岸僵硬的政治文化的侯德健。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臺灣和大陸,他都曾經(jīng)是一面旗幟。他一九八三年從臺灣投向大陸,受到熱烈歡迎和特殊待遇,成為當時兩岸三地的話題。六年后,再度成為左右不討好的風云人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臺灣和大陸在向商業(yè)社會一同“忘記前嫌”攜手并進的時候,當年最愛熱鬧的政治明星演藝明星侯德健卻在天涯海角人煙稀少的新西蘭鉆研《易經(jīng)》,成為一位風水大師。

琳達與侯最初的交往是在臺灣和香港,他們是有著二十多年交情的摯友,分享了他們各自生命中最不安分也最理想主義的時刻。所以,這本書也是琳達自己的心路歷程,你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東方的好奇和摯愛,她與中國朋友的交情和誤解,還有她對西方流行藝術和時尚對中國文化啟蒙的影響的理解。無疑她是希望以個人的故事來寫一個大時代。其實琳達自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離開大陸就開始了該書的寫作。也許她早就預知自己曾目睹了的這份歷史的凝重和時光流逝將帶來的遺忘的后果。因此書寫中國的八十年代不僅是她個人的懷舊,而且有一種倫理的責任。經(jīng)過幾年的研究和資料搜集,她寫成了第一稿,可是那種客觀的學術式敘述連她自己都不滿意。于是她推倒重寫。當這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在澳洲出版時,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jīng)開始了。
可惜反諷的是,時光流逝對于書中的那片土地和人群卻有了別的意義,在神州大地處處以高鐵的速度奔向未來的時代,很少還有人停下來,想想我們的過去,我們從哪里來。前段時間,我認識的一位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后到中國去做田野調(diào)查,追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界的歷史,幾乎沒有人有空甚至愿意去回憶。他們很不理解為什么一個外國學者會對那“原始”的階段感興趣:與如今的書籍種類和包裝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簡直不值一提。與現(xiàn)在無關,甚至有些牽制現(xiàn)在前行的記憶,他們自愿放棄。
當然,大概也很少有年輕人知道侯德健是誰。雖然侯最有名的歌曲“龍的傳人”依然傳頌,而且隨著中國的盛世崛起,這首被定位為民族主義的神曲應該越唱越響。不過,讀了琳達的書,你會注意到我們很少意識到的這首歌所具有的模糊語義;你也許還會注意到歷史的反諷:在這只熱情、敏感、不安分的猴子與龍的搏斗中,龍究竟是什么?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藝術家自己也參與了制造龍的神話,當年侯一心回大陸尋根,尋找他父親的故鄉(xiāng),卻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已棄他遠去,他才是時代的落伍者。
也許侯的歸隱,才是他真正的覺悟。

| 4 |∣二○○八年五月的一個周末,我跟一位朋友,麥克考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Pal Ngril坐火車去悉尼西南郊的小鎮(zhèn)Campbelltown。那里的藝術中心自從二○○五年改建后成為大悉尼地區(qū)一個很活躍開放的社區(qū)藝術中心。我們這次是去參加一個新書發(fā)布會,順便看看就要結(jié)束的艾未未的畫展。
新書發(fā)布會就是琳達主持,她的客人是遠道而來的加拿大名記者兼作家黃明珍(Jan Wong)。 黃是來推介她的新書《中國秘檔》 (Beijing Confidential: A Tale of Comrades Lost and Found,英國版名為Chinese Whispers: Searching for Forgiveness in Beijing)。我在溫哥華讀書時經(jīng)常能在Global and Mail上看到黃的文章,那時她有一個訪談名人的專欄。黃以言談激烈尤其在宗族歧視上非常敏銳著稱。她是第二代、第三代華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美讀書時就是個理想主義的毛分子。一九七二年中國一恢復與西方世界的聯(lián)系打開國門,她就是最早到中國的北美留學生,是周恩來總理特批的兩個到北京大學的留學生中的一個。那年她十九歲。這段留學經(jīng)歷使得她寫出后來成為亞馬遜暢銷書的《紅色中國布魯斯—從毛到現(xiàn)在,我的長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而新書《中國秘檔》就是黃以當年她做的一件讓她負疚的告密事件為引子,二十多年后再訪北京的所見所聞。不難看出,從個人經(jīng)歷和對中國的情感上,琳達與黃自然惺惺相惜。
文化中心能容納三四十人的小會議室坐滿了,中國這個題目對澳洲人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三十年的急劇變化,不僅中國人自己,就是像琳達與黃明珍這樣當初最早目睹中國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的感慨。
那天新書發(fā)布會和簽名結(jié)束后,已經(jīng)是下午三點了。我們一行人在文化中心的室外咖啡館坐著,享受著澳洲秋日金色的陽光。談話的題目東拉西扯,天南海北。中國似乎離我們真的很遙遠。
| 5 |∣近年來琳達又開始追尋莫里循的故事。
莫里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大概是在中國最有名的澳洲人,他的故事現(xiàn)在幾乎是人盡能詳。近年來國內(nèi)陸續(xù)翻譯出版了莫里循的各種傳記(包括他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不大有文化的人也能從那部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xù)劇《走向共和》記住了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非凡痕跡的澳洲人。
莫里循二十一歲就在澳洲本土以冒險家而出名,他長途跋涉,兩次穿越了這片不久之前還是蠻荒之地—以不守法律而著稱的新大陸。年輕的他隨后又跑到其他大陸上探險。在南太平洋上的新幾內(nèi)亞島與土著人遭遇。那一次遭遇在他身體里留下了兩塊矛頭。他在愛丁堡大學醫(yī)學院治傷之余,讀下醫(yī)學博士學位。畢業(yè)后又到美國、西班牙和法國巴黎學習行醫(yī),直到一八九○年才回到澳洲的維多利亞州。但年輕不安分的他不久就選擇再次漂流世界。一八九四年進入中國西部。翌年出版的《一個澳洲人在中國》(An Australian in China)為他贏得了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也贏得了英國《泰晤士報》的賞識。一八九七年英國《泰晤士報》終于決定聘他為該報第一個永久駐華記者。莫里循從此在皇城北京定居下來,逐漸成為中國問題的專家。在世紀交替的那幾年,中國北方尤其是滿洲成為列強明槍暗炮的爭奪目標,而莫里循跨越大洋的電報稿常常因其驚人準確的預言使《泰晤士報》成為遠東時事的權威。在一九○○年義和拳攻占北京的六月到八月間,他又因保護婦女組織反擊成為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中人人皆知的英雄,而且七月間因為誤傳他陣亡,《泰晤士報》還發(fā)了兩版追悼文章,更使他成為帝國的一面旗幟。莫里循在華期間也結(jié)交了大批上層人物和政府官員,有時為他們與外國政府引介周旋。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間他一度成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和談中還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和談。不過,雖然莫理循一生超過一半時間是在遠東中國度過,但一九二○年他死時還是選擇在英國,在內(nèi)心深處,他畢竟還是大英聯(lián)邦的臣民。
這個被外界所知的“北京的莫里循”在歷史上留下他個人痕跡的同時,也具備一個天生的歷史學家對史料的敏感和勤奮。除了冒險和時事新聞,他的另一個傳奇就是他的圖書館。在北京的幾十年,他搜集了大量圖書文獻,從傳教士的內(nèi)部通訊,到他自己拍攝的各類照片,從各式各樣的日常用品、名片到最珍貴的中國典籍,這些東西他都悉心收藏并分類,保管得井井有條。一九一七年,他把這個圖書館的部分藏品以三萬五千英鎊的價格賣給一位日本商人,后來成為東京遠東圖書館的鎮(zhèn)館之寶。莫理循去世后,這個圖書館按他的遺囑被全部搬回故鄉(xiāng)澳洲,如今在新南威爾士州博物館里。幾年前,移居澳洲的中國藝術家沈嘉慰把其中的老照片收集到一起,編成了三卷本的視覺歷史書《莫里循眼中的中國》。據(jù)說這本書對國內(nèi)出版界有一定影響。我不久前回中國,就看到大量翻譯的外國人回憶錄。在晚清民國歷史被嚴重毀壞和丟失的情況下,形形hB/hCVMV0zZb8YJXdeavog==色色的外國人,從傳教士到外交史官到記者作家,他們的視角和記憶成為一個彌足珍貴的資料庫。
莫理循傳奇般的經(jīng)歷和大于凡人的性格無疑是史學家傳記作者們最好的素材。在他們的筆下,這個有著人類冒險和博愛之心的先行者,這個十九世紀殖民文化的產(chǎn)物,無疑也帶著歷史的局限和爭議。所以莫里循也被一再書寫。
如今,一個女人,一個小說作者也想寫莫里循,而且她想寫他的私人生活,被他的公共形象或人格面具所掩蓋的私人生活,而這段私人生活又是從莫理循與一個不守常規(guī)的女性的遭遇講起,那將是一個多么“不正經(jīng)”卻有趣的故事。這個故事有個最恰當?shù)拿帧耙粋€最不正經(jīng)的女人”。
| 6 |∣《一個最不正經(jīng)的女人》(The Most Immoral Woman) 截取的是歷史的一個片斷,一九○四到一九○五年日俄開戰(zhàn)的那一年。熟悉歷史的人知道西方各國對日俄戰(zhàn)爭的關注度。而對中國人,這是近代史上又一個侮辱性的事件,兩個爭奪霸權的國家在第三國的土地上開戰(zhàn),讓那里的人民遭殃,滿清政府無力無能到如此程度。因為莫理循準確地預言了戰(zhàn)事的發(fā)生以及戰(zhàn)爭中來自某些方面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場戰(zhàn)爭又被稱為“莫理循的戰(zhàn)爭”。
但在莫理循的個人歷史上,這一年也許是他,這個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的滑鐵盧。這一年早春,他在山海關遭遇了梅·珀金斯(Mae Perkins)小姐,被他愛稱為梅西的一位自私任性、放蕩奢華的美國女人。即使對見多識廣的莫理循,珀金斯小姐代表了他所不熟悉甚至也不能理解的新型女性。二十世紀最早出現(xiàn)的“新女性”,從時尚畫報上的Gibson Girl,到現(xiàn)實生活中的愛麗絲·羅斯福(Alice Roosevelt,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女兒),她們掀起了爭取教育權利、工作權利,甚至選舉權的運動,并開始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梅正是上流社會開風氣之先的這類新女性,雖稱不上真正獨立的女性—她的父親是加州的百萬富翁,也是加州在國會的議員,這是她揮霍交游的基礎,但無疑她享受著豐厚的物質(zhì)帶來的精神上的自由以及社會變革給女性帶來的機會。早在一九○三年就以單身未婚女性的身份到歐洲和東方旅行,一路上屢屢出擊,艷遇不斷。從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到舊金山的牙醫(yī),從荷蘭的外交官到駐遠東的美國記者,她把他們玩弄于股掌之上,絲毫不擔心自己的“前途”—她繼承的家產(chǎn)足夠養(yǎng)活她自己。

也許正是她的無所事事,她的不計功利,使她對她周圍的雄性政治性動物的虛偽與野心有了局外人的洞察和了解。在書中,她是唯一敢挑戰(zhàn)和調(diào)侃莫理循的人。時過中年的莫理循,已經(jīng)不再是當年那個穿越澳洲大陸、探險亞洲的有著朝氣與信念的青年,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以及作為帝國代表的權威。幾十年殖民地政治文化的熏染,使他身不由己地成為另一個殖民主義和男權社會的維護者,即使時不時他也許會在他持續(xù)幾十年的日記中流露一點矛盾與遲疑。
于是,在琳達的小說中,梅這個新女性才是小說的主人公,她帶著美國物質(zhì)文化的奢侈自信,帶著女性對自己的權利和欲望的充分認同張揚,嘲笑并顛覆著莫理循的世界,使他陷在這個“最不正經(jīng)的女人”營造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一方面,她的聰慧、直覺,她的純感性的美,以及在性愛關系上的主動進攻,一次又一次把他吸引到她的裙下,成為眾多的崇拜者之一,并為此常常“玩物喪志”;另一方面,她的浮華享樂“毫無廉恥”,是對他所崇拜的傳統(tǒng)女性美德的挑戰(zhàn)。他不能娶她為妻卻又對她無法忘懷,這種為情感左右的局面威脅著他幾十年雄性邏輯和殖民文化所建立的理性世界。
小說的另一個主角是年輕的剛剛被《泰晤士報》派到遠東報道日俄戰(zhàn)爭的戰(zhàn)地記者詹姆斯(Lionel James)。詹姆斯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yè)有著理想主義的執(zhí)著和堅持。為了能及時報道戰(zhàn)爭進展,他試圖引進最先進的無線電臺發(fā)送電報技術,但是卻受到環(huán)境的限制以及日軍的層層阻撓,最后也沒有成功。但在小說中他的先行者的勇氣使他“雖敗猶勝”,他是作為與已經(jīng)變得世故圓滑、只為政治利益盤算的莫理循的對比而出現(xiàn),讓我們再一次感嘆世事對人的精神的侵蝕。同樣,莫理循的中國隨從Kuan的理想和行動—他最后與愛人私奔,投身反清革命組織,為自己的民族尋找新的出路,也向莫理循的世界提出了道德的質(zhì)疑。
就這樣,《一個最不正經(jīng)的女人》以莫理循在日俄戰(zhàn)爭中所扮演的道德含混的角色和他的私人生活中的矛盾處境兩條線的平行發(fā)展,給我們呈現(xiàn)了英雄的另一面,或說讓我們看到了英雄的末路。琳達的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批評視野無疑重寫了歷史。
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給他同時代的一位歷史小說作家的信中曾說,恰恰是現(xiàn)代人的“歷史感”成為小說存在的理由。“你應該盡可能搜集歷史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雖然用我們現(xiàn)代的頭腦來穿鑿和表現(xiàn)過去的意識、靈魂、感覺和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你必須用盡全力,用你現(xiàn)代的頭腦來想象。”他似乎在暗示,正是這種在歷史的蛛絲馬跡和現(xiàn)代頭腦之間的張力或說平衡造就了小說的歷史感。
澳洲國立大學著名的年度種族學講座自一九三二年開設以來就是以莫里循命名。在二○一一年七月的第七十二次講座上,琳達受邀成為主講人。面對臺下眾多的權威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史學家,小說家琳達不無抱歉但充滿自信地為自己辯護, 引用英國小說家L. P. Hartley一九五三年的小說The Go-between那段經(jīng)典的開場白:“‘過去猶如異國,在那里人們不尋常地行事。’在那片充滿異國情調(diào)的土地上,小說家可以和歷史學家一樣成為我們的向?qū)?(‘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 The historian and the novelist can both be guides to that exotic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