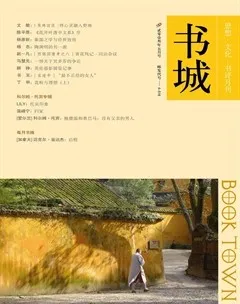英倫攝影展覽記事
今年一月的倫敦,天氣比想象的要好。少有淅瀝的陰雨,氣溫也比預想的要稍高。這樣的天氣,無疑有助于觀眾出行觀展。此行英倫,既有已經想定要去一觀的《威廉·克萊因+森山大道》(以下簡稱《K+M》),也有意外得知消息而涉足的展覽,如要展出到四月上旬的《來自中東之光:新攝影》。當然,還有臨行一刻知悉的展訊,如已經結束的《萬事皆在變動—六○、七○年代的攝影》。

一、當紐約與東京相遇
抵達倫敦的第二天,即去泰特現代美術館。泰特現代美術館聳立于泰晤士河南岸,是一個以現當代藝術為主的美術館,也是倫敦的地標之一。由泰特現代美術館第一位攝影策展人西蒙·貝克(Simon Baker)策劃的《K+M》正在那里熱火朝天地展出。說熱火朝天,似乎夸張,但如果去過此展現場,并且也見識過一些自稱為大展但觀客無多者,相信《K+M》的入場人數當得起“熱火朝天”這四個字。國外的一些優質美術館,如果所辦展覽確實是大展,那么觀眾人數在相當程度上是能夠確保的。尤其是在像倫敦這樣的地方,還是有較多的人視去美術館與博物館為精神生活的重要一環。在此需要對我所說的“大展”作個說明。在我看來,那就是展覽有上好的概念,策展人對于展品作了長久的調查,展覽展出了足夠分量的作品,精致的空間布展,出版了具學術價值的圖錄以及具有較為悠長的展期。具體到《K+M》,它的展期為三個月,展出作品共有三百多件,包括印放的照片原件。而展覽的籌備時間則長達五年。
以上似為題外話,現在回到展覽本身。
克萊因是美國攝影家,二戰后滯留巴黎不歸,師從立體主義畫家費爾南德·萊熱習畫。后涉足攝影,于一九五六年以攝影集《紐約》一舉成名。《紐約》以動蕩的畫面與粗放的顆粒打破了已趨精致的攝影美學,成為攝影史上的經典。而森山大道受克萊因的反攝影風格的影響,于一九六八年加入日本前衛攝影團體“挑釁”,之后始終活躍在攝影創作的第一線。這次泰特現代美術館將兩人放在一起展出,是對兩人長期以來的藝術成就的致敬。
《K+M》的展覽空間的分配,從平面圖看,是一個展覽兩造,既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咬合”,又呈現對看狀態的空間分布。克萊因的展區分成七個展室,而森山大道的展區則是六個,但再另加一個森山大道攝影畫冊的閱讀區。因此總的來說,雙方的空間分配基本均等。
展覽所規劃的路線,是先從克萊因展區進入,然后一路魚貫而行至森山大道展區結束。因為出了克萊因展區就馬上進入森山展區,中間沒有緩沖,人們會有一種被“強迫”進入森山展區的感覺。也因此,人們也許會問,策展人為什么把克萊因與森山大道放在一起展覽?雖然兩人的展區相對獨立,但所構成的關系則是雙人展的形式。雙人展之難在于兩個藝術家之間有什么樣的相同與不同。而更難的可能是相同之處,而不是表面的不同。如果不熟悉日本攝影史以及森山大道的創作經歷,也許只能從兩人風格以及克萊因與日本的關系(他在《紐約》出版之后來到日本拍攝了一本《東京》)來思考。兩人個人之間的接合點雖然不能通過展覽突出,但事實上卻有精神接點。
森山大道曾經坦白,也是平面設計師的他,就是因為克氏的一幀把曼哈頓的林立高樓拍攝成昏暗墓地的照片,令他驚覺攝影可以這么強烈地表現自我。他自一九六○年代起步攝影,到一九七○年代后期,在創作上進入了一個瓶頸期。此時,他趁赴奧地利格拉茨參加展覽的機會,于一九八○年轉道巴黎訪問了克萊因。這次訪問,他從克萊因那里獲取了現在所謂的“正能量”,開始了新一輪的創作。時至今日,他的創作勢頭仍無衰退的跡象。
在他的散文名著《犬的記憶·終章》中的“歐羅巴”一章里,森山談到那時他處于抑郁癥期間,體重從平時的六十五公斤左右劇減到五十公斤。他對于來自奧地利格拉茨的展覽邀請也鼓不起勁。經當時在格拉茨工作的日本攝影家古屋誠一的再三鼓勵,他才勉強配合。在結束展覽后,應日本攝影雜志的邀請,他到巴黎采訪了克萊因。當然,在這次展覽中,策展人貝克并沒有提到這段往事。他不想刻意突出所謂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連此次展覽的圖錄,也都是兩人各管各地分別制作與出售。或許是這兩個攝影家不習慣被機械地安置或“捆綁”在一本書里,但從空間布置看,克萊因與森山大道的對話關系確實建立了起來。
在克萊因部分,除了攝影是重點外,還包括了克萊因的電影、抽象繪畫等作品。這既顯示了克萊因是一個跨界藝術家,也似乎符合對于大師進行回顧的要求。他本來就是從繪畫開始自己的藝術生涯,只是在強敵如林的美術界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而在攝影界卻一舉成名。在我看來,曾經是平面設計師的克萊因的抽象繪畫確實沒有什么新意,只是以字體設計(typography)的概念在安排造型元素。但是,這種通過繪畫訓練出來的對于視覺元素的敏感一旦在他的攝影中發揮開來,卻相當有助于他的攝影,并因此成就了他的事業與名聲。七個展室中,第一個展室放映了他于一九五八年拍攝的、受到了奧森·威爾斯稱贊的《百老匯光影》。此外,還有一個展室則專門以三屏形式放映他拍攝的多部紀錄影片。這里面包括了他作為一個左派藝術家所拍攝的諷刺美國政府而使得他一度難以回國的電影《自由先生》。同時,展覽期間還要放映他拍攝的多部影片,以求展示他作為一個跨媒介藝術家的完整形象。
當然,整個展覽還是給了他的成名作《紐約》以充分的展示空間。從《紐約》中選出的一些照片,在展墻上以三十五毫米膠片能夠達到的尺寸極限加以放大,并且密集排列填滿墻面。這樣的展示方式,使得這些得之于紐約街頭的照片,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一種撲面而來的氣勢。除了展示《紐約》之外,展覽也從他的《東京》、《羅馬》與《莫斯科》這三本攝影集中選取了相當數量的畫面加以重新組織并展示。但坦率地說,后面這三部作品沒有《紐約》所具有的沖擊力與光彩。這可能與這三個城市本身所積蓄、擁有的能量級數無法與紐約相提并論有關,但也可能與克萊因本人在《紐約》之后在攝影觀念與語言上也再無建樹有關。他或許是一個需要強烈作用因而才能激發強烈反作用的人。如果對手不夠強大,或許他也無法動員足夠的自身能量與才華來與之對抗。雖然這么說,他的如拳擊手般頻頻出擊式的拍攝手法,的確具有開創性。他的攝影所具有的無政府主義式的暴力,也一舉動搖了剛剛稍顯穩定的攝影美學的根本,因此在攝影史上留下了深重的痕跡。此外,他將膠片印樣放大并且在上面以畫筆再作圈點的作品此次也有展出。
而森山大道展區則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于攝影這個媒介的執著追求與對攝影語言的開發。尤其是突出了他對于攝影畫冊作為一種攝影表現形態的高度重視。因此展室里的作品多以他的攝影集為結構安排組織,展室與展室之間的關系也以不同展室中的攝影集里面的作品來加以區分與聯系。

第一展室以他的成名作《日本劇場》為主,第二展室則有借用了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同名著作的《遠野物語》為核心內容的照片展示。此次展覽還特地編輯出版了《遠野物語》的英文圖錄。在第三展室里,我們可以發現,策展人從森山的深受克魯亞克的《在路上》的影響的《獵人》以及另外一本名作《再見,攝影》中抽出部分作品,然后加以重新組合后的展示。在某些展室里,策展人可以把似乎沒有直接聯系的某些作品安排在一起,藉此建立新的對話關系,激發觀眾新的思考,也重塑攝影家的形象。比如,在第五展室里,一面是他的北海道照片,另外一面則是精心排列的他拍攝于一九九七年的寶麗來照片墻面。一九七八年,他在北海道待了三個月,不停地拍攝,以圖克服自己的精神危機。這部分作品近來被編輯成了大型畫冊。森山于一九七一年拍攝了那條回頭凝望的“彷徨之犬”。這條頻頻出現于各種森山攝影集與平面媒介中的狗,其實已經成為了攝影家本人的自畫像。在第六展室,一個有趣的展示是,策展人收集了他以各種尺寸與朝向印放的那條狗的照片加以集中展示。我們因此看到,森山其實并不在乎這條狗到底是向左還是向右。但確實是在這種自己也不能確定的展示形式中,更鮮明了他本人作為一條攝影的“彷徨之犬”的真實性。在六個展室之外,在最后區域還特地設立了一個森山攝影畫冊的閱讀區。配合展覽共展出了他的四十一本攝影畫冊。攝影家、也是攝影畫冊收藏家馬丁·帕爾告訴我,這次泰特展出的這些畫冊,都是由他出借。
與克萊因的照片相比,森山的照片似乎更體現了一種日本人的“無常”美學觀所襯底的虛無。從《日本劇場》的異人們到只對街頭物件與影像下手拍照,森山的世界其實步步深入到了一種“存有之無”的境界。如果說克萊因是對人還保存希望因而發動影像叛亂的話,那么森山的照片中的虛無,則是從骨子里沁出的。但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他們與現代都市的格斗中。
二、“云水怒”、“風雷激”時代的全球攝影樣貌
由倫敦巴比肯中心畫廊策劃的《萬事皆在變動—六○、七○年代的攝影》,被英國《衛報》通過網絡評選評為二○一二年十大展覽之第七位。展覽共展出了除去大洋洲之外的全球十二位攝影家的四百多幅作品。

一九六○、七○年代,用毛澤東的話說是“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二戰后,殖民主義體系崩潰,冷戰取代熱戰,新興獨立國家紛紛涌現,同時而起的有蘇伊士運河危機、越南戰爭、中國“文革”、法國“五月風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日本“全共斗”斗爭等。所有這些,都是那個社會動蕩、政治激變的時代的新聞熱點與話題。而攝影本身,按照策展人的觀點,也已進入到所謂的“成人時代”。那個時代的攝影,不再只是為媒體所用,其自身特性的開發與使用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因此,無論是社會政治,還是攝影本身,都在這個歷史的大潮中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展覽的意圖,似乎既要展示那個年代的“世界圖景”,也要展示攝影作為一種視覺媒介所具有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展區分為上下兩層。按照地區分,展廳下層是南非與美洲,上層是蘇聯、亞洲與西非。被安排在南非與美洲展區的,有來自北美的兩位美國攝影家布魯斯·戴維遜(Bruce Davidson,1933- )和威廉·埃格魯斯頓(William Eggleston,1939- ),來自南非的兩位攝影家恩斯特·柯爾(Ernest Cole,1940-1990)和大衛·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1930- ),以及南美洲墨西哥的女攝影家格拉西埃拉·艾圖比德(Graciela Iturbide,1942- )。而被安排在上層展區的攝影家,并不以國籍為標準,而以作品的內容為根據。因此,拍攝了印巴地區的德國藝術家西格馬·波爾克(Sigmar Polke,1941-2010)也歸入此展區。同樣的,英國攝影記者拉里·伯羅斯(Larry Burrows,1926-1971)因為展出的作品有關越南戰爭,所以也被安排在此展區。在此展區里,有三位亞洲攝影家,他們是:剛剛被宣布了死訊的日本攝影家東松照明(1930-2012),中國攝影家李振盛(1940- )以及印度攝影家勞古比爾·辛格(Raghubir Singh,1942-1999)。而現為烏克蘭攝影家的鮑里斯·米哈伊洛夫(Boris Mikhailov,1938- ),其作品屬于蘇聯(USSR)時期拍攝,因此放在上層展區展出。而馬里攝影家馬里克·西迪伯(Malick Sidibé,1935/36- )則屬于西非地區的攝影家。這些攝影家生活工作過的一些國家,有些在當時處于極權高壓狀態,如南非處于種族隔離狀態,而前蘇聯的米哈伊洛夫則因為拍攝了女人體照片而丟掉了工程師的飯碗。
在下層展區,觀眾首先可從戈德布拉特的展廳開始參觀展覽。他是此次展覽中擁有最長展線的攝影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見策展人對他的重視。他的作品呈現了一個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有良知的白人攝影家所看到的南非社會真相。在戈德布拉特之后,是埃格魯斯頓這個屬于美國“深南”地區的一個“高富帥白”眼中的南方景象。他以彩色攝影成名,但所展出的照片并不太多直接涉及種族議題。通過策展人的挑選與編排,他的色彩鮮明的照片以較為中立的方式呈現了埃格魯斯頓這個美國南方人眼中的社會情景,并且從彩色照片特有的氣氛渲染方面給當時的時代作出了一種注解。
走出埃格魯斯頓展室,就是“紐約客”戴維遜的空間。他是紐約人,有更多機會直接地面對當時的時代風云。他參與了當時的一些示威進軍,因此留下了一份當時民權運動的生動記錄。他作為一個參與者所獲得的影像,其溫度顯然不同于埃格魯斯頓的照片。
艾圖比德以超現實主義氣息深厚的照片聞名于世,這次展覽展出的是她的早期作品。這部分作品以反映特定的墨西哥人生活為內容。她在這次展覽中占據的空間最小。與相對都以動蕩與階層矛盾為主題的攝影相比,她的攝影似乎并不那么激烈。當然,策展人或許是要告訴人們,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還有如此不同的地方與人。艾圖比德之后,就是最近被重新評價的柯爾。他因為給自己標上“有色(coloured)”而不是“黑色(black)”而獲得在種族隔離的南非從事報道的方便,因此拍攝了大量的反映種族隔離真相的照片。后來,他因不堪當局的迫害,只得流浪海外并死于貧病交加。當他在紐約去世時,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才剛獲釋一個星期。戈德布拉特與柯爾占據了此次展覽中最長的展線。作為兩位南非攝影家,一為白人,一為“有色”,因此展覽就構筑起了不同的觀看當時南非現實的視角。
上得樓來,最先接觸到的是米哈伊洛夫的作品。他展出的作品《昨天的三明治》可能是這次展覽中最“當代”的了。他在一九七○年代苦惱于克格勃的檢查,偶然發現把兩張透明反轉片疊加可以夾帶“私”貨。他以這種對自己的影像加密的方式,來模糊自己的訴求,這種相互遮掩并不單單只是偷運一己之“私”,也是反抗與不服從的證明。
出了米哈伊洛夫的展廳,就是被尊為“日本現代攝影之父”的東松照明的展廳。這個展覽選用了東松照明拍攝的東京街頭抗議活動中的一個青年扔石塊的畫面作為展廳的主題照。他展出的是包括了攝影家本人對于日本的美國化、沖繩的美軍基地化所表現出來的深入觀察。他被認為是既有深刻的題材意識,卻又能夠不被題材所綁架的攝影大家。
拉里·伯羅斯的越南戰爭新聞照片,被策展人按照當代攝影的處理方式放大成巨幅,因此再次召喚出美軍深陷泥濘沼澤的越南的現場感。從伯羅斯的展室出來,就是中國攝影家李振盛的展室。當伯羅斯在越南戰場出生入死地拍攝美軍窘境時,李振盛在支持越南的中國的東北地區黑龍江拍攝方興未艾的“文革”。李振盛畢竟是電影攝影出身,所以他以三張一二○底片拼接成紅海洋的大橫幅照片,既克服了單張照片畫面視野有限的不足,也在擴大了畫面的視野,給出一種錯位的動感的同時,在渲染群眾運動的氣勢上給人以特別的感受。而相對于“紅海洋”這樣的集體主義空間對于個體的淹沒,展柜里展示了他精心制作的自拍像冊頁,展示了攝影家在當時難得的個體意識,也與背后的照片形成強烈對比。他的自拍是一個持續的拍攝舉動,因此也確實顯示出攝影家的一種不同于當時的主流時代意志的個體意識。
而馬里克·西迪伯作為一個照相館攝影師,他的照片則較為集中地反映了當時西方流行文化在非洲的影響,尤其是在非洲青年人的時尚與日常生活中的影響。與西迪伯相對的是印度攝影家辛格的展室。他是印度最早使用彩色膠片的攝影家。這次展出的是他以彩色攝影的方式所記錄的印度的日常生活。從他對色彩的運用看,他對于色彩的表現與理解完全可與美國的埃格魯斯頓相媲美。
與辛格相鄰的是現已去世的德國觀念藝術家波爾克。他在一九七○年代有阿富汗之行。這是當時的嬉皮們的時髦之舉。他給后人留下了一九七四年拍攝于興都庫什山的當地兩只狗斗熊的照片。在這些被他處理得模糊骯臟的影像里,熊似乎隱喻了蘇聯的存在,而弱小而又好斗的狗,似乎成為了阿富汗的隱喻。有意思的是,從事后諸葛亮的觀點看,這批照片成為了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并陷入戰爭泥沼的預言性的圖像。
這個展覽被稱為是雄心勃勃的。確實,要給出當時世界的一個“云水怒風雷激”的動蕩景象,需要多元的視角與豐富的影像。展覽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這點,而且也考慮到了攝影表現的豐富性。從觀念性的影像到傳統紀實風格的影響,從白人攝影家到黑人攝影家,從亞非拉到歐美,從男性攝影家到女性攝影家,應該考慮到的策展人似乎都有考慮。但所有這些出自于不同攝影家與藝術家的影像,最終都歸結于表象。什么是深藏于人類行為背后的更為深層的東西?在探索人類心性這方面,攝影能夠做到什么?這些問題確實需要不斷地探討,包括像這個展覽所嘗試的那樣,通過對過往的攝影的重新組合,來對過往的歷史作出新的呈現與解釋。
三、“來自中東之光”
在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以下簡稱V&A),則有一個跨年度展覽《來自中東之光:新攝影》(Light from the Middle East)。這里所指的“中東”是一個“大中東”(the greater Middle East)的地理概念,包括了北非和中亞地區。此展是由V&A的詞語與形象部策展人馬爾塔·威斯(Marta Weiss)策劃。她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系,以攝影史研究獲得博士學位。此次展覽也是在英國第一次全面展示地理概念中的“中東”(Middle East)的當代攝影。威斯告訴我,這個展覽推出的多為新人。此“新人”有兩重意義,一是創作經歷上的新,二是對于英國觀眾的新。因此,當我問她如大名鼎鼎的出自伊朗的雪琳·納謝特(Shirin Nashat)為何不入此展時,她說一是她太有名了,二是相對有限的展覽籌資,也負擔不起這樣的大牌藝術家的購藏費用。

此展覽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記錄”(Recording)、“重構”(Reframing)與“抵抗”(Resisting)。
展覽共展出了來自中東地區十三個國家的三十位攝影家與藝術家的作品,所選作品開始于阿巴斯(不是也從事攝影創作的伊朗電影導演阿巴斯)拍攝的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結束于二○一一年的埃及解放廣場的阿拉伯之春。展覽所涵蓋的時間有二十多年,從多個側面反映出該地區的政治動蕩、社會變動的歷史與日常生活現狀。
展覽以阿巴斯拍攝的伊朗革命為開篇,然后就進入到“記錄”展區。“記錄”似乎毋庸置疑地被認為是攝影天經地義的使命。然而,記錄如果克服簡單的記錄而具有觀點與立場,更具挑戰性。在這個展區里,最為引人注意的攝影家可能是女攝影家Mehraneh Atashi。她拍攝伊朗男子柔道館,但卻巧妙地通過訓練場里的鏡子的反射來展現自己的工作姿態。在伊朗,這種男性出入的地方絕對是女子禁足區,但她卻能夠設法進入并且以曲筆法充分反映了這種男女有別的狀況,而且也頑強地達成了呈現自身存在的目的。在“重構”展區,集中了一些攝影家對于過去的老照片進行重新處理的創作。他們從老照片里挖掘過去的文化與傳統積淀,從今天的立場加以引用與再闡釋,以達成對于當下的重新認識。這里面較為引人注目的是Shadi Ghadirian的“卡扎爾”(Qajar)系列。畫面中,與肖像照被攝對象的身體語言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象征欲望的各種現代性事物(山地自行車、百事可樂、收錄放機等),和身穿卡扎爾朝代時的服裝,把身體嚴密包裹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強烈的沖突。此外,攝影家Taysir Batniji拍攝的以色列軍隊建立在巴勒斯坦西岸領土上的瞭望塔系列,雖然按照貝歇夫婦的類型學攝影的方式排列起來,但他的冷靜觀察中其實有著強烈的現實反感,反映了巴勒斯坦地區活生生的現實。因此不僅僅是審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而最后的“抵抗”展區,主要體現了策展人試圖給出當代中東攝影家對于攝影的權力本質的抵抗與瓦解。也就是說,這部分作品更著重于如何給攝影“去魅”。比如,Sadegh Tirafkan以身份照和抓拍上學少女照片為兩種素材,經過數碼處理,遠看形如肌理細密的波斯地毯。而Nermine Hammam的反映埃及革命(也是阿拉伯之春之一環)的作品則作為展覽的結束。她的畫面中,帥氣的埃及武裝部隊的士兵們,不知怎么被她“派遣”到了阿爾卑斯山、櫻花盛開的日本等地。被他們擊打過的她,認為他們可以出現在世界任何地方,就是不應該出現在解放廣場。他們背后的明信片式的風景,既削弱了他們的強力形象,也如同風景中的游客,被她先從視覺上解除了武裝。
威斯女士說,此次展覽是由英國的Art Fund所贊助。Art Fund是英國特殊的國家機構(http://www.artfund.org/ about-us/art-fund-faqs),其目的是專門為英國公共美術館收購藝術作品。但是這個機構的購買資金不是來自政府,而是完全依靠個人、企業和基金會的支持籌措。Art Fund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就《來自中東之光》這個展覽來說,V&A與大英博物館這兩個美術館一起從Art Fund獲得十五萬英鎊,用來共同購買一批中東攝影作品以供展覽展出。一般認為,大英博物館的攝影收藏側重于社會記錄,而V&A的攝影收藏重點在于攝影表現的豐富性。但是,策展人決定為這個展覽購入什么樣的作品,需要同時獲得這兩個美術館的批準。也因為有了Art Fund的支持,V&A也可以讓觀眾免費參觀這個特展。一般來說,這樣的特別策劃的展覽往往要收入場費。因此,此展雖然在V&A展出,但卻是它與大英博物館合作舉辦,包括經費上也有分擔。
參加這個展覽的藝術家和攝影家中,有半數是女性,共有十五位。這或許與策展人是女性有一定的關系,但不可否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天中東地區的藝術現狀,那就是盡管這個地區以男性強勢為主導,但仍有大量的女性藝術家活躍在當地的藝術現場,并且以各種方式獲得了國際關注。人們往往在現實中看見中東女子頭戴面紗行走于街頭,因此想象她們在自己的社會中深受壓制。男性中心的現實確實沒有多大改變,但事實上由于相當多的中東國家因為石油致富,所以許多中東女性有機會接受教育,甚至包括出國接受西方的高等教育。因此她們中的很多人教育程度很高。加上在中東國家女子多不能從事男子通常能夠就業的行當,因此她們往往選擇向藝術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發展。因此,反映、記錄當地社會文化生活的任務與使命,往往落到了女性藝術家身上。這有時會形成一個相當吊詭的現象,那就是她們對于男權制度的抨擊可以很猛烈,但男性依然故我發揮其強勢。一邊廂女性藝術家們通過藝術(包括攝影)對于這種父權制批評得緊,一邊廂大男人們仍然三妻四妾的迎娶得歡,而且對于來自少數女藝術家的“批判”也不以為忤。經濟蒸蒸日上的現實之下,普遍性的女性地位的改變非常緩慢。可是,在文化上,所謂的文化繁榮卻是由女性來承擔諸多使命。被壓制的女性成為性別觀念陳舊的當地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而她們的女權(主義)觀念(往往來自西方),也得以通過她們的藝術創作反映出來。所以,像這個展覽所顯示的,反而是許多女性攝影家表達出了相當尖銳而又機智的女性立場,也提出了許多論題。
順便提一句,在V&A的詞語與形象部的攝影策展人蘇珊娜·布朗(Susanna Brown)的交談中得知,該博物館的攝影收藏竟然有五十萬件之多。從這個數字看,“老牌帝國主義”果然名不虛傳。因為那些后起之秀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急起直追努力收藏攝影,但仍然被V&A的這個數字遠遠地甩在了后頭。比如,在亞洲穩居第一的東京都攝影博物館,攝影收藏品為兩萬八千多件,而擁有北美最大的攝影收藏的波士頓美術館,則有兩萬兩千件左右。從這些數字看,所謂的文化崛起與跨越,絕對是漫長的需要耐心的跋涉。而且,最終,這個收藏整體的量與質的關系是有某種保障的,可以令人放心的。放眼今天的中國,許多地方與機構都在說要建立攝影博物館。或許,沖動之下,量可以馬上實現,但質如何保證?那就涉及主事者的眼光與品位,稍有不慎,公帑浪費之外,甚至還有可能為后人留下一堆垃圾。

在V&A,除了《來自中東之光》這樣的策劃性的特展之外,還有其攝影收藏的常設展示可供觀眾細細觀摩英國攝影的歷史。對于擁有豐富藏品的美術館與博物館,如何“顯擺”并且經常性“盤活”其收藏,既是對于公眾的責任,也是其自身的價值實現,而且也會影響人們對于攝影與攝影文化的認識。因此,V&A會利用其豐富的收藏,經常策劃一些主題性的展覽。這既是對于這么豐富的資源的盤整,同時也是給予本館策展人以展覽策劃的實踐機會。比如,現在同時展出的一個名為《島國故事》的小型攝影展覽,展陳了包括英國國內外的攝影家所看到的英國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里面既有本土大攝影家比爾·布蘭德,也有外國攝影家卡蒂-勃烈松。這個展覽的規模雖然較小,卻也別致有趣。
四、誰誘惑了攝影?
繪畫與攝影的關系一直是現代藝術史的重要課題。攝影更是經常宿命地被與繪畫捆綁在一起加以討論。其中原因之一,當然是攝影確實在其手法與觀念上參考了繪畫的許多慣例性的做法。但另外一個可能是,許多藝術史從業者也許更樂于從他們更有自信的繪畫這個專業角度來看攝影表現。討論攝影如何被繪畫所影響,也許是他們更能發揮專長的一個方面。
收藏了大量從十三世紀開始一直到現代的繪畫精品(素描、版畫、油畫與雕塑)的英國國家畫廊,由于某種歷史慣性(或者說歷史包袱),對于攝影的態度向來較為曖昧。但最近,國家畫廊也終于放下身段,開始把攝影的藝術表現納入視野,并且結合其收藏展開具學術性的探討。《被藝術所誘惑—攝影的過去與現在》(Seduced by Art: Photography Past and Present)是該美術館自稱的第一個有關攝影的主要展覽。“第一個”,國家畫廊在今天用這個詞確實需要一點勇氣,因為這只能說明它保守得太久。盡管有評論認為這有點晚,但其態度的變化仍然值得肯定和關注。當然,即使它這么做了,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某種不變的、甚至有點倨傲的立場,那就是攝影的發展主要是從繪畫這個視覺樣式獲得資源并且壯大起來。因此,這個展覽容易給人一種它仍然在強調來自繪畫的對于攝影的單方面影響的印象。當然,也不要奢望這個展覽會討論攝影對于繪畫的影響。即使這樣,我認為這個立足點在于早期與當代攝影家如何利用美術傳統為攝影創作注入活力的展覽仍然很有看點。
收入展覽的攝影家,既包括了像馬丁·帕爾、克萊爾吉·霍斯菲爾德、理查德·比林漢、杰夫·沃爾、薩姆·泰勒-伍德這樣的當代重量級攝影家,也包括像裘里婭·瑪格里特·卡梅隆、古斯塔夫·勒·卡雷、奧斯卡·雷蘭德等這樣的攝影的古典大師。而被列入“誘惑”了攝影的美術大師,則有德拉克洛瓦、戈雅、庚斯波羅、安格爾、德加、康斯特布爾等人。因此,這樣的新老名家大師會聚一堂的展覽,實屬難得,而且也非一般美術館所能夠完成。雖然今天以攝影為手段的藝術家和攝影家不再有申辯攝影重要性的需要,但他們不斷地回首傳統、從與傳統的對話中獲得動力與靈感的態度,也仍然值得贊賞。
展覽基本上按照不同樣式來并列展示攝影與繪畫的實踐,從歷史畫、肖像、人體、靜物以及風景等傳統的樣式分類來呈現攝影表現的豐富性與可能性,同時也涉及到攝影的工作方式。當然,按照這樣的樣式分類來討論也比較安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出其保守性。仍然以早前的繪畫樣式分類來讓攝影鑲嵌進套,似乎不脫其對于攝影的屈尊俯就的歷來姿態。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策展人這次確實苦心孤詣地表現了一種開放態度,包括特約了M.M.布洛德海德與杰克·柯爾合作一部三分鐘長度的錄相作品《給希爾與亞當遜的頌歌》(2012)。大衛·奧克太維斯·希爾與羅伯特·亞當遜是十九世紀英國早期攝影中的肖像攝影大師,一個是畫家,一個是攝影家,兩人的無間合作為肖像攝影的一些基本美學原則與手法奠定了基礎。這部錄相請手持手機的當代模特進入預設的相框中,扮演希爾與亞當遜拍攝的《伊麗莎白絲·里格碧》中的里格碧。
進入展廳的第一組作品是德拉克洛瓦的作于一八二七年的油畫作品《撒爾旦納帕魯斯之死》,以及杰夫·沃爾和湯姆·亨特的攝影作品。策展人根據油畫中亞述王撒爾旦納帕魯斯放任眼前事物崩潰、畫面呈現傾覆與崩解的特點,安排與此畫面具同構性與內容上具類似性的沃爾和亨特的作品在一起,形成一種藝術史脈絡與視覺關系上的對話。這樣的做法,基本上貫穿了展覽的始終,不過除了將繪畫與攝影并置以外,還有將早期攝影作品與當代攝影作品安排在 一起、將當代作品安排在一起的做法。像十九世紀納達爾的攝影作品與當代攝影家毛德·蘇特的作品被放在了一起,告訴人們早期攝影如何成為當代攝影的靈感來源。而薩姆·泰勒-伍德的《靜物》(2001)與奧利·葛斯特的《爆炸》(2007)的并肩而立,又給出了新的比較視角。這個展覽雖然以樣式作為板塊來結構,但由于并置作品間的年代間隔大多有相當跨度,因而也拉開了一定的時空,具有了某種歷時性。此展展期從二○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到二○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新裝不久的“攝影家畫廊”是位于牛津街近邊的一個攝影中心。它地處市中心,方便了攝影家們的出入。該畫廊擁有三個樓面的展廳(2、4、5三層),一層是辦公室,底層(G層)是咖啡廳,地下一層則是書店,出售攝影書籍與照片。而三層則是攝影棚。可見,從樓層分布看,這是一個功能相當完備的綜合性攝影設施。由于去得晚了,沒有看到在四、五層的《射擊!實存的攝影展》,只在二層看了一個相對小型的展覽。令我印象較深的是那里的書店與咖啡廳。書店反映了畫廊的品位,選什么書出售當然是一種立場,肯定要與其專業標準和美學趣味吻合。在書店里,我沒有看到在中國可以看到的只要有錢就可以出的那種所謂的攝影畫冊。而底樓寬敞的咖啡廳則反映了畫廊對于交流的重視,也反映了畫廊服務攝影家與攝影愛好者的態度。我們各地的攝影家協會,能夠找到、讓出地段位置好的空間給來來往往的攝影家們以落腳之處,讓他們喝咖啡或茶交流交流嗎?
從以上相當活潑的倫敦攝影展事看,可以發現,倫敦的美術館與畫廊,都已經擁有了對于作為一種表現樣式的攝影的深切認識。
據說,丘吉爾早前曾經說過:“我們與歐洲在一道,但不是它的一分子。”倫敦,無疑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相對來說又有其歐洲地理上的邊緣性。但是,這種邊緣性絲毫沒有影響其文化心態,反而使其在心態上更為獨立與自由,同時,反映在文化上的表現也更為自主獨特。通過自己的杰出表現,倫敦顯示其地理上的邊緣性似乎并不影響其文化上的重要性。地處歐洲邊緣的倫敦,反而成為了給歐洲大陸以至西方世界以一種新鮮的文化刺激與活力的源泉之一。而且,通過開闊的視野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多元性,倫敦告訴人們,在整個西方世界里,語言上的、文化傳統上的、尤其是思想與文化上的價值觀所具有的一致性,其可供驅使的資源,仍然是那么豐富。而這在倫敦的攝影文化表現上也充分地體現了出來。倫敦雖然在一些新興國家的感覺良好起來的人看來是“日薄西山”,但由于其體制上的靈活性,因此仍然在文化上呈現出較為強勁的表現。以上各展,都是倫敦各美術館的自主策劃,展現了倫敦藝術策展人才的充裕與展品藏品的豐足。不像今天的上海,雖然多了幾個看似堂皇、甚至在世界上也堪稱空前寬敞的展覽空間,但自主策劃卻仍然乏善可陳,只是砸大錢引進國外大展以招引客流,制造眼前的熱鬧景象,但這似乎不是長久之計。做出、做好自己的獨特內容,集納、盤整自己的優秀收藏,才是每個有品質、有品位的美術館的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