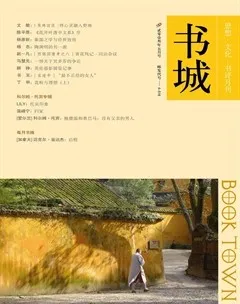悼張暉兄
平生第一次寫悼念逝者的文章,而這第一次竟然是為我們的好兄長、好學友張暉兄。文章何用?喚不回堅毅誠篤的他。在三十六歲的大好年華,這樣突然地離開了,留給我們(更不用說他的家人)巨大的震驚和傷痛。一連這些天,每次想起來都有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微博上,友人們轉發著他過去的照片。看著他沉靜溫厚的面容,老在心里問:張暉,你真的不在了嗎?
三月十五號下午正在網上逛,看到衛純的微博,瞬間極度緊張。怎么會?怎么會?我們十三號晚上跟陳國球老師聚會時,大家還談起今年五月他要來香港演講的事情,都非常期待。到時一些年輕朋友可以一起座談論學,老師甚至說,結束以后大家可以就來這個大排檔吃飯接著聊。而十四號收到曾誠兄一封電郵,說起因為張暉,和我也像是極熟的朋友了;那一晚睡覺前,我腦子里想著他今年春節時跟我說的要編近代文學輯刊的事,設計他讓我幫忙組的那一期,正準備過兩天寫信問他的意見后就著手組稿呢。而說來更巧,就在十五號下午,我去中文大學的商務書店買書,看到架上擺的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張暉的《詩史》,又順手翻到最后看后記,其中記錄了他博士階段在科大跟陳國球、陳建華老師讀書的情景,說他跟老師討論各種各樣的學術話題,每次往往都是不知不覺幾個小時就過去了。—剛回來打開計算機,竟然就看到那樣的噩耗,讓人如何接受?但給北京的朋友打電話,得到確證。又打給我們共同的友人,問他我們現在還能做點什么嗎。“現在又能做什么呢?”他黯然,我啞然。
嚴格意義上我不是張暉的同門師弟,但他這些年對我的關心照顧,完全是同門之誼了。他對友朋的提攜之力,顯然在我們這個薄情寡義的時代里是少有的。他本人這些年走來并非一帆風順,其艱辛之處多難為人道;他更同樣承受著這個權力和資本肆虐的社會中有心向學的年輕人們所共同面對的多重壓力和深刻焦慮;他拼命地做研究寫文章,也許都跟這些因素有些關系,畢竟學界的“承認的政治”也是頗殘酷的。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一面毫不自滿、虔心治學,不斷開拓研究的新境;另一面全力鼓勵和支持同樣在學問路上奮斗著的同輩和后進們。他始終以自己的道德文章為我們作無言的表率,但他從來沒有大聲疾呼,沒有把他的道德文章作為高高在上的資本或者表演,相反,他從來對在惡劣的學術生態中掙扎的學友后進有著那樣深切的“同情之了解”,并努力提供自己的幫助。這兩天在網上讀到好些年輕學人談到他所給予的幫助和照顧,那是他一直在給我們打氣加油啊。我們不要忘記,他自己也是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中生存與做學問的,我想他也一定有過郁悶和傷感的時刻,但他這些年還能始終堅持自己的選擇,保持心術的純正,并且還能那樣古道熱腸、樂于助人,力所能及地推動良性的學術氛圍,這是多么難得啊。他不是一個向黑暗叫陣的勇士,但他是一個在黑暗中點亮蠟燭的使者。他那樣有抱負有擔當,又是那樣謙遜和溫和。我每次想到他,總是感到既佩服又慚愧。相對于他的純凈,我的私心雜念是不是太多了;相對于他的勤奮,我是不是太懶惰了;相對于他的平和,我是不是太焦躁,抱怨也太多了?
早在讀本科的時候,就聽說過他的大名了。那時他的《龍榆生先生年譜》剛出來,當時我還沒有讀過這本書,但一個大三學生的學年論文能讓古代文學研究界如此青眼相加,功力深厚一定是毫無疑問的了。讀碩士時,讀到他所編的《量守廬學記續編》,才意識到他確實自覺承接了南京大學所代表的一種舊學傳統。從做年譜到編學記,一個年輕人能以這樣的進路作為立學根基,可見學術圈中譽他為從程千帆先生傳下來的第三代學人的代表,洵非虛言。二○○七年我來科大從陳建華老師讀博士后,就更經常地聽到師長們提起張暉,而且都是贊不絕口。我從圖書館借來他研究“詩史”的博士論文,讀后也極為佩服。他不僅有很深的史料和文獻功底,而且又有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對前沿問題的敏感。而他能三年多就寫出皇皇的博士論文,更可知他的勤奮超過常人。

我跟張暉聯系多起來,是這兩年的事。當我逐漸明確博士論文要做南社的問題后,老師們都讓我聯系張暉,說他是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的秘書長,應該會有一些幫助。我怕麻煩人,拖著也沒主動聯系。他有一年在新加坡教書,正好和我過去的老師倪文尖同住一間套房。文尖師后來跟我談起來,多次稱贊過他的勤奮和學術上的抱負。忽然間有了這個聯系,我從內心中更覺得張暉親切起來。二○一○年夏天,陸胤、袁一丹在北大組織了一個叫“活在‘現代’的‘傳統’”的會議,約了不少年輕朋友聚在一起。當時我們那一場的點評就是張暉,那也是我們唯一的一次見面。我很清楚自己對于古代文學文化的理解何其膚淺,那篇花拳繡腿的論文從古代文學學科看來當是屬于完全沒有入門的那種。但張暉的評論卻極客氣,而你又分明感到他的客氣沒有在這種學術場合一般的客套甚至虛偽。他是認認真真寫了點評發言的,他真誠地理解和解釋你的視野和方法,也極為細致地指出你文獻使用上尤其是腳注的疏漏,甚至還有錯別字—他讀得是多么認真啊,而他對后進的鼓勵又是何其慷慨和寶貴。我記得那一場我的朋友張耀宗的論文是討論詞學的,張暉對論文并不是完全贊成,但他也相當溫和甚至謹慎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后來耀宗內心也視他為畏友,因為他是那樣“真”的人。會議之后,他特地問我要地址,說是要寄一些南社的材料給我。果然,大約半年以后,我收到他給我寄來的南社通訊等內部數據一共十幾冊。他在附信中說,本來想找齊寄我,但還有幾期找不到了。我看了非常感動。他對別人的研究都有如此熱腸,而且不是一般地鼓勵,而是盡他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幫助。這份感動我沒直接跟他講過,卻寫在了論文的后記里。
二○一一年秋天我回蕪湖家中寫論文, 感覺前途茫茫,心境很差。讀到張暉訪談陳國球老師的文章,我發現他也很困惑于一個問題:在今天,文學或者說文學研究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他的這個困惑一定源于他對今天中國社會生活乃至于學術狀況的思考,也道出了我們很多年輕人心中的無力感。這并非(至少很大程度不是)因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更牽連到更大的對于學術意義的追尋。二○一二年春在蘇州有一個關于南社的會議,他好像跟我講過,但我在趕寫論文,后來也沒去。五月他來香港演講,也向孔健問起我的近況。我的博士論文寫成后,自己覺得拿不出手,所以也沒敢發給他指教。改了一篇小文章發給他,他在回信中不吝鼓勵,還問起我工作事。十月在廣州和思涯小聚,思涯說起張暉幫他聯絡出書事,我們還為他終于升等而感到高興。畢竟,以他這樣的才華和成果,早就應該獲得學界更多的承認。
終于,他關于“詩史”的大著被收入“哈佛燕京叢書”,由三聯出版了。我由衷地為他感到高興,給他去電郵祝賀。他很快回我:“謝謝。今天凌晨剛從上海回來,高鐵晚點六個小時,早上四點才到家。苦極。工作是否已定?甚念。拙著兩種幫兄留著。等《無聲無光集》拿到樣書后,一起寄奉。不知寄到何處較為方便?盼告。”我馬上回信告訴他我的近況,說來年想申請的學校,還說:“前幾天跟陳國球老師聊天時,談到你,陳老師說你剛去社科院時一切都很艱苦,但這么多年仍然堅持讀書寫作,非常不容易。但只要堅持,最終學術界還是會承認的。我覺得你是我們的好榜樣。”張暉又回信說:“這段日子是比較難熬的,但工作很快就會有。……我高中時就喜歡去×××散步,還記得校園里的很多小書店。” 他還提醒我 “反而是工作之后”將面臨當今的學術環境,“容易淹沒其中”。說得如此坦誠親切,他顯然沒有把我當外人。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又來信,說已經把《詩史》寄給我,又問:“近況如何,××今年要招六七位博士,簡歷的截止時間是四月,有沒有考慮試試這邊?”可知他對我找到一個穩定工作是多么上心。我匯報了我的近況和想法,也說我過年時會好好讀他的大著。我今年四月要出本小書,到時也會寄上請他批評。渴望閱讀對方的書和文章,為彼此的學術進步而高興,這大概就是我們的秀才人情吧。今年春節回家開始讀他的大著,給他寫信:“昨剛讀了開頭,細密而扎實,我對古代了解甚少,但還是覺得你代表了一種古代研究的‘正格’。”張暉回信說感謝,又說想請我編一本書。
二月十六日我回港前,在機場給他打了個電話。那次我們聊了二十多分鐘,我才知道他想編近代文學方面的研究輯刊。他特別說,自己也不算什么主編,就是朋友們一起來做事,給年輕學人提供一個平臺。我在近代文學研究中還很難說是否已入門,但張暉對我的提攜卻是如此不遺余力。我們談了學界的狀況,感慨現在即使不顧慮生計壓力,只想找一個穩定的教職靜下來做學問,都不那么容易。他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我工作的事,囑我一定要上心;又勉勵我不要灰心,好好的做下去。—我本想以后聯系會密切,更多機會跟他聊天論學了。誰知道,這成了我們之間最后的通話。
張暉平時是一個相當低調的人,但他內心確實有著大抱負。他經過多年的積累,現在正是在學術上卓然自立的時刻。無論是他最近出的兩本書,還是如未完成的《帝國1+9L2+z8a0zFUmT0NBsTxA==的流亡》,還是他正在著手的那些研究和編輯計劃,你能看到他在學術上不同凡響的視野和境界,更能看到他對中國學術內在的、深切的熱愛和期待。
也許正是因為我們大家早已在內心把他立為了一個標桿,我們才會對他的逝去感到那樣的傷痛。我們當然替他未及展開的學術宏圖而惋惜,千古文章未盡才固然非常可惜;不過,我個人更傷痛的是斯人而有斯疾的天道不公,是他的不幸留給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巨大的悲哀。而如果不是我的夸張,我想說,張暉的逝去真實地觸及了我們這一代年輕學人共同的隱憂:在今天,做學問,做好學問、真學問,還可能嗎?又要為此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而我們真的能承受嗎?沒有了他的陪伴和鼓舞,在逼促的前徑上,誰能保證精神世界不變得越來越狹窄?在充斥著功利的世界里,誰又確信僥幸地向上流動不是另一種沉淪?
張暉,我們永遠記得你,懷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