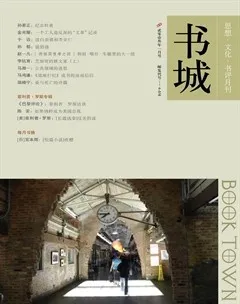夜櫻
在阪急電車的御影站一下車,綾子就在春風吹拂下,腳步沉沉地走在幽靜的住宅區坡道上。明亮的路上,盛開的櫻花無聲散落。
腰帶綁得太緊,太陽穴那里很難受。綾子就到五十了。跟丈夫分開過了約二十年,因交通事故失去獨生子修一也快一年了。
在陡峭的坡路上停步,回頭望去,看見了大海。神戶的海,在春霞之中閃亮,像一塊銀板。無論心情多好的時候,綾子都從沒有帶著幸福感去眺望從這里看見的海。看見了拖航的大型客船或貨船,她心頭就涌起奇特的落寞,駐足坡道好一會兒,注視著遠方的大海。綾子家要再往上走一百來米,夾在某銀行董事長的邸宅和一個德國商人的洋樓中間。這所房子是從一個投機商人手上便宜買下的,他在婚后第二年就沒落了;二層樓的柏木建筑,有高高的綠籬環繞,院子挺大。
往左一點看,六甲連山就在眼前。開上收費公路的汽車變得豆子般小,消失在綠色之中。坡道上除偶爾傳來小孩子的喊聲外,再沒有任何其他聲音。綾子又邁開步子。隨風起舞的櫻花瓣令人心煩。一個面熟的女學生從對面走過來,錯身而過時,她笑著說:“您好像有客人。”
綾子緊趕慢趕,氣喘吁吁,頸脖、后背滲出了汗。向右一拐,看見了站在家門前的山岡裕三—她的前夫。

“不好意思,我去了一下梅田的百貨店,所以就……”
在去年修一的葬禮上,綾子時隔二十年見到了裕三。裕三在三十五日、四十九日都過來陪她聊天了。他在神戶經營一家船舶運輸公司,比綾子大三歲。
“這怎么回事?”
裕三說著指指貼在門柱上的紙。那是綾子出門時貼的,上面寫著:“歡迎寄宿,僅限學生,須有擔保人。”
“我想二樓空著……”
“……錢方面不方便?”
裕三皺了皺眉,問綾子道。見綾子沉默,他瞪她一眼,說道:“不弄這種東西,跟我說一聲不就行了嗎?”
“那不一樣。一個女人挺多事的,有個人同住的話,心情上也輕松。”
“現在的學生古怪的也很多,反而不省心。”
“是嗎?”
進了門,綾子請裕三到面向庭園的八疊間。這房間以前作客房使用,修一死后,綾子就住在這里。綾子一打開外廊的大玻璃窗,裕三就站在一旁看院子里的櫻花。
“開得正好啊。”
“今年好像比去年早了五天左右。”
修一死于院子櫻花盛開之日。四月十日。
“這里的櫻花特別棒。”
確如裕三所說,跟其他人家栽種在院子里的櫻樹相比,綾子家開的櫻花不論顏色還是數量都好得多。寬大的庭園中央,矗立著三棵巨大的櫻樹,枝葉交纏。裕三的父親戰后從投機商人手上買下房產時,已有這三棵櫻樹。
“我家那頭的櫻花開也開得寒磣。”
綾子真希望早一刻把和服換成便裝,但客人是裕三,反而較真了。葬禮和七七忌日都有綾子家的親戚在,所以今天才是綾子時隔二十年真正單獨面對從前的丈夫。裕三在綾子遞過來的坐墊上盤腿坐下,說道:“修一一周年忌日的事,您盡管放心,全部讓我來搞定。”
“你”字剛要出口,裕三慌忙改成“您”。綾子看著裕三開始變得雪白的、硬硬的頭發,感覺他迄今隱忍了二十年的東西,正慢慢滲透出來。于是,她坐在榻榻米上,把目光定定地投向院子里的櫻花。仿佛一只堆放過滿的木籠子,里頭的東西不斷外溢—花瓣和春光一起,不住地落在地面上。
“鄰居那德國人,還活著嗎?”
“對。聽說今年八十歲了,但還挺精神的。據說最小的孫子娶了日本人,他不喜歡,鬧得挺大的。”
“來到別人的國家,弄個獨立王國自得其樂,所以就有些頑固不化吧。”
“您工作上還順利?”
綾子問裕三。
“不景氣啊。社會上不景氣嘛,沒辦法。平時在公司工作到十點左右。”
“跟年輕女人玩的時間,肯定留出來了吧?”
綾子笑著打趣他。
“已經沒那個精神啦。”
裕三說著,神情落寞地看了前妻一眼,“要是知道修一會先走,當時就不會跟你離婚。真是不可挽回的錯誤……”
二十多年前,裕三就是說著類似的話,向綾子求婚的。當時裕三二十五歲,在位于神戶北野町的一家會員制餐廳里說得很起勁。這是一家外國人經營的、當時很少有的高級餐廳。
“若不是參了軍,早就求婚了。即使明知要死,也得先擁有你。真是不可挽回的錯誤,我一直這樣看的……”
綾子覺得奇怪,這些話怎么記得如此清楚?朝鮮戰爭開始了,裕三父親經營的船舶運輸公司大賺特賺。跟綾子離婚的第二年,裕三就繼承了去世父親的事業。
“之前都沒有機會說出來,老爸其實挺牽掛你的,臨死前還說:要是她找到好男人再婚,我也就卸下負擔了……”
綾子想起了家公的白頭發和瘦削身軀。那是跪在御影這個家的門口向綾子賠罪、懇求二人不要離婚的家公。當時綾子邊哭邊孩子氣地叫喊著不答應。
“不是我親眼看見的話,我還能忍。可是,我就在跟前看見的。我親眼看見,裕三抱著別的女人……所以,我絕對要離。”
說到“不可挽回”,自己當時說的話確實就是“不可挽回”,綾子心想。經過長時間戀愛才結合的裕三和綾子,只經過了三年多的婚姻生活,就分手了。把才一歲的修一交給綾子、把御影這個家給了綾子的,都是家公。雖然每月收到孩子的撫養費,但綾子在修一滿三歲時,就出來工作了。伯父在六甲口開了一家進口雜貨店,最初綾子幫忙做些簡單的事務工作,后來她慢慢掌握了進貨和與客戶打交道的訣竅,三年過去,就負責管理店子了。可是,她沒有打算自己當老板。直到去年四月修一去世,她一直在伯父的店里工作。雖也有人來說對象,綾子卻沒這心思。大的理由是自己有房子,生活也輕松。但最重要的是,綾子忘不了已經分手的山岡裕三。綾子有時會想,雖然丈夫是個不知何為吃苦的公子哥,但想來自己也一樣是個千金小姐。聽說裕三再婚了時,綾子像傻了一樣,牽著修一的手,在石屋河邊來來去去走了好幾個小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綾子一邊往水壺里倒水,一邊看看裕三的春季西服。是灰色帶一點藍的、做工精細的三件套。
“還一身年輕人的西服,頗有抱負啊。”
“饒了我吧。大女兒都要出嫁了……”
裕三爬過榻榻米,雙手捧起裝飾在壁龕上的青瓷壺,說道:“真令人懷念啊。”
青瓷壺是家公心愛之物,綾子與裕三離婚時,家公給了綾子。她眼前浮現出家公親切的大眼睛,意料不到的話脫口而出。
“我就饒你這一回,再來我可就受不了了—那時候,要是這樣說就好了……”
說到“修一也死了”,綾子突然哭了起來。裕三把青瓷壺捧在胸前,默默地看著綾子。
“我也孩子氣,你也是個公子哥。”
哭著哭著,綾子被無邊的絕望感籠罩了。孤零零被丟棄在茫茫荒野上的那種寂寞感,從綁得緊緊的腰帶上,直勒入綾子身體里來。原以為自己不是會在男人面前這樣子哭哭啼啼的女人。總之并不喜歡夫妻的生活。自己一次也沒有主動去找對象。離婚之后也從沒有感覺到這樣的寂寞。自己屬于淡泊的女人吧。所以,連修一也死掉了—沒有邏輯的思緒一下子涌現出來,綾子止不住淚水。也許跟裕三這樣子單獨相對而坐,讓此刻的綾子更加難受。綾子站起來,不做聲地去了旁邊的房間。她解開腰帶,脫下和服,手捧要換穿的連衣裙呆站著,目光怔怔地落在房間一角。
“我老婆住院了。”
裕三的聲音隔著拉門傳來,綾子從外廊走回裕三所在的八疊間。
“是子宮肌瘤。”
“要做手術嗎?”
“醫生說,可能還不止這個問題。不開還弄不清楚。”
“什么時候?”
“手術是下周二。人瘦得有點不正常……”
談話暫時繼續不下去了,綾子和裕三又把目光移向院子里的櫻花。
“這里的櫻花晚上很漂亮,對吧?”
“是啊。鄰居董事長院子里的水銀燈,做照明正合適哩。”
“喲,那真是好看了。”
裕三叮囑完絕不可收留人寄宿,就回家去了。看看時鐘,是兩點。綾子在廚房洗洗刷刷時,門鈴響了。出去一看,一名陌生的年輕男子站在門外。
“我想問一下紙上說的事—已經有人了嗎?”
年輕人說道。他身材很高,穿著藍色工裝,怎么看也不像學生。
“還沒有。是剛才貼的……可是,我想算了。”
“算了?”
綾子走到年輕人身邊,揭下貼紙,胡亂折起來。
“原想租二樓出去,但我突然改變主意了……”
“二樓,是朝南的房間嗎?”
年輕人說著指了指。他看綾子點頭,滿臉歡喜,從胸前口袋里掏出名片遞上,鄭重地鞠了一躬。
“就今天一個晚上,請租二樓房間給我好嗎?”
“就一個晚上?”
“我絕對是正經人。被子我也帶來了,我會打掃干凈,明天一早離開,不會給您添麻煩的。”
事出突然,綾子不知怎么回答好,只是窺看那年輕人的模樣。年輕人又鞠了幾個躬。看他坦誠的笑臉,不像打壞主意的人,但綾子可不會答應把二樓房間只租一個晚上的事情。這小伙子看上去蠻善良,但也完全可以想象他會突然變臉,半夜里亮刀子。
“一個晚上的話,找間旅館、酒店就行了嘛。抱歉,我不能答應。”
“……還是不行啊。”
年輕人滿心遺憾地仰望著二樓,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說道:“那根電視天線—因為固定它的鐵絲松了,所以圖像效果不好吧?我幫您修一下。我是做電器安裝的。除此之外,我幫您檢查一下家里所有的電器,幫您調好。住宿費我也付,就請您把二樓房間租給我一個晚上吧。”
“你為什么就想住一個晚上呢?”綾子生氣了,正顏厲色地問年輕人。
“我想在都是這種大宅子的安靜小區好好睡一個晚上試試。”
這古怪的說法讓綾子笑了起來,不由得說道:“既然那樣,你現在就幫我修理電視天線?微波爐的定時開關也壞了,電冰箱除霜也不靈了—你都幫我修的話,可以考慮。”
當她心想“壞了”時,年輕人已跑向停在一邊的輕便客貨兩用車。他拿著工具袋返回來,徑直走進大門。綾子小心翼翼地帶他到廚房,沒說話,指指微波爐。
“干其他事我都不行,就修理電器是天才。”
果不其然,年輕人擺弄了五六分鐘定時開關,就輕輕松松修好了。
“這里往東面一點,有一戶牙醫,對吧?”
年輕人說道。綾子看著他剪短發的健康臉龐,心里頭漸漸安穩下來。她到冰箱里拿了罐可樂,倒進杯子里給他。年輕人應該察覺屋里就綾子一個人了,若是他有歹心,早應該動手了。
“那位牙醫在醫院旁邊新建了房子。是三層的豪宅,從他樓上,看這邊院子很清楚。”
“啊,都能看見?”
“家里頭看不見,但院子里的櫻花看得很清楚。很大、很漂亮的櫻樹……”
年輕人拔了冰箱插頭,把它移到廚房中央,從后側檢查機械部分。
“那房子的布線全是我安的。我從五天前就一直在欣賞您院子里的櫻花了。”
年輕人說,恒溫器壞了,這東西一下子修不好。于是先修屋頂的天線,二人上到二樓。打算出租的朝南八疊間,一年前還是修一住的。書柜、衣櫥還是原樣,修一學生時代就珍愛的三支網球拍掛在墻上。綾子打開關了兩三個星期的窗簾。南北向行駛的阪急電車軌道也好,國營鐵路的軌道也好,甚至更遠處的阪神電車軌道,從這房間均可一覽無遺。從六甲山山麓,直至遠方神戶的大海,都以庭中櫻花為中心伸展開去。
“招租的是這個房間嗎?”
年輕人站在窗邊,問綾子道。
“是這么想過,但已經作罷了。”
年輕人望著網球拍和書柜,突然想起似的從屁股兜里掏出五千日元的鈔票。
“我的預算就這么一點啦。”
“我還沒有決定租給你呢。”
年輕人以笑臉回應綾子的話,拿起鐵絲和鉗子爬上屋頂。
“摔下來可受不了!你小心啊,屋頂很陡!”
“太太,打開電視機好嗎?”
年輕人在她頭頂上方喊道。綾子慌忙到樓下去,照吩咐打開電視機,然后走出院子望向屋頂。
“圖像怎么樣?”
綾子聽了,又進房間去看電視畫面。她試調了好些頻道,然后跑到院子里大聲喊道:
“哎!已經很好啦!”
年輕人的臉從屋頂一角露出,又縮了回去。綾子上二樓,等年輕人下來。她感覺像跟年輕人認識了很久似的,心情難得地輕松起來。既然他那么想在這個房間住一個晚上,那就租他一個晚上吧。年輕人下得房頂來,一額汗水。燦如初夏的陽光,照耀著遠處家家戶戶的屋頂。
“這個房間,是您公子住過的嗎?”
對年輕人的這個問題,綾子坦率地點了點頭,從窗戶探出臉,指著石屋河的方向說道:“他迷迷糊糊出去買煙,在那個拐角被車軋了。”
“……是這樣啊。”
“他死了。當場死了。”
年輕人也學綾子那樣從窗戶探出臉,凝望著石屋河邊。他曬黑的大手粗糙、裂痕縱橫。
“大學畢業了,剛進入商社工作。”
前方阪神國道上,無數汽車在奔馳。天氣晴朗,但天空中卻沒有藍色;海港蜿蜒的沿岸,矗立著一排排工廠的煙囪,一直延伸到大阪灣那邊。綾子和年輕人并肩站在二樓窗前,好一會兒眺望著開闊的景色。
“今晚請租給我,好嗎?”年輕人小心地說。
“就一個晚上。而且不提供飯,也沒有任何服務。”
年輕人說傍晚拿被褥過來,高高興興地走了。他走后,綾子突然被后悔的念頭籠罩,心里頭七上八下,借洗衣物和收拾廚房挨過傍晚前的時間,中途好幾次手拿年輕人的名片,站在電話機前。她猶豫著要不要給年輕人工作的電器店打電話推掉住宿的事,內心一番掙扎之后,才終于下了決心。她想,既然說定了,就不改了;這年輕人看上去溫和開朗,并無惡意。
因鄰居太太來邀去購物,綾子去了一趟車站旁的超市。鄰居太太自顧自地東拉西扯說什么最近參與的志愿者活動啦、法式薄餅的烤法啦、杏子醬的做法啦等,綾子隨口附和著,心里浮現的是裕三的面容。感覺他的來訪,并不單為修一的一周年忌日,但二人分道揚鑣都二十年了,相距甚遠。對搞了公司年輕員工的裕三,自己為何一次也不肯原諒呢?在櫻花飄落的、安靜的坡道上,綾子和饒舌的朋友并肩走著,不住地想。
突然,她頸脖火辣辣的。陽光和煦,脖子以上卻上火,是奪去了腰腿的熱量。自修一出事以來,月事變得不規則了,大約三個月前,只來了一點點就停了。雖說年齡有關系,但綾子感覺不安和焦躁,感覺到自己身上某種自然的東西正在消失。
家門前放著個大大的被袋,換了一身西服的年輕人兩手插在兜里,在等待著綾子歸來。綾子與鄰居太太道了別,一邊將冰冷的手往熱乎乎的臉上捂,一邊走向大門。
“打擾啦!”年輕人大聲寒暄道,扛起了沉重的被袋。然后麻利地把被袋擱在二樓,就下來了。
“你挺不客氣的嘛,可以做個好生意人。”
綾子照直嘟噥道。自作主張卻又不會給人帶來不快,是這個年輕人天生的特質吧。
“不好意思,我八點左右再來。電冰箱我明天一定會修好。”
沒等綾子說話,年輕人已經駕駛電器店的輕便客貨兩用車下坡去了。
八點剛過,年輕人來了。不止他一個—他帶來一個穿著一條樸素的米黃色連衣裙的女孩子。綾子慌了。她覺得被人耍了,像要攔住二人似的讓他們在玄關口坐下來。她正要說話,年輕人先開了口:“這位是我老婆……不過是今天才結的婚。”
“……今天?”
“打擾了。”姑娘害羞地鞠一躬,小聲說,“婚禮還沒辦呢,只是打了申請給市政所。”姑娘沒有給人絲毫輕浮的感覺,但肯定算不上美貌。
年輕人隨即拉起姑娘的手,徑直上了二樓,留下目瞪口呆的綾子。自己家被陌生男女當情人旅館使,讓綾子生一肚子悶氣。她想叫他們走,卻沒有那種追上二樓去斷然逐客的氣勢。唯一寬心的,是二人落落大方。綾子無奈關了門,給大門也上了鎖,返回自己的房間。浴池已放好熱水,但無心入浴。不時豎耳傾聽二樓的動靜,但結實的房子完全隔音。鄰居董事長家映過來蒼白的光,看來水銀燈開了,凸顯出綾子家院子的櫻花。
過了十點,綾子壓下復雜的心情,洗了澡。不上班,外出也少了,綾子幾乎不再化妝。附近的太太朋友取笑說她因此反而更顯年輕了,但臉上有了多余的肉,她感覺那是到了某個年齡的一種風情。突然,她想起裕三老想一起入浴的事。綾子一拒絕,裕三就不高興。于是綾子勉勉強強隨他進入池子,蜷縮在裕三手臂里不動。在男人跟前舒展赤裸的身體,她怎么也做不來。
擦拭身體時,一種不妙的預感突然掠過腦海。“情死”一詞突然冒了出來。她擔心起來:這對男女是否為了某個原因,要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呢?綾子慌忙穿上衣服,到樓梯口去窺探二樓的情況。聽不見說話聲和其他動靜。看樣子二人不會變臉為竊賊或搶劫犯,但好像要發生什么大事情。二樓的走廊和房間都滅了燈。漆黑的樓上,此刻確實有一對陌生的年輕男女。
綾子甚至想到了報警。但一想到若是自己的不安只是杞人憂天,就太難堪了,于是又遲疑起來。她返回自己房間,不由自主地鋪了床。她往睡衣外面套了開衫,靜靜地端坐在被子上。過了十一點時,她終于下了決心,走上二樓。心怦怦跳。她輕輕走近八疊間,想要打招呼,這時微微聽見二人像是躺著說話的聲音。綾子在漆黑的走廊止步,側耳細聽。
“可不許睡著啊。”
“……嗯。”
傳出移動的動靜,年輕人的聲音移到了窗邊。
“過來這里。”
“不、不行……害羞嘛。”
“漆黑一片,看不見啦。”
“我穿上衣服過去。”
“今天不冷,不穿也行。”
“不是冷不冷的問題啦。”
女子的聲音也移到了窗邊。綾子明白是自己過慮了,身上的力氣仿佛泄掉了。
“遠眺大海,盛開的櫻花環繞,住一個晚上,且費用只有五千日元—為了滿足你這樣的愿望,真是絞盡腦汁啦。”
女子含混的笑聲,銘刻在綾子心中。
“美麗的夜櫻。”
“真的……太美了。”
“神戶的夜景看得也很清楚。”
說話聲中斷了,女子輕聲笑著。看樣子二人藏身窗邊,正在欣賞著院子燈光下的夜櫻。
“我覺得,女人想幸福,絕對要嫁富翁。”
“我也這么想。”
“像在說別人呢……我們好歹也要住上這樣的房子呀。”
“……嗯。”
“……好勉強的回答嘛。”
綾子又悄悄下了樓梯。
關了自己房間的燈,打開外廊的玻璃門。溫暖的夜。明天也許會下雨,綾子心想。她坐在外廊,久久地眺望著盛開的櫻花—別說下雨,一點點風也會吹落的、盛開的櫻花。從沒有如此端然注視過。仿佛一團巨大的淺桃色棉花,由青光鑲邊,飄浮在空中。也仿佛一個妖艷的生命,簌簌紛紛地散落著、減少著。綾子決定,這個奇特的不眠之夜,就陪伴著櫻花度過。
看不見星星和月亮,庭石和陶椅也都不見蹤影。心頭只有夜櫻不斷飄散的情景,沉醉在花雨拂面的心境中。二樓的人一定已經離開窗邊,重新鉆進被窩了吧。仿佛連二人的體味也聞得著。綾子就這樣久久沉浸于夜櫻之中。思緒紛涌,當中忽有看得見的。啊啊,就是這個嘛,綾子想道。究竟什么是“這個”,綾子卻又說不準。她覺得,此時此刻,她可以成為任一種女人。從今天飄逝的花中,她看見能成為任一種女人的訣竅一閃而過,但那種朦朧的動靜,當她把目光從夜櫻移開時,隨即消失得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