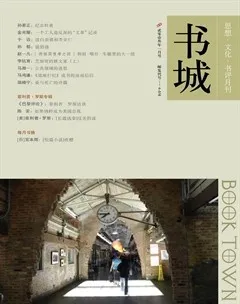關于“傳神”的一個注記
《紅樓夢》二十七回,旺兒來問“往哪家子去”。因為王熙鳳在李紈處閑聊,平兒就代鳳姐回了,并派小丫頭小紅來向鳳姐報告家里的安排。這個小紅原名紅玉,是林之孝的女兒。—
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里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里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里。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紈道:“噯喲喲!這些話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
有“紅癖”的人常喜歡考證這兒的“我們奶奶”、“這里的姑奶奶”、“奶奶”、“五奶奶”、“舅奶奶”和“那邊舅奶奶”各為何人。其實,這一段不長的對話的真正精彩之處,或在于一下子把當時在場的三個人都傳神地表現出來了:小紅的伶俐,李氏的木訥,鳳姐的明晰練達,—甚至不在場的平兒,也栩栩然如在目前。鳳姐喜歡小紅的“口角簡斷”,后來就把她要到了自己房里,認為“一調理就有出息了”。在前八十回中,小紅出現并不多,但小紅以及她和賈蕓的故事卻如千里灰線,斷斷續續,結合脂批的線索,大部分讀者都相信,在不可見的后四十回里,應當還有重要的發展。由此看來,小紅的“奶奶爺爺一大堆”應當不是偶爾的插科或閑筆,而是作者對人物的刻意勾畫。

汪曾老曾經寫過一篇小品談“傳神”,收在《汪曾祺小品》,要求用盡可能少的筆墨完成這種勾畫。細看上面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悟出在這兒“傳神”是通過“什么‘奶奶’‘爺爺’的一大堆”實現的。小紅的“簡斷”在于準確地使用了一系列的稱呼:她說話的地方是李氏的住處,所以有“這里”“那邊”;她說話的身份是奴才,所以更有“爺爺”“奶奶”,真是一絲不亂。一口氣轉換了五六個人稱,李紈是暈頭轉向,而鳳姐卻深愛其說得齊全。
這種在稱呼上的細致深入的考究,或者可以作為汪曾老要求簡潔和傳神同時成立的一個注記。《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起于他和項梁看秦始皇南巡。當其時也,良將信臣,金城千里,秦帝國正當如日中天之盛,而手無尺寸的黃毛孺子項羽,竟然輕飄飄地說—“彼可取而代也。”嚇得項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一個“彼”字,項羽的霸氣躍然紙上。細細品味這個“彼”字,似乎可以有若干個替代,但事實上沒有哪一個能更傳神地表現少年項羽當時目空一切的既豪邁又輕狂的神態。《平原君列傳》中有人人耳熟能詳的“毛遂自薦”的故事。毛遂隨公子往楚國說合縱,要楚王出兵。楚王猶豫,平原君陳說利害,反反復復,至于日中。這事兒本來就是不太容易。楚國是大國,雖然頗受秦國的壓力,但要楚國為趙國參加對秦作戰,趙國是有求于人,是以小求大,楚王少不得有些傲慢。于是毛遂挺身而出,—
按劍歷階而上……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爾君言,汝何為者也!”
三句話,就把當時的情形生動地展現出來。在嚴肅的外交談判當中,忽然有人“歷階而上”,楚王的反應先是詫異,遂有是問,語氣是符合他的身份的。當他知道來者不過是平原君的門下客,不禁大怒,于是有“汝何為者也”的斥責。從“客何為者也”到“汝何為者也”,一字之差,一個代詞的替換,刻畫了楚王從詫異到憤怒的轉變。與之相應,代詞“爾”、“汝”的運用則恰如其分地表現了楚王藐視毛遂的態度,為下文毛遂要和他拼命時楚王在態度上前倨而后恭的轉變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事實上,楚王氣撓,“唯唯,誠若先生之言,”— 稱呼也改為“先生”了。
這種稱謂代詞看似小技,其實在描摹人物神態乃至內心上有不可替代的功用。《項羽本紀》中另有膾炙人口的一段寫劉邦: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一連四個代詞,“吾”、“若”、“而”、“我”,摹寫劉邦的言語之傳神,真到了不可替換一字的地步。司馬遷從來沒有給劉邦貼上“流氓”的標簽,但是就這幾句話,就這幾個字,人人看到的,就是一幅痞子的嘴臉。我當然不是說這幾個字就成就了對劉邦的描寫,而且這些字的換用很可能還有語法上的要求,但是它們對于描寫劉邦的貢獻卻是可以體會出來的。
這種對人稱的講究在各種語言的作品中都有。保爾·柯察金注意到冬妮婭把“您”字換成了“你”字,少不得有些激動;不少法文小說中也特別注意 vous 和 tu 的用法,甚至愷撒臨死前最后一句 et tu 的 tu 字也讓歷史學家增加了不少評論和遐想,但是在我們中文中這一件事似乎更加值得特別的注意。這是因為在傳統社會中,— 其實就是在今天的非傳統社會中也一樣,稱呼是人和人相互關系的一個特別明顯的、極具代表意義的表現,而對于長幼尊卑的關心又是我們在文化上的一個突出的方面。《紅樓夢》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由當年“太太的陪房”周瑞家的帶去見鳳姐。進門以后,看見這位“鳳姑娘”“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 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慢慢的問道:“怎么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著呢。這才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時,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著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說。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快攙起來,別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
忙回道:“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可以留意的是,這是書中第二次,也是總共兩次之中的一次,對鳳姐的正面介紹。前一次是在黛玉剛到之時,鳳姐張揚瀟灑,而賈母把她作為“鳳辣子”介紹給初來的黛玉,使得后者“不知以何稱呼”(第三回)。這次我們看見的鳳姐是內斂安詳,無怪乎脂批要說是一幅美人圖,而她的客氣話竟然也是“不知是什么輩數,不敢稱呼”。稱呼,小術也,何至于如此大費周章?
梁章鉅《稱謂錄》序:古人稱謂,各有等差,不相假借,其名號蓋定于周公制禮之時。章鉅,乾道間人,生于書香門第,嘉慶七年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江蘇巡撫兼理兩江總督。《稱謂錄》成于一八四八年,在撰寫過程中和成書以后,得到如阮元、林則徐之屬的關注,至于“心目為之炫耀。”何也?因為稱謂之事一下子被提到了周公和“禮”的高度,這是很嚴肅的事,因為“禮”正是我們文化的核心概念。正是因為如此,稱謂才集中地反映了人物的社會地位和關系,進而反映了當時的文化環境和習氣。汪曾老的文章中說傳神的精妙在于對眼睛的描摹,這兒“眼”似并不一定要坐實真實的眼睛。古人論詩有詩眼之說,文章小說也常有這種一語中的的大筆,且形態更臻豐富,稱謂當也能稱其一面。
《水滸》深諳此道。第七回(回目從上海古籍百二十回本)陸虞侯要酒保找董超商量害林沖:
董超正在家里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里的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
三十八回戴宗出場時,說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緊接著則特別加上一段說明:“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院長’。”這些稱呼以最經濟的筆法,為讀者構建了一種環境,使得讀者恍然置身于“故宋”,而當時的人對于稱呼的敏感,也常常出現在故事情節之中,成為故事的一個部分。第三十五回,宋江收編各路人馬,“隨行十數人”,投梁山泊來,進路邊酒店,一時擁擠,酒保就要同在店堂里吃酒的石勇換一副座頭:
酒保……道:“有勞上下,挪借這副大座頭與里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什么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
由此引出了石將軍。而先前武松在酒店和孔明、孔亮兄弟爭吵,似乎也是由稱呼不合而引發的(三十二回):
…… 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
就為了說武行者不該自稱“老爺”,這店主吃了一頓好打,“半日掙扎不起,”而孔氏兄弟也因此介入,把武松拖到莊院里,又陰錯陽差地見到了宋江。至于五十九回魯智深,問題就更嚴重了。為的是誤用了稱謂,竟一下子被賀太守識破就里:
魯智深道:“灑家又不曾殺你,你如何拿住灑家,妄指平人?”太守罵道:“幾曾見出家人自稱灑家。這禿驢必是個關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強盜……”
這三例特別提醒我們,稱呼絕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小節,它和人物身份、地位高下,甚至故事的情節,有直接的關系。書中人如此留意,讀者或聽眾自然也會留意,因為在真實的生活中真是這樣,要想再現真實的場景,這一細節自然馬虎不得:
林沖和魯智深當然是在《水滸》寫得最飽滿的人物之列。他們兩人在第七回相見時,魯智深正和一群潑皮在酸棗門外的菜地里演示器械。林沖“看得入眼”:
口里道:“這位師父,端的非凡……”眾潑皮則說“這位教師喝彩,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
這是初見,第一段,林沖稱魯智深為“師父”,智深稱林沖為“軍官”,— 尚未結識,泛泛而已。林沖受邀,跳入墻內,林沖改口稱智深“師兄”,智深答稱“教頭”,自稱“灑家”。“灑家”即“沙家”,《字典》說是“五代宋初人自稱……音‘蛇’”。兩人又近了一步。而林沖作為“頗識幾字”(第十一回)的軍官,用詞自然比智深要稍稍文一些。待到使女錦兒來報,林沖妻張氏在岳廟有了麻煩,林沖匆匆趕去,撞著高衙內,“一時被人勸了”。轉出來見著智深,“大踏步搶入廟來,”這是第三段,形勢緊迫,不暇多說,用的是“我”、“你”:
林沖見了,叫道:“師兄哪里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廝打。”
林沖說明緣由,情形并非如此火爆,原來是高衙內,而他也不想把事情鬧大,
智深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灑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灑家三百禪杖了去。”
用“你”,用“灑家”,用“俺”,用“他”,悃愊率直疾惡如仇的魯提轄躍然紙上。最后一段,“眾潑皮扶著智深”,智深和林沖夫婦告別,雖然有些醉,但是不失親切,不失智深的憨戇:
智深提著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會。”
“阿哥”“阿嫂”,是為傳神。短短一千字,場景情節迅速轉換,稱呼凡十數變,而與人物身份、故事發展,絲絲入扣,絕無一分錯亂,足可稱縝密精深。無怪乎人物豐滿,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種文字,入口即化,咀嚼無滓,自然位列經典,而細節的考究則貫穿始終。錦兒稱張氏為“娘子”,林沖則稱她為“大嫂”(第七回),張清叫孫二娘為“渾家”(第二十七回);梁中書的蔡夫人稱丈夫為“相公”(第十六回),徐寧的妻子稱他為“官人”(第五十六回),而何濤的老婆則叫他“丈夫”(第十七回);黃文炳稱蔡九知府為“公相”,自稱“小生”,蔡亦以官職稱之為“通判”,自稱“下官”(第四十回),至于吳用自稱“小生”,宋江自稱“小吏”,當然也不是隨口為之,而讀書人當有能品其滋味、道其奧妙者。至于桃花山上的土匪小霸王周通夢寐有人壓寨,下山掠奪,稱劉太公的女兒為“我的夫人”,自稱“老公”(第五回),倒是和我們現在不少人的用法不謀而合了。
稱謂,小術也。對于“傳神”的貢獻,仍不宜忽略。我們不得不拳拳服膺經典著作家精細的琢磨,不得不深深感嘆勾欄說話人百年的推敲,因此有此“注記”,不避小題大做之嫌,實為芹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