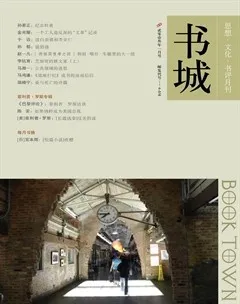一影三千世界
認(rèn)識(shí)王寅,沒(méi)有讀他的詩(shī),卻喜歡上了他的攝影作品。有攝影近作他都會(huì)電郵過(guò)來(lái),我則會(huì)花時(shí)間一一打開(kāi)來(lái)細(xì)細(xì)品味。他背著相機(jī)全世界轉(zhuǎn)悠,攝得無(wú)數(shù)的“剎那”。光憑那種風(fēng)情萬(wàn)種的異國(guó)風(fēng)貌,再加上詩(shī)一樣的鏡頭捕捉,這種結(jié)合使得他的作品讓人十分喜歡。
我相信王寅喜歡法國(guó),他的不少上乘作品都是在法國(guó)拍的。一個(gè)國(guó)家就像一個(gè)女人一樣,風(fēng)情氣韻均是天成,絕不會(huì)是后天修飾、增補(bǔ),抑或整容打補(bǔ)丁。從根底里散發(fā)出來(lái)的基因是真的氣質(zhì)。法國(guó)的浪漫絕對(duì)是人的本性與本色的圖像。王寅的《巴黎之吻》,當(dāng)時(shí)我看了就驚叫,巴黎的旅游總局應(yīng)該把它收為他們的明信片。在無(wú)數(shù)浪漫的照片中,這是一張非常好的作品。一對(duì)戀人騎著自行車(chē)在馬路上迎面邂逅,驚喜之余,腳沒(méi)有離開(kāi)自行車(chē),扭過(guò)身去深深地接吻,旁若無(wú)人,身后是車(chē)水馬龍的都市背景。那幅異常有名的《維爾旅館前的接吻》已是巴黎的明信片了,王寅的《巴黎之吻》與之相比有另番的浪漫。
看了王寅的作品,不覺(jué)很煩惱,自忖也該走遍世界,隨身帶一個(gè)“傻瓜”,但……王寅是個(gè)狙擊手,他可以為了那一剎那而耐心地等待捕捉那幾個(gè)小時(shí)。符號(hào)學(xué)大師羅蘭·巴爾特發(fā)明了“刺點(diǎn)”攝影理論,有點(diǎn)像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理論的詩(shī)眼。王寅的實(shí)踐告訴我們,有知點(diǎn)才會(huì)有“刺點(diǎn)”。可以想見(jiàn),王寅那張心的底片早已是無(wú)數(shù)次地被曝光。正因?yàn)橛辛诉@張無(wú)數(shù)次被曝光的心的底片,他才可能獲得那難得一見(jiàn)的剎那,這就是王寅成功的原因。

《巴黎之吻》可以說(shuō)是王寅作品的基調(diào),有滲透著明媚草香的文本快樂(lè)。他喜歡捕捉詩(shī)意的畫(huà)面,他的感覺(jué)是為了詩(shī)意的畫(huà)面而去展開(kāi)的。換一種說(shuō)法是,詩(shī)意畫(huà)面的閃現(xiàn)正契合了他的詩(shī)心。讀他的照片可以得出如此結(jié)論:攝影術(shù)是畫(huà)家發(fā)明的,攝影藝術(shù)卻是詩(shī)人發(fā)現(xiàn)的。
有趣的是,我在讀王寅作品的同時(shí),又看到了北島的攝影作品《圖》。詩(shī)人去捕捉生活中的詩(shī)照片,好像成了一個(gè)必然。北島的攝影語(yǔ)言明顯地偏于抽象、變形、夢(mèng)幻,有不少是色、形、光的形式表現(xiàn),比之他的詩(shī)歌語(yǔ)言明顯是兩種路數(shù)。詩(shī)性的復(fù)雜、神秘,卻讓那么可視、客觀的攝影去承擔(dān),似乎有點(diǎn)吊詭。詩(shī)性也可視是相去甚遠(yuǎn)的事,現(xiàn)在要讓詩(shī)的意味無(wú)比的揮發(fā)性與攝影的毫發(fā)畢現(xiàn)性結(jié)合起來(lái),這正可以彰示當(dāng)今藝術(shù)的一種新趨勢(shì):美學(xué)語(yǔ)言、藝術(shù)語(yǔ)言在更新中。
王寅的《攝手記》鮮有中國(guó)的照片。是心的底片沒(méi)有準(zhǔn)備好,還是根本就沒(méi)有這張心的底片?中國(guó)的當(dāng)代是一個(gè)有另類(lèi)詩(shī)意的發(fā)現(xiàn)點(diǎn)。二○一二年十月的中國(guó),中央電視臺(tái)記者現(xiàn)場(chǎng)采訪(fǎng),訪(fǎng)到一個(gè)街頭揀垃圾的人。記者問(wèn):“你幸福嗎?”回答:“我姓曾。”一問(wèn)一答重復(fù)了兩次。這一幕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是無(wú)數(shù)的悖論。這里有語(yǔ)義學(xué)意義上的悖論,有邏輯學(xué)意義上的悖論,有倫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悖論。這些悖論的充分解讀可以顯現(xiàn)當(dāng)今社會(huì)現(xiàn)狀的復(fù)雜矛盾,以及應(yīng)對(duì)矛盾上的多重荒誕。這種荒誕和畸變?cè)诋?dāng)今中國(guó)俯首皆是。荒誕也是一種詩(shī)意,另類(lèi)的詩(shī)意,后現(xiàn)代的詩(shī)意。我相信,王寅會(huì)對(duì)此有興趣。

《攝手記》讓人最大的感悟是,藝術(shù)語(yǔ)言的更新在當(dāng)今必須是藝術(shù)的時(shí)髦。藝術(shù)體與自然體的最大區(qū)別是:前者是以修辭來(lái)立身、立法、立行的東西,沒(méi)有修辭就沒(méi)有了藝術(shù)。很多人把修辭看作是一種手段、方法或者過(guò)渡,這是很大的誤會(huì)。橋梁是人到彼岸可以忽略掉的東西,修辭卻是文體的生命。從本質(zhì)上而言,沒(méi)有修辭就沒(méi)有藝術(shù)。修辭格中的比喻是第一位的,從比喻到象征,到暗示,到寓言,到游戲,到迷宮,是無(wú)窮盡的延伸,比喻是基礎(chǔ)的基礎(chǔ)。把藝術(shù)的語(yǔ)言延伸到無(wú)窮狀態(tài),比喻是元敘述的根本。所以我們必須在文本研究中講究比喻的研究。在后結(jié)構(gòu)主義與符號(hào)學(xué)的理論中,已經(jīng)充分地認(rèn)識(shí)到“表面上看來(lái)可以取其字面意義的,實(shí)際上都帶有喻義”(《解讀后現(xiàn)代主義》170 頁(yè))。比喻的技巧和比喻表達(dá)的含義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哲學(xué)、文化學(xué)、文學(xué)等人文研究的顯學(xué)。王寅的作品使隱喻(或稱(chēng)換喻)與轉(zhuǎn)喻有了一個(gè)明顯的區(qū)別。在今天很多研究理論的人眼中,隱喻與轉(zhuǎn)喻是沒(méi)有根本區(qū)別的,有的人甚至不承認(rèn)有轉(zhuǎn)喻這樣一種藝術(shù)語(yǔ)言的存在。這個(gè)看法有極大的片面性,之所以成為片面是
因?yàn)樗麤](méi)有認(rèn)識(shí)到,新的時(shí)代需要新的語(yǔ)言。我們必須看到,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已經(jīng)充分證明轉(zhuǎn)喻現(xiàn)象已經(jīng)不盡然是一個(gè)修辭格的存在,而且是一種新型的美學(xué)語(yǔ)言和藝術(shù)語(yǔ)言的表現(xiàn)。
認(rèn)識(shí)轉(zhuǎn)喻確是后現(xiàn)代的事,羅蘭·巴爾特在他的著名作品《從作品到文本》中已對(duì)轉(zhuǎn)喻有了明確的認(rèn)定。我們?nèi)绾蝸?lái)比較隱喻和轉(zhuǎn)喻的區(qū)分以及它們的特征,如下的敘述只能是概而言之而又概而言之。隱喻和轉(zhuǎn)喻的第一個(gè)區(qū)別是:隱喻是信息發(fā)布者明確有意所為,反之是轉(zhuǎn)喻。(羅蘭·巴爾特把藝術(shù)說(shuō)成有三個(gè)信息:語(yǔ)言信息、編碼的圖像信息和不編碼的圖像信息。《視覺(jué)文化研究讀本》112頁(yè))隱喻是編碼的信息,轉(zhuǎn)喻是不編碼的信息。第二個(gè)區(qū)別:從信息發(fā)展的范圍來(lái)看,隱喻是有范圍的,而轉(zhuǎn)喻是沒(méi)有范圍的。第三個(gè)區(qū)別:從信息內(nèi)容的成像性來(lái)看,隱喻的信息呈現(xiàn)出來(lái)的一般是成像的信息,它是一種具體的形象,無(wú)論是感覺(jué)還是知覺(jué)都構(gòu)成了一個(gè)形象。信息最終是可知的,包括用言語(yǔ)符號(hào)可以作明確的圖釋?zhuān)坏D(zhuǎn)喻的結(jié)果就不一定是可知的,從可知發(fā)展到不可知,有可能是不可測(cè)的,甚至像謎語(yǔ)一樣。第四,從信息的狀態(tài)來(lái)說(shuō),隱喻信息的發(fā)生、發(fā)展的狀態(tài)是一種契合現(xiàn)象,喻面與喻底的信息基本上是契合的;轉(zhuǎn)喻信息的發(fā)生、發(fā)展的狀態(tài)是一種伸延現(xiàn)象和揮發(fā)現(xiàn)象,是一種轉(zhuǎn)態(tài)的狀態(tài)。第五,隱喻信息的成立必須有語(yǔ)境條件的存在;轉(zhuǎn)喻則可以突破語(yǔ)境條件,作某種放大的伸延。第六,從喻面信息的量和存在形式看,隱喻的喻面信息的量不是很大,存在形式較封閉;而轉(zhuǎn)喻喻面信息的量卻很大,往往呈多維度、多向性的開(kāi)放狀態(tài)。第七,從信息的反饋現(xiàn)象看,隱喻信息的承接方是一般意義上的生產(chǎn)方;而轉(zhuǎn)喻信息的承接方必定是特殊意義上的生產(chǎn)方,更大的生產(chǎn)方。
當(dāng)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截然區(qū)分,隱喻與轉(zhuǎn)喻有區(qū)別,但它們又有粘連、延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攝手記》里面有兩張照片,拍的是同一個(gè)地方—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yíng)。一張拍的是鐵絲網(wǎng),一張拍的是一條鐵路,時(shí)間都是冬天,白雪皚皚。這兩張照片都很成功。我的解讀,鐵絲網(wǎng)的照片像隱喻的藝術(shù)語(yǔ)言,鐵軌的照片更像轉(zhuǎn)喻的藝術(shù)語(yǔ)言。鐵絲網(wǎng)的照片拍的不是單向照,如果拍的是單向照,那就沒(méi)有意韻。照片顯示的完全是一個(gè)立體的跨面,占了整個(gè)畫(huà)面五分之四的電網(wǎng),側(cè)面的電網(wǎng)向無(wú)限的天邊一直延伸過(guò)去。這樣的鐵絲網(wǎng)幾乎把整個(gè)視覺(jué)都囊括了。白雪,刺骨的寒風(fēng),遠(yuǎn)處有一排矮矮的房子。這張照片給人一種寒徹心脾、了無(wú)人氣的刺激。法西斯專(zhuān)政的暴行的喻義不言自立。但應(yīng)該看到,這張照片所表現(xiàn)的喻底和喻面的語(yǔ)言所指是很清楚的,是線(xiàn)型的,而且喻底與喻面的語(yǔ)言是契合的,能夠從這張照片延伸的意義是有限的。另一張照片拍的是鐵路,背景的遠(yuǎn)處仍然是集中營(yíng)那種矮矮的房子。雙頭肩跨的構(gòu)圖是一個(gè)無(wú)限延伸的透視現(xiàn)象,給人一種一直要延伸下去的姿態(tài),從這樣的一個(gè)角度去拍攝集中營(yíng),喻義不但強(qiáng)烈而且深遠(yuǎn)。在鐵路的旁邊是冰雪、枯草,遠(yuǎn)處赫然在目的是集中營(yíng)的進(jìn)門(mén)口,這條鐵軌的延伸給人一種沖擊力,直接沖擊到人的內(nèi)心深處。這張照片的基本構(gòu)圖非常成功。它是一種無(wú)限擴(kuò)大式的構(gòu)圖,所以才會(huì)有如此強(qiáng)烈的感染力。同時(shí),這張照片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喻底無(wú)限延伸,喻底清晰又不明確,有所指范圍,又沒(méi)有范圍,由此達(dá)到了沖擊力量。它用的是轉(zhuǎn)喻。讀這張照片,心里會(huì)涌現(xiàn)出很多的問(wèn)號(hào),這條鐵軌還在嗎?它在哪里,還在延伸嗎?它最后要通往哪里呢?當(dāng)代猶太人的生與死是從這條鐵路開(kāi)始的嗎?這場(chǎng)悲劇的起點(diǎn)在哪里,終點(diǎn)在哪里?人類(lèi)的悲劇有結(jié)局嗎?……這些問(wèn)題都會(huì)紛至沓來(lái)地敲進(jìn)人的心里。浪漫藝術(shù)和象征藝術(shù)更多講的喻面和喻底的無(wú)限擴(kuò)大,讓喻面和喻底的不同處越來(lái)越多,距離越來(lái)越遠(yuǎn),于是,喻底和喻面的不同處就產(chǎn)生了張力。但是,隱喻的張力是必須讓喻底與喻面契合一塊,有了共同的語(yǔ)言才會(huì)讓張力生發(fā)出意味來(lái)。契合是張力的歸宿。轉(zhuǎn)喻就不是這樣,轉(zhuǎn)喻是由一點(diǎn)而起的無(wú)限波瀾,無(wú)窮盡的延伸,張力是延伸。王寅的奧斯威辛鐵路就是這種有無(wú)窮藝術(shù)意味的轉(zhuǎn)喻。

《哈佛像前的少年》是一張成功的照片。夕陽(yáng)下,背景的明亮與銅像、少年的逆影有明顯的差別,這個(gè)背景與背影有了三層次的混唱。鏡頭用仰拍,哈佛銅質(zhì)雕像的原色拍得很細(xì)膩,低頭沉思的少年仿佛成了一幅剪紙,只形成落寞一詞。哈佛的頭是仰視的,落寞少年的頭是俯看的,這種對(duì)比一下子就會(huì)令人引伸出一種思緒來(lái)。這種思緒就是一種決心,一種勃勃向上的暗示。但是,這終究還是在一個(gè)信息有限的范圍內(nèi)的擴(kuò)展。《十四地鐵站出口》是一張更精彩的照片。照片如同黑白剪紙,地鐵站逼仄的一角,出現(xiàn)一位行走中的漂亮女生,馬尾辮,曼妙的動(dòng)態(tài)手指,前進(jìn)著,占了畫(huà)面的中間。背景是矗切面的大廈,正中上方露出晴藍(lán)的天空,縱橫交叉的是飛機(jī)的白色航跡。照片的黑白對(duì)比,靜與動(dòng)的寓意充分顯現(xiàn)出現(xiàn)代文明的對(duì)峙,以及對(duì)峙中人的走向等無(wú)窮盡的邏輯聯(lián)想。符號(hào)的可視性與能指的不可比擬性有了交融。《攝手記》在表現(xiàn)后現(xiàn)代文明世界的困境話(huà)語(yǔ)上有很多照片,而且很成功。后現(xiàn)代的人們正生活在一個(gè)充分異化、充分荒誕的環(huán)境中。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人該怎么活著,人類(lèi)文明該怎么發(fā)展,這些都是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文本母題。對(duì)于這個(gè)母題,可以用比較淺顯的語(yǔ)言去表現(xiàn),也可以用更深?yuàn)W的語(yǔ)言去表現(xiàn)。可以看兩幅照片,一幅是《攝手記》中的照片叫《德里電器市場(chǎng)》,背景是一幅巨大的廣告,一個(gè)漂亮的女人手挎手提電腦,傲然而去,轉(zhuǎn)身斜睨的一瞬間。巨大廣告下方的陰暗處站著四個(gè)衣衫襤褸的、渺小的男人。這張照片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人與人、人與物、大自然與人、廣告與人的異化現(xiàn)象是充分的,強(qiáng)烈的,但也是有限的。另一幅照片《白夜》,也是表現(xiàn)后現(xiàn)代文明困境的,但用轉(zhuǎn)喻的語(yǔ)言去表現(xiàn),所見(jiàn)就更深更廣。《白夜》的背景是一個(gè)若明若暗的詩(shī)歌朗誦會(huì)的一角,前方是詩(shī)歌朗誦會(huì)的廣告牌:“詩(shī)歌的今天。”拍攝的主角卻是兩雙鞋子,一雙是男性的大頭登山鞋,一雙是穿著大裙子的女性的涼鞋。不見(jiàn)鞋的主人形象,只是兩雙鞋子,在朗誦會(huì)的廣告前面。這張照片的“刺點(diǎn)”就是女性的涼鞋。照片的喻義正是在物質(zhì)世界與精神世界、男性與女性、夏天與冬天等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與沖撞之間引申出來(lái)的無(wú)窮語(yǔ)言。
讀《攝手記》,品之有無(wú)窮意味的作品還有《后臺(tái)》、《瞭望山莊》,還有《再也不會(huì)老去的時(shí)間》。
美國(guó)著名畫(huà)家安特魯·懷斯的畫(huà)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是一幅帶動(dòng)了一代畫(huà)風(fēng)和一種藝術(shù)語(yǔ)言表達(dá)的巨作。我認(rèn)為它是一幅特別具有轉(zhuǎn)喻意義的作品。畫(huà)作的大背景是一大片荒草地,在它的下方,一個(gè)作匍匐姿態(tài)的少女伏在地上,向前方伸出了不屈服的手,場(chǎng)面是空曠而又孤寂,少女的神態(tài)是凄慘而又執(zhí)著,遠(yuǎn)方是一棟小小的房子。它并不是簡(jiǎn)單地在象征一個(gè)什么,或者在比喻一個(gè)什么,更不是在狀物寫(xiě)人,它是把人與物、空曠與人物、凄慘與執(zhí)著等等作著無(wú)窮的比較,然后展開(kāi)了一個(gè)很長(zhǎng)的對(duì)話(huà),對(duì)人性作著默默的禮贊,讓人在感悟中心靈隨之震顫。這的確是一幅偉大的作品,這幅作品曾經(jīng)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引來(lái)了中國(guó)無(wú)數(shù)青年油畫(huà)家的追捧和模仿。像這樣一種藝術(shù)語(yǔ)言的表達(dá),我認(rèn)為《攝手記》中也有。最成功的就是那幅《冬天里的第一場(chǎng)雪》,這張照片可以讓人無(wú)窮咀嚼,品至無(wú)限。畫(huà)面全部被雪覆蓋著,遠(yuǎn)處的一條河流還在流動(dòng)。冰封的道路和暗黑的河流是一個(gè)明顯的對(duì)照,形成一個(gè)起伏。樹(shù)是這個(gè)畫(huà)面的主角,一棵玲瓏剔透、枝丫分明、像一朵花一樣的樹(shù),是作這個(gè)世界的凝照,還是作人的凝照?就在這棵樹(shù)的下方,一個(gè)矮矮的人在默默地行走著,在快速地行走著。人是黑色的,背景是白色的,人仿佛可有可無(wú),自然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但人仍然是固執(zhí)地向前走去。照片的右上方歪歪地豎了一個(gè)路牌,上面指著路的方向似清楚非清楚。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說(shuō)明今天的世界是何等復(fù)雜:大自然與人的矛盾,規(guī)范與失范的矛盾,方向的矛盾,時(shí)間和空間的矛盾,永恒與瞬間的矛盾,存在與意義的矛盾,等等。人類(lèi)的一切行走意味著什么呢?大自然有指向性的方向嗎?在新藝術(shù)面前,讀者與觀眾必須成為廣義上的生產(chǎn)者。羅蘭·巴爾特聲言“作者已死”的真正含義是作為上帝的作者已死,讀者與觀眾已成為了生產(chǎn)者。對(duì)王寅作品的解讀可能正是再創(chuàng)造的開(kāi)始。
照片是靜態(tài)的思路,必須把動(dòng)態(tài)的東西引進(jìn)來(lái),才會(huì)引起人的欣賞語(yǔ)言的生發(fā),比如說(shuō)在照片《瞭望山莊》中,對(duì)于嵐氣的拍攝,那就是很好的動(dòng)態(tài)拍攝。最成功的是《下午的廚娘》,是一個(gè)非常成功的畫(huà)面:一個(gè)少女,那么優(yōu)雅、莊重,廚娘打扮的她,正在料理食品。一種慈祥的美麗,最成功是那一片午后的陽(yáng)光,那種通體光明的輝照,陽(yáng)光下少女慈悲而溫柔,讓人有圣女降臨般的肅然起敬。美是多么好的一件東西,人是可以美的。在這里,法國(guó)詩(shī)人瓦雷利的名言“溴化物被證明遠(yuǎn)遠(yuǎn)勝于墨水”,可以得到印證。
攝影藝術(shù)以其毫發(fā)畢現(xiàn)的真實(shí),讓人深感蘇珊·桑塔格所言的“侵略性”。題材的無(wú)所不在,方法的無(wú)所不用,讓攝影藝術(shù)的趣味追求有無(wú)窮可能。我認(rèn)為這種追尋有很多層次,從物趣到意趣,到思趣,到禪趣。物趣是比較單純的,能夠悟出大自然與世界的意味的,比如說(shuō),他的作品《圣納澤爾》。意趣是一種感覺(jué)上的升華,比如他的作品《在等待朗誦會(huì)開(kāi)始的時(shí)候》。《后臺(tái)》是一幅很成功的照片,背景是一個(gè)中老年男人的巨大的模糊背影,照片的下端,是一雙靈巧的、跳著芭蕾舞的手指,靈手清晰無(wú)比。這會(huì)讓人有無(wú)窮的感覺(jué)與思緒的升華。《海灘上的凳子》面對(duì)著地中海,海邊一排的凳子都坐著人,只有中間有一個(gè)空位,一個(gè)男人在凳子的背后悠閑地跨步行走,這是令人深思的一個(gè)作品。《攝手記》拍了很多人物照,記錄了很多人物,但真正生發(fā)趣味的,我認(rèn)為是《翟永明》的照片,背景是整整一個(gè)墻面的涂鴉,連消防水龍都是涂鴉,青灰色的基調(diào),翟永明支著腳斜靠在電線(xiàn)桿旁,側(cè)臉看別處,松弛而又別樣的站姿,綠色調(diào)子的著裝,與整個(gè)背景相映成趣,生發(fā)出無(wú)窮意味。
藝術(shù)本質(zhì)上的最高層次一定是對(duì)于生命和宇宙的思考,生與死,開(kāi)始與結(jié)束,滅亡和新生,在這里面,人類(lèi)表現(xiàn)出那種追求,執(zhí)著,無(wú)奈甚至虛幻,從最大的秘密上探尋下去,這就有了禪趣。《攝手記》有七幅拍墓地的照片,可見(jiàn)作者對(duì)于生死、宇宙這種大命題的興趣。墓地,陰與陽(yáng)、生與死、明天和今天都在這里交接,如何讓攝影這種寫(xiě)實(shí)的東西去揮發(fā)哲學(xué)意味,的確是有意義的探險(xiǎn)。那張拍攝薩特與波伏娃墓地的照片,可能是陽(yáng)光與其時(shí)地不能作比較,也可能是把兩個(gè)妙齡少女與墓主人作了太明確的比較,照片的意味并不多。拍喬伊斯墓地的那張卻很有韻味。照片的主角是喬伊斯的塑像,蹺著二郎腿,左手拈煙,轉(zhuǎn)過(guò)頭去,悠然的姿態(tài),緊瞇著雙眼,向遠(yuǎn)方投去思索的看。最靈奇的是照片的中上角,一大片陽(yáng)光突然撕開(kāi)了綠蔥籠撲面而來(lái)。這片陽(yáng)光好像打通了前世與今生、存在與意義的無(wú)窮話(huà)語(yǔ)來(lái)。攝影要去作這樣的禪趣追求,終究在能力上好像還不如繪畫(huà)。繪畫(huà)因其特殊的虛構(gòu)創(chuàng)造性,可以作出像斯塔夫·克林姆《生與死》這樣的作品。這種作品會(huì)讓人思之無(wú)窮到望而生畏。
環(huán)顧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視覺(jué)藝術(shù),無(wú)論是繪畫(huà)、攝影,還是電影,藝術(shù)話(huà)語(yǔ)的生成地點(diǎn),或者叫載體,越來(lái)越喜歡這樣幾個(gè)物體:窗、門(mén)、橋、船、樓梯、鏡子等。它們?cè)絹?lái)越成為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元話(huà)題。蒙克的《嚎叫》是在橋上的一種思考。電影從《魂斷藍(lán)橋》到《廊橋遺夢(mèng)》,都是從橋指向夢(mèng)。繪畫(huà)、攝影以窗作為畫(huà)中畫(huà)的更是無(wú)數(shù)。窗、門(mén)等元話(huà)題的成立,果然有其物理學(xué)聚焦法則的作用,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理論窺視欲的擴(kuò)大,藝術(shù)學(xué)理論實(shí)與空、虛與實(shí)、小與大的落實(shí)等無(wú)數(shù)理由,其根本還有人類(lèi)的藝術(shù)趣味在更新,在重塑,追求更大的虛空,更多的延伸成為必然。在這一點(diǎn)上,在藝術(shù)語(yǔ)言的建構(gòu)上,王寅的《再也不會(huì)老去的時(shí)間》是一種探索。攝影最適合制造時(shí)間的創(chuàng)傷。這張照片也是窗外與窗內(nèi)作著無(wú)窮延伸意義的比喻象征,作者面對(duì)的更多是窗內(nèi)的景物,引申的意義正如他的文字:“誰(shuí)曾經(jīng)到過(guò)這里,曾經(jīng)在這里坐過(guò),克格勃?斯塔西?FBI?東西柏林交界處的一家餐館,大而無(wú)當(dāng)?shù)目臻g,只在窗前放了這張小桌,一把木椅和兩把表面破損的沙發(fā)。……你想到了冷戰(zhàn)小說(shuō),想到了《竊聽(tīng)風(fēng)暴》,那些隨波逐流的人們,那些無(wú)法蘇醒的噩夢(mèng)。現(xiàn)在,誰(shuí)還會(huì)坐在這些椅子上抽一支煙,喝喝咖啡,聊聊天氣,是那些喬裝改扮的間諜,還是再也不會(huì)老去的時(shí)間?”攝影的旁邊加文字是一種必要,也是一種不必要。圖景與文字會(huì)互相吞噬,互相消融,把各自的翅膀都折斷了。讓它們交疊而不消融、對(duì)峙而不吞噬是一種藝術(shù),是不同文本同呈的藝術(shù)。這幅照片的文字附言只需要“東西柏林交界處的一家餐館”即可。
很抱歉,我前面的文字是借王寅的酒澆我的塊壘。當(dāng)然,我的塊壘也適合他的酒,我的固執(zhí)是人類(lèi)現(xiàn)在要面對(duì)越來(lái)越復(fù)雜的世界,象迷宮一樣深不可測(cè)的世界,人從哲學(xué)思維到藝術(shù)思維的發(fā)展是宿命般的真實(shí)。人類(lèi)的整個(gè)藝術(shù)思考從語(yǔ)言學(xué)革命開(kāi)始,已經(jīng)從索緒爾的所指、能指的理論發(fā)展到了后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hào)學(xué)的理論。在后結(jié)構(gòu)主義哲人德利達(dá)看來(lái),“文字的降臨就是游戲的降臨”(《語(yǔ)言,身體,他者》117頁(yè)),現(xiàn)代科學(xué)-信息論-語(yǔ)言學(xué)-藝術(shù)論,這是一條不斷生發(fā)的鏈條革命。我的固執(zhí)的最后落腳點(diǎn)就是一句話(huà),轉(zhuǎn)喻作為新的美學(xué)語(yǔ)言、藝術(shù)語(yǔ)言屬一個(gè)后現(xiàn)代范疇。
現(xiàn)代攝影的命運(yùn)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言的那種無(wú)奈:“攝影的主要效果都是把世界轉(zhuǎn)化成一家百貨公司或無(wú)墻的展覽館。”(《論攝影》182頁(yè))這既是說(shuō)明攝影作為一種歷史索引物存在的客觀性,也是指攝影對(duì)于人的文化侵略之深的一個(gè)特征。我要搜索我腦中中國(guó)攝影巨大存在的話(huà),可能只能找出兩張照片。一張是比利時(shí)著名攝影家普列松在一九四九年拍攝的,在上海外灘銀行前排隊(duì)擠兌金元券的那個(gè)匪夷所思的畫(huà)面。還有另一張照片,就是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批斗國(guó)家主席劉少奇的照片。除了這兩張照片,其它的那些照片已經(jīng)非常非常之淡化了。在中國(guó),照片正是用它強(qiáng)大的侵略性而給人留下虛假的現(xiàn)實(shí),冒充歷史的索引。
佛經(jīng)有言:一念三千世界,一悟三千世界。是指人的一念在實(shí)相的基礎(chǔ)上,不受時(shí)間與空間的限制,不可言說(shuō)、不可思議地將千差萬(wàn)別的宇宙萬(wàn)象圓融而建立起來(lái)。這非常像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理論、文本理論與欣賞理論。一影三千世界是指文本呈現(xiàn)。佛教的一念與三千的關(guān)系非常辯證。既不能理解成一念在前,萬(wàn)法在后;也不能理解為萬(wàn)法在前,一念在后。只能說(shuō)心就是萬(wàn)法,萬(wàn)法就是心,二者的關(guān)系既非縱亦非橫,既不相同也不相異。這樣奧妙的理論比之以前我們崇尚的、愚蠢的反映論,何止霄壤相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