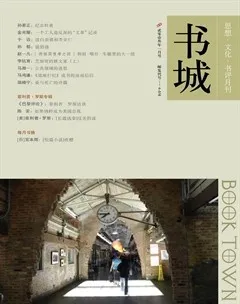媒介中的現代主義者—施蟄存

施蟄存先生與世長辭已經九年了,這樣一位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家、學者,理應受到持續的關注和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不計算單篇論文,九年來我只見過兩種研究專著,即《永遠的現代—施蟄存論》(楊迎平著,2007年5月光明日報出版社初版)和《現代之后:施蟄存1935—1949年創作與思想初探》(王宇平著,2008年5月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初版),后一種還是海峽彼岸出版的,可見施蟄存研究現狀不如人意。因此,當讀到張芙鳴女史這部《施蟄存:媒介中的現代主義者》書稿時,我的欣喜也就可想而知了。
話又得說回來,研究施蟄存確實存在相當的難度,這大概也是目前施蟄存研究相對滯后的原因之一。施蟄存具有多種文化身份,他不是一位單一的作家,只會寫寫小說和散文,而是正如他自己一再所說也已經廣泛流傳的,他一生開了四扇窗,東窗:新文學創作;南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西窗: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北窗:古代碑帖研究。他這四扇窗,每扇都開得很大,開得有聲有色,成就斐然。因而,研究者面對這樣一座礦藏豐富的文化大山,自身的學養、識見和可供利用的學術資源很可能遠遠不夠,能夠登堂已經不錯了,如何再窺堂奧,再深入研討?對這一點,施蟄存自己已有充分的估計。他生前就不止一次親口對我說過:某某研究我,他是好意,但他實在不懂,一些常識都弄不清楚,怎么研究呢?(大意)所以,選擇研究施蟄存,在學術上是個不小的挑戰。
本書作者長期研究施蟄存和“新感覺派”,已經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她這部新著又獨辟蹊徑,把施蟄存一九四九年以前多姿多彩的文學傳播活動與他的現代主義文學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分析探討,對施蟄存的文學成就作出了新的評估,也使本書成為一部別開生面的施蟄存文學前傳。
即使不算早期發表舊體詩文的《蘭友》,施蟄存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學傳播活動幾乎與他的文學創作伴隨始終。從《瓔珞》到夭折的《文學工場》,從《無軌列車》到《新文藝》,從《現代》到《文藝風景》,從《文飯小品》到《現代詩風》,從《活時代》到《大晚報》副刊《每周文學》和《剪影》等等,施蟄存或主編、或合編、或當發行人,他的文學傳播活動實在是豐富多彩。特別是他主編的《現代》,成為一九三○年代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進程不可或缺的一環,影響深遠。施蟄存參與文學傳播活動的時間之長,主編刊物之多,簡直直追新文學巨子魯迅。直到晚年,施蟄存還主編了享譽海內外的《詞學》叢刊,風華不減當年。或許可以這樣說,施蟄存一生實際上不止開了四扇窗,還有第五扇,那就是文學編輯之窗。


本書正是對施蟄存這第五扇窗進行系統的梳理和闡述,書中的描述不僅是全景式的,而且可圈可點。不妨舉個例。施蟄存早期主編或參與編輯的文學雜志,大都帶有同人刊物性質。從主編《現代》起,施蟄存改弦更張,力圖使之“成為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一切文藝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既倡導現代派文學,又提供一個讓各種傾向的新文學家傳播其作品和評論的盡可能寬廣的平臺。本書從商業運作下的《現代》、“新型知識傳播的《現代》”、“作為物質與技術形式的《現代》”、“現代的”文學和“自由的”文學的《現代》等多個角度切入,深入論述了施蟄存如何主編這份“一二八”事變之后“崛起于城市廢墟”中的大型新文學刊物。書中把《現代》置于“新型知識傳播”的背景之下,詳細分析施蟄存通過《現代》的“編輯座談”(后改稱“社中座談”),傳遞作者、編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指出施蟄存在實踐現代派文學的同時,也主動承擔起文學教育者的職責,“力求使文學的現代性體驗不僅發生在創作者、研究者層面,更能在處于知識轉化中的大眾讀者層面展開”,而這正是以前的施蟄存研究者很少論及的。
當然,本書的亮點還有很多。作者視野開闊,論證有條不紊,闡釋施蟄存的文學傳播活動,無論編輯、出版還是翻譯,都著力揭示其與他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實踐的關聯,與他的文學追求的關聯,與一九三○年代新文學態勢的關聯,乃至與整個中國新文學進程的關聯,從而使全書增加了厚度和說服力。這也是值得肯定的。
我才疏學淺,連施蟄存先生的私淑弟子都算不上,但由于工作的關系,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與他老人家有不少交往。我有自知之明,沒有專門研究過他的文學創作,更遑論其他幾扇窗,只為他編過《施蟄存七十年文選》、《北山散文集》(上下)初稿、《老古董俱樂部》等幾種著譯集而已。承張芙鳴女史不棄,要我為她的新著寫幾句話,只能就閱讀所得略陳鄙見,但愿這部新著的問世有助于施蟄存研究和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