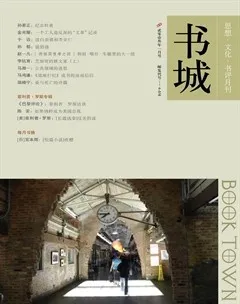郁達夫的東梓關


郁達夫于一九三二年發表的小說《東梓關》里,描寫了一個恬靜、悠閑、安然、自足的江邊小鎮,充斥著純樸溫暖的民風,鎮上住著遠近聞名的老中醫,岸邊有輪船碼頭,人們用早班輪船和晚班輪船的汽笛聲來判斷時間,傳統和現代化在這塊小天地里無聲地碰撞;航運也曾給小鎮帶來小小的繁華,池塘邊的青石板小街,一度店鋪林立;鎮側有突出到江中的石崖,崖頂有小廟和石雕欄桿,登臨可見“藍碧的天,澄明的水,和兩岸的青山紅樹”,以及“隔江的山影”,既可供豪邁之士“橫槊賦詩”,也可供飄零之人“把欄桿拍遍”……
二○○七年秋,我來到這里的時候,小鎮已經很破敗了,然而郁達夫所描寫的那些屋舍、道路和全鎮的格局,卻又歷歷在目,對得上號,以至逝去的那些笑語晏晏、噓寒問暖和往來熙熙,仿佛都并未走遠,或者都化作煙云,仍籠罩著這方土地。
郁達夫說:“東梓關本來叫作‘東指關’的,吳越行軍,到此暫駐,順流直下,東去就是富陽山嘴,是一個天然的關險,是以行人到此,無不東望指關,因而有了這一個名字。”后來,“這里所植的都是梓樹,所以以后,地名就變作了東梓關。”
除了一派古民居和石板小道,這個村突出的特色一是臨富春江,有一條風景不錯的江岸,二是村內多池塘。現在從公路進去,首先就碰見長塘,一百多米長的池塘邊一條小道,臨水一側是垂柳,另一側是帶木板門窗、鋪臺的老屋,也夾有磚石的高墻,大多就是當年的那些店鋪,據說鼎盛時期除了分門別類的油鹽柴米醬醋茶之外,還有一些本地特產,主要是糕點和中藥,不僅附近村鎮的人經常來買賣,富陽、桐廬、杭州也有人來,碼頭上很有點繁忙。池塘里長滿了水葫蘆,村里人對我們說,以前水很清,是大家淘米、洗菜的地方,更有人說起,以前這里是賞月的好地方。是啊,踏著石板小道踱步,看馬頭墻下印在水里的月,正是老派鄉紳常態的日子,就算販夫走卒,不論辛勞還是清閑,也難免自然沐浴在同樣的月光里。

這個一度繁榮、美麗的村子,基本上是注定要衰落的,和江南所有舊時小碼頭一樣,靠當年內河小航運業帶給它們的那點繁華,早就像退潮一樣迅速冷清下去。當東梓還是東圖鄉鄉鎮府所在地時,可能還有相當的人氣,后來撤鄉并入場口鎮,就更加冷清了。然而事情都有兩面性,正因為冷清,它才保留了比較濃厚的歷史和文化的痕跡,從另一面看,它也是資源和財富。
作為古村,東梓現存的“元素”是比較豐富完整的,古樹、小巷、門樓、徽式高墻大院、江邊小廟、江水和池塘……走進村里,也有很多細節可供駐足細觀。曾經改作“東梓供銷社”的大店鋪,如今鐵門緊閉,但仍有雄踞道口、財大氣粗的派頭;一位三歲兒童在磨出凹槽的木門檻上吃飯,飯粒漏了一地,他的爺爺推開木門,讓我們看天井四周的雕梁畫棟;幾處斑駁的高墻邊長著高大的枇杷樹或香泡樹,后者密集地結著大圓果,垂掛到廂房閣樓的圓孔窗戶前,伸手可及;有些庭院里還保留著舊時殷實人家觀花賞魚的格局,一般徽式建筑的天井是一個回字,四邊屋檐的滴水正對一圈水溝,有一家卻把回字的內圈建成一個井闌,雖然犧牲了天井的空闊,但增加了別樣的趣味,石井闌上的花草和瑞獸雕得細膩精美,兩條大青魚在里面慢騰騰地游,一位老太太背對井闌、面朝堂屋墻壁在看電視……距我去東梓之后兩年多,我的一位朋友也曾前往,拍回來的照片上,仍然是那位老太太在那個位置上看電視……
郁達夫用一個村莊的真實名字作為小說的題目,可以想象村莊給予作家的感受一定復雜而美好,除了恍若隔世的鄉村生活觸碰了亂世游子內心的溫情和隱痛,鄉村的風光肯定也起了重要作用。我前面說,郁達夫提到的事物,現在都還在。郁達夫下船上岸之后,就沿著石砌的主道進村,他判斷“這大約是官道了”。當我走在這條道上的時候,我很清楚少了什么,當時給郁達夫帶路的一位農夫,“把自那里來為辦什么事去的歷史述說了一二十次,因為在路上遇見他的人,個個都以同樣的話問了一句,而他總也一邊前進,一邊以同樣的話回答他們”,現在缺少的就是這些重復一二十遍的問答,這是自然的村莊與純樸的人們高度融合的結果。郁達夫也注意到了有幾只鴨在游泳的池塘,現在缺少的是清澈和淘洗者的身影……
小說《東梓關》說的是一個長期漂流在外的富陽籍青年作家,回家鄉養病,專程到東梓尋訪一位世交名醫的故事,主人公顯然有郁達夫自己的影子。而遇見的當地老人對我們說,郁達夫的確來過,就住在那里……老人指著的地方,是一幅美景,可以說是現在游東梓的高潮。一個池塘,叫冬瓜塘,不像長塘那樣呈長條形,而是略作橢圓,岸邊有垂柳,徽式大宅倒映在水中,水中也還有鴨;滲出斑斑黑漬的五岳朝天高墻下,有一個涼亭門樓,亭里靠水一側是石板路穿過,靠墻一側是八字形石臺階,階頂是大宅的門。最絕的是正前方一所院落,正門臨水,兩廂前出部分夾著一個寬敞的檐廊過道,雖為過道,同時也是一個絕佳的水榭,當年可以釣魚,可以賞荷,可以顧影自憐,也可以在陰涼的檐下支個畫架寫生鴨戲圖,如今靠墻堆放著一排久已不用的木板手推車。內院是個精致的走馬樓式四合院,這正是郁達夫前來求醫養病的許家大院,當時的主人就是名醫許善元。




穿村而過,就到了江岸上,四處灌木叢生,夾著一些白楊、楓楊、垂柳、無患子,還有正在開花的木芙蓉,腳下是江水,對岸是群山和岸邊整齊的樹。盡頭是個不高而壁立的懸崖,崖頂一塊平地,當地人叫它廟山,一株粗壯的大樟樹后面是個小廟,叫越石廟,傳說祭祀的是鎮守東梓關陣亡的越國石將軍,廟墻外半圍小道,緊貼崖邊,所以又有一圈石欄桿,其中一塊石欄板上有精致的浮雕。
站在這塊浮雕前,正是看姐妹山的位置,這里大概是個制高點,所以當年郁達夫向村中少年問路:“小弟弟,要看姐妹山,應該是怎么樣的走的?”少年的回答說明了那地形:“只教沿著岸邊,朝上直跑上去就對。”這個石崖,當地人叫它廟凸頭。凸頭的兩側,都有自然形成的港灣,較大的一個叫廟灣,灣里的埠頭叫官船埠,就是郁達夫登岸進村和離村上船之處。
一塊巖石叫作山,已經與人們對山的一般印象不符了,而姐妹山更是小得可愛,只是江心里兩堆露出水面的石頭尖尖。然而,在中國的廣大農村里,很多對過客來說不起眼的事物,于本地人卻有著朝夕相伴導致的特殊情感和觀感,并粘附著有益于教化的傳說。在小說《東梓關》中,姐妹山的傳說通過徐竹園的口講出來,說的是明末年間一對父母雙亡的幼女,因唯一的兄長被拉壯丁,失去生路而跳江。老中醫的結論是:“戰爭的毒禍,你說厲害不厲害?”


我對東梓關的觀感就是這樣,它曾經是個美麗的小鎮,現在凋零而雜亂,我所見的東梓關,與郁達夫所見,既是同一個,又很不相同,但郁達夫已經把它的靈魂寫了出來,它的靈魂也就因此而不死了。
本文圖片均系作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