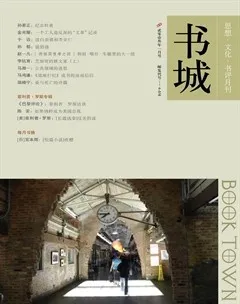讀白崇禧和李宗仁
白先勇先生編著的《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收集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和文獻,對認識和理解中華民國史上的重要人物白崇禧極有助益。白先勇先生是白崇禧的兒子,他在字里行間表露的對父親的敬愛尊崇,原是人之常情。但白崇禧是一位歷史人物,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功過是非,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便有不同的評價。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喜歡讀歷史,也喜歡讀雜書,有時也會從我們小老百姓的立場出發,對歷史上的大人物評頭品足一番。
我翻看《父親與民國》,不由得想起《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是民國時期的廣西雙杰,聲威赫赫的“桂系”首領,他們兩人從一九二四年起第一次見面,直到一九四九年底分道揚鑣—李宗仁流寓美國,白崇禧敗走臺灣—一直患難與共,親密無間地合作,以致世人有“李、白實為一人”之評,這是那個戰亂頻仍、無數人朝秦暮楚的年代中的一段佳話。
李、白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生死之交在一九四九年終止,李、白不再是“一人”,他們是不同的人了。將《父親與民國》與《李宗仁回憶錄》對照著看,他們兩人之間的不同便看得很清楚。


一、一將功成萬骨枯
我是平頭老百姓,我讀歷史,每當讀到名將彪炳史冊的輝煌戰績時,便想起這同時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哀吟。我常想,那些名將們,對使他們功成名就的萬骨,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因而我讀白崇禧傳記和李宗仁回憶錄,便對他們在暮年對自己軍旅生涯的反思尤感興趣。
李宗仁、白崇禧都是身經百戰、最能打仗的悍將,對北伐成功、抗戰勝利,均作出了巨大貢獻,這幾乎是所有中國人一致認同的歷史定論。到了國共內戰時期,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下野之后,李宗仁任代總統、白崇禧任“華中剿匪總司令”,兩人合力收拾殘局,先是希冀得到美國軍援,與共產黨劃江分治,旋即節節敗退,但仍組織兵力與共產黨解放軍周旋,直到打得不剩一兵一卒,離開大陸為止。
李宗仁晚年對他“劃江分治”的戰略有這樣的反思: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韓國、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

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到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的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李宗仁回憶錄》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10年版,下冊)
至于桂系在大陸打得不剩一兵一卒,《李宗仁回憶錄》則比《父親與民國》有更多的背景描述。據李宗仁回憶,共產黨解放軍渡江占領南京前夕(一九四九年四月),他飛返桂林。一連數日,廣西省軍政領袖懇求他接受現實,與中共妥協。他們寫了一封很長的建議書,請求李宗仁委曲求全,不要以卵擊石,廣西的文武官員幾乎全部在建議書上簽了名。但李宗仁拒絕他們的建議。他說他當時的心境是,“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辱”。“我國的傳統道德是謳歌‘斷頭將軍’,而鄙視‘降將軍’”。“我內心也知道,我們的失敗已經注定……但是我仍然強詞奪理,駁斥他們的投降論”。“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趕回桂林,一致反對投降,白崇禧尤其聲色俱厲,痛斥投降論者。……一般主和人士見到這種‘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辱志’的情況,知道多言無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隨我們和共軍作戰到底。”

事隔多年之后,李宗仁沉痛反省他當年的決定:
今日回思,深覺我們當時明知事不可為,純以意氣用事,與共軍火拼到底,致軍民多受不必要的犧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淺啊!(《李宗仁回憶錄》下冊)李宗仁所說的“我們”,應當包括白崇禧。在李宗仁的這段反思中,當年誓為“斷頭將軍”、打得不剩一兵一卒的勇邁,已被追悔為“致軍民多受不必要的犧牲和痛苦”的“罪孽”。白崇禧也是“打得不剩一兵一卒”的決策者和實行者,他是否也有李宗仁這種“罪孽”感呢?我讀《父親與民國》,看不到他有這種感覺。
據《李宗仁回憶錄》的記錄整理者唐德剛教授介紹,該書前后費時六七年,到一九六五年才定稿。這時,李宗仁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他的反思便是這段時間內記錄下來的。

在同一時段里,白崇禧在想什么呢?據白先勇先生在《父親與民國》中介紹,晚年的白崇禧“一心所系,仍為復國大業”,書中并附有白崇禧一九六六年二月寫給黃旭初的一封長信,白先勇先生說,“南宋抗金名將宗澤一心恢復宋室,臨終三呼渡河,父親信中國仇悲憤,庶幾近之”。
我將這封信細細讀了,不寒而栗。
白崇禧在信中從臺灣反攻大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美國越戰升級后的國際形勢,建議由美國促成組織東北亞同盟,裝備各國軍隊,共同對付大陸中國。
使我不寒而栗的是這段話:
反攻大陸開始時,美國應先將共匪蘭州、包頭兩處之核子工廠及海空軍基地,并政治、經濟、交通中心炸毀,使匪區各種活動陷于癱瘓,促進毛匪政權之瓦解。(《父親與民國》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版,下冊)
老實說,得知白崇禧一九六六年曾如此認真地要請外族將大陸中國全面轟炸摧毀,只為他心中的“反攻大業”,全然不顧億萬同胞的生命福祉,他在我心中的印象,便從北伐時的“小諸葛”、抗戰時日本人所畏懼的“戰神”變成視平民為草芥的戰爭狂人了。

我的這種反應,純粹是出于一個普通老百姓求生存的本能。如果白崇禧的這套反攻大陸戰略方案成功實施了,我和大陸的億萬百姓恐怕早就成了“萬骨”。一九六六年白氏有此戰略方案時,我還是個不知世事的十歲男孩子,他若“功成”,則我尚未長大成人即被炸死,到如今早已骨枯多年矣!幸虧他沒有“功成”!幸虧他沒有“功成”!
白崇禧未能反攻大陸,他死于臺灣。從他給黃旭初的信推斷,他晚年并沒有李宗仁那樣的罪孽感,也不會認同李宗仁反省歷史后所說“劃江而治”會成為民族罪人的感覺。僅就這一點而言,李宗仁勝白崇禧。當然,這是我這個普通老百姓的一己之見:李宗仁最終對“萬骨”有愧疚之感,顯示他尚有以天下蒼生為念的政治領袖的悲憫情懷,而白崇禧則不過是一有鋼鐵意志和鐵石心腸的職業軍人。白氏給黃旭初的長信,殺氣太重,我今生不會再讀。《李宗仁回憶錄》則可無事時再翻翻。
二、英雄的尊嚴和忠臣的委屈
比較白崇禧和李宗仁的晚年,令人不禁覺得李宗仁到底是個英雄,而白崇禧不過是個委委屈屈的忠臣而已。
我們普通老百姓在街談巷議中評論歷史人物,總要看他是否做過些可圈可點的事情,令人敬佩或是使人不勝惋惜。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民國時期的大人物,我們老百姓評他們,就要看他們對民國做了些什么事,是不是可圈可點。
民國民國,顧名思義,是人民的國家。我們評價民國人物,只能照民國的標準—他們對建設、保衛人民的國家是有貢獻還是有破壞。我們老百姓佩服孫中山,因為他創建民國,一輩子不屈不撓,為民族獨立奮斗,又提出三民主義,為建設人民的國家作出理論的指導。孫先生的憲政理論,最為重要,是中國從傳統帝制過渡到現代民主國家的指南。
照我們普通百姓的理解,孫中山憲政理論中,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人都不能違反破壞。憲法是民主的制度的保證,破壞、違反憲法則強人政治又會還魂復辟。沒有制度的保證,便沒有人民的國家—人民只會遭殃。我們看一部民國史,這方面的教訓是太多、太深刻了。
李宗仁、白崇禧都自命為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他們倆在一九四九年與蔣介石的一番爭斗,顯示一開始仍是“李、白一人”,后來終于分裂,分道揚鑣,成為完全不一樣的歷史人物。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通電下野,李宗仁依民國憲法由副總統而任代總統,白崇禧則不再擔任國防部長,被任命為“華中剿匪總司令”。李、白收拾殘局,很快發現,大權仍在蔣介石手中,他們根本無能為力。李宗仁從憲法的角度出發,指責蔣介石的行為是“幕后違法控制”—蔣介石本已下野,是一介平民了,仍在幕后控制,自是“違法”—違反憲法。
白崇禧也認為,“蔣先生既已引退下野,應將人事權、指揮權和財政權全部交出”(《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這是他于四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和李宗仁所說的話。蔣介石自然沒有交出任何權力。
到了五月初,李宗仁已由南京飛返桂林,白崇禧來看他,兩人密談中,白崇禧對李宗仁說,“蔣先生既然不肯放手,處處掣肘,倒不如由我(李宗仁)敦請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是這樣回答白崇禧的:
此事萬不可行。現在已是憲政時期,吾人必須維護憲法的尊嚴。今蔣介石已引退下野,即為一介平民,若不經國民大會的合法選舉而私相授受,由我勸他復任總統,則我將為千古的罪人。白氏見我態度異常堅定,遂不再言。(《李宗仁回憶錄》下冊)
真是擲地有聲!在那無可奈何的局面中,李宗仁仍要維護憲法的尊嚴,我讀史至此,亦覺得他有一份民國英雄的尊嚴。
《李宗仁回憶錄》中,有一段李宗仁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教訓蔣介石的記載,讀來令人神往。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民黨政權已土崩瓦解、毛澤東十月一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兩星期,李宗仁與蔣介石在廣州梅花村見面,據李宗仁回憶:
我二人坐定后,我對蔣先生說的第一句話便是:“今天我是以國家元首的地位來對你談話。”我所以要鄭重提出這一句,是因為蔣介石獨裁專政數十年,平日所見所聞都是一片奉承之態,阿諛之言,只有他教訓別人,斷無人敢對他作任何箴規,更談不到疾言厲色地教訓他了。這次我自思或是與蔣最后一面,然當今之世,論公論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訓語氣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搬出國家的最高名器來壓抑他“舍我其誰”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靜聽我對他的指斥。
在蔣先生默坐靜聽之下,我便把他過去的過失和罪惡一件件地數給他聽。
……
蔣先生專橫一生,目無法紀,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國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李宗仁回憶錄》下冊)
這真是一個可圈可點的故事。平心而論,李宗仁教訓蔣介石,不能說沒有發泄私憤的成份。他在回憶錄中,就一再說到蔣介石“欺人太甚”。然而,李宗仁對蔣介石的批評指責,最終是在制度上、在國家名器方面著眼,顯示他超出其他民國人物的眼光與襟懷。在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憲政民主的艱難跋涉中,種種制度性建設的努力和種種對制度被破壞的痛心疾首,都是值得回顧回味的。李宗仁在全盤不可收拾的局面中,仍念及維護憲法的尊嚴,有一種現代英雄的悲壯和尊嚴。
與李宗仁教訓蔣介石形成強烈對照的,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白崇禧致蔣中正密函。
白崇禧在這封親筆密函中,先是一再強調、重申他對蔣介石的忠心,最后提到,他發現自己被監視,有“便衣者積年累月跟蹤不舍”,他的住宅附近,“日夜均有便衣人員監視職之行動,并備有房屋汽車”。他請蔣介石“詳察”,謙卑地說:“如蒙鈞座不棄而召見之,職愿當面詳為報告。”
按白先勇先生所述,蔣介石并沒有在接到這封密函后召見白崇禧,而是讓副總統陳誠出面,對白崇禧說:“便衣人員是保護你的,我也有人跟隨。”白崇禧回答道:“你現在是副總統,當然有此需要。我并無此必要。”
白先勇先生寫道:
可是那輛吉普車卻仍舊一直緊緊跟隨父親,到他逝世。(《父親與民國》下冊)
蔣介石這樣把一代抗日名將玩于股掌之間,這樣長期地羞辱他、折磨他,實如李宗仁所說,真是欺人太甚!
白崇禧晚年在屈辱中生活,他會不會有時心中突發一念,也像李宗仁那樣,老實不客氣地教訓那欺人太甚的蔣介石一頓?以他的剛烈性格,相信他會有這樣的想法。只是沒有憲政保護的條件,他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都成問題,他只能隱忍偷生,絕無向蔣介石正面挑戰、教訓他一頓的機會。他只能做一個委委屈屈的忠臣。
從中國傳統眼光看,對蔣介石來說,白崇禧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忠臣。然而,這樣的忠臣,竟在屈辱中度過殘生,他那極不平凡的超強的心理素質和鋼鐵意志(他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本事),竟只能用于對付一個忠臣的無限委屈。這個故事,太過悲慘辛酸,令人不忍卒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