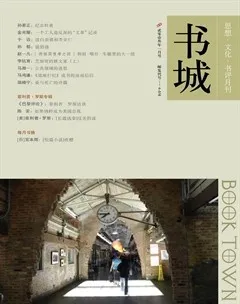成長與記憶
《歷史盲腸》由六篇回憶組成。二○一二年應邀給《收獲》寫一年的專欄,《收獲》系雙月刊,每年六期,這即是“六篇”的來歷,不是有意模仿著名的《浮生六記》或者《干校六記》。六篇回憶圍繞我的知青生活,收羅到一些近四十年前的舊事。這些片斷曾經東一截西一段地漂浮在雜亂的意識之中,現在慢慢地聚合起來了。我的知青生活十分短暫,六篇已經差不多了。此外還有一篇前言,一篇尾聲,補充交代一些來龍去脈。戴帽穿靴地打扮起來,真的有些像一本書了。
這些回憶的不少枝蔓超出了知青生活的范圍。我寧可認為,這些回憶涉及個人成長史的若干節點。下鄉插隊肯定是我年輕時遇到的一件大事,種種個人成長的零星經驗無不陸續匯入這件大事,繼而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自我認識,饑餓經驗,性,暴力氣氛之中的生存,孤獨與寂寞,神秘引起的精神顫栗,如此等等。當年,沒有多少現成的知識或者長輩的教誨護佑這一代人成長,電線桿上端的大喇叭里反復播放的高亢口號僅僅是一些隔膜的大詞。我們只能在蒙昧之中惶惑地摸索,嘗試和積累各種經驗,慢慢地、曲折地浮出成人的水面。顯然,時至如今,我的回憶已經消除了當時的惶惑而兌入了許多置身事外的感想。
延續了十幾年的下鄉插隊運動如同中國當代歷史的一段奇異插曲,每一個年度的夏季都有無數的城市家庭卷入這一場運動。下鄉插隊的覆蓋范圍天南海北。從大雪紛飛的北大荒到郁郁蔥蔥的海南島,從開闊的華北平原到南方的崇山峻嶺,不同地域的知青擁有迥然相異的生活。知青是一個人數眾多的龐大群體,每一個年齡段落的知青抱有不同的生活信念。光榮的夢想曾經激勵過相當數量的早期知青,后期的知青之間時常隱伏著特殊的頹廢氣息。從英雄主義情懷、底層意識到幻滅感或者厚顏地投機,這一切都可能成為知青的精神詞匯。我曾經對一個年輕的白領說,不該把當年的下鄉插隊想象為一次浪漫的郊游;然而,他的眼神似乎是一個詢問—那么,還能有什么?我一時難言。或許,這即是寫作這幾篇回憶的最初觸動。
回憶肯定包含了選擇。眾多昔日的碎片穿過三十多年的浮塵再度顯現,這是歷史與現在的對話。我們常常不由自主地對于歷史進行戲劇性處理,并且安排自己擔任戲劇的主人公。許多電視肥皂劇和勵志故事之中,“知青”仿佛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傳奇意味。天降大任的考驗與患難之中的愛情構成了情節的助推器。可是,我的回憶搜索不到多少傳奇,我的同伴之中沒有多少顯赫的企業家或者當權人物。多數人的經歷平庸乏味,如今各安天命地生活在不同的角落。我的記憶收藏了他們的瑣碎悲歡,這是我更為熟悉也更為相信的歷史。
編輯這本書的時候,很希望找到一些當年的照片作為插圖佐證。當然,一無所有。近三年的知青生活沒有拍過一張照片。對于現今這個數碼技術四處泛濫的時代,這幾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當年沒有照相器材,也沒有沖洗相片的費用。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心情。這種日子又有什么可拍照的?我記得有一天雨后,一個知青對我說,我們倆一起穿著蓑衣拍一張相片,最好旁邊還有一頭水牛。日后我曾在他的房間里見到了一件蓑衣掛在墻上,但是,照片始終沒有拍成。
我曾經出版過一本以回憶為主要內容的隨筆《關于我父母的一切》,談論的是上一代人。這本書以自己為主人公,行文或許更自由一些。不過,在我的心目中,這兩本書不啻于姐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