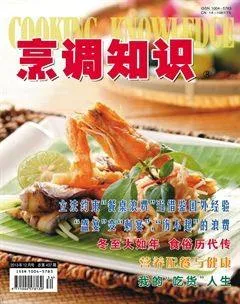我的“吃貨”人生
河 南 宋殿儒/文
很小的時候,我就是全家成員中最能吃的“吃貨”,不過,父母那時候給我封的一個名號不叫“吃貨”,而是“吃才”。意思就是,我粗茶淡飯,山珍海味、樹上結的、天上飛的,地上跑的,以及商店里人造的,食堂里東南西北風味的飯菜都能吃得滿頭大汗,席卷殘余,是個祖上八輩子都難遇到的一個“吃喝才子”。
我五歲那陣兒,大集體各家各戶都缺糧,那年剛過完年家里就揭不開鍋了,父母害怕把我這一根獨苗餓死了,就自己吃榆樹皮和野菜,把到舅舅家求來的二升玉米面讓我吃。可是就那一天,我不知怎么地就不當父母口中謾罵的“吃才”了,而是,趁父母不注意的當兒,將一個很小的玉米面饃饃掰成兩半,塞到了父母的野菜湯碗里,而自己則大搖大擺地到地里去捉一種叫“游子”的昆蟲和挖一種叫做“雞大腿”的草根吃。沒料想的是,在挖“雞大腿”的時候,挖出了一種像生姜似的塊根植物,因而,我就以為好吃,把它吃下肚子。結果,還沒吃下三口,我的嘴唇就火燒一樣的開始疼了。最后導致我昏睡過去,等從醫(yī)院醒來的時候,醫(yī)生才驚訝的說“這孩子真的命大啊!他吃的可是‘天南星’啊!這是一種毒性很大的藥材,有些人一沾上它就能沒命……哎呀……這孩子真是個好吃才啊!”
就連醫(yī)生都說我是“好吃才”,那后來人們把我叫成“吃才”,那就是一定的了。
上高中時,我家里沒錢也沒有那么多的細糧,因而,我就吃學校最差的飯菜。有些家庭好的學生不想吃粗糧,都把粗糧票換來的食物到處亂扔,而我則會把它們撿回來吃,吃不完就設法掰成小塊曬干,留作晚上上晚自習作夜宵。學校體育項目比賽,我總是能得獎,因為我好賴都能吃,吃得身強力壯,牛犢子似的有力氣。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家里就不愁沒啥吃了。每月,父母勒勒褲腰帶兒還能給我省出200元生活費。可是人家每月得吃七八百,我這200元怎么行呢!我有辦法,因為我是大名鼎鼎的“吃才”。我首先能多吃學校的“濟困飯”(那是國家給學校貧困生做的免費飯)。這“濟困飯”一般都是農村人吃慣了的那種糊糊面。現在的大學生,多數人不愛吃,另外他們都認為那種飯是一種人格等級飯,既是想吃,在師生面前也不想落得一個“窮字”。而我則不然,只要能填飽肚皮,能給父母省下一分錢,我就會去吃。再者,我在學校如果買書本把生活費花了時,我會從另一方面“吃出來”。那就是,我會每頓飯只吃白面饅頭,不吃菜,只喝開水不喝湯。富裕學生們丟到桌子上沒動的菜,有時候也會跑到我的肚里去。我一致認為,吃才,有時候能理解成一種愛,一種對生活的態(tài)度,一種對物質的敬畏,一種對父母的孝敬。任何一種吃材,都是大自然恩惠給我們的,我們無權去浪費。我作為一名貧困學子,總想著父母的不易,能為他們省出一分錢也是一份孝心。
因為我在大學里有這樣的生活,這樣個“吃相”,慢慢地我就被人叫做“吃貨”。吃貨在大學是一種諷刺語,只不過比“吃才”多了一點現代溫柔感。
由于家庭的貧困和童年艱苦生活的熏陶,使我的口味兒日臻完美,幾乎是東南西北的風味,酸的,辣的,苦的……什么都能吃。
現在工作了,我這個吃貨大號仍然戴在頭頂上。因為,作為秘書,我首先得會幫助領導完成“吃”的任務,東南西北的吃客,我都能應付。不過,我這個吃貨,有三禁:一是禁止吃貨被浪費,點了的菜,幾乎不能在我面前變垃圾;二是禁止吃變質食品,因為我這個吃貨現在更注重身體健康;三是禁止在客人和孩子面前暴露不雅吃相,因為現在的我要做的是文明吃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