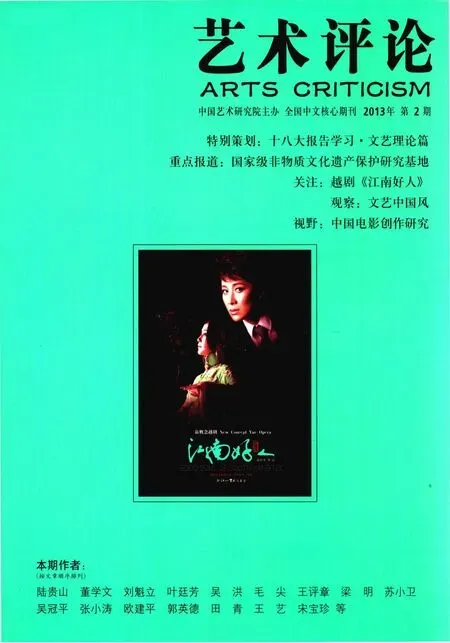“士”的傳統(tǒng)與“新文人畫”
——讀劉明康美術(shù)作品集《舊憶》
田 青

讀劉明康的畫作,不由想到“新文人畫”的概念,進(jìn)而聯(lián)想到“士”的傳統(tǒng)。在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這個(gè)詞是近代才經(jīng)日本從西方“轉(zhuǎn)口”而來的,與中國(guó)古代的“士”有同有異。相同之處很多,不但同指受過教育的“讀書人”,而且,無論中西,這個(gè)群體所強(qiáng)調(diào)、所擔(dān)負(fù)、所引以為傲的,還應(yīng)該是對(duì)“道”的擔(dān)當(dāng)及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追求。西方重視“知識(shí)分子”對(duì)社會(huì)的批判態(tài)度和對(duì)公眾利益的關(guān)注;古代中國(guó)的“士”,更是把舍生取義作為最高追求。從“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訓(xùn)到“文士”、“雅士”、“勇士”、“壯士”等大量與“士”有關(guān)的稱謂中,就可以了解到“士”這個(gè)階層在中國(guó)人心目中的地位了。
不同也有很多。當(dāng)代的所謂“知識(shí)分子”,越來越多地成了一群受過主流“高等教育”、掌握了某種專業(yè)知識(shí)的“腦力勞動(dòng)者”或“白領(lǐng)”的同義詞,在精神上越來越貧瘠、單薄、蒼白,失去了“士”的精神意義與文化意義。在中國(guó)歷史上,“士”從來不僅僅是“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在所有“有用”的知識(shí)之外,“士”還要“左琴右書”,懂得琴棋書畫“四藝”,甚至“士無故不徹琴瑟”,將藝術(shù)實(shí)踐作為最重要的生活內(nèi)容和終其一生的生活方式。“琴”與“書”,“情”與“趣”,不但完善了中國(guó)古代文人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他們“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在劉明康的畫作中,我似乎看到了“士”的影子,也看到了“新文人畫”的影子。
劉明康的畫作,是他個(gè)人生活的回憶,也是一代“知識(shí)分子”共同的記憶,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設(shè)法把走過的路,看到的事,用畫筆寫成小故事,向大家一一道來。”在他的這些“小故事”里,我們看到了異域風(fēng)情、看到了童年時(shí)光、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更看到了一些已被“現(xiàn)代化”的巨大橡皮涂擦掉的物質(zhì)或非物質(zhì)的文化遺產(chǎn)。而無論是歐洲月下的古堡、倫敦宏偉的大劇院,還是浦東的鴨場(chǎng)、吳淞的小火車站、生產(chǎn)隊(duì)的老倉(cāng)庫(kù),無不在觀畫者的心中勾連起某種情感、思緒,或清晰、或朦朧,或甜蜜、或傷感,甚或有一種淡淡的鄉(xiāng)愁與難言的惆悵。“舊憶”與“憶舊”也有不同,“憶舊”是動(dòng)詞,是一個(gè)情感的過程,以“憶”為手段,以“舊”為皈依;“舊憶”卻是名詞,是動(dòng)態(tài)時(shí)光的固化,像一本珍藏在祖母箱底的老相冊(cè),是由已逝的吉光片羽串起的珠串,應(yīng)該供在家堂正中的香爐前,可與同代人共享,也可供后人尋根覓祖。
我不是畫家,我也缺乏從技術(shù)上評(píng)判畫作的習(xí)慣與能力。但是我知道,中國(guó)古代最偉大的藝術(shù)鑒賞家們?cè)?jīng)為我們品評(píng)畫作奠定了一些原則。南北朝時(shí)代鐘嶸在《詩(shī)品》中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味”字,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將藝術(shù)給人的感覺用人們?cè)谙硎苊朗硶r(shí)的生理快感來形容。在談到五言詩(shī)時(shí),他強(qiáng)調(diào)五言詩(shī)“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反對(duì)“淡乎寡味”的東西,指出“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dòng)心”的作品,才是藝術(shù)的至境。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國(guó)人的語(yǔ)言習(xí)慣中,還常常在“味”字后面加上一個(gè)“道”字,“道可道,非常道”,“味道”二字,近乎體驗(yàn)藝術(shù)品的至境。在《舊憶》的一些貌似平淡的畫作里,我的確體會(huì)出一點(diǎn)“味道”。
也是南北朝,那個(gè)中國(guó)歷史上最富藝術(shù)氣質(zhì)的時(shí)代里,一個(gè)叫姚最的美術(shù)評(píng)論家在其評(píng)價(jià)體系里提出“畫有六法,真仙為難”的觀點(diǎn)。他特別推崇蕭繹的畫作“特盡神妙”,是因?yàn)檫@位畫家并非“職業(yè)”畫家,而是在其皇帝工作的“業(yè)余時(shí)間”里,“斯乃聽訟部領(lǐng)之隙,文談眾藝之馀,時(shí)復(fù)遇物援毫”,是我們所謂“畫著玩兒”的。也正因?yàn)樗诶L畫時(shí)“不加點(diǎn)治”,沒有把技術(shù)當(dāng)成繪畫唯一的追求,所以才能“造次驚絕”,成為“心師造化”的藝術(shù)典型。文人畫的高妙之處,在于重神似、重意境、重性情、以書入畫。早在西洋“抽象派”畫風(fēng)出現(xiàn)之前八百多年,蘇東坡就已吟出了“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的名句了。董其昌所謂“畫山水唯寫意水墨最妙。何也?形質(zhì)畢肖,則無氣韻;彩色異具,則無筆法”的話,雖失之為極端之語(yǔ),然亦被廣大“知識(shí)分子”視為圭臬。
當(dāng)然,劉明康不是蕭繹,蕭繹只顧畫畫而丟了正業(yè),成為歷史上最好的畫家之一,但同時(shí)又是歷史上最失敗的皇帝之一。劉明康在任中國(guó)銀監(jiān)會(huì)主席期間,中國(guó)的金融業(yè)頂住了“金融風(fēng)暴”,是歷史上中國(guó)銀行業(yè)發(fā)展最快的階段。劉明康將成功歸于“黨的領(lǐng)導(dǎo)和同志們的努力”,我還想再加上一條:他在工作之余還畫畫兒。可不要小看這一點(diǎn),這,就是“士”的傳統(tǒng),而他的畫,就是我所謂的“新文人畫”。

《放排》(一)

《放排》(三)

《夜》

《尋億——小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