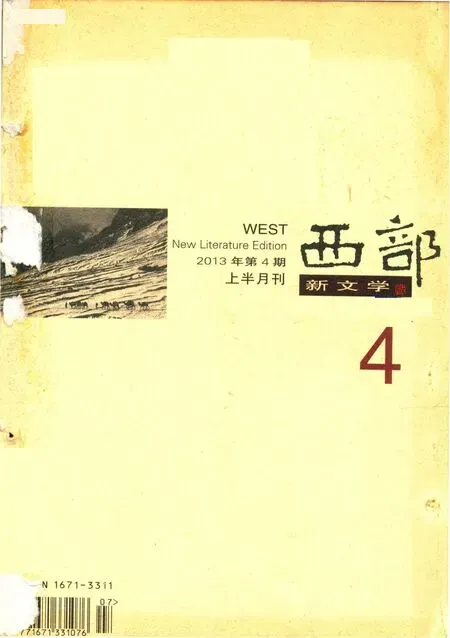明天以后
2013-11-15 22:58:29西洲
西部
2013年7期
關鍵詞:愛情
西洲
李一平那次發作之后,她算是徹底明白了他的感情。他對她終究是厭倦了。她只是覺得他過于可笑,明明是自己理虧,卻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有什么意思呢?
努力想一想,她已經記不起來他掌心的那顆痣究竟是在哪一只手掌,左手還是右手?大約是左手吧,從前他牽著她走在路上的時候,就用左手拉著她,他說你要永遠走在我的左邊,我的心永遠屬于你。她可以感受到那顆暗紅色的痣在她的手心摩挲,溫柔熱情又蠢蠢欲動。那顆痣和手心的皮膚是一體的,哪里能摸得到?這樣一想,她又實在不能確定,那顆痣到底在哪里。是啊,從前她以為,他們必定會相愛到老的,他掌心的痣,就像歌里唱的那樣,她“永遠記得在哪里”,但那時的她實在不懂,那歌詞為什么如此矯情:“恨不得一夜之間白頭。”如今,她已經完全了解。一夜白頭,這一夜就是地老天荒,就是海枯石爛,中間再也沒有變故,沒有分離背叛,沒有仇恨痛苦,沒有相逢陌路……可是已經太遲了。
女人的敏感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有些人,會漸漸地在平淡或者熱情中,悄悄地、一點一點地收斂起自己的敏感,不再輕易地把自己放在敏感的位置,這是無數次受到傷害之后總結出來的經驗,叫自己的心稍稍麻木一些,再麻木一些,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傷害。她其實早就知道他有了別人,她只是不想說出來,她不想像個審判者,看著他被拆穿后狼狽的樣子,她只是等他告訴自己,等他有勇氣說:“碧珠,我們分手吧;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散文詩(青年版)(2022年4期)2022-04-25 23:52:34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戀愛婚姻家庭(2021年17期)2021-07-16 07:19:34
海峽姐妹(2019年9期)2019-10-08 07:49:14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 02:12: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46
文苑(2018年23期)2018-12-14 01:06:28
金橋(2018年9期)2018-09-25 02:53:32
小說月刊(2014年1期)2014-04-23 09:00:03
延河(下半月)(2014年3期)2014-02-28 21: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