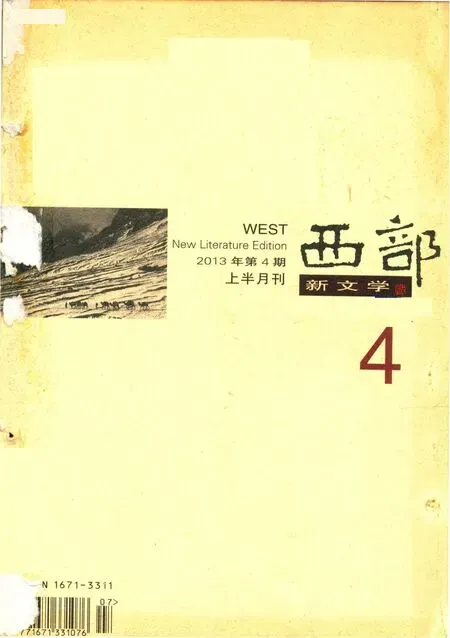最溫柔的摯友
董夏青青
阿山在世的時(shí)候,我當(dāng)他是家門口的一棵老樹(shù),哪會(huì)有出了門再見(jiàn)不到的一天?還曾想,我要是死了,阿山一定是幫著抬棺材的一個(gè)。沒(méi)想到他走在我前頭,由我來(lái)寫下這篇悼文。
他是我一生中可能遇見(jiàn)的,最溫柔的摯友。
第一次見(jiàn)他,聽(tīng)他說(shuō)自己叫“阿三”,于是我“阿三、阿三”地叫了很久,每回他都笑呵呵地答應(yīng),直到有一天在他工作的地方玩,聽(tīng)見(jiàn)他朋友叫他“阿山”,這才知道一直喊錯(cuò)了他的名字。我問(wèn)他,為什么不提醒我改過(guò)來(lái),他很不好意思,笑瞇瞇地說(shuō),名字就是個(gè)代號(hào),何況自己也不重要,叫錯(cuò)了有什么要緊。
聊天時(shí),他很少大聲發(fā)表見(jiàn)解,或者用侃侃而談的語(yǔ)氣給人提意見(jiàn)。多數(shù)時(shí)候,他總是微笑,有禮貌地注視著說(shuō)話的人。在他這笑容里,能看到與年齡不符的羞怯和單純,一種生來(lái)便與人交好的善意。而同時(shí),這笑容里還有某種不可名狀的警惕與憂慮,使他的臉無(wú)論何時(shí)看來(lái),既親近又疏遠(yuǎn)。
三年時(shí)間里,我和阿山每回見(jiàn)面、寫信,聊的都是有關(guān)寫作和信仰的事。聽(tīng)上去矯情,然而事實(shí)如此。我不知道他具體的家庭情況,不了解他某時(shí)是否有喜歡的女孩,也不清楚他喜歡吃什么。我們自從認(rèn)識(shí),就像是親人,跨過(guò)了相互交換個(gè)人基本信息的階段,直接進(jìn)入了彼此最迫切渴望有人作伴的小世界——言說(shuō)的世界。
我們每隔一段日子,便長(zhǎng)聊一番,先說(shuō)說(shuō)各自最近練筆的大致內(nèi)容,之后聊自己想寫的人、想講的好故事。他曾和我說(shuō),他想寫他在酒店工作時(shí)的一位師傅,這位師傅的老婆幾年前離家打工,至今音訊全無(w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