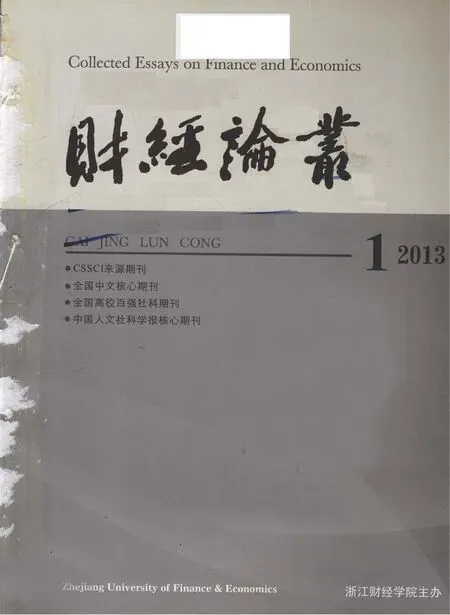價值鏈差距與中間品產品內分工的溢出效應
魏 瑋,姚 博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伴隨著產品內分工的快速發展,關于中間品產品內分工對價值鏈水平的影響效應也是一個前沿的研究素材,針對不同差距層次的價值鏈位置,研究中間品產品內分工的溢出效果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視角。目前,明確涉及這方面的國內研究并不多,國外有一些文獻(如Girma and Gorg(2007)、Griffith等(2004)、Castellani and Zanfei(2003))從行業或企業的角度說明在不同技術差距水平下外資參與分工對技術產生的溢出效應。本文則嘗試從國家截面的角度,研究中間品產品內分工產生的溢出效應對提升價值鏈位置的作用。
一、理論機制與模型設定
參照Hausmann等(2007)的成本發現模型[1],從出口部門的生產率角度來說明價值鏈位置的影響因素。這里假定一國出口部門的生產率函數為:

式中,K、L、N分別為資本、勞動力、資源,并規定規模報酬不變,即a+b+c=1;H為出口部門的技術參數,服從 [0,δ]上的一致均勻分布;δ為該國的技術稟賦,該值越大,表明該國的出口企業越有可能制造出口復雜度高的產品,從而使其在全球價值鏈中位置越高。假設一國技術稟賦是內部知識P、外部知識Q以及其他綜合因素T的函數,即δ=Θ(P,Q,T)。
根據成本發現原理,一國企業可以選擇生產自己開發出來的產品,也可以選擇模仿具有最高生產率水平(Hmax)的產品。假設企業的模仿效率為λ,且0<λ<1。假定共有n個企業,且E(Hmax)類似于Hausmann推導,出口部門的技術參數H的期望值為:

從而我們得到一國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價值鏈位置決定因素的函數為:

由上式可知,出口部門的價值鏈位置取決于人力資本、資源要素、內部知識、外部知識以及促進內部知識和外部知識的積累等。因此,假定一國參與中間品產品內分工若能對這些因素起到促進作用,那便會提高該國的價值鏈位置。結合理論分析,本文在實證方程中吸納了一系列解釋變量,得到的基準方程如下:

這里,divi,t*gapi,t是產品內分工與價值鏈差距交互變量,cap為固定資本投資,rd是研發支出比重,fdi為外商直接投資,hum是每百萬人中擁有的技術人員比重,eff是服務效率,gap為價值鏈差距。參考劉軍和邵軍(2011)的做法[2],我們對gap的定義如下:

通過將價值鏈水平與樣本中價值鏈位置最高值相除,可以得到i國的價值鏈差距值,該值越大,說明該國的價值鏈位置與最高水平相距越小。引入交叉項divi,t*gapi,t,目的是為了反映隨著價值鏈差距的變化,產品內分工對價值鏈位置影響的溢出效果。在后續的分位數回歸估計里,交叉項中div包括中間品、半成品與零部件三類樣本產品內分工程度。
二、變量測度與數據選取
產品內分工程度的衡量辦法較多。Amiti and Wei(2004)運用進口中間品占投入品總量的比率,陳健(2012)采用區位商指數LQ反映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區域專業化[3]。本文借鑒了唐海燕和張會清(2009)的算法[4],但考慮到比值太小會削弱產品內分工的影響權重,具體計算時采用中間品的進出口貿易額與一國貿易出口總額之間比重的辦法。對于中間品的進出口貿易額數據的選取,本文按國際貿易商品分類體系中的BEC標準,中間品包括的BEC代碼有121、22、322、42、53。基于法國CEPII機構對中間品的劃分,半成品代碼有121、22、322,零部件代碼有42、53。數據來自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庫集結計算得到。
關于價值鏈水平的測算,本文采用Rodrik(2006)的做法[5],依據以下公式進行計算:

這里,prodyj和EXPYc分別是某一產品以及某一國的出口技術復雜度,j代表產品,c表示國家或地區,xcj是c國j產品的出口額,Xc是c國總出口額,是c國j產品的出口額所占比重,GDPc是c國的人均GDP。本文采用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庫中SITC(Rev3.0)的三位碼標準,計算在1998-2010年間261種產品和181個國家的價值鏈水平。其他變量的數據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情況說明
三、實證分析
(一)對不同分組國家的回歸估計
從表2的分組國家回歸來看,中間品產品內分工與價值鏈差距的交互變量溢出效應存在國家層面的異質性。發達國家的該系數最為明顯(達到2.0659),隨著gap的增大,即價值鏈位置差距的增加,產品內分工的溢出效應也會提高,產品內分工引起了價值鏈位置更加接近于最高水平。固定資本投資系數雖然都為正,但值較小,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采用增加固定資本投資的辦法會更有利于提升價值鏈水平,但本文結合李小平和朱鐘隸(2006)對固定資本投資結構發揮效用、陸立軍和鄭小碧(2010)關于價值鏈下產業升級的觀點[6][7],認為固定資本投資結構會影響產品內分工的效率和價值鏈的水平,固定資本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導致估計系數降低,對價值鏈的提升作用不顯著。研發支出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研發實力以及研發支出比重都很薄弱,對價值鏈位置的影響不明顯,而發達國家的研發支出對提升價值鏈水平有顯著的正向效果。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估計系數為正,反映其人力資本的數量和結構都是合理有效的,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由于其人口基數大,可能擁有一定數量的高水平專業技術人員,但該供需結構和流動性存在不合理之處,導致對價值鏈的影響沒有預期的好。
外商投資和公共服務效率對價值鏈的作用效果在四組樣本估計中影響不一,但都很微弱,有的甚至不顯著。發達國家的外商投資效果不顯著,由于發達國家的本國資本或技術密集度已經很高,外國的投資對本國不一定具有競爭性。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來說,外商在較低價值鏈環節的投資可能會使生產與貿易結構處于低端層次,對價值鏈位置提升的實質作用不明顯。公共服務效率對價值鏈的影響只有在發達國家與最不發達國家兩組估計中顯著。

表2 不同分組國家的估計結果
(二)價值鏈差距與中間品(所有樣本)產品內分工溢出效應的分位數估計
按照通常的做法,取五個最為重要的分位數值,即10%、25%、50%、75%、90%。從表3的結果來看,在0.75分位點之前,當價值鏈水平較低且差距值較小時,隨著gap值的增大,中間品產品內分工的溢出傳遞效應就越好,對價值鏈位置的提升效果非常明顯。但到了0.9分位點處,該值大幅減小到1.2776,其原因可能是在高分位點上價值鏈水平較高時,隨著gap值的繼續加大,中間品產品內分工層次差異明顯,導致大量處于低層次環節的產品內分工溢出效應減弱,從而對價值鏈的提升作用不夠明顯,整體上系數變化呈向右傾斜的倒U型。固定資本投資結構的估計系數基本上呈增大趨勢,在低分位數水平上,區間樣本的價值鏈水平較低,低加工環節投資的固定資本結構不合理,使得提升價值鏈的作用微弱;在0.5分位點以后,這時區間樣本的價值鏈水平較高,促使投資在高附加值環節的固定資本結構逐漸合理,對價值鏈的影響也相應提高,具體表現為不斷增大的正效應。研發支出的估計系數在分位數0.5之前逐漸增加,之后不斷減少,可以解釋為當價值鏈處于低端水平時,研發對價值鏈的提升作用非常明顯;當價值鏈處于中高端位置時,研發支出已具備較高的含量,再增加研發支出對價值鏈提升的邊際效應就不再明顯了。
外商投資的系數值在各個分位點上基本都很小且顯著性不強,當價值鏈在低分位數水平時,外商在低端加工領域的投資對價值鏈整體水平的提升效果不夠顯著;處于高分位點時,國內的高端制造環節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外商的投資只能引起競爭效應,對價值鏈的進一步提升并沒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在價值鏈處于低端水平時,由于低層次加工領域需要的人力資本更多的是勞動密集型,對高技術專業人才需求不大,使得人力資本的系數估計值較小,從0.5分位點之后,該系數增大,說明在高分位點價值鏈水平上對人力資本的要求較高,高技術專業人才對價值鏈提升的帶動效應就愈發明顯。服務效率在各個分位點上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較大,在0.5分位點上系數值最低,然后往兩端的分位點水平延伸,系數值逐漸增大。一般來說,隨著價值鏈位置沿著分位數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配套的公共服務效率要求也越來越高,進而公共服務效率的增加都會使價值鏈水平明顯提升。而從該分位數回歸結果來看,在0.5分位數之前產生了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可能是當價值鏈水平在非常低的區間時,相應的社會發展和服務層次很低,各種公共服務變數和不確定性很大,導致公共服務對價值鏈的影響系數產生減弱的趨勢。

表3 所有樣本國家的分位數估計結果
(三)對中間品分類估計的進一步討論
根據中間品的分類,我們接著探討半成品、零部件各自產品內分工對價值鏈差距的溢出效應。表4中上半部分回歸結果顯示,價值鏈處于不同分位點水平時,價值鏈差距與半成品、零部件分工的溢出效應變動趨勢呈倒U型,零部件產品內分工的溢出效應在各個分位點上的系數要大于半成品,在價值鏈處于0.9高分位點處,零部件、半成品各自的產品內分工溢出效應系數都在急劇減小。由于本文著重考察價值鏈差距與半成品、零部件各自產品內分工的溢出效應,因此我們整理出固定資本投資、研發、外商投資、人力資本、服務效率等變量在半成品、零部件兩類估計結果中的平均值(見表4中下半部分)。從這些變量的估計平均值可以看出:研發與人力資本估計系數的變化趨勢剛好相反,研發的估計系數變動情況呈向左傾斜的倒U型;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變化趨勢呈U型;固定資本投資、外商投資、服務效率的估計系數均值與中間品所有樣本的回歸情況類同,原因前文已述及。

表4 半成品與零部件的分位數估計結果
四、結 語
在不同的價值鏈分位點水平上,隨著價值鏈差距的變化,中間品(包括半成品和零部件)產品內分工對提升價值鏈位置發揮了積極的溢出效果,但這種作用有大有小,變化趨勢基本呈倒U型。隨著價值鏈水平的提升,這種溢出效應不斷增強,但當價值鏈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這種效應就會減弱。零部件產品內分工對價值鏈的溢出效應要優于半成品,這種效應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分組國家具有異質性。長遠來看,其他因素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相應的政策含義有:首先,注重高層次加工領域的產品內分工溢出效應和帶動作用,多向零部件產品內分工環節與技術傾斜;其次,完善和優化低加工領域以及低端價值鏈環節的固定資本投資結構,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再次,關注價值鏈高端水平下研發作用的發揮及其背后的影響因素,重視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流動性;最后,創造外商在價值鏈高端環節投資的條件,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提升中高端價值鏈領域的社會服務效率。
[1] Hausmann R.,Hwang J.and 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pp.1 -25.
[2] 劉軍,邵軍.技術差距與外資的溢出效應:基于分位數回歸的分析[J].國際商務,2011,(3).
[3] 陳健.產品內國際分工、地區專業化與區域經濟增長[J].財經論叢,2012,(4).
[4] 唐海燕,張會清.產品內分工與發展中國家價值鏈提升[J].經濟研究,2009,(9).
[5] Rodrik D.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6,(14).
[6] 李小平,朱鐘棣.國際貿易,R&D溢出和生產率增長[J].經濟研究,2006,(2).
[7] 陸立軍,鄭小碧.全球價值鏈下地方化產業升級路徑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