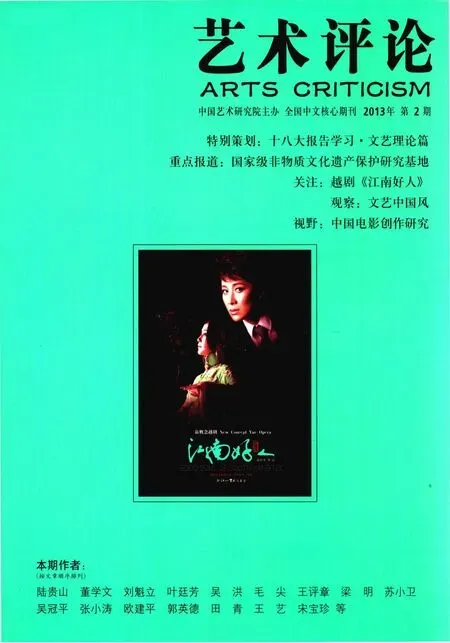戲曲音樂的集體情感表達特質及可表演性
王評章
王評章:福建省藝術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前段時間參加了中國京劇節和昆劇節,對京劇、昆劇音樂方面的成就尤為感嘆,也因此常常念及福建戲曲音樂。對于音樂我確是外行,只是憂心所至,說一些皮相感受。
京劇節的特點是流派紛呈,老生、旦的各個流派尤其齊全,都有新劇目新傳人,實在賞心悅目,看得人心花怒放。雖然現在也有理論家對戲曲流派極有微詞,但從地方戲視角看,我對戲曲流派卻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極度景仰和崇拜。因為只有形成流派,才能把戲曲音樂的好處發揮到極致,而且不應該僅把流派看成只是一種固定、僵化的唱法、技巧,它們確確實實是把不同類型的人內心的集體情感通過特定也是最好的歌唱方式表達得淋漓盡致。流派的創始人天才、深刻地洞察、尋找到這些共同的特定的集體情感及其表現的特定方法,他們唱出這樣一些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生命深處的聲音。或許是上帝假他們之聲,來度這些人們,來舒緩他們的內心,來引領他們歌唱。而唱流派的人又借由流派的引導,進入自己和同類人情感和人性深處,進入一種他們熟悉的有鮮活體會的集體情感,獲得這種情感回腸蕩氣完美的表達方式,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類的、情感的認同和皈依的快樂和幸福,于是一代代常唱常新,反復咀嚼、回味,樂而不疲。反對流派,力倡個性、創新的說法,反而讓人覺得與戲曲傳統的民族集體性、類型性的本質特性不搭調。也有人拿“文學藝術的本質、規律永遠是個性的、創新的”理論來反對,這當然是“理論正確”的,但也往往大而無當,把文學藝術的本質、規律絕對化肯定是有問題的。相對于唯個性唯創新而言,反而是集體的積累,傳統的形成是文化、文學、藝術更常態更穩定的東西,更本質更主流的東西。再說,相對于不斷變化的外部世界而言,我們怎么堅守傳統都同時會被時代之河裹挾前行,都會有些東西被沖刷有些東西被附著,我們甚至完全可以憂新不憂舊;而從人性、心靈內部來看,人類的變化并不大,返本也可以開新,溫故也可以知新,能對人自己有一點理解、想象、領悟、洞察的咀嚼、回味,就很了不起了,這也只能是通過“移步不換形”的努力才庶幾能夠獲得。我們似乎只能不斷借由著集體和傳統,才能認識自己,獲得一點新鮮。
流派的好處還在于規范、講究,借著集體的力量,“移步不換形”,能幾乎達到極致。福建地方戲由于劇種小,很難形成流派,唱腔上音樂上的規范、講究實在少見,大多還是停留在原始傳承狀態,所以唱得好的唱得有韻味的點不出幾個來。京劇的演員不同,歸不到流派就很難成角。而角的首要條件是要唱得好,唱不好幾乎什么希望都沒有。不僅演員唱得好,票友也唱得好。京劇的音樂研究、唱腔研究達到非常高明非常精深的地步,那些研究者的水平一點也不比專業院校教授對西洋音樂的研究水平差。尤其是對傳統劇目、流派的唱段唱腔,一聲一字爛熟于心洞若觀火,研究得極為透徹,聽聲辨音能力神乎其技。當然,他們對戲曲音樂的觀念也與福建不同,他們認為戲曲戲是“車”,曲是“轍”,車要怎么開你自己要看著辦,因為路只有一條,車只能受路規范。所以京劇(昆劇)的劇本音樂性強,一讀就有一種流暢的音樂感。當然,南北方的戲有各自的特點,北方看戲習慣叫“聽戲”,南方則習慣叫“看戲”。北方唱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演,南方講究“一句曲一步科”,演往往重于唱,或演、唱不相伯仲。福建的老百姓評價戲也總是說“戲搬(扮)得好”、“很會搬(扮)戲”。京劇劇本的文學規律要合音樂規律,要順音樂規律,甚至有時不惜走向極端。《二堂舍子》劉彥昌的兩個兒子打死奸官的兒子,二人爭相抵命,劉彥昌不知如何是好,公堂上唱了一大段周代叔齊與伯夷的故事,文不大對題,大家都覺得不好,但唱腔好,百年傳唱,無人敢改。因為音樂的美和情感力量完全超越、覆蓋、淹沒了文學。京劇里還往往有的唱段唱詞文字不通,不知所云,但卻成為名段。唱詞只是其聲律完美地協樂律而隨音樂不朽。福建京劇院林戈明先生生前曾舉過很多例子來開導我們。福建的劇本文學規律是主體、主導的,音樂規律要合文學規律,要順文學規律,而且長期以來不怎么研究不怎么講究文學與音樂這兩個規律的結合。省外專家常常批評福建的戲(其實指的是新戲)不好聽——其實我們也覺得不好聽,我覺得其中根本原因不在劇種音樂本身上,而在我們的觀念、創作出了問題。而如果一個劇目、一個劇種一直不好聽下去,這個劇目甚至這個劇種都會很快消失的,這是一點也不危言聳聽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福建的戲曲文學走出了一條以文學性、文學規律見長的路,這是很了不起的,是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傳統,也使得福建戲曲有了與他人不同的亮色、特點,這是非常寶貴的。但是我們抓劇本、抓劇目而不認識、不重視音樂結構,不重視音樂性也是顯見的。講這些不是要否定福建戲曲文學的傳統,而是希望能揚長補短。我特別反對“揚長避短”的說法,短只能補,不能避,戰術上可以打打“擦邊球”,繞著紅燈走,戰略上這樣做便是急功近利,便是短視,最終是會把一切都繞進去。
上世紀60年代、80年代,福建對傳統戲的整理改編走出一條非常著名的路子,那就是主題上能化腐朽為神奇,能點石成金。比如封建主題,我們把它倒過來變成反封建等等,其次是重視表演上有劇種特色的劇目。但是我們肯定沒有也不會像北方那樣,為了著名的唱腔唱段來整理改編一個傳統戲——而這在京劇、昆劇中是比比皆是的。這說明我們的路子是有局限的,至少不夠完整、不夠寬闊,不盡符合戲曲的藝術規律。其實傳統好的唱腔唱段的價值和寶貴程度一點不比文學的、表演的小。好的唱腔唱段不僅加深我們對劇目的認識,加深我們對劇種的認識,也會加深我們對人、對自己內心情感和人性的認識。而且很多戲是“戲以曲傳”的,是唱段使劇目傳世的。一個劇種的生命力,一個劇種傳統的深厚,甚至一個劇種的大小,音樂上相當程度是依賴好的唱腔唱段的積累和傳唱的,而不只是有多少支唱腔和器樂曲牌,多少套鑼鼓經的。關于這一點,我們的認識是很不夠的。
昆劇節的感受是老劇目比新劇目多。以福建的觀念,一定會認為一屆會演,新劇目要遠遠多于老劇目,并以之為會演是否成功的根本標志。其實戲曲是傳統的藝術、積累的藝術,會演的舞臺上新舊劇目有一個比例是非常應該的。把劇目的新創性、原創性強調到極端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戲曲的常態和規律的。昆劇節上很多老戲都是明清傳奇的經典劇目,文學本或者其他劇種的改本甚至演出,有的早已看過,故事情節都較熟,寫法也熟,但是每個戲仍然是非常吸引人的,關鍵是音樂非常好聽,能讓人聽上癮,能讓人迷醉。昆曲是曲牌體,音樂上尤其是唱腔唱法上的自由度遠沒有板腔體的大,曲牌約束力很大,所以曲牌體的劇種很難形成流派。但是我覺得每個戲不僅曲牌好聽,而且曲牌的連綴成套也很漂亮,似乎必須是那樣的一套曲一套曲地聽下來才過癮,曲不成套就意猶未盡,就不能盡興。套曲有它自身的力量,不僅可以把故事情節把人物情感表達出來,而且又有超出故事情節、人物情感的東西。比如大河載舸,沉浮從容,自身亦深不見底,滔滔不絕。我對昆曲音樂沒任何研究,但是每出一套曲(其實整個戲又何嘗不是一大套套曲)給人的流暢感非常舒服,內在的結構之美真正是“順理成章”,聽多了還讓人有了一種審美期待,覺得曲牌就該是這么銜接,一支支順下去,呼之欲出,如期而至。變化太大,反而感到不熟悉不快樂。
有的音樂家(包括戲曲的作曲家)說曲牌、套曲太簡單,寫起來很容易,把唱段套上去就可以,是簡單、低級的勞動。我覺得持這樣的觀念最好不要給戲曲作曲。套曲有非常嚴謹的結構,有更為精致、準確的表現力,它是集體創造、積淀而成的,需要戲曲所有的經驗、識見,獨具慧眼與創造性,有個體作曲家、音樂家遠達不到之深廣處。昆曲的套曲,有它自己的戲劇性處理、戲劇性發掘、戲劇性推力,對情感的抒發,有自己的一套起承轉合,總是能夠一步步把人物、把我們觀眾的情感勾引出來,然后醞釀、開展起來,最后發泄、爆發出來。它有另一種完整性、結構力,可以把我們內心的集體情感不管是我們意識到的還是尚未意識到的,召喚出來并調理得非常暢通舒服,有整合我們情感及其結構的力量。戲曲曲牌的套法,有它獨特的內在規律性、內在合理性和創造性,這如同人的經絡、氣脈,如同陰陽、五行,另有一種讓你看得見摸不著的東西。經過幾百年磨合,它自身已經血脈貫通,形意相屬,而且儀態萬千。說到底,音樂性中含有戲劇性,音樂規律中含有戲劇規律,音樂思維中含有戲劇思維。我們要做的更多的是如何與之神交,如何去心領神會。作曲只能“我注六經”,不能“六經注我”,不能師心使氣,自辟蹊徑。曲牌體與板腔體的作曲不太一樣,板腔體更動聲動色一些,曲牌體的更不動聲色一些,但是不動聲色也一樣是一種高明。板腔體淋漓盡致、震撼,曲牌體輕聲細語、貼心。如果說曲牌是詞、句的話,那么把它們套得好,你就是語言大師、文學大師,套得不好,你不過是說白話而已,而且還口齒不清。我們有的新戲,一個唱段,曲作者可以說我每一句都來自哪個哪個曲牌,句句都有來歷,可是串起來又什么味道都沒有,一場戲,曲作者可以說我每支曲都有出處,可是套起來又不是那么回事,原因大致也在這里。昆曲的曲作者更注意曲牌的完整性、套曲的規律性。說到底,他們精通并尊重劇種音樂的完整性,把個人的創造性巧妙地隱伏在傳統中,揮發在傳統樂理、樂律上。看過昆劇節,我反而認為有曲牌的劇種是非常幸福的,因為它們有遺產,有積累,很富有、很深厚。曲牌體的音樂思維,在我看來是曲牌思維、套曲思維。
關于福建的戲曲音樂創作,也談幾點感想。我覺得尤其是年輕的作曲家,除了對本劇種的曲牌曲譜要熟記于心,除了聽熟了前輩藝人的錄音唱片,研究他們是怎么處理行腔、潤腔之外,作曲家還必須多看戲,多看傳統戲、折子戲。除了要找到音樂與劇本的關系,還要找到音樂與表演的關系。前面說過福建地方劇種的特點是一句曲一步科,所以一定要經由樂舞一體的途徑,把本劇種表現、表達情感獨特的地方,把那千變萬化的曲折弄清楚,要把表演上身段舞蹈的韻律節奏與唱腔、伴奏的關系弄清楚。因為我們的表演都是附著在音樂之中,音樂都是體現在表演之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程式表演有它自己的規律,什么樣的曲牌,就會有相應的表演。所以說我們創作的不只是戲劇故事的音樂,也不只是表現人物內心情感的音樂,還必須是可表演的音樂。音樂要深化人物的意蘊、人物的情感,還要寫出音樂對肢體的呼喚,誘發表演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可能性,要音樂到哪里,表演到哪里。在過去沒導演的時代,作曲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導演,引導演員進入人物,進入情感,進入表演。北方的戲可以站在臺上抱著肚子唱,南方的戲肯定是不可以的。因為南北方劇種的音樂特質、內在規律不一樣。此外,曲作者看的戲多了,舞臺熟悉了,對行當之間的戲曲特殊的戲劇性、戲劇關系的理解也會加深,音樂的色彩也會更豐富,表現力也會更豐富,劇種的特點、特色也會更鮮明。所以說作曲家不僅要懂譜、懂戲,還要懂表演,功夫還要在曲外。要相信能與表演相彰得益的音樂才是好音樂,要記住戲曲的規律是以表演為中心。
順便說一說配器。戲曲音樂本來大致只有唱腔、伴奏曲牌,加上場景的器樂曲、鑼鼓經。后來引入了西方的作曲理念,交響化趨勢是欲罷不能了,主題音樂、人物個性音樂等創作理念以及西洋樂器大量進入等等也是不一而足。這些對作曲家們豈止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這些當然也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強調過頭了對劇種特色的解構、瓦解也是不爭的事實。其中的分寸,還是要精準把握。現在的問題是,劇本創作、演員表演越來越進入戲曲自覺的時代,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劇本寫得越來越簡練、干凈、透明,線索越來越少,人物越來越少,有時整臺戲人物就五六個,七八個,舞臺也越來越空、越來越透,漸得一桌二椅的精髓、深意。可是樂隊越來越大,人數往往成倍超過臺上的演員,這真是讓人不知道該怎么辦好。唱腔曲牌化,配器交響化,對于戲曲音樂算是最客氣、最尊重傳統的了。我不大清楚二者的思維是否有沖突、有矛盾,需要花什么樣的智慧和力氣來解決它。但我知道,樂隊是越做越大了,而且演奏員只看樂譜只看指揮,不看場上不看表演了;劇種打擊樂在總體音樂中的位置、份量越來越小了,表演與鼓板的交流、對話越來越少,互相逗引、召喚、應承、生發的空間和能力越來越小,鼓板的思維和主導、指揮的功能正在喪失。福建有稍變弋陽的大腔戲、四平戲,不被絲弦,只有鑼鼓、幫腔,音樂簡潔,常常是不斷重復、迭加,推向高潮,產生集體情感的轟然共鳴,讓人享受音樂、唱腔的狂歡。我不是說這種簡單的音樂多么好,只能這么做,但是它確有現代配器復雜的、交響的音樂所沒有的原始的好處和魅力。這次福建省第二十五屆戲劇會演,很多劇團樂隊演奏員只好臨時外請,花費很大,在劇目總經費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成為劇團的沉重負擔。當然還有以前唱腔與配器大多一人做,現在大多分開做,音樂越來越宏大,越來越復雜。配器尤其追求立體化、交響化,或者譽為戲曲的民族交響化、民族歌劇化,其中確實有許多了不起的成果、創造和創新,給古老戲曲以新氣象、時代氣息,但是也可以明白看到交響樂、歌劇創作理念、欲望不可阻擋進入的堅強意志,以及唱腔配器分開做二者之間常常產生的痕跡或者說裂痕。戲曲劇本、創作理念經由話劇化,現在正回歸戲曲化。我不知道戲曲音樂應該是怎么樣,只是希望把舞臺的焦點關注更多給表演。各門類的文學藝術的元素、創造成果,最后都得有效地集中、匯聚在演員表演上。我倒覺得,戲曲音樂重中之重是唱腔,其權重甚至可占百分之七八十,唱腔不好聽,這個戲的舞臺生命基本就差不多了。對一般觀眾而言,“戲以曲傳”,至今好像還沒人說“戲以樂傳”。

看昆劇《牡丹亭》杜麗娘和柳夢梅幽媾的戲,《玉簪記》潘必正、陳妙常追舟相會的戲,音樂與表演結合得非常漂亮,是極致的精雅,是美輪美奐的雙人舞。這當然是積幾代人才華、經驗、智慧苦心經營而得的。看福建的戲就很少有這樣的場面,福建戲曲曲牌體的劇種也是男女同腔同調。以后在梨園戲《呂蒙正》的“過橋入窯”,《朱弁冷山記》的“公主別”依稀看到,想象中莆仙戲《春江》也應有類似場面。當然戲有所不同,但是音樂與舞蹈配合達到極致的感覺還是不如昆劇。新創劇目只在梨園戲《董生與李氏》中“夜窺”二人隔墻的表演中偶見,場景音樂寫得很有表演的空間和舞韻,很有表演的召喚力、想象力和表現力。一支笛子,幾分鐘一氣不歇地流動吹奏傳統曲牌【柳青陽】,其間只有節奏的變化,照樣把情感、情緒吹上高潮,把表演吹上高潮。其讓人心馳神迷的程度,一點不亞于大交響。真希望我們的作曲家能在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多與演員們一起共同創造一些這樣的讓人癡醉的折戲或片斷,讓這樣一些劇種特點得到最精彩綻放的片刻。如果我們都不下苦功,都不如古人,我們還能拿什么振興戲曲?
此外是幫腔問題。福建的戲曲幫腔少,讓人印象深的更少。其實我們各劇種均不乏幫腔。我聽過的記憶比較深的是梨園戲《高文舉》中“冷房會”給王玉真的幫腔。這段幫腔不長,大約就兩三句。幾句幫腔一下子讓人感到是一個女性群體出聲幫她傾訴,是歷代這樣的女性群體擠附在幫腔上,幫助她同時也是在傾訴自己的悲慘命運和不幸痛苦,非常震撼人。其實因為是折子戲,只有兩三個小演員在幕后幫腔而已。關鍵是音樂寫得好,寫得恰當,寫出了類型的集體情感,寫出了深度和厚度,寫出了劇種音樂的力量。所以戲曲的作曲,不是只寫一個人的情感,而是要把這個人的情感植附到這種人的集體類型情感上。唱一個人的情感是歌劇,唱一類人的情感才是戲曲。當然一個人可以有典型性,但類型性表現得更多是民歌、民謠、神話、傳說的情感效應。所以唱腔寫不到位,就會變成一個人的歌唱,而不是一類人的歌唱。戲曲的曲牌曲調,積淀的都是類型的情感和表達方式,這是新的作曲者一定要認識、體會到的。曲寫新了,寫個性化了反而沒有味道。孔子學鼓琴,說“得其曲,得其數,得其意,得其人,得其類”,層次分得很清晰,先是能演奏下來,然后分析它的曲式結構,再來是理解了它的主題意蘊,接著是由樂及人,了解作曲家,最后才是領悟了它表現的類型的集體情感,它到底打動了哪一類人的情感,引起哪一些同樣命運同樣遭遇的人的共鳴。戲曲的曲牌、作曲亦當如斯看,庶幾近于道。
為了滿足當代觀眾的欣賞習慣,現在戲的演出時間縮短了,但是內容卻增多了,信息量增大了,這使得我們的新戲變得很緊促。但曲牌體的唱腔好處就在一字數腔、一腔數轉,劇種獨特的運腔潤、腔處理有足夠的空間、時間,如果把它們擠干占滿了,劇種的特色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是唱歌而不是唱曲了。我聽過梨園戲陳雪紅唱的“公主別”,幾支曲下來,竟給人雪花公主生命如同蠟燭一樣寸寸燃盡的領悟,給人必然是曲終人亡的心痛和悲傷,其中的唱腔回環轉折、淋漓盡致。后來看演出的“公主別”,因為戲的節奏需要壓縮,又加上曲子分給男女角色輪唱,似乎唱腔的完整性反而有了問題,感染人的力量沒那么大了。劇作家應該給作曲家預留足夠的空間,作曲家也應該給演員演唱預留足夠的空間。對于演員來說,這些歌唱的空間同時又都是表演的空間。只有這樣,劇種的特色、劇種過人之細的地方才能有從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表現,才能有韻致和回味,才能讓人過目不忘,過耳不忘。音樂是劇種的靈魂,這樣說大致是沒錯的。不尊重劇種的音樂,其實也就是不尊重劇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