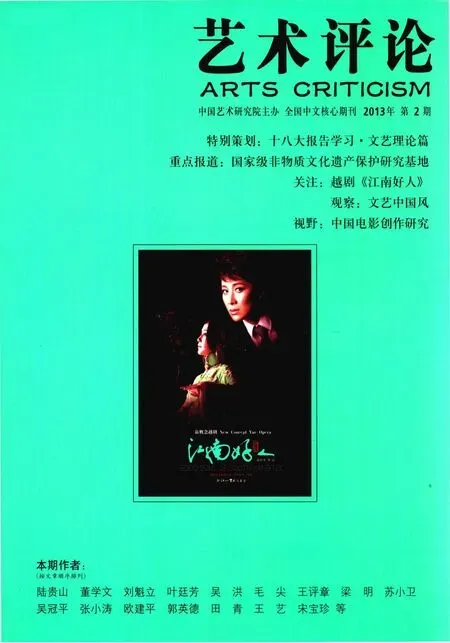郭小男:一場執著的相遇
唐 凌

《藝術評論》:《江南好人》是當下戲曲創作中非常引人注目和期待的一部作品,能否簡言其創作初衷。
郭小男:給中國戲曲找一條“突圍”的路,為了未來的戲劇,做點實事兒。我概括的是:面向未來的戲劇,居安思危的變革,叩問心靈的思辨,尋找精神的家園。
《藝術評論》:您說到《江南好人》的創作是一個突圍。那么,您想突的“圍”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這個“圍”?
郭小男:中國戲曲水土流失嚴重,中國戲曲到底往哪走?自然生態、生存形態頗為窘迫甚至危機。這十幾年沒了一百多個劇種,這是很可怕的事情。現存的劇種,生存情況更令人擔憂,生態環境越來越狹小,觀眾越來越流失,戲迷越來越老化。戲曲的向心力在縮小,但文化需求的格局卻越來越大,對藝術的復合和承載性要求也越來越高。當代人看戲的訴求與老戲迷的審美觀點也是永遠有代溝的。
那么,誰來思考中國戲曲往哪走?只停留在理論上的空泛和炫耀是不行的。劇團怎么辦?市場又怎么辦?這需要身在創作第一線的藝術家去考慮,去實驗,去探索,去趟路。于是我覺得應當做些“敢為天下先”的事,我偏愛做這種事。目的是再多走出些路來,哪怕挨些罵也沒關系。只要能夠得到更多的沒看過越劇的觀眾歡迎,挨罵也值了。
《藝術評論》:通過這部戲,您是否對這種嘗試更有信心了?
郭小男:是的,因為我走的每一步都已事先想好,而且我的創作團隊也已達成了共識。
中國戲曲的形態我很熟悉,越劇的形態我也很了解。“小百花”越劇的唯美已經達到了極致。它的詩意,它的吳越文雅,以及茅威濤的藝術成就都達到了相當的境界。這個團靠名氣、魅力再活十年是沒問題的。但是十年以后怎么辦?茅威濤不在舞臺上了怎么辦?這個劇種有沒有可能再往前走?越劇在其一百年的歷史中一直都在變化,而且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比京昆,越劇更年輕,更加有活力,它完全有能力改變。我們不止一天在想這個問題,我經常和茅威濤討論:如果這種“美”一直復制下去,這個瓶頸就越縮越小。現在人們討論“小百花”和茅威濤都是關于《梁祝》、《陸唐》、《西廂》,是的,“小百花”因為有自己的特點和成功才成就了今天的“小百花”。但是它的特點不應成為它發展的局限。如果想看原來的“小百花”可以來看《梁祝》,但是“小百花”必須還應有另一面,那就是今天的《江南好人》。
《藝術評論》:所以您并不反對過去業已形成的特點和優長,唯美可以延續,只是在此之外,還希冀有更開闊更新的路?

郭小男:我從來不否定舊的,因為那里面有傳統。但我一定要創新,我經常說到的八個字“舊中見新,新中有根”。這里面的辯證關系一直作用著我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
其實,茅威濤站在舞臺上,就等于越劇的存在,就等于唯美。但越劇的氣質是什么?越劇給人留下的精神狀態是否能像《江南好人》這樣?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部戲可能會一下子調整不過來,但我的作品不能僅為越劇的那一部分觀眾服務,我希望她的受眾群體越來越廣闊。所以我把《江南好人》定義為“面對未來的戲劇”。未來是什么樣我不知道,但這個劇團以及這個劇種需要具備這樣的準備和技術,我需要幫助他們轉型,從理性到感性,從演員到觀眾。
我做傳統可以做得很好,比如《梁祝》、《春琴傳》,但是我還能換一個樣子來做這個劇種。其實這也是給劇種、劇團尋找另一種活法和另外一種生存發展的可能性。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要“突圍”。
很多沒有看過越劇的觀眾,拿《江南好人》當音樂劇來看,我覺得也沒什么不可以。戲是永遠演給觀眾看的,觀眾只要喜歡。我最怕的是哪一天觀眾不喜歡了該怎么辦,所以我一定要“突圍”。實踐證明,這一次的突圍,“小百花’成功了。敢為天下先,就像我十幾年前排《孔乙己》一樣,讓觀眾不斷關注一個劇種,覺得這個劇種有東西可看,關注這樣的藝術家和這樣的作品。
《藝術評論》:這是在排演之前就已經考慮和預想得很清晰的嗎?
郭小男:首先是理念上要想清楚。嘗試一次“突圍”,著眼點非常重要。選題、審美架構、表現力、方式方法,頗費些精神;其次,是否有茅威濤這樣的演員;第三,是否有可以體現理念、完成創意的團隊。
我和“小百花”合作了十幾年,“小百花”早已不是一般意義上普通的戲曲劇團。這個團隊接受新鮮事物,十幾年前就開始請金星培訓舞蹈。平時“小百花”的素質教育課抓得很緊,還有現代舞、民族舞,甚至爵士舞、踢踏舞的日常訓練。演員有了這些技術,實際上為轉型做好了準備。去年四月為完成中韓邦交二十年的慶典活動,要趕排朝族劇目《春香傳》去韓國演出,其中演員們要表演韓國的長鼓舞。我請了一個朝鮮舞的老師來強化訓練半個月,結果在首爾演出時,“小百花”演員們的長鼓舞讓韓國觀眾非常震驚,這就是平時訓練的結果。
《藝術評論》:說到“突圍”,任何突圍都是很慘烈的,是否有必要以茅威濤這樣優秀的藝術家來進行“突圍”?
郭小男:第一,如果沒有功成名就的藝術家來做,那就失去說服力了。我和茅威濤做這件事,說明她不在乎所謂的功成名就,敢于突破,樂于犧牲。說明我們敢于擔當,敢破這個“圍”。第二,我需要有這樣的藝術家來演,茅威濤需要轉型,對不對?這一點我們十幾年前就討論過。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選擇什么樣的劇本來表達突圍了。《長生殿》恐怕不行,《西廂記》不行吧?甚至莎士比亞的作品也不合適。之所以選擇布萊希特的劇作《四川好人》,是因為作品中思考社會變革的聲音,適應了當今時代的需要。這一點,也表達出“小百花人”同步思考積極參與社會命題的愿望。
《藝術評論》:從首演這幾天來看,這個作品劇場效果如何?這部劇的特點何在,會比原來的作品更受觀眾喜歡嗎?
郭小男:今天我做的事對不對,這一定要放在劇場去檢驗。我認為《江南好人》比我以前的作品更難做。因為我的目標是要為年輕一代人創作,培養下一代的觀眾。《江南好人》主要是將布萊希特的戲劇哲理性與中國戲劇傳統銜接,將理性思辨的戲劇與感性移情的戲曲結合起來,找到一個很好的嫁接點,還要運用“間離”的技術方式。最重要是能夠吸納越劇圈內、圈外的觀眾,引起他們對這個劇種、劇目和演員的關注、興趣和熱愛。幾場戲演下來,這個目的實現了。
《藝術評論》:目前感到越劇成分有些弱,會令人不甚滿足。
郭小男:有人問我為什么這部戲里沒有讓我過癮的唱段?為什么沒有?因為布萊希特的作品嚴禁抒情,他是客觀理性的敘事體。如果加唱腔讓觀眾去“過足了癮”,這戲也就又回到傳統的戲曲形態里去了。
《藝術評論》:您選擇的布萊希特和越劇,從風格氣質內涵來說,幾乎是對立的兩極,這部的作品是否適合用越劇來做?是否能夠滿足廣大越劇迷?
郭小男:極端一點說,這個戲不是來滿足老觀眾的,我要做一個新東西,是希望在少傷害老觀眾的同時努力滿足新觀眾。布萊希特的風格讓我在創作過程中一句抒情的詞都不敢寫。我希望觀眾喜歡整部作品的形態。劇場是個網絡學,現在觀眾各有所取,導演按鍵盤傳達信息量給觀眾,觀眾用自己的密碼自己的文化去編。有的觀眾說茅威濤男人的形象帥,有的觀眾說劇中感受到江南風情,有的觀眾說以后茅威濤可以演旦角了,隨觀眾去吧,這些都是觀眾的體驗。而我想告訴觀眾戲曲還可以這樣,可以如此去演。我相信中國戲曲一百年后一定是要換形態的,如果不換形態一定是走不到世界的舞臺上。
《藝術評論》:如此,這部作品的目的性會不會有點重?比如說為國際而作?

郭小男:我還是在強調突圍,一定不能讓戲曲只有一條路越走越窄,因為它的受眾面已經出現問題,已經太窄了。我一定要努力讓更多的人來看越劇,這就是戲劇的生命,也是面向未來的姿態。我們不擔當是沒有人來做這件事的,所以我不在乎有人說為什么越劇的很多東西都沒了。我是在往里加新的元素,我需要它有一個新的機體狀態,微量元素是不斷要改變的。因為氣候變了,生態變了,水質變了,受眾體變了。讓新的觀眾在越劇原有的系統里出來都沒有關系。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探討戲曲是不是可以走這條路,是不是可以這樣。這部作品如果多爭取到一個越劇觀眾,都可以說是我對越劇的貢獻。
《藝術評論》:您理解通過這個作品爭取到新的觀眾的方法和原因在哪里?
郭小男:是一條路,但不是絕對的一條路。我不放棄原來的傳統,但我有新的樣式給你看。作為新樣式,一,它不是古典戲劇;二,它解構開“小百花”原有的一些詩意、唯美,重新建立下里巴人的生態學;三,“小百花”第一次演現代戲,茅威濤第一次演女人,“小百花”演員第一次穿現代服裝,這些都是革命。所有的元素進來的時候,它能吸收這么多新東西,表達出這么多新元素,這就是魅力,就是一個轉型。很多人激動于茅威濤能塑造出這么多生動的角色。茅威濤扮演女人,從氣質、形態甚至發力點都是不同的。演楊森的演員(陳輝玲)原來是演紅娘的,表演這部戲她有很大難度。這些戲曲演員坐科出來,骨子里都是小生、小旦。這部作品我排練了六個月,遠遠超出預計的時間,也是因為我低估了這個可能性,因為技術是最難的。戲曲的生、旦、凈、末、丑,那是從小練的功,這個戲把她的功給廢了,得重新練一個功。這不是簡單地說小生轉過去就能演女人,小生和花旦的發力都是不一樣的,骨頭都得掰過來,生理上要有很多改變。

《藝術評論》:其他且先不論,表演上這么大難度,團里包括其他演員是否對您支持?
郭小男:團里說,先決條件是茅威濤團長,我和茅威濤擔負的壓力比誰都大,這就是擔當。既然茅威濤敢,觀眾也應該嘗試去看看。當我排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就告訴演員我是要引領觀眾的,不是要迎合觀眾的。
《藝術評論》:觀劇時,坦率地說,我感到了一點導演的居高臨下,尤其是劇中最后的若干遍 “觀眾當思辨”,太生硬太強行了。
郭小男:這句話是本劇的文學顧問、翻譯丁楊忠先生幫我修改的,他只加了三句詞“世道若是不改變,好人怎救眾生難,觀眾當思辨”。我和他探討過,他覺得我寫的詞都很好,但布萊希特的精神就是一刺到底。如果劇場里沒有這樣的一種呼喚,那就不再是布萊希特。我認為有道理,應當矯枉過正。第一,告訴觀眾這是寓言;第二,告訴觀眾要思辨。希望觀眾看完之后要知道思辨,這就是布萊希特的特點,用他的東西就要走他的思路,走他的方式,要做就要做到極致。我希望達到的戲劇效果就是要逼著觀眾沉思,要破壞觀眾的審美系統。
《藝術評論》:其中有特別動人之處。最后的審判,沈黛跪在地上唱的那一段非常動人,因為這一刻達到了情理交加的境界。有情感,且是與自身的人生體悟相融達到的深刻情感,感概萬千而又思緒萬端,是情與理的極佳交融。
郭小男:這種思辨與中國戲曲之間是非常難平衡的,一不留神就成了哭訴。比如說當劇中沈黛得知被騙后,茅威濤穿隋達的服裝唱了一段女人戲,這段戲最容易回到傳統戲曲的抒情里去。而布萊希特的觀念是要唱出實質,唱出被騙的實質是什么,唱出人沒有誠信的根上,而不是去抱怨為什么被騙。劇中沈黛懷孕后也沒有抒情,而是只寫到“記不得哪個夜晚,數不清幾多星閃。流不完喜淚千行,述不盡依依愛戀。雖說他已人去遠,卻留下了愛的纏綿”。留下什么?留下讓我變狠!這是布萊希特厲害的地方,恰恰也是中國戲曲最缺少的。比如劇中我讓四個姑娘扇扇子,中國戲曲的雨是在扇子上綁著珠子來擬聲的,這是傳統戲曲的劇場效果。我讓四個姑娘在沈黛和楊森定情的時候在舞臺上扇扇子,這實質表現出這是一個假象、一個騙局。全劇結束前出現了一個剪影,分別穿著男女的服裝,這樣的一男一女代表雌雄同體,這是善惡同體的寓意。無論觀眾是否看懂,但這是我作為導演要給予觀眾的。當觀眾接受這部作品的時候,我相信我們的觀劇方式都會在變化。
《藝術評論》:劇中用到的爵士舞、Rap等,是更多地作為間離手段破除幻象?還是認為這種形式能夠吸引新觀眾?
郭小男:破壞中國戲曲的程式,同時也豐富中國戲曲的程式來表達思想性。為什么我要用這些元素,這和我選擇布萊希特的作品有關。就是反戲劇、反傳統。我要告訴觀眾,不能依賴以往的看戲經驗,這里沒有幻覺,不是體驗,更不是欣賞大段唱腔。我會給你特別多的信息量,比如說茅威濤是唱小生的,隋達唱的是尹派,那沈黛唱什么?茅威濤不是學旦角的,那旦角唱什么?茅威濤沒有女腔,這也逼著我為之建立。之所以叫“江南好人”,因為我可以把一切江南的元素吸收進來。我讓茅威濤唱評彈,以評彈為基礎可以加入很多民間曲調,但隋達一張嘴還是越劇。又因為這是現代戲,許多古典程式就被放棄了,我用很多其它的東西來豐富其表達手段,來建立起一種新的可能性。想好做什么戲是思想家,想好怎么做就是藝術家。我為什么要用現代舞以及Rap呢?這是根據形態而定的。為什么劇中背景定在民國,這可以意在今天。這里文明的幾個落點是有的,抽煙、戴帽子這些元素都有,我們也加入了紡車。我們為做這個戲曾去過桑田和絲綢廠采風,紡車這場戲無論如何都是震撼的。紡車的出現就馬上告訴觀眾工業革命來了,剝削來了壓榨也來了,人的觀念就變了。這場戲的震撼和意義,在中國戲曲舞臺肯定是第一次。
《藝術評論》:這些手段和辦法對于“小百花”是首次嘗試,如果放到更大的范圍來看,此前在其他戲劇演出中都曾嘗試過,那么這種革命性究竟有多大?況且這些新元素并非越劇演員所長。
郭小男:但這次是在越劇中使用多種藝術元素,而中國戲曲有很強的規定性,這是很不同的。另外,如果外國劇團演這部作品,我們就能更容易接受他們,因為我們觀眾看劇前就設定成要接受他。如果我們用A在看B,但做A的人告訴你我們能做成B,我們為何不重新欣賞一下呢?為什么不能多種形態呢?這不在于這些演員跳得好不好,而是我運用了這些元素,改造了他們,既可以做傳統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我們做的是一個新概念越劇,回到原點這還是越劇,這是新概念,希望審美者不要糾結。
《藝術評論》:擁有更開放的心態和審美,對于觀眾也是非常重要的。很敬佩你們創作探索的勇氣與付出,這種精神永遠是值得尊敬的。但就作品本身的藝術呈現而言,這部作品是否達到和實現了您的想法和標準?
郭小男:這是個理論問題。一個劇種有什么和沒什么決定了它的表達能力。京昆之所以凝固是因為它的內容實在太多,甚至現在還沒表達完。但越劇才有一百年的歷史,簡單說就是民間小調,并沒有太多深厚的東西,負擔和羈絆也就相對少許多。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袁雪芬就創作了《祥林嫂》,剛剛解放又創作了《梁祝》,因為上海的文化給了這個劇種吸收其他元素的可能性。而吸收其他藝術元素是否成功,這就需要導演來把度。
《藝術評論》:我一直認為這次布萊希特與越劇的相遇是一場艱難的相遇,與您談過之后,尤其感到這更是一場執著而清醒的相遇,從十幾年前的心愿暗藏到今天舞臺上的粲然呈現,甘苦自知,衷心希望這場相遇是一段開啟!
郭小男:我們一定不能總是“復印”美,我們要迎接挑戰。我們已有過《孔乙己》,有過《藏書之家》、有新《梁祝》、《春琴傳》,為什么不能繼續?觀眾的審美永遠不是障礙,真正的阻力常常是我們自己的能力。只要堅守住越劇的根,弘大它的精神,只要不斷地給觀眾提供新的審美可能,劇種和劇團就可以繼續向前走,去贏得更加廣闊的市場和未來。這就是我做這件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