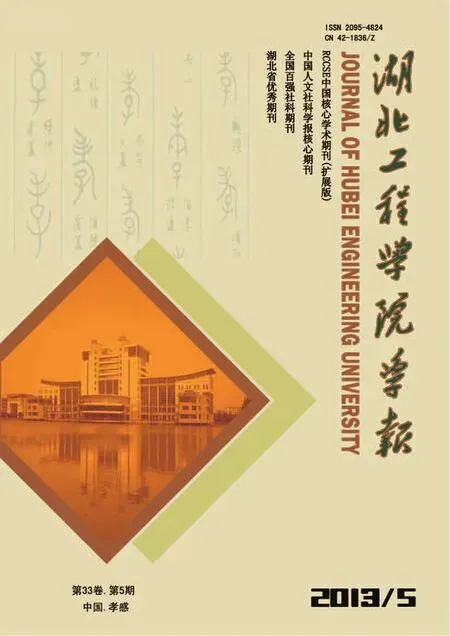論薩義德的“世俗批評”
2013-10-29 10:20:16蔡天星
湖北工程學院學報
2013年5期
關鍵詞:文本
蔡天星
(廣東警官學院 公共課部,廣東廣州510440)
自1978年《東方學》面世以來,愛德華·W.薩義德(1935-2003)一直成為全球知識界競相評說的人物。薩義德的真實形象被遮蔽在人言皆殊的眾多評論中:中東恐怖主義教授、巴勒斯坦民主斗士、美國的獨立知識分子、第三世界后殖民主義批評領袖。而掀開“世俗批評”之窗,最能看清薩義德在“現世”里的真面貌。
“世俗批評”對于薩義德來說,具有立場性的意義,其對立面是“宗教批評”。在《世界·文本·批評家》一書中,薩義德用“世俗批評”和“宗教批評”來命名該書的緒論和結論,體現了他旗幟鮮明的態度:弘揚世俗批評,反對宗教批評。
“世俗批評所處理的是局部的和現世性的情景,以及從本質上說它反對大規模的封閉體系的生產”[1]42。薩義德用了“現 世性”、“在世”、“境況”、“因應時事”等詞語來強調文本與時代背景、現實事件、社會世態、人類生活、歷史階段不可分割,比黑格爾《美學》里的“情境”更強調作家、文本、批評家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緊密關聯性。“現世性”等詞語出現在薩義德文論里的頻率非常多。“世俗批評”意即:批評家在作品所展現的文學世界里“進入現實”,“在對世俗生活進行透徹淋漓的觀照過程中……領悟到有關現實、歷史、人生、世界的許多難以明言甚至無法明言的底蘊與真諦”[2],并用評論揭示以干預現實。
一、薩義德“世俗批評”的緣由背景
雖然“世俗”與“宗教”兩個詞拈自宗教改革的歐洲近代歷史,但是,對于薩義德而言,“世俗批評”、“宗教批評”是正發生在“現世”的當今現實。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藝術評論(2020年3期)2020-02-06 06:29:22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18年11期)2018-12-29 12:30:58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語文知識(2015年11期)2015-02-28 22:01:59
語文知識(2014年1期)2014-02-28 21: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