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風骨
○劉火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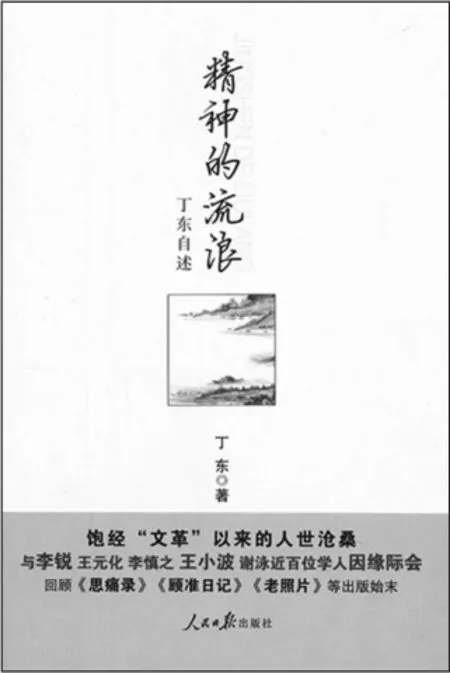
《精神的流浪:丁東自述》,丁冬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真正的知識分子多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想起人類的未來,他們不時眼含孤獨的淚水;真正的知識分子常持批判的眼光,一如北島的回答: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中國語境中的知識分子譜系,追溯至古代往往讓人聯想到“士大夫”。中國士大夫矢志不渝的至高理想多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抑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民國以降,無論是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條,還是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擔當……就其精神內核而言,他們與古代士大夫的終極追求一脈相承,與西方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也同聲相應。
歷經“反右”、“文革”等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一度集體沉淪,伴隨著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大潮,新老知識分子再次覺醒。近些年來,許紀霖、林賢治、謝泳等學人對知識分子的議題各有研究。近年來,丁東編選出版了“背影書系”——《先生之風》《追憶雙親》《此生此前》《風雨同窗》,大多也關涉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人民日報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的《精神的流浪:丁東自述》一書,從傳主自身經歷及其與黃萬里、李銳、王元化、王小波等學人的因緣際會,不難管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多種氣度。
“文革”爆發時,丁東只是北京師范大學一附中的一名初二學生。因父親是民主建國會的普通干部,母親為中學實驗室管理員,丁東既非“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很快被邊緣化,以致常有一種不能充當學校“革命”主力的失落感。他只好在家屬院里參加“革命”,跟著年齡大一點的學生發布通告,要求全樓居民主動交出“四舊”。丁東所在家屬院居住的多為民主人士,100來戶人家交上來的“四舊”堆滿了整整一屋子,光書籍就不下萬冊,包括外文書、古書乃至成套的二十四史。
此后,丁東歷經“知青”、“機關干部”、“大學生”、“編輯”、“學者”等身份的轉換。為了重返北京,以便自主地進行學術研究,他選擇了不參評研究員職稱,并于1997年辦理了退休手續。友人多有不解,當時他年僅46歲。
這位沒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組織了《顧準日記》《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王申酉文集》的整理與付梓;間接促成了韋君宜《思痛錄》、黃萬里傳《長河孤旅》、章詒和《最后的貴族》等著作的出版;參與編輯的《老照片》文叢和三冊《大學人文讀本》等,都是文化含量相當高的精神食糧。
在謝泳看來,丁東的主要傾向始終是現實關懷和社會正義,他的所有學術工作,都保持著對現實的熱情,他有關中國當代民間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基礎性的學術工作,這些工作雖然并不彰顯,有時甚至是默默無聞的,其意義卻極其重要。丁東曾在《中國青年報》等報刊開設專欄,出版有《思想操練》《與友人對話》《反思歷史不宜遲》等著作,或傳播新知,或針砭時弊,在學術領域與社會現實中,他向來保持著“發聲”姿態。
“沒有比知道我們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況改變這件事更使一個人的處境變得令人難以忍受的了。”哈耶克的這句斷言正是黃萬里人生的寫照。人如其名,作為新中國第一代水利專家,黃萬里平生與萬里江河緊密相連。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被提上議事日程。在70名學者、工程師參加的論證會上,眾人噤若寒蟬。唯獨年近半百的黃萬里站了出來:“一定要修三門峽水庫將來要闖禍的,歷史將要證明我的觀點。“一定要修,請別將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覺悟到需要沖刷泥沙時,也好重新在這里開洞。”寡不敵眾,黃萬里的意見被否決,不久后他被劃為“右派”。宣布處分決定時,他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事后,有人問黃萬里:明知說破會遭慘禍,為什么還要直言?黃萬里坦言:“父親(黃炎培)常對我說,‘中國有史以來,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統治階級。’讓我一輩子為農民服務我謹記著父親的教誨,學水利,學治黃河就是想為農民服務。我不能看著要禍及農民不說話。至于為此而付出的沉重的代價,我一生無悔。”
20世紀60年代初,三門峽大壩建成并下閘蓄水,一兩年之后,潼關河床淤高了4米多,淹毀良田數十萬畝,渭河泥沙淤積直逼西北經濟中心西安。此后多年三門峽工程淪為“雞肋”,難逃不停被改造翻修的命運。這與馬寅初“錯批一人,多生三億”的悲劇如出一轍。
與黃萬里交往時,丁東對其水利思想感觸深刻。在黃萬里看來,正是黃河攜泥沙而下沖積而成的黃河三角洲平原,養育著幾億中國人口。在此意義上,黃河非“害河”而是“好河”,“黃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規律。丁東寫道:“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黃老學說的高明之處,正在于他能把河流當作活的生命來尊重。”
李銳曾任毛澤東秘書、燃料工業部水電工程局局長,無獨有偶,他也曾反對三峽工程倉促上馬。論證會上,李銳條分縷析,既分析當時中國還沒有能力消化這樣大的電量,也闡述防洪須堤防、湖泊蓄洪、干流及支流水庫并重,不能用一座水庫畢其功于一役,待時機成熟再考慮三峽這樣的大工程。毛澤東采納了他的建言。
李銳可以說服毛澤東放棄建設三峽工程,卻不能預料自己的命運。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因同情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意見,李銳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打入別冊20年,其中8年牢獄之災在秦城監獄度過。復出之后,李銳寫出《廬山會議實錄》,其史料價值與反思深度,震動學界。
耄耋之年,李銳仍“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丁東給李銳寫過口述自傳,兩人有過不少接觸。據丁東記載,李銳每天不是閱讀,就是寫作,日記從不間斷。這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使命感,令丁東非常感佩。
李銳曾手書條幅贈給王元化,內容為劉禹錫的《浪淘沙》:“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很珍愛這幅字,將其懸掛于家中,這首詩恰恰是其跌宕人生的縮影。
作為一個“胡風反革命分子”,王元化冤案歷經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昭雪,長期的孤獨與壓抑使他一度患上心因性精神病。莎士比亞與黑格爾的經典作品,陪伴他度過了精神危機。1983年,王元化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丁東因為編輯《顧準文集》而與王元化結緣。他第一次與王元化見面,正趕上慶祝香港回歸,電視臺想采訪他并請他發表感想。王元化說,不要采訪我,這件事上我談不出新的見解,而應景的話我是不說的。王元化還向丁東透露:他剛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時候,有人對巴金在香港報紙發表隨筆反思“文革”很不高興,于是通過上海市委讓他出面做工作,想換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協主席職務。王元化對市委書記說,你們代表市委作決定,我服從,但讓我先提出報告,我不能干。最后,巴金作協主席的職務并沒有被換掉。
德國學者沃爾夫·勒佩尼斯發現,“知識分子天生就是一個憂郁癥患者,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無法使其理想具體化,因而陷入一種隱性的憂郁癥中,或者躲藏在一個美好的想象世界的烏托邦中。”在“烏托邦”與“憂郁癥”之間游走的知識分子,王小波算是一個典型。“王小波”這個名字就頗有意味,他的父親王方名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邏輯學教授,就在王小波出生的1952年,王方名被劃為“階級異己分子”,家庭突遭變故,“小波”之名于是取意“小小風波”。
同樣當過“知青”的王小波,自身也歷經坎坷,特別是作品一度不為人所重的苦悶,常人自是難以體味。丁東與王小波夫婦相熟。有一次參加《湘聲報》在北京舉辦的組稿會,丁東和王小波的座位挨著交談中,王小波說:“銀河是‘叛徒’,黃梅是好樣兒的。”王小波與李銀河的愛情佳話眾所周知,兩人情書集《愛你就像愛生命》還曾被出版。何來“叛徒”之說?原來,中國社科院評職稱,一律考外語,李銀河參加了考試,評上了研究員。按她的學術成就,這本理所當然。黃梅覺得讓自己去考外語是一種屈辱,于是抵制了考試黃梅是英國文學專家,如此考外語,好比把成人送進幼兒園。
于平凡中發現世界的荒誕,正是王小波的深邃之處。當越來越多的人自稱是“王小波門下走狗”之際,是淪為沉默的大多數,還是甘當一只特立獨行的豬,這種王小波式的追問越來越考量一個人的心靈。胡適當年曾感慨: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面對當今社會一系列喧嘩與騷動,真正的知識分子一步步拱卒前進的精神更難能可貴。
如果說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么很大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一代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骨薪火相傳、歷久彌新,這足以讓來者有理由相信未來,相信這個世界終將更加美好誠如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所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