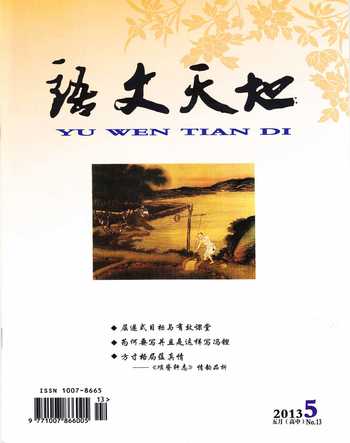方寸格局蘊真情
劉紅麗 周廣平
《項脊軒志》借述一軒格局之變化,寄寓了自己家世變遷、身世沉浮的深沉慨嘆。對于這一點,讀者在品析時往往容易忽略,實際上這恰是歸有光的匠心所在。關于項脊軒格局的變遷,作者雖簡言淡語,卻意味深長。姚鼐曾評價“歸震川能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有風韻疏淡,此乃于太史公深有會處。”
一、從軒的環境變化品作者讀書之喜悲
文中并未直述作者家道沒落之悲慨,但從項脊軒所處的環境——歸家庭院的格局變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家族由衰轉敗的過程中作者的心緒變化。
“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歸家的庭院最初是一個整體。雖然昔日榮光不在,以至庭中“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但畢竟“南北為一”,這個沒落的大家族至少維系著形式上的完整與和諧。正是在這種家族一體、相對和諧的氛圍中,年幼的歸有光才得以 “前辟四窗,垣墻周庭”,“雜植蘭桂竹木于庭”,盡力營造項脊軒雅致的周邊環境;才有了“借書滿架,偃仰嘯歌”的讀書之樂和“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的情趣與心境。這樣逍遙愜意的讀書生活甚至讓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的陶淵明的田居和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的劉禹錫的陋室。雖然不超然于物外,而是以考取功名、重振家業為自我要求,但在這樣的讀書時光中,歸有光感受更多的應該是單純充實、憧憬滿懷的讀書之喜悅。
然而,昔日完整一體、和諧有序的大家族畢竟走向了分崩離析。這是一個家族最為無奈的悲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象征家族完整的大庭院最終經歷了“為籬”、“為墻”的悲劇命運,曾經融融樂樂的兄弟姊妹儼然成了路人。“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的幽寂已然無跡可尋,只落得“東犬西吠”、“雞棲于廳”的喧囂雜擾。曾經的名門望族,而今卻淪落到“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的地步。“扃牖而居”、埋頭苦讀的歸有光當然讀得懂家道沒落之時,將重振家業的全部期望都寄予在他身上的祖母的殷切之情,“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這是一位老人深深的期盼、信任,甚至是一種傾其肺腑的祈求。眼看著家族破落的歸有光,在祖母期盼的眼神中,終于更清楚地明白:復興家族——那不再僅僅是一種源于自我要求的自勉,更是決定家族命運的他必須擔負起的家族使命。而在那個時代,要想改變現狀、振興家族,最有效的途徑便是刻苦讀書,博取功名。項脊軒中的讀書時光,不再如從前那般單純愜意、滿懷喜悅了,作者從中咀嚼到的或許更是家族衰敗之悲傷、肩負使命之沉重。
二、從軒的稱謂變化悟作者心境之浮沉
作者在文中對項脊軒的稱謂其實不止“軒”一個名字,而是經歷了“閣子”——“室”——“軒”——“室”——“閣子”的變化的。“軒”的前后稱謂變化,恰恰寄寓了作者不同時期的心境浮沉。
文中說“余自束發讀書軒中”,歸有光到了“束發”的年紀——約十五歲的時候,這個曾經極其普通的小房間成了他個人專用的“書房”后,作者才開始正式稱它為“軒”。
在此之前,作者先稱之為“閣子”,后稱之為“室”。文章開篇便介紹了項脊軒的來歷,“項脊軒,舊南閣子也”,這個小房間從前只是偏南一隅的極為普通的小閣子,作者在介紹這一點的時候,語氣很是客觀,可見作者對作為“南閣子”時的這個小房間并未融入過多的主觀情感。而當稱呼由“閣子”變為供人居住的“室”的時候,作者的情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因為作為“室”的時候,“先妣嘗一至”。這個小房間曾鐫刻了老嫗和作者關于“先妣”的共同回憶,并帶給作者以母愛的回味與溫暖。
在歸有光的心目中,項脊“軒”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當作者稱“軒”的時候,這當中包含了他對這個生活場所的特殊感情。
在項脊軒中,少年歸有光不僅度過了一段單純快樂、自在閑雅的讀書時光,更是在家庭分崩離析的悲痛中自覺地擔負起重振家業的重任。在這里,他回味咀嚼著母愛的溫暖、母親的期待,并以祖母的關愛與期盼自勵,他“扃牖而居”、埋頭于圣賢書中,甚至“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此時的歸有光雖尚未功成名就,但他對于自己的未來滿懷憧憬,相當樂觀。在原著刪去的一段文字中,他自比蜀清、孔明,認為雖然目下自己身處“敗屋”,可是終究會像蜀清與孔明那樣揚名天下。
婚后,項脊軒仍然是青年歸有光最重要的生活場所。在閉門苦讀之余,妻也會“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幾學書”。而妻“歸寧”,和姐妹們說的最多的恐怕也是這軒中時光,以致諸小妹直追問“姊家”的“閣子”。歸有光在《請敕命事略》中曾記述“(先妻)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妻子對于丈夫的未來,也是充滿了信任與期待。此時的這個小書房,給予了歸有光太多幸福的回憶和前進的動力。軒中讀書的日子,在他筆下由最初年少筆調明快的“喜”轉為家庭變故后凝重的“悲”,最后筆調還是積極而明朗的。
然而,“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作者對于這個小房間的稱謂由“軒”重歸于“室”,此時的歸有光多次參加科舉,均未能博取功名,期望屢遭挫折,又遭遇妻子早亡的內心創傷。“室”,這種對于眼前屋子相對隨意的稱呼,恰恰表露出作者內心的哀傷與苦痛,我們甚至可以這樣推斷:軒中的生活是美好的,軒因人而有了更好的稱呼,但隨著人去軒空,作者內心的失意與苦痛令他不再關注,或是因為怕被觸痛而不再愿意流連軒中,軒自然就變成了室,而室的命運不可避免的就是“壞”,不僅“壞”了,且“不修”了,“不修”二字簡短至極,背后卻蘊藏著一段痛苦的回憶。
“后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這個曾寄寓著作者、母親、大母和妻子那么多期望的小房間,最終又由“軒”而“室”,重新歸于無人居住的“閣”。還未從功業無成、愛妻早亡的打擊中振作起來,自己又遭逢“久臥病”的際遇,庭前亡妻手植的枇杷樹已亭亭如蓋,而自己過了而立之年,曾經的期盼卻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從“軒”到“室”又到“閣”的轉變,寥寥幾語,卻飽含著作者對于愛妻亡故的難言苦痛和自二十歲考中秀才之后,“八上春官不第”的凄涼無奈,以及無力改變家族命運、重振門楣的悲痛自責。
可見,歸有光通過對項脊軒格局變化的描寫透出了自己命運的沉浮和心境的跌宕,一座宅子的命運不僅象征著一個家族的命運,也寄寓了一個人的命運,其間的真情蘊藉是長久而深沉的,若不然,何必在時隔多年之后依然有補敘之舉?至此,作者情意已在項脊軒格局的變遷中流轉起伏,這也是我們在解讀此文時應該緊扣的脈絡。
作者單位: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學(32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