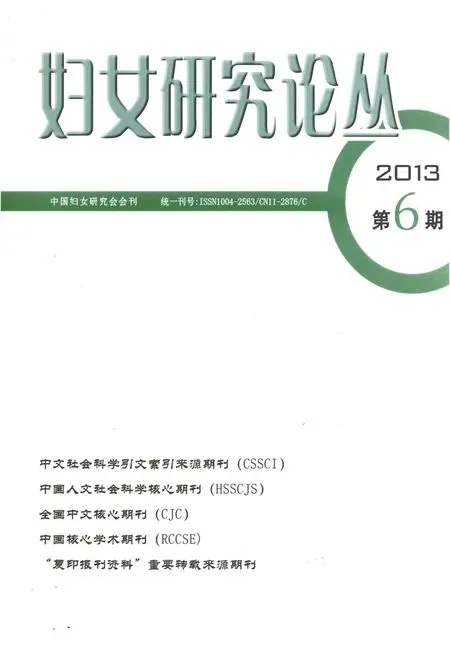性別與倫理*:重寫差異、身體與語言
2013-04-18 09:18:39王楠
婦女研究論叢
2013年6期
王楠
(北京師范大學 外文學院,北京 100875)
性別是當代思想界的一面利劍。作為一種學術視角,性別研究中有關倫理向度的思考一直承載和刷新著幾乎所有學科的不同層面。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對性別的思考采取理論“介入”的姿態,試圖改寫理性、言語、行為的慣性思維,在“生命于何處存在”這個基本倫理問題上,開啟了因身體的物質性差異而引發的人類理性的討論,包括關于語言、文化、社會和知識體系的討論。正如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性的政治譜系學式的考證所示,在后結構主義的批評視角下,生命已成為權力和知識干預的客體。思考性別也成了人類自我反思的一種方式,成為我們理解自身的一個倫理學母題,其中充滿了困惑和矛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諸多學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奉行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立場,從而表現出明顯的“性別盲視”。它或者堅守以男性為中心的學術本位,排斥、貶抑乃至無視女性的視角、經驗與價值;或者固守男性優勢地位的假定,斷言女性弱于男性,宣稱女性對男性的從屬是有益的或適宜的,排除女性能夠成為“知識主體”的可能性。為了跳出學術研究中男性偏好的藩籬,當代諸多女性主義者試圖通過對“性別”這一研究變量的引入和強調,來發出女性自己的不同聲音,建構女性自身的理論話語,從而一改諸多學科中所存在的那種視男性及其相關議題為唯一正統與標準的偏狹。①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伊蓮·肖沃爾特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重審西方文學價值觀的“經典化”過程。……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名作欣賞(2021年24期)2021-08-30 07:02:24
南大法學(2021年3期)2021-08-13 09:22:32
阿來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 07:39:04
中國自行車(2018年9期)2018-10-13 06:17:10
文學教育(2016年27期)2016-02-28 02:35:09
金色年華(2016年13期)2016-02-28 01:43:27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4期)2015-06-23 08:50:19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6期)2015-01-22 07:22:22
語文知識(2014年7期)2014-02-28 22:00:18
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學術沙龍輯錄(2011年0期)2011-10-27 02: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