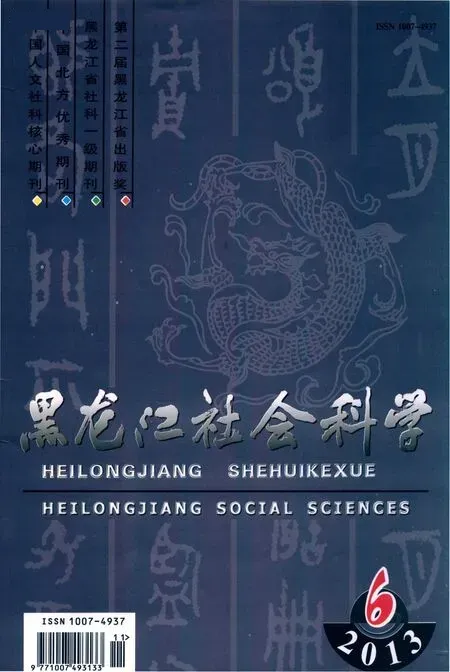近十年來“儒墨關系”問題研究綜述
2013-04-11 05:58:59薛柏成
黑龍江社會科學
2013年6期
薛柏成
(吉林師范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吉林四平136000)
儒墨兩家學說同是戰國顯學,聲勢浩大,兩家之間不僅是對立、攻擊,還有互相影響和相互吸收。儒家學說的興盛并不僅僅是靠其本身的優越性,而是吸收了包括墨家學說在內的道家、法家等先秦諸家的學說。唐代韓愈首次明確提出:“孔墨相用”。明清學者李贄、焦竑、顏元、汪中、孫詒讓等也認為“儒墨相用”[1]。近現代以來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魯迅等人偏重于墨家科學與人文精神的探討與實踐,以墨釋儒[2]。但近年來,學術界在儒墨關系這一問題上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比較儒墨異同等方面上,而探討二者之間聯系的論述較少。專門研究“儒墨互補”的著作更是空白,有代表性的文章也僅有10篇左右,下面僅就近十年來學術界“儒墨互補”的研究情況作一簡要評述。
一、儒墨思想比較研究現狀
1.儒墨哲學思想比較研究
儒墨兩家都有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對兩者的比較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趙馥潔從儒墨兩家價值觀方面分析認為“儒家崇尚仁義道德之價值,倡言‘義以為上’‘義然后取’,而墨家卻‘貴兼’(《尸子·廣澤》),‘泛愛兼利而非斗’(《莊子·天下》),‘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荀子·非十二子》)。一言以蔽之,儒家崇尚道德,墨家弘揚功利,以功利為基本價值是墨家價值觀的根本特征。”在價值實現與生命歷程的融通這個哲學命題上,他認為:“墨家和儒家都認為人除了重視生命之外,還應重視社會道義價值。……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4期)2022-06-15 03:23:36
華人時刊(2022年7期)2022-06-05 07:33:26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當代陜西(2021年13期)2021-08-06 09:24:34
原道(2019年2期)2019-11-03 09:15:12
人大建設(2019年4期)2019-07-13 05:43:08
當代陜西(2019年12期)2019-07-12 09:11:50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天府新論(2015年2期)2015-02-28 16:4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