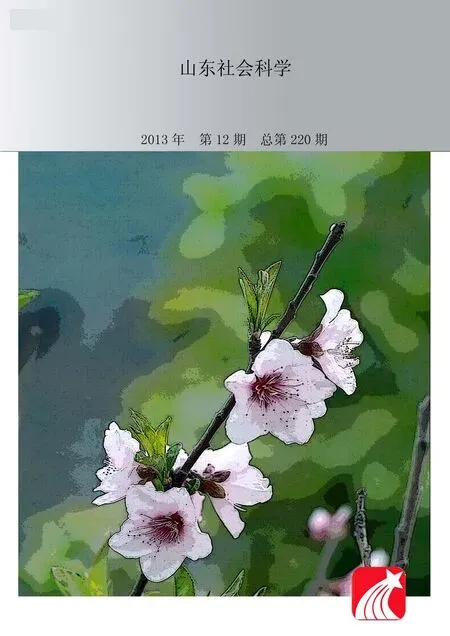大革命時(shí)代的“中間體”觀念與政治自由
張夏子
(浙江大學(xué) 光華法學(xué)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眾所周知,在法國大革命的目標(biāo)中,除了反對君權(quán)和教權(quán)外,還包括了摧毀包括行會(huì)在內(nèi)的享有特權(quán)的中間組織,它們泛指介于國家和個(gè)人之間的各種社會(huì)或政治形態(tài),如協(xié)會(huì)、行會(huì)、工會(huì)、政黨、地方政府、民間的各種自治組織等, 本文稱之為“中間體”,是借用了法國當(dāng)代學(xué)者皮埃爾·羅桑瓦龍先生的說法。①[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引言第13頁。
正是這個(gè)“中間體”,尤其行會(huì)組織,在法國大革命時(shí)期可謂命運(yùn)多舛。1791年6月14日,勒沙普里埃在廢除行會(huì)的法律草案辯論中,對其有這樣的描述:“國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行會(huì)。除個(gè)人特殊利益與整體利益外,不存在其他利益。任何人不得以中間利益之思想迷惑公民,不得以行會(huì)之精神使公民與公家相分離。”②勒沙普里埃在1791年6月14日頒布了禁止同行業(yè)集會(huì)和結(jié)社的法律,簡稱勒沙普里埃法。[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8頁。不僅是行會(huì),在人們眼里“所有協(xié)會(huì),無論其種類為何,在國家生活中都始終是危險(xiǎn)的”③[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82頁。。無怪乎大革命的重要任務(wù)之一便是消滅一切行會(huì)的存在,以保證“公共利益支配個(gè)人利益”④[法]西耶斯:《論特權(quán) 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第80頁。,所有被羅桑瓦龍稱為“中間體”的社會(huì)存在都被視為“哥特式的余孽”和“社會(huì)分裂的威脅”。那么,為什么“中間體”在大革命時(shí)期被近乎全盤否定呢?被否定的根源何在呢?
羅桑瓦龍?jiān)诤艽蟪潭壬习研袝?huì)被廢除的原因歸結(jié)為“雅各賓政治文化”,國內(nèi)學(xué)者樂啟良在該判斷的基礎(chǔ)上把這一原因歸結(jié)為法國盧梭的“絕對主權(quán)”觀念⑤樂啟良:《法國大革命與結(jié)社自由的遺產(chǎn)》,《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而遍覽《舊制度與大革命》,筆者以為,除了文化和觀念上的因素外,托克維爾關(guān)于行會(huì)問題的分析頗有洞見。他通過對革命前法國社會(huì)的研究,將行會(huì)制度的興衰與政治自由有無聯(lián)系了起來。他認(rèn)為是君主專制導(dǎo)致了行會(huì)利己主義,要想將行會(huì)從封閉與利己之中解救出來,需要的是政治自由。“16世紀(jì),我剛才提到的行會(huì)大多數(shù)就已存在,但其成員在處理好他們各自聯(lián)合會(huì)的事務(wù)以外,不斷地與所有其他居民相聚,以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在18世紀(jì),他們差不多完全閉關(guān)自守,因?yàn)橛嘘P(guān)市政生活的活動(dòng)已漸稀少,并且全由受委托人代理。因此,每一個(gè)小團(tuán)體都只圖私利,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⑥[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136頁。正是公共生活被君主專制取代和市政生活的減少,導(dǎo)致了團(tuán)體的個(gè)人主義,而行會(huì)對小團(tuán)體利益的關(guān)注,使得人們往往將其與特權(quán)、不平等、壟斷等特征聯(lián)系起來。可見,行會(huì)公用精神的減少根源于“政治自由的毀滅”。因此,“敗壞了的”中間體逐漸喪失了其原本具有的優(yōu)點(diǎn),留給人們的只是它極具危害的特征且常常被放大,以至于被視為與普遍利益相對立的特殊利益而遭人們拋棄。由此,托克維爾在政治自由和法國人對中間體的評價(jià)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
一、“中間體”的兩個(gè)面向
在托克維爾看來,政治自由的喪失對中間體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它導(dǎo)致了團(tuán)體個(gè)人主義風(fēng)氣。這種只顧自身利益的“敗壞”風(fēng)氣,阻斷了相互競爭的團(tuán)體通過公共平臺進(jìn)行商談、合作的可能性。在集權(quán)官僚體制背景下,腐敗、壟斷、團(tuán)體特權(quán)等現(xiàn)象會(huì)出現(xiàn)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它使各種社團(tuán)的利益訴求不得不訴諸于更為激烈的手段。這樣一來,中間體既呈現(xiàn)了守舊(特權(quán))又呈現(xiàn)了激進(jìn)(革命)的兩個(gè)面向,導(dǎo)致了人們對于中間體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前者以極端保皇派為代表,他們極力維護(hù)中間體的特權(quán);后者以社會(huì)主義者為代表,依靠中間體的激進(jìn)行動(dòng)來爭取政治權(quán)利;前者所維護(hù)的恰恰是后者要摧毀的。盡管在革命后的很長時(shí)期內(nèi),現(xiàn)實(shí)對中間體的需要也很強(qiáng)烈,但是1810年刑法典第291條規(guī)定禁止結(jié)社,在1834年對第291條作了更加嚴(yán)格的闡釋[注]樂啟良:《近代法國結(jié)社觀念》,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頁。。本本上的規(guī)定與實(shí)踐分道揚(yáng)鑣,中間體處于兩難境地。這種兩難,通過極端保皇派和社會(huì)主義者的不同主張與行動(dòng)而顯得更加復(fù)雜。
一方面,極端保皇派主張恢復(fù)中間體。 一是因?yàn)樾袠I(yè)的混亂給秩序帶來了威脅。重建行會(huì)不僅僅是為了方便行業(yè)管理,更重要的是行會(huì)的分散治安機(jī)制被認(rèn)為比公共治安更高效。二是因?yàn)闃O端保守分子當(dāng)時(shí)也懷有現(xiàn)實(shí)的政治斗爭的目的。“他們因?yàn)檫h(yuǎn)離權(quán)力,因?yàn)椴辉缚吹阶约罕恍路▏慕ㄔO(shè)進(jìn)程拒之門外才越發(fā)支持地方分權(quán)。”[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29頁。當(dāng)時(shí)還是年輕議員的維萊爾在議會(huì)掀起首次辯論,他指出:“當(dāng)我們和地方行政機(jī)關(guān)的利益聯(lián)系被抹殺……我們的公共精神也就被破壞,我們就最終使民族分崩離析、道德敗壞,最終把一個(gè)個(gè)的法國人相互隔離開。”[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29頁。用他的話說,地方行政機(jī)關(guān)存在的目的,就是讓一個(gè)迷失了方向的國家“重組為人民的集體”[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29頁。。可見,重建行會(huì),分權(quán)于地方,是極端保皇派尋找的一條走出個(gè)人主義的自私自利并形成公共精神的出路。他們的主張因?yàn)榻⒃趯Υ蟾锩瓌t的拒絕和否定之上,實(shí)際上是企圖重建特權(quán)團(tuán)體,所以其提出來的所謂“診治”個(gè)人主義“病癥”,不過是對“民主社會(huì)”的否定。及至復(fù)辟時(shí)期,在極端保皇派的行會(huì)重建運(yùn)動(dòng)被貼上擬古、迂腐或是懷舊的標(biāo)簽時(shí),維萊爾及其同仁則對行會(huì)的復(fù)興、宗教與傳統(tǒng)主義風(fēng)俗卻大加贊賞,很多政論家都在辯護(hù)恢復(fù)這種帶有君主制色彩的制度的好處,試圖找回君主制思想。[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43頁。
在保皇派捍衛(wèi)行會(huì)的時(shí)候,法國的下層民眾則用自己的行動(dòng)表達(dá)了對中間體的看法。在19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的工人協(xié)會(huì)試圖以集體行動(dòng)的方式來拯救大革命之后的個(gè)人主義,尋求政治權(quán)利,企圖通過中間體來擺脫“局外人”的身份。因此,此時(shí)的“工人協(xié)會(huì)問題不再是簡單的社會(huì)或社會(huì)學(xué)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43頁。。1831年震驚世界的法國里昂工人起義在工人運(yùn)動(dòng)史上被譽(yù)為工人階級開始成為獨(dú)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可見,極端保皇派與社會(huì)主義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重建中間體的問題,并引起了當(dāng)時(shí)資產(chǎn)階級的掌權(quán)者對可能的復(fù)辟和革命的憂慮。極端保皇派在民主的共識之中日漸式微,而革命的激進(jìn)傾向在各種社會(huì)團(tuán)體中愈演愈烈。由于統(tǒng)治者受自身利益的局限,無法理解中間體兩種極端面向根源于政治自由的缺失,鎮(zhèn)壓和瓦解中間體自然成為他們的選擇,以此重建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為中央集權(quán)套上了議會(huì)制的外觀。由于對混亂的恐懼,政治自由被局限在狹隘的范圍之內(nèi),形成了一種新的顯貴政治。因此,雖然如何在專制與革命之間尋找出路是19世紀(jì)30年代以來法國理論家們討論的主題,但由于對中間體和政治自由以及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缺乏認(rèn)識,使得他們始終無法逃脫專制和革命的怪圈。對空論派與1848年革命的梳理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點(diǎn)。
二、空論派與集權(quán)的代議制
“在19世紀(jì)的法國,逐步常態(tài)化的‘例外時(shí)局’和傳統(tǒng)的對協(xié)會(huì)的理論排斥共同造就了協(xié)會(huì)的命運(yùn),我們很難將這兩者分開。”[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59頁。這是羅桑瓦龍對19世紀(jì)為何中間體會(huì)屢屢在政治實(shí)踐中受阻的洞見。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法國歷史中一個(gè)悖論式的現(xiàn)象:掌權(quán)者往往是從一個(gè)政治團(tuán)體發(fā)展而來,一旦他們掌權(quán)之后卻開始排除和壓制中間體。時(shí)局與理論的混淆構(gòu)成了這種怪相,基佐便是這一政治時(shí)局與特殊觀念混淆的典型例證。[注]基佐在七月革命剛剛結(jié)束時(shí)稱刑法典第291條是“惡法”,而在不久以后,“例外時(shí)局”的看法便占據(jù)和毒害了他對現(xiàn)實(shí)的看法。參見[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沈菲、梁爽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59頁,注2。
“整個(gè)19世紀(jì)的法國之所以對中間體充滿疑慮,對混亂的恐懼起了決定性作用。”[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55頁。當(dāng)時(shí)的空論派猶如驚弓之鳥,希望廢除所有令人膽戰(zhàn)心驚的中間體。在針對1834年法律是否對協(xié)會(huì)性質(zhì)加以區(qū)分的態(tài)度上,議員們更是堅(jiān)決地表態(tài):“應(yīng)該把它們?nèi)珨?shù)取締”,否則“那些最危險(xiǎn)的協(xié)會(huì)也能輕松逃脫法律的限制”[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57頁。。空論派代表人物基佐說出了多數(shù)當(dāng)政者的心聲,將當(dāng)時(shí)的大政簡化為如下的表述:“保障良民的安全,先生們,這就是政府的原則所在。這就是為什么協(xié)會(huì)在我們眼里是重大的威脅。”他甚至進(jìn)一步恫嚇道:“我們不能等到那些協(xié)會(huì)做下不法的勾當(dāng)(再行動(dòng)),我們現(xiàn)在就取締他們以防不測。”[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58頁。從空論派對協(xié)會(huì)等中間體的極端恐懼中,可以看到他們將中間體問題的實(shí)質(zhì)與時(shí)局的因素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也隱約可以在“保障良民安全”的政府原則中窺見到“資產(chǎn)階級秩序的確立在這里成了雅各賓派世界觀的一種延續(xù)”[注][法]皮埃爾·羅桑瓦龍:《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huì)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高振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58頁。。
政治秩序的混亂使空論派對中間體持否定態(tài)度,而其代表人物基佐的早期理論卻把中間體與“前民主時(shí)代”相聯(lián)系,把中間體視為人們在前民主時(shí)代追求解放的手段,并因此認(rèn)為中間體的存在與民主時(shí)代的普遍性要求不相符。可見,政治局勢并非基佐否定中間體的全部原因,中間體與舊貴族特權(quán)和特殊利益的聯(lián)系可能也是一個(gè)原因。可見,基佐的理論體現(xiàn)了對上述中間體的兩個(gè)面向的拒斥。因此他以他的方式繼承并重組了之前基于這兩種批判而形成的關(guān)于政治制度的概念:“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區(qū)分與中央集權(quán)制[注]西耶斯在進(jìn)行這樣的區(qū)分時(shí)同樣受到傳統(tǒng)政治理性主義的影響。。不過他用政治民主和社會(huì)民主的區(qū)分與理性主權(quán)重新粉飾和融合了它們,并用代議制把政治和社會(huì)聯(lián)系起來,使其成為表達(dá)理性——普遍性——的機(jī)構(gòu),并把理性與自由和中央集權(quán)相聯(lián)系以調(diào)和自由和中央集權(quán)之間的矛盾,構(gòu)建了一種可以稱之為“代議制的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形式。他將政治自由局限于議會(huì)之內(nèi),用代議制替代中間體的功能。代議制也因此成為了基佐理論中的重中之重,表達(dá)了一切可欲的價(jià)值。但是,理性的標(biāo)準(zhǔn)畢竟虛無縹緲,最終財(cái)產(chǎn)標(biāo)準(zhǔn)依舊成為獲得政治權(quán)利的標(biāo)準(zhǔn)。一小部分金錢貴族和一大部分作為“無產(chǎn)者”的工人的出現(xiàn)似乎重現(xiàn)了1789年前的社會(huì)狀態(tài)。
最終代議制發(fā)生了扭曲[注]關(guān)于代議制扭曲的原因可參見[法]喬治·杜比主編,《法國史》(中卷),呂一民、沈堅(jiān)、黃艷紅等譯,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第949頁。,政治自由在社會(huì)中的缺席使無產(chǎn)者與新貴族產(chǎn)生了隔離、對立的情緒,并最終在1848年徹底激化。托克維爾在二月革命后給西尼奧爾的信中總結(jié)了革命的根本原因,他說:“這場革命總體性的、真實(shí)的原因在于一種可憎的精神,在整個(gè)王朝期間它都一直是政府的動(dòng)力所在,這就是欺騙、卑劣和腐敗的思想,它煽動(dòng)并敗壞了中產(chǎn)階級,使它完全喪失了政治見解力,而提供給它的則是一種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是如此愚蠢,以致中產(chǎn)階級到最后完全與產(chǎn)生它的人民分離了,它讓人民任由別人去指引,而所有這些人都以幫助被拋棄的人民為借口,把那些錯(cuò)誤的思想裝進(jìn)人民的頭腦中。”[注][法]托克維爾:《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黃艷紅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153頁。托克維爾認(rèn)為七月王朝的政治權(quán)力長期被顯貴們掌握,在政治生活中也就不可能存在政治沖突,也無法引起真正的政治辯論,這使得中產(chǎn)階級中間產(chǎn)生了廣泛的政治冷漠癥而逐漸忘卻了政治生活。因此,“對于民族的其他階層來說,這個(gè)階級逐步變成了一個(gè)腐敗的、庸俗的狹隘貴族階級,由它來領(lǐng)導(dǎo)似乎是件可恥的事”[注]參見[法]托克維爾:《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黃艷紅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153頁,注釋1。。對中間體的遺棄伴隨著對政治自由的剝奪,而政治自由的喪失又導(dǎo)致了代議制(事實(shí)上可視其為一種官方的中間體)的敗壞,這似乎隱約預(yù)示了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聯(lián)系,而革命的重現(xiàn)也告訴我們應(yīng)該重視這種聯(lián)系的重要性。
三、托克維爾的“中間體”觀念與法國的困境
在民主政治社會(huì)的“常規(guī)政治”狀態(tài)中,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中央集權(quán)化過程與個(gè)人主義化過程之所以會(huì)引起法國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產(chǎn)生憂慮的原因,也是民主內(nèi)部存在的悖論。托克維爾高瞻遠(yuǎn)矚之處在于他認(rèn)為人的個(gè)體性和個(gè)人自由只有在政治自由中才能實(shí)現(xiàn)和保全,也只有通過對政治自由的追求和體驗(yàn),人們才能逐漸培養(yǎng)出自由習(xí)性,真正熱愛自由,并為了自由而去追求自由。他不僅僅把政治自由理解為代議制或是選舉權(quán),還把它理解為地方分權(quán)、政治結(jié)社的自由等等。他強(qiáng)調(diào)實(shí)實(shí)在在的對公共事務(wù)的參與過程,而不論事情大小。因此,在他的觀念中,中間體與政治自由二者是息息相關(guān)的。因?yàn)榈胤叫姓淖杂珊徒Y(jié)社的自由可以為人們提供必要的商談和合作的場所并促進(jìn)他們對政治生活的熱愛,促進(jìn)培養(yǎng)人們的自由習(xí)性和政治美德。這樣,一方面使人們能夠超越利己主義并正確理解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養(yǎng)成公共德性;另一方面也能增強(qiáng)人們的獨(dú)立性以抵抗中央權(quán)力的侵犯。由此,中央集權(quán)化與個(gè)人主義化這對在民主政治中一體兩面的敗壞傾向才能得以糾正。我們可以從托克維爾為法國民主問題提供的解決方案中看到,政治自由不僅意味著政治權(quán)利,它還是培養(yǎng)和維持人們自由習(xí)性和公共美德的基礎(chǔ)。而中間體則是人們實(shí)現(xiàn)和培養(yǎng)這種種美德和習(xí)性的必要場所。因此,政治自由和中間體在各自發(fā)揮其應(yīng)有作用時(shí)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何以對法國的未來如此悲觀。[注]對這種悲觀情緒的分析參見[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第215頁。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的困境在于政治自由與中間體這兩個(gè)原本相輔相成的事物在法國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和政治社會(huì)史中完全被分離,且在分離過程中發(fā)生了“異化”。由于政治自由的缺失,中間體出現(xiàn)了敗壞和消極影響,不僅在革命時(shí)甚至在革命后還表現(xiàn)出激進(jìn)的革命傾向,從而不斷地遭受到限制和壓制。在中間體被抑制的過程中,政治自由也逐漸成為統(tǒng)治者的專利,同時(shí),人們從追求政治自由墮落到僅僅滿足個(gè)人對自由的要求,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的,人們尤其是統(tǒng)治階級開始變得腐敗和庸俗,自由習(xí)性和公共美德消失殆盡。最終在革命中以政治權(quán)利之名確立的普選權(quán)也不過只是滿足了人們對政治平等的追求而已。可見,對中間體的拒絕和政治自由的衰敗呈現(xiàn)出一種惡性“循環(huán)”,并被空論派的理論所吸收。如何使它們正確地被人們所認(rèn)識并重新培養(yǎng)人們的自由精神或許就是托克維爾在尋找改革之道時(shí)所面臨的問題。托克維爾對中間體獨(dú)到而全面的理解與法國的歷史經(jīng)歷向我們展現(xiàn)了政治自由和中間體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也讓我們認(rèn)識到對它們的正確認(rèn)識在現(xiàn)代民主建設(shè)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