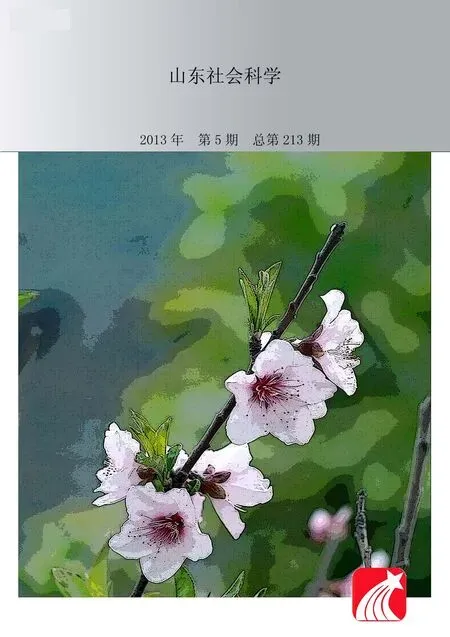瘋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與魯迅作品的“黑暗世界”
陳相因
(臺灣“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所,臺北 115)
一、果戈理與魯迅的文學關系
1933年,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自述,在寫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前從未看過小說作法的理論書籍。完成小說集《吶喊》的最大助因,魯迅認為,主要是自己寫作前曾大量地搜尋、關注并閱讀外國短篇小說、文學史和文藝批評等類別的作品。注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頁。下文涉及《魯迅全集》皆使用此版本,他版則另注。美國學者韓南 (Patrick Hanan) 的研究指出,這些搜尋、閱讀,甚至是翻譯外國文學,尤其是俄羅斯與東歐作品的過程,絕大部分是魯迅在1906年到1909年居留于東京期間所完成的。見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18.“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魯迅說,“是俄國的果戈理 (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 (H. Sienkiewitz)”。注魯迅:《我怎么作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25頁。后來,魯迅負責編選叢書《中國新文學大系》里的《小說二集》,在其序中以編者的身份,說明自己創作幾篇短篇小說背后的靈感與思想來源: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也早借了蘇魯支 (Zarathustra) 的嘴,注即今日較常見的譯名《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一書的主角,為古波斯祆教 (Zoroastrianism) 的創始人。徐梵澄根據英譯名Zoroaster譯為蘇魯支,見徐梵澄譯:《蘇魯支語錄》(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盡管魯迅將最初此書譯為《察羅堵斯德羅緒言》,但僅譯了第一卷前三小節,后囑徐梵澄將全書四卷譯出,交鄭振鐸出版,故此處應是采用這一版本的譯名。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哪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 (L. Andreev)[注]Л. Андреев(1871-1919),較常見的譯名為安德烈夫或安德烈耶夫。式的陰冷。[注]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46-247頁。
上文中,魯迅點名并暗示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與安特萊夫的陰冷風格,以及他所能理解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的進化論觀點,三者在其創作小說的過程中具有啟發性。隨著魯迅的自承不諱,其弟周作人與不少研究者紛紛論述:魯迅的小說集與上述幾位外國作家的某些特定作品,在體裁、內容、情節、主旨、技巧與角色的設定上,皆可找到相互對應或相符呼應的顯著痕跡。[注]直陳這一影響論點的各家研究甚豐。舉例而言,周作人在《魯迅的文學修養》論及,給予魯迅影響的第一個外國作家,要屬果戈理,關于這點魯迅自己大概也承認。見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滄桑——兄弟憶魯迅(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頁。美國的韓南與李歐梵、俄蘇的謝曼諾夫(В. И. Семанов)與日本的藤井省三等人,亦曾論證這些外國作家給予魯迅的影響。在幾篇關于魯迅的文章中,周作人回憶早年魯迅的外國文學閱讀史,更進一步解釋與詮釋魯迅的作品與思想如何受到這些作家與哲學家的影響。[注]周作人:《關于魯迅》與《關于魯迅之二》,收入止庵編:《周作人集》下冊,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604-623頁。一些學者如韓南與李歐梵等,除了鉤沉魯迅如何藉由閱讀、認同、喜愛、模仿這些外國作品,到有意識地借鑒、介入或干擾了自身創作的歷程,進而呈現出其作品里多種語言(中、德與日語)駁雜和多種文本交沓的互文性現象。除此之外,這些學者更回溯了魯迅所承繼的中國古典文學遺產,勾勒出他如何融合或并置舊與新的雙重文體(文言文與白話文)、轉化古意而超越傳統,而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注入新意。[注]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p. 217-244;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然而,較少研究論述的是,串起魯迅與果戈理、顯克微支、尼采和安特萊夫的紐帶,并非僅是認同外國作家的某一作品,進而啟發自我創作的單純關系,也不完全只因借鑒模仿而帶來的沖擊影響,更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某一層面上純粹的供需問題;譬如,直指作家生平與各時期的經濟狀況,就斷定其創作動機。事實上,魯迅與這些外國作家的寫作動機、哲學思考與個人世界從來就無法歸類為單純、單一而簡單的性質。他們的作品時常描繪人性在人際關系的互動中展演著多重面貌的變化,常見的手法就是在內在情境(自我想象、幻想、妄想或夢想)與外在環境(現實、宗法與體制等等)交逼沖突而生的錯綜混亂里,展開在心智上矛盾命題的層層詰難,且緊扣與著力于五四作家普遍認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人道主義——對人類殫精竭慮卻未知的靈魂深處與非理性力量無窮盡地追問、探索,并對俗成的禮制與理性的規范無時無刻地存疑、批判。
在魯迅與果戈理、顯克微支、尼采和安特萊夫的作品中,一些用“理智”(在這些中外作家的文本里常被暗喻為正常、光亮或白晝的化身)無法得悉的激烈情感、孤獨性格與危險心靈,如果挪借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專有詞語,即是“以一種手勢作為排拒措施 ”[注]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4.中譯本參考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把這些不屬于理性的論調劃入了神秘的宗教觀、異端的無神論,或者是“瘋狂”。莫楚爾斯基 (К. Мочульский) 與夏濟安先后評價果戈理與魯迅時,則分別將這些精神現象稱之為“黑夜意識”[注]Мочульский К. Гоголь. Соловье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С. 49.與開啟“黑暗閘門”[注]Tsi-An Hsia,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p. 101-145.的界限。正是這些在當時無法以上述作家同時代人們的“理智”所能解釋的激烈情感、孤獨性格與“危險”心靈,較于微觀角度下外顯的文學關系與學習行為的聯系,更能牢固地串聯起魯迅與果戈理、顯克微支、尼采和安特萊夫之間的共同點。在這些作家中,特別是果戈理與魯迅,對于宏觀世界具有十分相似的內在感知 ,在寫作時皆易受中俄評論家所謂“黑夜”或“黑暗”的靈感召喚,筆者將兩者歸類統稱為“黑暗意識”。由此論述,我們不禁要問:此一內在感知與黑暗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又以何種形式、主題、象征、面貌或化身表現在這兩位中俄作家的文本里?其共通或迥異之處何在?果戈理與魯迅之間的關系和其作品的異同又能夠說明什么?最后,在中俄小說發展的過程里,此種特征又扮演著何種角色與地位?
二、“瘋狂”與“黑暗意識”的連結
幾乎所有研究魯迅或果戈理者皆無法不去注意,“瘋狂”的主題對其創作所顯示的意義與重要性。原因不外類屬于“瘋狂”的用字遣詞、變體化身、氛圍營造、角色設計、行為勾勒、心理描述、事件串連與情節鋪陳等……種種的文學成分,頻繁地出現在他們的小說里。同時,這些關于瘋狂的文學因素,往往與小說中“黑暗”的異端意象與“非理性”的偏激情緒或極端情感連結。然而,“瘋狂”、“黑暗”與“非理性”這三個相關主題在文本中鏈接時,卻顯現出似疏似緊、時近時遠的特性。我們可以看到,有時作者將一些看似毫無關系的事件串連起以上三個主題時,由于缺乏外顯而直接的連結關系,導致讀者產生無法解讀、常態所不能解釋與邏輯難以連貫的讀后感。但是,作家再現的現象又讓我們確信,以上三者不但“珠胎暗結”且盤根錯節,還常和諧地并置共處。在下文的分析里,我們可以看到,果戈理與魯迅對這三個相關主題的安排與處理,不但承繼了傳統與古典的韻味,同時,在兩人各自處于俄國與中國漸受歐化威脅、西化派與傳統勢力分庭抗禮之際,在小說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文藝體裁的青黃年代(前者1830-1840年,后者1910-1920年)里,其二人作品適時地符合了十九至二十世紀前半葉,俄國文藝評論家時常強調的小說的創新元素:自然 、偶然與非典型。本論文主要專注于果戈理與魯迅,然而兩位作家諸多作品涉及“黑暗意識”,文本脈絡呈現的意義豐富且內涵深廣,限于篇幅,僅可針對這兩位中俄作家作品中可能形成此意識的來源及其幾樣重要特征做粗淺的比較。藉由列舉并對照這兩位作家的類似文本,以歸納特性、提出問題與剖析現象。
王德威教授將魯迅文本里咸認的“正”、“負”面價值觀視為一條模糊的界線,認為“瘋狂與理性、禮教與吃人、革命與封建等種種名目,看似涇渭分明,實則飄浮雜沓,難以廓清”[注]王德威:《眾聲喧嘩》,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沿此觀點深入,我認為將“瘋狂”、“黑暗”與“非理性”的相關主題與(或)所列的種種相對名目,做同時性的并存,使相關者出現異化 、相對者產生矛盾,故而造成每一層次上真假混雜——現實與虛幻交替更迭、內在情境與外在環境相互作用的處理手法——正是果戈理與魯迅表現所謂的“人道主義”的高明寫作策略與共通之處,并由此預留空間給讀者與學者思考、詮釋和探討。一般常見對魯迅《狂人日記》所下的評論——“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注]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47頁。所做的引伸,簡化了《狂人日記》在構成元素與形式架構里所具有的高度復雜性,并不足以說明這篇作品在文學史與思想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與意義,并指向其背后的時代意義。
在針對中俄文本的《狂人日記》,就其中所呈現真假摻和,與明暗交錯的層次現象展開更復雜的論證之前,讓我們首先來看一段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注]《古典時代瘋狂史》的第一部后經傅柯刪節、增補和修訂后,集結成為另一本書《瘋狂與文明》,其英譯本為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其法文原文與中、英譯本的不同版本及其當中的差異,可詳見林志明:《譯者導言:傅柯Double》,收入《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頁V-LXIV。中對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巴洛克時代的歐洲文學作品里多次出現瘋狂形象的節錄:
這種藝術,努力尋求掌握一個自我追尋的理性,它認識到瘋狂的存在,也認識到它自己的瘋狂,把它圈圍起來,又侵入其中,最后將它征服。[注]《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英譯本則刪節了此段敘述。
瘋狂被人操縱宰制,卻仍維持著它表面上的主宰權。它現在是理性的工具和真理工作的一部份。在萬物的外表和日光的閃爍之中,它玩弄著表象的所有把戲,玩弄著真實和幻象間的曖昧,玩弄著真理和表象間毫無限定、永被重復、永被打斷的分合脈絡。它既隱藏又顯現,它同時說著真話和謊言,既是陰影又是亮光。[注]Michel Fouca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32;《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頁。
這一敘述總結了傅柯發現的:歐洲作家群或作品,如《唐·吉訶德》、斯居德里的小說、《李爾王》、羅突或是隱者特里斯坦的戲劇,是如何體驗、認同與再現人物的瘋狂。[注]Michel Fouca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25-31;《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0頁。這一主題下所表現的幾項形式特征,像是現實與幻覺交雜、真理與謊言互滲,或是黑暗與明亮交錯等等,正如果戈理和魯迅筆下多種相關與相對的元素和特質,同時性并置是如此具有雙重性、多面性與多變性,且緊扣著時代、理性,抑或后來被傅柯改稱為“文明”的發展狀態。
《古典時代瘋狂史》一書內容主要以歐洲精神醫院的歷時發展和內部監禁的“瘋子”為研究對象,來探索其瘋狂精神與生存狀態,進而論述這些存在的現象。對傅柯而言,監禁的意義在于控制和管理、懲戒與矯正,其作用在導向馴化的目的和結果。在此書的全文脈絡下,所謂的“馴化” 若以文藝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則是一種近似、或重迭于“理性化”、“正常化”和“社會化”的范疇。傅柯先敘述不同時代里,歐洲的不同社會與文化對于“瘋狂”這一疾病概念的歷時性發展,并觀察到相對于瘋狂的一個所謂“正常的”或“平均的狀態、規范、模式”,如果沿時間軸線開展來看,其定義遠非固定不變。換句話說,變的是人類對瘋狂的知識與認定。
傅柯繼而提出質疑并展開論述,強調且批判自十八世紀末期以來,“瘋狂”被建構為一種心智疾病,處在道德性排拒的空間里,被視為社會邊緣性的存在,同時被歸類為一種被社會隔離、被正常排除、被理智宰制的結構。這一結構無疑地長期被忽略,更因無法以理性言說自我以成為主體,因此被排擠且納入了異質單元——“他者”,最終“消失無蹤”。傅柯說明,這部“瘋狂史”的進行并非為“瘋狂”這個語言寫史,而是為“此一沉默的考古”。[注]林志明:《譯者導言:傅柯Double》,收入《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頁XLV、頁XI。但也由于這種沉默較少也較難表現在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上,故被傅柯稱之為“瘋狂便是作品的缺席”。[注]林志明:《譯者導言:傅柯Double》,收入《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頁XLV、頁XI。正因為“瘋狂”這一主題在果戈理與魯迅之前的俄國與中國文學作品極為罕見,誠如傅柯所指的“沉默”,所以在眾聲喧嘩、吵雜的變動時代里,以瘋子為主角的兩篇《狂人日記》的產生與出現,反而更顯與眾不同。
若沿傅柯對“瘋狂”歷史的論證角度來看中俄《狂人日記》兩文本,兩作品的出版期間,一為1833年,另一為1918年,正值兩國分別面對歐洲十八世紀以降“理性”與“科學”主導而興起國際間強權與帝國的挑戰。果戈理與魯迅同以日記為形式,兩位瘋狂的文人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與主角,同在彰顯時代變遷中“他”強“我”弱、他“明”我“暗”、他“大”我“小”的生存窘境。兩文本中的“他者”,除了意指狂人主體之外的人,更暗指當時不容狂人的兩國社會,進而含沙射影地包涵他國,將歷史脈絡分別從19、20世紀的中俄社會向外擴展成為將“理性”與“科學”視為“普世價值”的國際社會,發展的競爭與潮流是如此不容弱者。因此,不被理解的弱者必須既怪異又瘋狂,連狗都瞧不起他們,正因見不得人所以無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正當生活,否則只是面對一連串他者的嘲笑與奚落。狂人只能在月光皎潔的黑夜中茍活,以日記抒發情緒。兩作家同將此主題與多種層次、多重意義與多方意象連結,但是果戈理著墨更多的是對一心追求歐化文明的城市圣彼得堡所發展出來的奇怪現象提出質疑,而魯迅則專注于對一直恪守中國文明的小城所擁有的怪異習氣提出批判。前者是因俄羅斯歐化而顯怪誕離奇,后者卻因歐化入侵但中國卻不改變而變得瘋狂怪異。俄國狂人進入精神病院的結局是作者以“瘋狂”對歐洲文明的“理性”無止盡地嘲笑,而中國狂人最終卻回歸了對中國傳統文明的馴化,是魯迅對舊體制“理性”(抑或非“理性”?)強烈地批判。但不論是果戈理還是魯迅,不管認不認同歐化的“理性”或“科學”,中俄兩篇《狂人日記》都顯示了作者對于“他”強“我”弱、他“明”我“暗”、他“大”我“小”的時代洪流下,弱小文人無力回天抱持著同情卻又無可奈何的態度與心理。
除了兩篇《狂人日記》外,果戈理的《彼得堡中篇小說集》與魯迅的《吶喊》和《彷徨》等小說中不斷地重復探討一系列“瘋狂”、“文明”與“馴化”之間關系的群組和主題,兩位作家對此關懷至深,當中寓意、脈絡、思想與世界觀體系值得再三探究。囿于空間,本文僅能點出“瘋狂”與“黑暗”連結的現象,簡單地分析如何以傅柯視角重新看待果戈理與魯迅,然而關于“瘋狂”、“文明”與“馴化”這一群組,筆者欲另撰專文詳述。緊接著“瘋狂”與“黑暗”兩者的關系,我們要問:在這兩篇《狂人日記》之前,中俄兩位作家與其作品世界里,那些將“黑暗”、“非理性”與“異于常者”劃入“瘋狂”的“手勢”是如何被形成而表達的?藉由傅柯將明暗與真假的多種層次鏈接“瘋狂”的研究視角,啟發我們一窺果戈理和魯迅的“黑暗世界”。同時,本文勘探這兩位作家是否各自繼承了俄國與中國傳統文學遺產,尤以與“黑暗”息息相關之文本為優先考慮的條件。如果真有相關于此類文本的話,那么兩位作家又是如何從中體驗、認識?更如何在吸收之后,轉化并書寫在自己的作品內?這些作品又能否說明有關個人、社會、文化,抑或時代的意義?此外,在果戈理與魯迅的文本對照之下,是否能找出兩者的共通性或差異性,而凸顯中、俄兩國文學的互文性,與各自所代表的獨特性?
三、鬼·神·人的遠航想象與黑暗世界的形成
(一)“夜話”與“鬼話”的“小傳統”:異類、異端與異化的接受
果戈理的早期作品《迪坎卡近鄉夜話》下文皆稱《夜話》)和《和平城》[注]考慮果戈理的創作風格與寫作技巧后,本文決采意譯,以符合作家創作這一中篇小說故事集的目的。坊間不少譯者將此書書名音譯為《密爾戈羅德》或《密爾格拉得》,參見王愛末:《迪坎卡近鄉夜話·導讀》,王愛末譯注,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在處理人類與大自然之間關系的技巧與手法上,雖與魯迅作品相比,其迥異之處比比皆是,但更重要的是兩者在內在感知上共通的部分,尤其以與魯迅那些反映舊時代的“世界觀體系”的作品,如《社戲》、詩集《野草》,及與一些雜文如《女吊》相比時,連結果戈理與魯迅先后分別對“舊俄羅斯”與“舊中國”的相似的感知與認識的正是,誠如莫楚爾斯基與夏濟安針對前后兩者早期作品的研究,不約而同指出的一個相同文題:“來自黑暗的魅惑”。[注]Мочульский К.. Гоголь. Соловье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 48-51;Tsi-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pp. 151-153.
在演變至《彼得堡中篇小說集》的“文明的瘋狂”之前,果戈理的前兩部作品《夜話》和《和平城》主要專注于描繪十四至十六世紀小俄羅斯尚未邁入西化(或民族國家化與現代化)變成大帝國的一部分以前,農村的人們是如何在一天的忙碌后打發夜晚的時間;而在感受黑暗與利用自己豐富的想象力中,勾勒出人類(此處特別指涉斯拉夫民族)與群魔群妖之間的戰斗狀態或和平共處。以上兩部作品在斯拉夫民俗文化的主題中皆具有鬼魅與靈異色彩。
正如多數斯拉夫研究的學者贊同的:《夜話》和《和平城》的烏克蘭民間故事對于果戈理創作《彼得堡中篇小說集》產生了明顯的作用,[注]Храпченко М. Б.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уть величие писателя. М.: Наука, 1993. C. 104-208; Манн Ю. В.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 М.: Вода, 1996. С. 39-53;不少中國文學的研究者亦注意到:中國“小傳統”[注]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5.的書籍,如先秦古籍《山海經》、唐雜俎《酉陽雜俎》、明代神魔小說《西游記》、清代志怪傳奇《聊齋志異》、清代志怪筆記《閱微草堂筆記》和《玉歷鈔傳》等,書中奇幻世界對魯迅在寫作歷程上所具有的重要影響。[注]夏濟安指出,魯迅對他幼年的世界描寫標記著一種對”黑暗之力”的迷戀,是具有啟發性的研究。參見Tsi-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pp. 146-162。沿此看法,李歐梵更將這種黑暗之力的迷戀追溯自魯迅幼年時期喜愛的書籍,包括《山海經》、《酉陽雜俎》、《西游記》和《聊齋志異》等書,見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pp. 4-6。周作人認為,魯迅與《山海經》的關系匪淺,后者使他在了解中國神話傳統上,扎下創作的根,參見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滄桑——兄弟憶魯迅(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頁。《迪坎卡近鄉夜話》全書,顧名思義,主要是以烏克蘭(在十九世紀前半葉有“小俄羅斯”之稱)迪坎卡附近的農村為背景。這地區在十八世紀時曾是反抗壓迫且熱愛自由的哥薩克軍隊聚集之地,在1775年尚未被凱瑟琳大帝解散以前,與所謂代表中央的“大俄羅斯”關系總是若即若離。[注]關于這一部分的歷史與果戈理自己對故鄉小俄羅斯的認識,參見果戈理:《略論小俄羅斯的形成》,《果戈理全集》,《文論卷》第7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2頁。這樣看來,如果李歐梵將上述以神鬼志怪為題材的筆記、傳奇等廣義的小說文類,定義為中國文學“小傳統”的說法成立的話,依其邏輯方式推衍,作為“小俄羅斯文學”代表之一,而且主要描寫民間傳說中各種妖魔鬼怪的《迪坎卡近鄉夜話》,便可說是十九世紀前半葉俄國文學的“小傳統”。在此,套用“小傳統”這一術語來形容果戈理的成名作是具有多重意義的:因為不論是在政治上、地理上、社會上、文化上和歷史上,《迪坎卡近鄉夜話》都扮演著“異質”、“邊緣”和“他者” 的角色。對照比較和綜合歸納上述這些中、俄“小傳統”文學的內容主題、寓意、結局、人物形象、讀者印象,或其他等等作品要素,我們可以發現不少驚人的相似之處。
首先,由內容來看,果戈理的兩卷《夜話》和中國的《酉陽雜俎》、《西游記》、《聊齋志異》(以下簡稱《聊齋》)與《玉歷鈔傳》的故事主題多與降服邪魔歪道相關,并具有怪異色彩和荒誕奇情的情節安排。不論是講述人與人、鬼與鬼,抑或人鬼之間如何爭斗或合作,還是描寫人和鬼都有善惡之別,皆具有貪、嗔、癡、愚、淫的特性等方面,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夜話》里,人物的個性和特質通常透過角色間的雙向或多向對話被突顯出來,鬼的形象描繪尤為鮮明生動。利用對話形式來讓讀者明白,一般人都有懼怕妖魔鬼怪,卻又期待著某種代表善的力量來克服內心恐懼的心理,這個手法與中國的《西游記》和《聊齋》較為接近。舉例而言,《夜話》中《索羅欽西市集》里的紅袍妖怪,猶如《西游記》里豬八戒的化身,其不僅有著豬臉的外貌特征,亦間或發出豬的叫聲驚嚇眾人。不過,雖然同是豬的化身,兩部作品在細部描寫上亦有不同,例如前者拿的是鞭子;后者拿的是耙子,前者來自于地獄,后者來自于天庭,分別代表著邪惡和趨善的形象。
事實上,在《夜話》故事集里可以看出,果戈理相當喜愛用豬這種動物的特征和特性來勾勒妖怪或人的外貌,并藉由其象征懶惰、貪婪和難纏的性格特質。例如,《圣誕節前夕》里的德國專員和亞列斯柯夫村村長,都具有這些外在特征和內在特質。然而,在這些敘述的文字烙下象征的同時,上下文脈絡卻也營造著滑稽詭異和嘲笑諷刺的氛圍。如果戈理筆下的豬不論是人或鬼,多數被人類法治下的階級或是魔法賦予了權力,因此比一般平民百姓更具權勢。然而,在人們驚恐畏懼這些角色的權力或權勢之余,又想象著豬的外征和象征,進而營造出戲謔感。但是,這種感覺又常伴隨一連串緊湊事件的發生而起嬗變 ,或如果戈理專家尤里·曼所用的術語,衍生了多種情感的“變體”。[注]Манн. Ю. В.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Вариации к теме.果戈理描繪這些豬的形象和特質,類似于高家莊時期的豬八戒,而不是跟隨唐三藏后已被點化、渡化與馴化的豬八戒了。
《五月的夜,抑或女落水鬼》里從貓精化身為人的后母,和《聊齋》里常出現的狐精亦可相比,因兩者外貌總是美艷不可方物,膚白似雪。在這篇故事里,被繼母所害的女兒委屈受累,不幸溺水變成水鬼,只能等待機會含冤待雪,這樣的形象在中國的民間傳奇與《聊齋》中亦時有所聞。《失落的信函》里亦出現類似中國鬼怪傳統中的“馬面”,然而其只不過為一妖精,而并未成為陰界閻王的部下。在《夜話》里,也有不少哥薩克農民,甚至是各路妖魔的形象,其既瘋癲胡鬧又貪婪狂妄,且喜歡喝酒玩樂,并善于唱歌跳舞。而《聊齋》里也有不少這類的人物角色,常見的情節鋪排和《夜話》類似,故事常始于主角與妖怪(或是長得像魔鬼的人)共飲,酒酣耳熱或引吭舞劍之際,方能得見之奇聞軼事,如《羅剎海市》、《狐諧》、《黃英》、《馬介甫》和其他等等的故事。
《夜話》與《聊齋》一樣,由其名稱可知,是適合晚上聽的故事。除了時間上表現出人在思緒上理性較為松懈的狀態之外,在星月的空間中也體現了人們對非理性,如愛恨情仇的釋放。有趣的是,從這中俄兩文本的細微之處可以察覺:其在描述非理性的情緒中,皆具有一種特殊的表達形式,即對于外國人或外來者的主體想象展現出奚落嘲笑、戲弄辱罵的語言、態度與行為。例如,《圣誕節前夕》里敘述者將德國佬比擬成豬,在索羅欽西這個地方把所有外國來的人都叫成德國佬,因此不管對方可能是意大利人或法國人,而對“他者”做一致性的歸類貶抑。不過,果戈理處理有斯拉夫血緣的波蘭人的形象時,又與德國佬截然不同。在他筆下的多數作品中,波蘭人就是叛徒。[注]E. M. Bojanowska,Nikolai Gogol: Between Ukrainian and Russian Nationalism, p. 175、pp.114-115.如在《可怕的復仇》中,與波蘭貴族合作的烏克蘭巫師,則被描繪為一個“叛徒”的形象。這種對外國與外來的非理性情感,在《彼得堡故事集》里表現得更為明顯,并已有學者指出這一點,[注]E. M. Bojanowska,Nikolai Gogol: Between Ukrainian and Russian Nationalism, p. 175、pp.114-115.然其卻未將此回溯與《夜話》連結而做更深入的比較和探討,并用以呈現果戈理創作思想與道路的演變。
同樣地,《聊齋》中的幾篇故事也丑化和異化外國人。例如,在《羅剎海市》里把羅剎人的外貌形容得奇丑無比,而且官職等級按照文本里羅剎人所認定的美丑標準來界定,越丑的越能當上相國和國王。如宰相的面貌被描寫如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注][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142、142、142頁。而群臣面目“率猙獰怪異”,[注][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142、142、142頁。以現代眼光來看,這些外國人猶如外星人。盡管如此,由此文本卻可看出:《聊齋》比之《夜話》在敘事的面向上,卻又多了一層雙向思考的軌跡,并具中國文人閑情逸致的趣味。《羅剎海市》故事中,全知的敘述者同時也解釋,正如羅剎人在主角眼里一樣——中國人在他們看來也是丑怪畸形——故“街衢人望見之,噪奔跌蹶,如逢怪物。”[注][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142、142、142頁。舉論另例,《狐諧》一文描寫“紅毛國”國王:孤陋寡聞,連“狐”都沒看過,更不知此字如何書寫。盡管此情節中,狐之本意乃于自嘲嘲人,以示其機智詼諧。《夜話》與《聊齋》皆具強烈的排他情感,來敘述對外國與外來的主體想象;一方面展現了民族性色彩,另一方面卻說明了作者的國族主義立場。前書是果戈理奠定這兩種寫作特性基礎的開端;后者則影響了魯迅,成為他在建構小說上,具有的一個來自中國傳統的主體,繼承文藝遺產的兩種特性。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魯迅在選擇其他外國作家作品時,更易接受果戈理。并能明白為何魯迅在多篇文章中,對所謂的“假洋鬼子”顯現嬉笑怒罵、蔑視嘲笑而挖心刺骨的語調風格。由此觀之,“假洋鬼子”之于魯迅,可以模擬為波蘭人之于果戈理。
上面論及的內容、主題、形象、象征、風格、氛圍、層次豐富且變化多端的情感與其變體等種種因素的交錯綜合,使得《夜話》如同《西游記》和《聊齋》一般,讀來豐富有趣。這些書中各種寫作技巧縮短了作者、敘述者和讀者的立場和距離,釋放這三者的想象力,任其自由馳騁。但是,這種寬廣的想象卻又被控制在一個比寫作當下的時代更能先一步覺知未來的作者手上。果戈理對人與鬼的遠航想象,帶著瘋狂與固著的熱情,與傅柯筆下巴洛克時期作品的“被馴化的瘋狂”相符:
藝術中的構思,必須歸功于不受規范的想象力;所謂畫家、詩人和音樂家的一時奇思 (Caprice),只是用一個委婉文明的名詞去形容他們的瘋狂(Folie)。[注]圣艾弗蒙 (Saint-évremond):《政治爵士當如是》(Sir Politik Would Be),第五幕第二場。《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瘋狂質疑著另一個時代、另一個藝術、另一個道德的價值:但它也反映出當前的主題:人類想象力的所有形式,甚至其中距離最遙遠的形式,以混亂攪擾的方式,在一個共同幻影里,彼此奇特地相互妥協。[注]《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
誠如別林斯基對《夜話》的評語,果戈理故事縱放了人類非理性的迷醉與抒情,“信手拈來,充滿著生命和魅惑”,[注]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Гоголя/ Н.В. Гоголь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М.: Гос.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56、C.40、C40.卻又同時將理性和非理性自然融合在一個寬闊的宇宙里,達到了他所認為詩人寫作的最高境界:“無目的而又有目的,無意識而又有意識”。[注]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Гоголя/ Н.В. Гоголь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М.: Гос.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56、C.40、C40.從別林斯基的視角來看,果戈理不僅為“作家”而已,因為這一名詞僅具一般和正常的水平。果戈理卻是比同時代作家更優異且具獨創性,故能接替了普希金所遺留下來的“詩人”的地位和桂冠。[注]В.Г. Белинский. 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 Гоголя/ Н.В. Гоголь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М.: Гос.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56、C.40、C40.
由上得知,果戈理和魯迅在創作《狂人日記》之前,早已具備了高度同構型的內、外在條件。中、俄兩國小傳統民間文學的相似性,不僅說明了果戈理所描述的小俄羅斯,是一個完整地保存了歐亞游牧民族混合的多神教迷信傳說,并同基督教混合起來的斯拉夫神話的區域,同時更凸顯了兩國在民族性與國家主義的特點上確實有共通的地方。且看中、俄作家與文評家各自點評這兩國的“小傳統”文學,以總結這些內容主題和人物刻畫的類似特點:《迪坎卡近鄉夜話》具“強烈的民族性”兼“荒誕怪異”,而《聊齋》的作者“喜人談鬼”,[注]蒲松齡:《聊齋志異》,第1頁。魯迅評之,嘗謂《聊齋》“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頁。。這些評語豈不恰巧正能互通中、俄“小傳統文學”之有無?
(二)滑稽感與笑的種種問題
1.原始的神話魅惑
果戈理的創作道路始于收集、改寫和出版小俄羅斯民間故事集的《夜話》和《和平城》(兩者的內容情節多涉及魔鬼,故亦可稱之為“鬼話”),而后才出版了《彼得堡中篇小說集》里的《狂人日記》,用以嘲諷當時全俄羅斯最為“歐化”與“文明”的沙皇首都圣彼得堡,是如此輕忽與排拒小人物的存在。相較于此,魯迅的創作道路則完全反其道而行,先以石破天驚之姿發表了《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在中國某一小城內,千年禮教與“高度文明”是如此教化和馴化“異類”的過程。在展現“歐化的文明”與“中國禮教的文明”對比和對立的《吶喊》之后,才有了一些改編神話的創作,先后收入《彷徨》與《故事新編》。
魯迅和其他的五四知識分子一樣,愛讀報章雜志并將之視為文人間相互溝通(亦包括筆戰)的渠道。嘗言,自己寫作時“一律抹殺各種批評”,因為他認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注]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28頁。。不過,魯迅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幼稚”的批評,也是他寫作的靈感來源之一。例如,魯迅在創作《不周山》[注]后改題為《補天》。一文中途、停筆休息時,看到一篇日報里的文章評論汪靜之《蕙的風》,“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一話語使魯迅產生了難以扼抑的寫作沖動。故再繼續執筆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注]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2卷,第353、353頁。。這是一幕魯迅描繪渺小的“文明”,對抗、攻擊與謾罵巨大的“原始”的象征場景:
那頂著長方板的卻偏站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見伊一順眼,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伊接過來看時,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比檞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
“這是什么?”伊還不免于好奇,又忍不住要問了。
頂長方板的便指著竹片,背誦如流的說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注]魯迅:《補天》,《魯迅全集》第2卷,第364頁。
胡夢華的《讀了〈蕙的風〉以后》指摘這一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注]胡夢華:《讀了〈蕙的風〉以后》,《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24日。轉引自《故事新編·序言》注釋2,《魯迅全集》第2卷,第355頁。魯迅則將此評論視為是一種“可憐的陰險”。從這一刺激,到促使他改筆的沖動與創作動機,則被他解釋為“滑稽感”作祟。[注]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2卷,第353頁。后來,章鴻熙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同年10月30日)發表《〈蕙的風〉與道德問題》反駁胡夢華。胡夢華也在《覺悟》(同年11月3日)上以《悲哀的青年——答章鴻熙君》進行答辯。魯迅針對后者文章,署名風聲,亦作《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一文,登于《晨報副刊》,1922年11月17日,此處引自《魯迅全集》第1卷,第427頁注釋2。于是,魯迅如何轉化對胡評論所生的滑稽感,并將所謂“可憐的陰險”的批判,融合自己在《吶喊》中欲表達的思想,更進一步地注入“不周山”呢?
這一文本原先收入于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然而,因成仿吾的一篇評論,直陳書中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皆為“淺薄”、“庸俗”之作,僅有《不周山》勉強算是杰作[注]成仿吾:《〈吶喊〉的評論》,《成仿吾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1頁。,魯迅對其批評心生不服,進而產生了輕視的心理。在1930年《吶喊》再版之際,魯迅索性抽出了《不周山》,如他自己所云,僅為了“回敬”成仿吾,讓《吶喊》徹底地成為了“庸俗之作”。于是,這一“集子里,只剩著‘庸俗’在跋扈了”[注]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2卷,第354頁。。魯迅對待胡夢華與成仿吾,這些他所認為不能茍同、不能心服卻又無法坐視不理的人們時,處理的邏輯與手段,通常是使這些人直視他們所詰難的;譬如,就讓胡夢華面對愛欲的尷尬,給成仿吾只看庸俗的難堪。從《吶喊》第一版的所有故事,尤其是《不周山》的要旨來看,魯迅覺得胡夢華的可憐,就在于他壓抑且否定了人類原始的欲望,徹底地被千年歷史發展出的道德觀——同時也是中國士大夫階層認同且建構的“理智”與“文明”所代表的中國禮教——馴化了。
李歐梵教授從魯迅搜藏或已出版的木刻、畫作與插圖中,對照他描繪女媧氛圍的粉紅色調與頹廢美的筆法,來說明西方的希臘神話與佛洛伊德的學派理論如何影響魯迅勾勒這原始的欲望——“愛欲”的主題。[注]李歐梵:《魯迅與現代意識》,收入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22-236、230頁。李認為,女媧的裸體正是體現了毫無虛飾的“真”。[注]李歐梵:《魯迅與現代意識》,收入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22-236、230頁。立足于此論點上,筆者進一步地補充解釋,魯迅筆下女媧同時具有美的特質。魯迅賦以女媧絕美的形象,“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注]魯迅:《補天》,《魯迅全集》第2卷,第358、358、357、357、357頁。于是她的美,“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注]魯迅:《補天》,《魯迅全集》第2卷,第358、358、357、357、357頁。我認為,魯迅想象中的原始的美,應是源自于他所搜藏并設法出版的高更畫冊筆下的原始女土人,[注]王觀泉:《魯迅與美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并非是克林姆特與畢亞茲萊畫中的“尤物”。[注]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31頁。
女媧與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人類對話,平鋪直述的幾句簡單白話顯示了原始與大自然的不善言語描述且不懂用典修飾的質樸特質。即使故事從她夢醒這一事件起始,她懊惱地“覺得有什么不足,又覺得有什么太多了”[注]魯迅:《補天》,《魯迅全集》第2卷,第358、358、357、357、357頁。,孤獨地面對顏色斑斕絢爛的宇宙:
天邊的血紅的云彩里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巖中;那一邊,卻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會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注]魯迅:《補天》,《魯迅全集》第2卷,第358、358、357、357、357頁。
僅一句慵懶的“唉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注]魯迅:《補天》,《魯迅全集》第2卷,第358、358、357、357、357頁。不去計較動態的日落月升,也就沒有無窮的抱怨叨絮,更不需因此探索自己的情緒,計較著瘋狂與文明,以及其他對立元素的定義與界線。作者在此處設計的太陽與月亮的象征意象,連結著女媧不理世事的樸實。這一事件的敘述,暗喻著隨著故事后續發展,當語言體系的建立隨著人類的“文明”開展而侵入。不論是“光芒四射的太陽”,抑或“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日落月升隨著時間流動“神話”與“鬼話”時代的結束,在中國“文明”與西方“理性”的言語論述中皆逐漸地被賦予了瘋狂的意義。
《鐵屋中的吶喊》一書具體地論證了《狂人日記》與《故事新編》的創作動機相似,表現出魯迅思想的復雜性。李歐梵教授解析魯迅,有別于儒家或以中國王道為尊的大傳統論述,試圖以“小傳統”體系作為出發點開展對中國文化遺產的藝術性做另一種反面觀點的詮釋,也就是對于“被官方歷史視為文明,事實上卻可能是野蠻;而被蔑視或被忽略的,反而更能顯出永恒的價值。”[注]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p. 54、p.56.此書亦列舉了尼采對《狂人日記》里雙重事實的顯著影響,特別是較之外顯事實的吃人主義還更是晦澀的真理——關乎于人類進化的真正本質。有趣的是,魯迅雖與果戈理同樣注重以滑稽感與笑作為相關于“黑暗”、“瘋狂”與“文明”的創作來源并依此營造作品氛圍,但是晚了七十余年的魯迅卻比果戈理走得更遠,在面對歐洲理性與文明入侵之際,采取了又褒又貶的態度,不同于果戈理的質疑與悲觀態度。在魯迅筆下,瘋狂源于自詡的光明。例如,代表西方文明的理性與進化觀點的尼采,象征光熱無窮的太陽,瘋狂如影隨形,魯迅比果戈理更進一步地離開了純粹的黑暗與灰暗色彩,在雜文中開啟了文明與瘋狂、光明與陰影、陰影與黑暗、西方與東方之間錯綜復雜的辯證。且看魯迅在晚期生命中如何連結太陽、尼采與瘋狂,重啟中國的進化與文明再造的問題與思考:
當然,能夠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后呢?幾百年之后,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只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注]魯迅:《拿來主義》,《魯迅全集》第6卷,第39頁。
魯迅思想的復雜性可從上述文字中呈現:乍看之下邏輯詭譎混亂,但事實上卻以“珠胎暗結”、“暗渡陳倉”的方式與他創作以來的各種主題相互聯系、自成一體。他一面以尼采自詡為太陽,但從發瘋的結果來證明他并非太陽的這一敘述,來暗喻發瘋的中國也不是太陽,怎能自詡僅給予而不拿外國的好東西?另一面卻在贊美尼采思想“豐富”與“大度”的同時,批判他自比太陽的“超人”思想,終究證實只是個“瘋人”的呢喃,而非屬女媧“神人”的質樸智慧。魯迅鋪陳的這一辯證邏輯,主在解釋進入近代的中國,無法像上、中古的泱泱大國一般,在精神與物質方面僅供給而不輸入。同時,他也批判尼采的瘋狂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產物,故拿來主義必須有所選擇,而非全盤西化,否則與“假洋鬼子”并無二致。尼采對太陽的譬喻,遙遙與《不周山》中女媧對日月全不理會的姿態相對。只有在故事結尾,巨大的原始(女媧)滅亡之后,讀者才能明白:人類的進化與快速現代化就是一場“日月可鑒”與“日月爭輝”的戰爭。而這戰爭的序幕,正由魯迅的《狂人日記》中主角的瘋狂掀起,意圖顛覆千年以來儒家界定的理性主義,并使原本二元對立的范疇界線,如“理性”與“非理性”、“白晝”與“黑夜”、“熱日”與“冷月”、“西方”與“中國”等藝術主題的元素,開始呈現混亂而模糊的狀態。
按魯迅在《不周山》呈現的中心思想,就在于諷刺、嘲笑并詰難那些如胡夢華等的一般群眾,在否定原始與自然的同時,還要將之視為“禽獸”,斥責排拒,以“禁”為刑作為矯正與懲戒的手段,達到他(們)自以為的道德教化的最終目的。同樣地,魯迅認為,成仿吾“以 ‘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注]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2卷,第353、354、354頁。,將之劃入淺薄之作的行列,“隨意點染,鋪成一篇”[注]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2卷,第353、354、354頁。,以“罵”作為立論的依據,“倒無需怎樣的手腕”[注]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2卷,第353、354、354頁。,只為達到評論家自以為的“純文藝的宮廷杰作”的目的。必須注意的是,在這兩個例子里魯迅反對的,并非全然是一般評論所指的道德禮教或者是純文藝的宮廷之作,比起這些更令他反感的是,以這些道德禮制的或是純文藝的理論作出粗暴手勢,將活生生的生命或有機的主體群(《吶喊》中每一篇故事雖然都有自己的主體,但內在主旨相互關連)硬納入了排拒措施,而導致毀滅或消失的境地。
魯迅所謂的”滑稽感”,源自于作家主觀意識里想象的對立元素,在意象中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并列,從可憐的與可惡的(陰險)開始觸發聯想,一路自巨大的與渺小的、原始的與文明的、白話的與文言的、孤獨的(個人的)與庸眾的、自然的與人工的、犧牲的與予取予求的、緩慢的與快速的(時間流動),到創造的與破壞的種種對立因素同時并置。再加上其他元素,例如將中國神話加入西方基督教色彩的描寫等等手法聚合,而產生出突兀有趣的創新,均充分地表現在《不周山》的文本中。盡管這篇故事后來從《吶喊》中被抽離,但作為1930年以前此書收入的最后一篇小說,毋寧可說是一篇企圖串起各篇小說要旨的試驗之作。在這一篇神話新編中,可以看到人類在自以為是的理性中對抗、反噬,并試圖監禁、控制到消滅創造他們的女媧,亦即象征人類文明的理智無法理解的原始大自然。故事關注的并非僅如部分研究者所云的“人與神的碰撞”[注]袁盛勇:《魯迅:從復古走向啟蒙》,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98-104頁。,關懷更多的反是神、人、獸之間的界線被一自詡巨大文明卻屬渺小野蠻的暴力手勢,與其背后所支持的和人類自以為長久發展的話語、系統和體制,應庸眾之聲被區隔,甚至被排拒開來。魯迅在這樣的過程里非但呈現并回敬了他以為庸眾的滑稽可笑之處,同時開啟了理解現代的與快速的一系列“瘋狂”病例——《狂人日記》、《阿Q正傳》、《長明燈》與《白光》——的另一種由原始到文明的窗口,提供了另一種分析文藝遺產的可能方法。
2.人間笑聲與陰間幻象
著名俄羅斯象征主義的僑民作家與學者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從《夜話》到《彼得堡中篇小說集》,果戈理創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與魔鬼斗爭。其小說中描寫的惡魔是一種隱喻,是社會的惡和人性中的一種司米爾賈科夫精神[注]司米爾賈柯夫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的一個角色。身份是卡拉馬助夫家的仆人兼廚子,但街坊傳言他的身世其實是老卡拉馬助夫強暴了街頭流浪的瘋女后所生的私生子,老卡拉馬助夫對此也不予否認,有時在酒后反而故意地以曖昧而夸張的口吻對此事張揚說嘴。在小說中,司米爾賈柯夫與作者一樣都患有癲癇癥。司米爾賈柯夫在孩提時代喜歡收養流浪貓,但其用意則在于將它們吊死并埋葬。故事中司氏常見的形象就是孤獨而寡歡,后來對伊凡宣稱,因為受了后者“超人主義”的哲學思想,而產生了弒父行動。梅列日科夫斯基指的“司米爾賈科夫精神”,就是人類一切罪惡的化身,以一種瘋狂的外顯形式表現。的神秘體現,他所有的作品就是為了“研究這一神秘本質的機制”,而他的笑就是人與存在人心的魔鬼的抗爭。[注]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Гоголь и чортъ: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Скорпион, 1906. С. 95.中譯部分引自張建華:《果戈理的狂歡化傳統與當代俄羅斯后現代主義小說》,《第二屆斯拉夫語言、文學暨文化——果戈理兩百周年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2009年5月16、17日,第4頁。然而,蘇聯學者巴赫金、普洛普、李哈喬夫與尤里·曼卻對果戈理作品里的“笑”與所生的滑稽感與幽默感等問題,更進一步地分別做了更多不同面向的論述與駁證。從這些果戈理的俄文研究中,可以啟發我們反觀魯迅作品透露的“滑稽感”與作家所體會的“幽默感”,[注]參見魯迅兩篇雜文:《從諷刺到幽默》與《從幽默到正經》,《魯迅全集》第5卷,第46-49頁。以多面向的角度重新評價魯迅作品并檢驗過往的魯迅研究。
巴赫金駁斥十九世紀著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對果戈理作品所作出的評價,他認為僅僅將這位作家視為一個純粹的、或是狹隘的諷刺家,并不足以說明其作品思想的廣博與復雜。必須先探索影響作家的西方來源,如浪漫主義之笑(它的狂歡本源)、唐吉訶德以及其他等等之外,還得回溯作家從俄羅斯文化里所汲取的淵源,像是民間節日之笑、廣場滑稽之笑、宗教學校學生之笑與飲宴之笑。由此探索開啟果戈理作品中“笑同陰間幻象的特殊聯系”,“笑與死的悠久聯系,導致一種特殊體裁的創建——笑謔影像的體裁。”[注]錢中文等編:《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頁。由此論點反觀魯迅,筆者認為,誠如不少學者所指:魯迅的中外閱讀史寬廣而復雜,在動手下筆《狂人日記》之時已是三十七歲。在此之前,對其后作品的種種主題所下的閱讀功夫與反復的思考能力等方面來看,皆使我們無法單純地將他視為只是一般評論所認為的,或是后來因政治因素而遽下結論的一位純粹地諷刺世俗、嘲笑社會與批判封建的作家。[注]關于這一論點,夏濟安與李歐梵的研究業已論證。見Tsi-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pp. 146-162;誠如夏濟安在研究中,對魯迅其人與其作的評價:
把他(魯迅)歸入一種運動,派給他一個角色,或把他放在某一個方向里都不啻是犧牲個人的天才而贊揚歷史粗枝大葉的泛論。到底魯迅所處的時代,即使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是什么樣的時代呢?用光明與黑暗等對比的隱喻永遠不能使人完全了解它,因為其中還有一些有趣的,介乎暗明之間深淺不同的灰色。天未明時有幢幢的鬼影,陰森的細語和其他飄忽的幻象。這些東西在不耐煩地等待黎明時極易被忽視。魯迅即是此時此刻的史家,他以清晰的眼光和精深的感觸來描寫;而這正是他有心以叛徒的姿態發言時所缺少的特質。[注]夏濟安:《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30頁。
夏濟安正確地指出了魯迅作品中,較少被一般學者關注的“死亡”、“陰間幻象”與“陰郁面”。但是,夏的研究卻將魯迅之“笑”視為一種“玩笑”或“俏皮”,如別林斯基批評果戈理的諷刺手法,并未廣義地正視它的嚴肅含義和特點,而將它的中國傳統與外國淵源——果戈理作品——類似的特質做比較分析。
普洛普不同于巴赫金的主要之處,則是將探討果戈理作品中“滑稽與笑”的問題,立足于別林斯基的論點上來伸展。巴赫金著重果戈理早期較具非理性的狂歡性質來表達瘋狂概念的民俗作品,而普洛普則將研究焦點放在作家中后期進入十九世紀文明時代討論理性與瘋狂的社會創作。兩位學者皆一致認可,“笑”在果戈理這兩個創作時期當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普氏認為,別林斯基以果戈理為例說明喜劇性也可以具有重大意義,來反駁十九世紀俄羅斯文藝界普遍地貶低喜劇、褒揚悲劇的唯心美學,是一重大創見。[注]Пропп В. Я. Проблемы комизма и смеха. М.: Исскуство, 1976. С. 4-5、C.8-10、C.8-10.普氏由此進而申論,果戈理的作品從藝術處理和風格上來看是喜劇,但論及其內容時卻是悲劇,《狂人日記》與《外套》就是最顯著的兩個例子。[注]Пропп В. Я. Проблемы комизма и смеха. М.: Исскуство, 1976. С. 4-5、C.8-10、C.8-10.普氏亦舉例駁斥,盡管果戈理不少作品的主角涉及了低級的或卑劣的滑稽毛病,讓不少評論家落下話柄以為果戈理的作品是失之卑俗的喜劇,然而這正是不了解他的幽默的重大意義:其中藝術與道德的價值值得再三琢磨思考,屬于審美的領域。[注]Пропп В. Я. Проблемы комизма и смеха. М.: Исскуство, 1976. С. 4-5、C.8-10、C.8-10.
巴赫金與普洛普兩人評價果戈理的作品,對人觀察能如此細致入微,而以如此諷刺、幽默、正經或滑稽感的笑作為一種體裁、形式或手段,來表現作者與不同讀者之間在抽象情感的對話里產生藝術的多層次觀感,并營造出上述的悲喜劇性質。魯迅與兩位學者一樣,對于果戈理有相同的理解,在生活的境遇中也發出類似的同感。在《從諷刺到幽默》與《從幽默到正經》兩篇雜文里,魯迅不但諷刺了時下不同種類的諷刺家,還以諷刺的口吻反駁他的評論者并不理解他的世界觀體系,所以對他的觀感是“謾罵、俏皮話、刻毒、可惡、學匪、紹興師爺”[注]魯迅:《從諷刺到幽默》,《魯迅全集》第5卷,第46、47頁。等等。就算如此,他“倘不死絕,肚子里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注]魯迅:《從諷刺到幽默》,《魯迅全集》第5卷,第46、47頁。然而,他所認同的果戈理式的諷刺與幽默,一旦進入了中國社會里,如他所云,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也就只得變成一種隨波逐流而偽善的“正經”,因為諷刺與幽默不但會被誤解,還要被陷害。
魯迅接續著從諷刺到幽默的演變,在《從幽默到正經》中以一種看似幽默(比諷刺更隱誨)且滑稽的口吻,說著:“‘聰明人不吃眼前虧’,亦古賢之遺教也,然而這時也就‘幽默’歸天,‘正經’統一了剩下的全中國”,實則頗具感慨地暗喻全中國刻意擺出來的正經面孔,是要強迫人不笑不言,這種粗暴的手勢簡直是“刻毒”。[注]魯迅:《從幽默到正經》,《魯迅全集》第5卷,第48-49頁。作者認同果戈理,藉由諷刺與幽默的筆法,向讀者展示了一個他認為已經被馴化的中國“正經人”的面貌,以及一般群眾所謂“正常的、平均的規范”的精神。那么,不愿順從這種面貌和這一精神的魯迅,在正經與非正經、正常與非正常的鐘擺之間,選擇了以“叛徒”和“狂生”的姿態,利用滑稽感與不同種類的笑,時隱時現、時明時暗、時真時假并時褒時貶地閃爍其機鋒或譏諷。于是,果戈理與魯迅作品中瘋狂世界的邏輯誠如傅柯所云,“戲弄著萬物表象,戲弄著現實和幻覺間的曖昧混淆,戲弄著真理和膚淺間永無界定、永被重復、又永被打斷的分合脈絡”(頁四),也就不再令人感到費疑難解了。
魯迅除了是一位思想層面寬廣而復雜的作家之外,還是一位先于他的同時代人更具藝術慧眼的文評家。在評論果戈理的名著《死靈魂》時,他列舉相當清晰且具代表性的例子,闡明了這位俄國作家在創作里經常使用的經典手法與其代表的含意:
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注]魯迅:《幾乎無事的悲劇》,《魯迅全集》第6卷,第383、383頁。
這些評論顯露魯迅以其天才的內在感知,盡管只學了幾個月的俄文而無法閱讀原文作品,[注]周作人回憶,1907年秋天魯迅在日本時曾與六位中國同學一起向一位俄國女子學俄語,過不了幾個月則半途而廢。雖然后來魯迅說是因為學費太貴,但周作人則認為,主要的原因是俄文詞組的發音較長較難,學習時容易讓魯迅和許壽裳感到緊張。見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滄桑——兄弟憶魯迅(一)》,第119-120頁。卻在德、日的翻譯中確然洞悉并消化了果戈理的藝術世界。此外,他還以自己獨到的藝術眼光,比之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研究者更早一步地指出,主要以小說作為形式的果戈理,觀察人與生活的敏感度猶如詩人一般,故將果戈理視為詩人這一觀點,在從十九世紀發展至今的俄國文藝評論界中已被普遍認可接受。魯迅繼而以“含淚的微笑”[注]魯迅:《幾乎無事的悲劇》,《魯迅全集》第6卷,第383、383頁。闡明果戈理小說的悲喜劇性質,這些評論說明了魯迅作為一個作家與文評家所具有的高度敏銳性。
四、結論
由上述論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果戈理與魯迅兩位作家在早期作品與早期創作生涯的發展中,所具有的高度同構型與相對相似性。這些性質并非單僅奠基于魯迅對果戈理的喜愛、認同、模仿與消化等創作過程,更在于兩位作家在處于西風東漸的潮流下,面對著自我與他者,展現出值得注意的、并且類似的內在世界的經驗、感知,以及對外在世界的態度。
此外,在俄、中兩篇《狂人日記》生成之前,兩位作家已經各自繼承了兩國傳統文學遺產中早已具備的共通性——對“黑暗世界”里種種精神現象,所展現的興趣、觀察與探討。兩位作家文學知識生成的背景與發展階段中,對于所謂的“黑暗意識”、“黑暗閘門”與“小傳統”的喜愛,確立未來作品中對于異類、異端與異化的接受與關注。《聊齋志異》與《迪坎卡近鄉夜話》之初探與比較,試圖論證的不僅是一般所云的“向俄羅斯學習”的中國現代性,更是跨歐亞的俄羅斯特質中潛藏的中國東方特征。本論文說明兩者雖然多有迥異,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相通之處。這些共同點,才是使得果戈理在魯迅寬廣的中外閱讀史里,最獨受青睞的重要原因。
最后,果戈理與魯迅在早期作品中,鏈接原始、黑暗與瘋狂,在手法上選擇了滑稽感與笑,展現其衍生的種種問題。經前所論,我們可以直陳不諱,這兩種“黑暗之力”,在他們的生花妙筆下,遠比一般現實主義小說中道德性的說教更具力量與份量,更能顛覆所謂西化的文明。兩位作家的早期作品在贊揚原始的狂歡性質之余,并不產生低級的、卑俗的“滑稽的毛病”,反而吊詭地提升悲喜劇的美學特質,成為不朽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