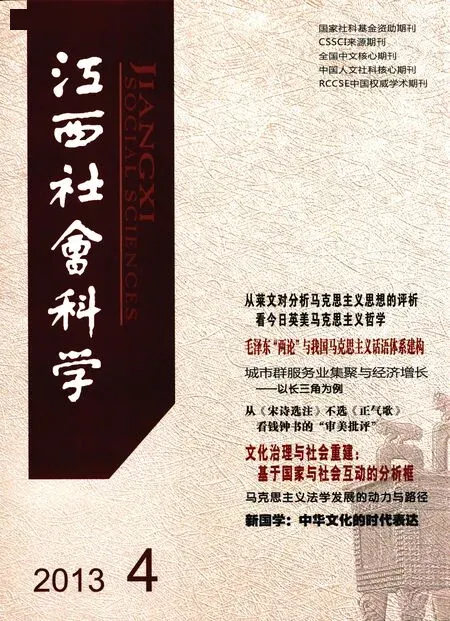行政成本過度增長與制度控制
■羅文劍
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職能的前提和基礎,但近年來其快速增長的態勢令世人關注。科斯指出:“政府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實際上有時它的成本大得驚人。”[1](P22)有效控制龐大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節約資金為民辦更多益事,這成為世界各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追求。在我國,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導下,最近國務院提出了“本屆政府內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等控制行政成本的實在舉措。我國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長表現在哪些方面?主體的行為邏輯如何影響其增長?如何去促進行政成本合理化?本文將沿著這一思路進行闡述。
一、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長的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長,危害了社會的公平與和諧,損害了政府形象與公信力,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口誅筆伐”。我國政府行政成本快速增長突出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行政成本總量過大
對《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進行核算,不難發現我國政府行政成本總量很大、增長很快。1978—2011年,政府行政成本從52.9億元快速攀升到17 601.63億元,增長了331.7倍,年均增長率為19.24%。而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2億元增長到472 881.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5.89%;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由1122.09億元增加到109 247.79億元,年均增長率僅為14.88%。這說明,我國政府的行政成本不僅總量龐大,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遠遠超過了同期經濟發展和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沉重壓力。
(二)行政成本所占的比重偏高
數據顯示,1978—2011年間,我國政府行政成本占GDP的比重、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不斷提高,分別由1.45%和4.71%上升到3.72%和16.11%。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越來越高,也說明了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不平衡,本來可以用于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的公共資金被嚴重擠占,降低了維護社會公平與和諧的機會。另外,1978—2011年,我國人均行政成本負擔由5.5元增長到1306.39元,增長了236.5倍,年均增長率18.03%。但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長到21 809.8元,僅增長63倍,年均增長率只有13.4%。這種不對稱關系,說明國民收入增長帶來的“幸福”小于行政成本攀升帶來的負擔。
(三)行政成本的結構不合理
對于行政成本的結構劃分,學界沒有統一的標準,受信息公開程度的限制,目前要細化行政成本的每項具體支出內容并獲取相應的數據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從“行政管理費類”支出的結構,去探討行政成本的結構特點。根據《中國會計年鑒》的統計口徑,“行政管理費類”支出主要包括工資福利支出(人員支出)、商品和服務支出(公用支出)、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三類。《中國會計年鑒2011》對78.7萬戶全國預算單位的基本支出決算統計結果顯示,2010年的工資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務支出、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分別占41.3%、38.7%和20.0%,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占了很大比重。而根據《地方財政統計資料》中“地方行政管理費類支出統計表”的數據顯示,2003—2006年的三項支出中,增長最快的就是“商品和服務支出”,增幅為68.9%。而商品和服務支出中,增幅最大是“培訓費”(124.4%),然后是招待費(94.8%)和差旅費(82.9%)。可見,行政成本中的支出結構亟待規范。
(四)行政支出浪費問題突出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指出,行政支出浪費主要表現在“公款吃喝;公務用車;公費旅游、出國;冗員嚴重、辦事效率低;建豪華辦公樓;‘政績工程’;政府會議浪費;政府用水用電等能源浪費”[2]等方面。根據《審計署績效報告 (2010年度)》顯示,2010年,地方各級審計機關共審計(調查)15.7萬個單位,共查出違規問題金額3280.5億元、損失浪費問題金額427.6億元。如果加上中央部門的浪費與違規資金,數額將更加龐大。
二、主體的行為邏輯與行政成本的增長
國外學者探討政府支出增長的代表性觀點很多。瓦格納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使得政府直接參與生產的活動大大增加,這就導致公共部門的膨脹,從而帶來公共支出的增長;A·皮科克和J·懷斯曼的“替代-規模效應理論”認為,公共支出增長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正常時期的內在原因 (經濟不斷發展,政府稅收增加就喜歡多支出),二是政府在非正常時期的外在原因(如災難時期,為了維護發展與穩定,政府就必須多支出);馬斯格雷夫等人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強調,公共支出增長的原因是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政府發揮不同的作用強度;尼斯坎南則指出,官僚機構通常以機構規模最大化為目標,從而導致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國內學者何翔舟、張雷寶、楊宇立等人都認為,經濟增長過快會引致一定的行政需求增量,進而推動行政成本增長。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都表明了行政成本增長的合理性一面,但卻無法詮釋我國行政成本過快增長的態勢。筆者認為,主體的行為邏輯是持續推高政府行政成本的重要動力。
(一)官員的行為邏輯——一種理性思辨的結果
1.官員的自利偏好拉升行政成本。政府是官員的集合體,政府的支出偏好常常體現為官員的偏好。對理性的官員而言,趨利避害是其本能,維護個人或小團體利益是其行動準則。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官員所面臨的利益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巨大,其“經濟人”的沖動被不斷地刺激而膨脹起來,手中的公共權力容易演變為攫取私利的利器。如此,公共資金就會被用來優先滿足政府自身消費而不是公共利益訴求,或者通過各種途徑演變為“合理”的官員福利以及仕途升遷的資本,從而推動行政成本的大幅提升。例如,2010年,審計署對中央部門的收支審計時發現,82個所屬單位采取截留收入、虛列支出等方式,套取和私存私放資金4.14億元。國家審計署總審計師孫寶厚推算,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小金庫每年可能有827億的規模。這些極具隱蔽性的小金庫資金,基本上都被用來滿足官員的“暗箱”開支、職工福利等私利需求,成為腐敗的“財政支柱”。
2.財政信息透明度差助推行政支出亂象。以前,國家財政收支等統計資料一直被定為國家秘密,不得對社會公開。實踐證明,信息不公開就會導致黑箱現象,縱容“忽視委托人利益、隨意性行政支出”等不規范行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出臺后,政府的財政收支與行政成本不再顯得神秘,但上海財經大學和清華大學對財政透明度的研究表明,“全國31個省級政府無一及格,81個市級政府僅有7個及格”[3]。另外,由于財政支出明細不清,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獲知公共資金尤其是行政開支的具體去向。法制不健全以及“官本位”作祟下的利益糾葛成為信息公開透明的羈絆,為官員的違規支出提供了可乘之機,推動著行政成本的快速攀升。
3.錯誤的政績觀導向下官員不計成本地投入。政績觀對官員的行為選擇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錯誤的政績觀不僅會危及官員的健康成長,而且造成行政浪費與腐敗,損害干群關系。現行體制下,以經濟增長為核心指標的政績依然是考核、提拔官員的重要依據,官員的升遷往往是“以政績論成敗”,這是導致錯誤政績觀產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錯誤政績觀的導向下,官員會視“政績”為邀功立身乃至仕途高升的墊腳石,片面追求所謂的政績,為了完成一個“項目”而不惜大舉投入和隨意增加經費,進而催生各種各樣融入了個人虛榮心和政治功利性成分的“政績工程”。尤其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官員在制造經濟發展的“奇跡”方面有著先天的不足,轉而追求短期轟動效應,斥巨資打造“政績工程”以撈取政治資本。只算政治賬、不計成本地支出,對行政成本的快速增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4.制度不完善縱容官員的行政支出。制度不完善使得官員僥幸心理得以延伸、機會主義之風盛行。首先,從預算制度的缺陷看,我國的財政預算制度沒有形成倡導節約和懲罰浪費的規范,政府官員會在任期內追求預算最大化,因為預算越大,官僚的效用就越大[4]。同時,我國的財政預算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基數+增長”的做法,形成了鼓勵政府哪怕采取“年底突擊消費”等方式也要使用完預算經費的不正常現象。正如奧斯本指出的那樣,“精明的政府管理人員會把每一個明細分類中的每一分錢都花掉,不管他們是否需要。……我們的預算制度實際上是在慫恿每一個政府管理人員浪費錢財”[5](P57)。其次,從監督制度的不完善看,我國的制度設計中,倡導行政支出的監督主體多樣化,然而,現實中卻形成了人大的監督基本淪為形式、紀檢監察部門的監督往往“抓大放小”、審計機關的監督通常是“整改”和“建議”等現象。另外,我國對于職務性消費的“灰色地帶”缺乏有效的制度管控,縱容產生了大量游離于制度邊緣的支出行為。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驚人的支出浪費與腐敗,行政成本被大幅抬高。
(二)公眾的行為邏輯——從消極參與到積極監督的困境
1.知情權保障乏力造成公眾消極參與。在行政成本持續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公眾態度與參與程度的影響至關重要。從理論上說,作為納稅人的公眾,理應是政府財政收支的天然監督者,他們“供養”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良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顯然應當擁有獲取政府具體支出等信息的知情權。然而,由于目前社會上尚未形成普遍的現代公民意識,公眾對政府的收支行為往往產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消極心態,加之政府對行政支出的信息處于相對壟斷的位置,信息不公開或公開不到位成為公眾獲取知情權的桎梏。筆者在某縣調研時,一位財政局官員就說,財政數據一般不對外,該公布的數據都在網上公布了,沒有在網上公布的都是不能公布的。而該縣政府網站上并無財政局網站的鏈接,只能在縣政府官網中找到粗略的政府財政收支報道。行政支出信息的匱乏加重了公眾消極參與的心態,公眾依法表達自己意志的參與權和主導權受到影響。在公眾消極參與的環境中,政府行政性支出中自由性和裁量權就會被再次放大,行政成本的不規范現象就會增加,行政成本必然越來越高。
2.監督成本偏高致使公眾面臨積極參與的困境。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公眾的現代公民意識逐漸增強,參政議政的熱情也逐漸被調動起來,對行政成本的監督亦即成為題中應有之義。然而,當公眾對行政成本的監督訴求遭遇監督成本的“難題”時,一種無奈的情緒就會在社會中蔓延。首先,財政支出不透明、公布的數據缺乏準確的表述和預算明細,為公眾監督設置了人為障礙,迫使公眾的監督在巨大的信息搜尋成本面前只能停留于“外行看熱鬧”。其次,公民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欠缺加大了公眾的監督成本。我國公民監督政府的渠道主要包括人大會議、信訪、聽證、領導接待日等,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保護機制,這種匱乏的現實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往往會在公眾內心的后怕效應——“我會不會被報復?”中顯得更加脆弱。直到當今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一些公眾開始摒棄傳統渠道而選擇網絡這種兼具匿名性和自由性等特點的渠道,去實現對政府行政成本的監督,即便如此,行政成本依然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監督成本偏高引致沖突性的結局:一方面是社會的進步刺激了公眾監督行政成本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卻是客觀障礙下公民的唏噓與無奈。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成本正是在公眾的“漠視”中持續走高。
三、制度控制:促進行政成本合理化的出路
行政成本的增長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能讓行政成本的增長實現合理化。通過剛性的制度駕馭和激勵,正確規約與引導主體的行為,促使官員約束自我膨脹的欲望和樹立行政支出的“民本”導向,讓公眾從消極“漠視”邁向積極作為。
(一)財政信息公開制度建設是前提
信息公開才能形成“魚缸效應”,才能讓官員慎微慎行,才能讓公眾重塑政治參與的信心,這是解決行政成本亂象的最佳切入點,也是跳出主體行為選擇惡性循環的首要前提。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縣級以上政府的“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列為重點公開的范圍,規定應當“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因此,政府首先要加強內部管理,督促各級政府落實行政支出的信息公開工作,積極推進政府財政收支向社會公開。其次,財政預算制定過程要公開透明,以便于社會組織或公眾的有效參與,提高預算的規范性和資金的使用效率。再次,規定項目支出明細化,防止預決算資金中的隨意性,理清像“其他支出”之類的“模糊的萬能乾坤袋”,讓“外行看得懂、內行說得清”。香港特區政府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香港財政預算案文本,是總共七大本大16開黃色封面的大書,七本預算案總量加起來近20斤。有些部門的開支細到添置座椅,香港某部門今年換十只燈泡的支出都被列出來。預算案七本大冊子全文一字不落全數上網”[6]。因此,筆者認為,公開透明才是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手段。
(二)監督制度的完善是關鍵
“在內部監督制度不完善、外部監督機制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機構總能輕易使得用于自支的行政經費在公共財政總支出中占據優先位置。”[7]因此,必須完善監督制度,為快速增長的行政成本戴上“緊箍咒”。首先,加強財政預算制度的約束力。當前非常緊迫的任務是必須強化財政預算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避免預算編制過于粗糙、隨意以及非制度安排的政治權力過多干預預算決策等預算“軟化”現象,通過不斷完善預算制度并加強其硬性約束力,使政府預算真正進入法制化軌道,實現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其次,加強人大、紀檢監察、審計乃至社會力量的監督。可以考慮人大代表專職化,使其能經常性地行使調查等權力,實現對政府行政支出的日常監督;強化紀檢監察部門的監督,實現對貪污腐敗、行政浪費等行政支出亂象的“零容忍”,打造廉潔政府和節約型政府;創新審計制度,提高審計水平,保障審計機構權威的獨立地位,充分發揮審計部門在治理行政成本中的監督作用,同時也要加強人大對審計部門的監督,防止審計部門與其他部門的“利益共謀”;充分調動媒體和社會公眾的監督積極性,發揮互聯網和手機網絡在社會力量監督政府財政支出中的重大作用。還要不斷拓寬公民參與的現實渠道,提高他們參與的積極性和效率,“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營造良好的監督氛圍。
(三)問責制度的建立與落實是保障
如果行政成本問題被監督曝光出來,但卻缺乏強硬的責任承擔與糾錯機制,監督的價值何在?建立與落實問責制、構建責任政府,是控制行政成本的重要保障。因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決不會無節制地擴大支出,而必然會合理控制支出規模,千方百計節用財力,充分發揮政府支出的效能”[8]。當然,問責制度的核心理念并非僅僅是事中、事后責任的追究,還在于事前對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能力不足、信息不公開等進行質詢與“合理的懷疑”,使公職人員以崇高的責任感履行其職責。首先,要具體規定政府財政收支信息公開的職責,讓他們對所有公開的信息的真實性與完整性負責,通過“責任意識”的強化來提升政府支出的服務意識和民本意識,避免支出“黑箱”。其次,引入績效評估制度對政府支出的“成本-收益”進行綜合考量和監督,對行政支出亂象以及監督不力的現象堅決依法處理,“一個都不能少”,少一些“抓大放小”,多一些“零容忍”。再次,建設回應型政府。回應型政府,“就是以公共治理為理念,以解決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為責任,具有自覺、穩定、可持續的回應性和回應機制,以及有效回應社會所需的回應力,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9]。King和Stivers指出:“政府是屬于其公民的,應將公民置于首位,政府強調的重點不應放在為政府這艘航船掌舵或是劃槳上,而應放在建立明顯具有完整性和回應性的公共機構上。”[10](P21)對于控制快速增長的行政成本而言,信息不對稱增加了建立有效對話渠道的必要性,而建設回應型政府的意義正是在于促進政府在以民為本的基礎上,對民眾關心或提出的行政支出等問題進行及時有效地回應,同時建立保護機制,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表達權,推進公眾與政府之間“參與-回應”的良性互動,讓公民體會到在監督政府行政成本支出中的自我價值,并不斷強化自己的積極參與意識與行動,實現“錢為民所用”。
四、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行政成本持續快速增長。筆者認為,主體的行為邏輯是持續推高行政成本的重要動力。因此,本文關注的重點并不是如何通過優化支出結構等辦法解決政府行政成本表現出來的問題,而是透過行政成本持續快速增長的現象,探尋主體行為邏輯對于行政成本的“助推之效”,并在此基礎上,力圖通過剛性的制度建設與執行以激勵主體行為的規范化,進而實現行政成本合理化。或許,道德教化對于引導主體行為進而控制行政成本具有一定的現實作用,但剛性的制度激勵,不僅有助于約束官員的行政支出行為,而且有利于吸納公眾的積極參與并提升參與效益,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強制度建設并認真執行恐怕才是行政成本標本兼治的可靠保證。
注釋:
①本文研究的行政成本,借鑒陳共在《財政學》(第7版)中的界定,2007年以前行政成本主要指國家財政按功能性質分類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2007年以后的行政成本用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外交支出來計算。
[1](美)羅納德·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劉守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行政浪費八大現象[E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7-04/08/conent_5948934.htm.
[3]王亦君.財政透明讓誰感到糾結[N].中國青年報,2012-06-16.
[4]張國慶,朱慧濤.革新觀念與明列規范:新時期中國政府降控行政成本的現實選擇[J].湖南社會科學,2009,(3).
[5](美)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M].周敦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6]警惕“其他支出”里的腐敗[E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3/10/content_10980124.htm.
[7]楊宇立.公共財政框架內的行政支出變化趨勢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09,(11).
[8]趙長茂.政府就該節儉為民[J].瞭望,2007,(14).
[9]盧坤建.回應型政府:理論基礎、內涵與特征[J].學術研究,2009,(7).
[10](美)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M].丁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