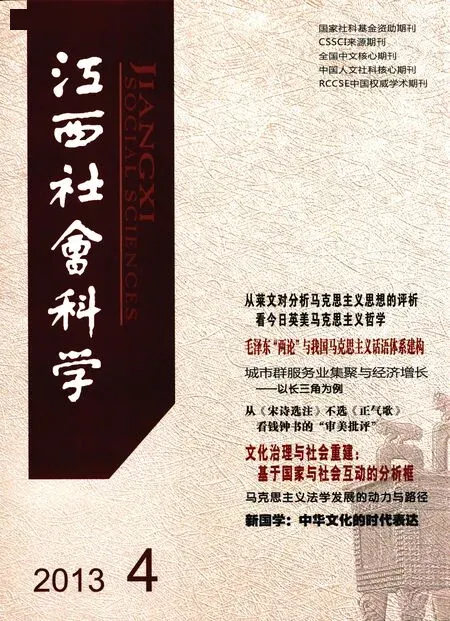菊與真——《紅樓夢》37至41回的背后旨意
■安 寧 袁廣濤
在西方傳統里,“哲學與文學之爭”早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已經存在,[1]爭論的重點在于:文學能否作為探討“人應該如何生存?”的一種有效手段。倫理學作為西方哲學的一個古老分支,自古至今,與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大體說來,西方倫理學有兩個傳統:其一源于希臘文明,關注幸福的本質以及幸福人生;其二根植于猶太-基督教傳統,強調責任與人的行為的正當性。[2]亞里士多德是前一種倫理傳統的代表,“什么樣的生活是好的?”或者是“活得好意味著什么?”構成了亞氏倫理學的基本問題。
20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Fredric Jameson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對傳統的文學倫理學批評進行了批判和解構,文學的倫理學解讀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然而,就在20世紀80年代末,一些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又試圖重新找回文學與倫理學的內在聯系。他們多從希臘的倫理傳統汲取營養,重新發掘文學是如何探討“人應該如何生存?”這個古老的命題。[3]
本文意在借鑒西方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方法,探討隱含在《紅樓夢》背后的道德關懷,并且關注此種道德關懷與其道德傳統之間的關系。要完成這一探求,需針對《紅樓夢》這部作品提出一個基本的問題:作者是如何通過此部作品來闡發這一古老命題的,即“人應該如何生存?”或者說“什么樣的生活是好的?”筆者認為,《紅樓夢》的37至41回不僅是整部小說的核心部分之一,而且,作者亦通過對這五回敘事結構上的巧妙安排透露出了隱藏在作品背后的深層旨意。
一
盡管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小說的37至41回,然而,卻不能將目光鎖定在這五回。不僅要看到這五回本身的結構特點,還要看到它們與前后章回的聯系,更要看清它們在小說整體結構上的位置和重要性。對于小說的37、38回,有些評論家樂于把它們與36及其之前的章回聯系起來,將其看做是對“夢兆絳云軒”等事件的深化與總結,而把39至42回劃為一個小單元,完整地講述了劉姥姥二進榮府的過程。[4]這顯然是合情合理、易于為人接受的一種劃分方式。然而,37至41這五回,亦構成了2+1+2這樣一個完美的對稱結構:37、38回把大觀兒女進行詩歌創作的詩意生活推向了高潮,而40與41回則寫盡了一位鄉村老嫗以一己之村俗樸拙對此種唯美生活所造成的警醒與沖擊,39回則是這兩起高潮之間的過渡與銜接;整體看來,娓娓而敘,渾然天成。
《紅樓夢》中,類似于此的對稱結構不止一處,再比如64至70這七回,以《五美吟》開始、《桃花行》結尾,皆嘆美人薄命,中間夾雜65、66回,重在敘述尤三姐情案,又有68、69回講述苦尤娘之遭際,再有67回中之半回涉及黛玉睹物思鄉之情。這七回明看是寫尤氏二姐妹的悲慘命運,而實則影射黛玉在賈府的艱難處境,這一明一暗兩條線索交相呼應,起到了很好的奏鳴效果。
37至41回不是這么一明一暗的結構,而是兩種有著可謂天壤之別的生活方式之間的激烈碰撞與相映成趣。照如此說,我們不禁會有一問:劉姥姥何能有如此大力氣,以一人之力來挑戰作者精心策劃的整一理想世界?[5]然而,劉姥姥就有這么大力,而且,這份力量的體現,不止是單個層面上的。首先,我們看她在小說整體結構這個層面上的不可替代之處。這在作者介紹她出場時,已顯露無遺。當作者對如何講述賈府故事感到束手無策時,想到了劉姥姥一家:
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并無個頭緒可做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倒還是頭緒。(第6回)
要想弄清作者在敘事技巧上的匠心獨運以及劉姥姥在整部小說結構上的作用,我們需要緊扣此段,挖掘三個關鍵意象之間的深層聯系。為了說清楚劉姥姥與賈府之間的關系以及這個人物在整部作品結構上的意義,作者運用了三個意象,分別是:“亂麻”、“芥豆”,和“瓜葛”。賈府內部幾百號人之間的大小事務以及如蛛絲般細微巧妙的糾結,亂作一團,猶如亂麻,給小說的講述帶來了麻煩:一是不知從何說起;二是難尋出一條主線作為綱領。此處,撇開作者在元小說層面拋出的障眼法,我們需留意“亂麻”這個意象本身的特點以及與賈府之間本質上的聯系。見過“麻團”的人,都知道那是干燥枯黃的一團,是作為成品或半成品存在著的,與土地之間的血脈聯系已被切斷,喪失了生命力,不能夠再次經歷“出生——成長——死亡”這樣一個健康的循環過程。作者用這一意象來指涉賈府,是再貼切不過的了。作為封建大家族的一個代表,賈府“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第二回)。賈府的存在是社會形式的一種,它會逐步被新的社會形式所取代,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亡。
與之形成對照,作者把劉姥姥一家比作“芥豆”。“芥豆”是藤蔓植物,扎根泥土,把枝葉向著最為有利、最遠處伸展,吸取盡可能多的陽光雨露,通過藤蔓運回根部、運向果實。這是個生動活潑而又生生不息的意象。它所象征的不是一種階段性的社會存在方式,而是具備與人類共存亡的長久性。自有人類以來,就賴以土地而存活,并且生生不息。在馮其庸纂輯的《八家評批紅樓夢》中,就有評者依據《易》反復強調劉姥姥之為“坤”、之為“土”象,是生命不息的代表。此處,恰與“芥豆”這種極具生命力的意象相吻合。
更為有趣的是,作者把“亂麻”與“芥豆”之間的關系,用“瓜葛”這一意象來形容。作為“芥豆之微”的劉姥姥一家,正要伸出芥豆的觸須,來修復這一段“瓜葛”,重新疏通與賈府之間的關系,目的自然是順藤摸瓜,得到些好處,來熬過即將到來的嚴冬。但是,如果我們對這對關系的解讀停留于此,就枉費了作者的一番苦心經營。有脂評在此處提醒讀者,切勿輕易看過,因為這劉家將是賈家落敗之后,巧姐的歸宿。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已經如“亂麻”并且喪失了生命力的存在形式,賈府又將通過劉姥姥修復的這條“瓜葛”被重新連接到土地上,以此獲得一線生機。換句話說,代表著賈家未來的一條血脈——巧姐——將順著這條藤蔓流回到讓人類生生不息的土地,過起自耕自足的生活。表面上是賈家照顧了劉姥姥,而實際上,是劉姥姥提供了賈家生的契機。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看到“亂麻”、“芥豆”、“瓜葛”這三個意象背后的深層旨意,那么,它們又是如何在結構層面發揮作用、埋下千里伏線的呢?賈家事務如一團“亂麻”,缺少一條“綱”,來理出“頭緒”;作為“芥豆之微”的劉氏,伸出了藤蔓,修復了“瓜葛”,從而得以探入“亂麻”,不僅給枯黃的麻團平添了些許色彩與靚麗,亦給了它一條綱領,不再做無頭腦狀。因此,兩家關系的修復對于整部小說來說,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這種作用的具體發揮體現在小說的開頭(第6回)、中間(第41回)以及小說結局處。我們所關注的37至41回把賈府的享樂生活推向了極致,而在這享樂的背后隱藏著危機。劉姥姥的到來,不僅對賈府的生活提出警示,亦為落敗后的賈府播下了一線生機。出現在41回的兩個新的意象很好地隱含了這種承前啟后的作用:
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玩的,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便也要佛手。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才罷。
有脂硯齋在此留批云:
柚子即今香團之屬也,應與緣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兒之戲,暗透前后通部脈絡,隱隱約約,毫無一絲漏泄,豈獨為劉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顯然,脂硯齋強調了劉姥姥這一人物在小說結構上的突出地位。卻于劉姥姥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作用,并未提及,即:她在作者探求“什么樣的生活是好的?”這個問題上,又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
二
若要回答上面這個問題,需要重新返回到37至41回,再次挖掘這五回結構上的特點,并且,需要了解這五回中間包含的一個關鍵意象以及這個意象所蘊藉的深刻內涵。在讀過《紅樓夢》之后,讀者也許會生出這樣一個疑問:作者為何要在描述了大觀兒女極雅致的詩歌創作活動之后,緊接著插入劉姥姥進大觀園這一大段看似插科打諢的文字?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有機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紅樓夢》的37、38回描述了大觀園里第一次集體詩歌創作活動。37回的海棠詩是集體創作的開始和熱身,38回的菊花詩則是一次極盛的表現,再后來的蘆雪廣聯詩,以及桃花詩、柳絮詞,都不及這次活動組織的細密而又高潮迭起,十二首菊花詩更成為整部《紅樓夢》詩詞歌賦成就的一個集中代表。然而,盡管大觀兒女們在38回里如此大張旗鼓地歌詠菊花,但并未有一朵真正的菊花出現。反倒是在第40回,劉姥姥一進大觀園,就被插了個滿頭,就是飽經世事的賈母也僅得一朵。37、38與40、41回就被如此巧妙地勾連在了一起。對這一細節,我們是粗心看過,還是把它當成是作者高超技藝的又一番展示?這個問題,我們姑且不做回答,但菊花這個意象卻不可以輕易錯過,需就此做一番探討。
提到菊花,不可以不提到一個人——陶淵明。[6]在黛玉等人的菊花詩里,也多次指涉到這位大詩人,如:“絕塵埃”、“陶令”、“東籬”,“彭澤先生”等。在整部《紅樓夢》中,牽涉到陶淵明的地方大約有四處:第一處是在第二回賈雨村的高談闊論里,列其為“逸士高人”;第二處就是在此處的菊花詩里面;第三處是香菱學詩時,黛玉引了陶潛《歸原田居五首》中的一句,說明王維不及陶潛之處(第48回);第四處便是在“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那一回,襲人抽到了“武陵別景”一簽。通過觀察這四處的指涉,我們不難發現陶淵明在作者曹雪芹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而這一切又都化在了曹氏的小說里。它不僅贊頌了陶氏的詩歌成就,更是對陶氏所代表或開創的三種傳統做到了鬼斧神工般的運用。這些傳統,具體說來有:歸隱的傳統,田園詩的傳統,以及桃花源所代表的中國式的烏托邦傳統。而這三者之間又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一種共同的精神蘊含其中,起著一以貫之的作用。這一精神集中體現在下面的這首詩里: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其五)
若要指出這首詩的詩眼,那定是“真意”二字。“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真意”二字究竟何意?我們又如何能夠透過這兩個字看清《紅樓夢》37至41回中大觀兒女、陶淵明、劉姥姥之間的本質聯系?這層本質聯系又如何揭示作者對人生、對人應該如何生存諸類問題所做的探求與闡釋?
袁行霈在《陶淵明的哲學思考》[7]一文中,對陶淵明的哲學思想做了精彩而獨到的闡發。在袁先生看來,陶氏的哲學思考有三個要點:一是“自然”,二是“順化”,三是“養真”。容筆者就著袁先生的論述對此三點做一大膽總結:人應該順應自然、順應天性,自由自在地生存著;如果真能夠如此,便是得了“真意”,可謂“真人”。袁先生亦對陶淵明做出了中肯的評價:陶氏雖然創設或者是說捕捉到了一種理想的生存方式,但他自己卻未必已然做到。筆者亦覺得,重點不在于陶淵明是否完全做到了,而在于他開創了一種精神追求的傳統。
此外,筆者想要重點關注的是“真”這一概念與傳統。據袁先生所說,對“真”的闡發最早見于老莊。在《莊子》中,對“真”與“真人”有著比較明確的界定:
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真者,精誠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碌碌而受變于俗,故不足。(《莊子·漁父》)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忻,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
這兩處引文告訴我們:“真”是每個人天分中固有的,得自于天。我們應該謹守這份“真”,不受外物和俗事的干擾。守得住天分中這份“真”的人,就是“真人”。“真人”就可以處于一種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保持自己的天性。筆者進一步認為,李贄的《童心說》是對老莊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首先,我們看他如何定義“童心”: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書·童心說》)
比較李贄與莊子兩人的說法,可以發現李贄在兩個方面對莊子的思想有所深化:首先,他強調了“童心”與“真心”的關系,把“童心”看作“真心”的源起之處;其次,他同時又強化了一個對等的過程,即:人之初具備的是“童心”,“真人”具備的是“真心”,要達到真人,有一個在生活歷練中持守“童心”以保“真心”的過程。
筆者認為,相對來說,在《紅樓夢》中具備“真”這種品質的人物有兩類,一是以寶黛為首的大觀兒女,二是劉姥姥;并且,兩者相映成趣。他們一個是在詩歌中求真、求美,一個是在艱苦的農村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窮心”(第 39 回)、“本色”(第 40 回)。兩者的區別在于,后者是經過了生活的磨煉之后而保有的“真”,前者則是“童心”之真。這大概也足以說明為什么眾評家認為劉姥姥對黛玉等人有警醒的作用。巧妙之處在于,作者于隱約之處把兩者以“菊花”相連,而“菊花”背后,我們隱約看到的又有陶淵明。陶淵明把自己的一生譜成了一首詩,[8]而這首詩亦記載著大詩人覓尋“真意”的足跡。
三
通過對《紅樓夢》37至41回敘事結構及關鍵意象的分析,能夠發現隱藏在它們背后的一條信息,那就是:怎么樣活著是好的?人因該遵循天性,順應自然,自由自在地生存著,不為俗務所縛。陶淵明可以說是此種生活的化身。《紅樓夢》中隱含的對這位大詩人的指涉,透露出作者曹雪芹對其生活方式的肯定和詩歌創作的激賞。接下來,我們要問:撇開劉姥姥和大觀兒女與陶大詩人的相似之處,即:對“真”的持守,他們跟陶淵明之間又有什么差異呢?這種差異在小說中又是如何透露出來的呢?
要解答上述問題,有一對鏡像需引起我們的注意。[9]在劉姥姥游玩大觀園的結尾,她撞進了寶玉的臥室,被一面鏡子擋住了去路。同樣一面鏡子,出現在小說的56回。在賈寶玉知道還有個甄寶玉之后,陷入了深深地思索和困惑,想探求一個究竟,卻是求而不得:
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有;若說必有,又并無目睹。(第56回)
寶玉就這么思索著,恍恍惚惚睡去,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與自己別無二致的另一個寶玉,繼而哭喊醒來。醒來之后,才發現大概是鏡子惹的禍,讓他忘記了鏡內境外本是一個人。透過這一個細節我們看到,小說通過一面鏡子,展現了寶玉對自我身份的思索和探求,繼而引發了“有——無”、“甄(真)——賈(賈)”之辨。這直接觸及小說一開始就透露給我們的一個核心議題: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第1回)
鏡子切分了現實與幻象,我們的神思得以在二者之間穿梭,恍惚于有無、真假之間。過多的探求,帶來的是恐慌與無助,并無出路可言。
其實,與寶玉相比,小說當中對自我和生存問題探求最多的,應首推黛玉,集中體現在她頗具代表性的幾首歌行體的詩歌里,如:《葬花吟》、《秋窗風雨夕》,和《桃花行》。黛玉透過其詩歌試圖尋找的是一處凈土,可以保有其真純。但上天入地,這么個地方求而不得。總體看來,黛玉展示的是一種悲觀甚至絕望的人生觀、宇宙觀,帶有些許頹廢色彩。如下面引言所示:
愿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凈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而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葬花吟》
通過這些詩行,我們可以看到黛玉在自怨自艾中的自問自答、反復辯論。所有的痛苦來自于有所求:求出路、求知己。求而不得之后,選擇了悲觀消極的人生態度,帶有虛無的色彩,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這與劉姥姥的“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形成既鮮明又有趣的對照;同時,也深別于陶淵明詩歌中體現出的積極務實的態度。[10]黛玉對人生認識上的這種悲觀虛無色彩,在后面兩首詩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如:
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秋窗風雨夕》)
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桃花行》)
這幾句詩滲透出這樣的信息:愁苦無窮無盡,充斥宇內的是排解不開的寂寞。黛玉對自我的過度關注和反省,使其陷入難以自拔、求生不得的境地,帶上了頹廢的色彩。
依眾評者所言,劉姥姥的出現是對黛玉消極悲觀人生態度的一種警醒。但同時,我們亦需關注劉姥姥式的生存方式本身所帶有的局限性。這在她面對寶玉臥室的鏡子時,有所體現:
劉姥姥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墻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踩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里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后得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劉姥姥詫異,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他親家只是笑,不還言。劉姥姥笑道:“你好沒見過世面,見這園里的花好,就沒死活戴了一頭。”他親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里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第41回)
在同一面鏡子前,寶玉做出了對人的生存的思索,試圖找出真我,體現的是一種對自我認識的覺醒。而劉姥姥面對同一面鏡子,除了極度的新鮮感所帶來的困惑,她沒有探求自我的意識,而只是對著自己的鏡像做了一種行為方式上的評判,“你好沒見過世面,見這園里的花好,就沒死活戴了一頭。”繼而急著尋找出口,沒有思考和反思的空間。至此,看官也許在笑筆者對一農村老嫗提出了過高的苛責。但是,問題不在于此,而在于農村老嫗所代表的生存方式的局限性,它缺少一種建立在思索基礎之上的超越性。這種超越性是寶玉、黛玉試圖達到,而早已存在于陶淵明的詩歌里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陶淵明是一種理想生活的化身。在《紅樓夢》中,寶黛等人與劉姥姥各自代表了這種理想生活的某個方面,但他們又各有局限,無法實現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想生活。
[1](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2]Peterfreund,Denise White.Great Traditions in Ethics.Beijing:Peking UP, 2005.
[3]Parker,David.Ethics, Theory and the Novel.Oxford:Oxford UP, 1998.
[4]馮其庸.八家評批紅樓夢[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5]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6]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增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8]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M].北京:中華書局,2007.
[9]詹丹.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10]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