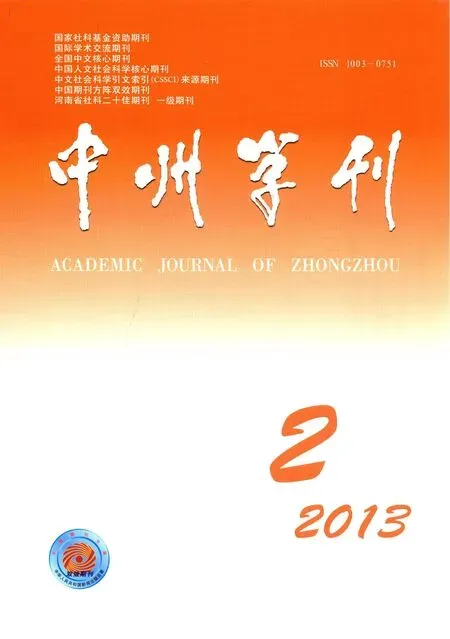農村征地拆遷中的階層沖突*——以荊門市城郊農村土地糾紛為例
楊 華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征地拆遷的規模急劇擴大,由征地拆遷引發的沖突成為農村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主要形式。根據功能沖突學派代表科塞的定義,社會沖突是關于價值以及對稀缺的地位、權利、資源的要求之爭,雙方獨立的目的是要壓制、破壞以致消滅對方。①征地拆遷中的沖突概指在農村征地拆遷中引發的沖突,它是不同利益群體在獲取土地利益的過程中因矛盾激化而表現出來的一種對抗性心理或行為的互動過程。②
與農村征地拆遷同時存在的現象是農村的階層分化。農村階層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農民大量轉移到其他領域,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成為其他身份主體和地位的過程,它使農村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矛盾明顯化,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③農村各階層在村莊利益再分配過程中處于不斷地互動與博弈之中,互動與博弈的結果取決于它們各自的特點、社會稟賦以及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征地拆遷是農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過程,這個過程必然會出現農村階層間的互動與博弈,并由此引發階層間的沖突。征地拆遷是引發農村階層沖突的重要原因。
征地拆遷引發的社會沖突形式較多,有農戶與農戶的沖突、農戶與基層組織的沖突,也有小組與行政村、基層組織的沖突,以及農戶個體與個體的沖突、群體與群體的沖突、農戶個體與基層政權的沖突、農戶群體與基層組織的沖突,等等。學界對這些沖突已有豐富的研究④,而對征地拆遷中階層沖突則較少涉獵。本文要考察的就是征地拆遷中的階層沖突,且主要是農村其他階層與農村管理者階層的沖突。農村管理者階層既是黨和政府在農村的代理人,它代表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及其合法性,也是征地拆遷的主體和利益再分配者。農村管理者階層與其他階層的沖突不僅會影響到村莊內部階層之間的關系,也會影響到農村其他階層對黨和政府的態度及合法性認定,進而影響到黨和政府在農村的階層基礎和群眾基礎。因此,探討征地拆遷中的階層沖突并尋找化解沖突的策略,具有顯著的政治意義。
二、農村征地拆遷中的階層博弈與利益再分配
(一)農村征地拆遷中的階層
筆者在荊門市城郊農村調查發現,當地農村階層分化已趨顯現化,階層內部關系已經超越傳統血緣、地緣和人情關系,成為人們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最重要的關系。階層之間關系和利益的協調、處理及整合成為村莊治理的基礎任務之一。在征地拆遷中,農戶之間的合縱連橫與傾軋反制以及其他策略和行為均帶有明顯的階層化傾向,乃至階層化的沖突成為征地拆遷過程中社會沖突的主要類型。根據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等資源的占有情況⑤,可以將荊門市城郊農民劃分為管理者階層、精英階層、中上階層和普通農戶階層等四大階層。在這里,權力是指村莊中的政治權力,它既可以是正式掌握的政治權力,也可以是非正式掌握的政治權力。經濟是指經濟財富、家庭收入,包括經商、務工和務農的總體收入,其中務農的收入主要是指土地上的收入,隨著土地上收益的增加,占有土地的多少也成為劃分階層的重要標準。社會關系是指農戶的社會關系質量,既包括村莊社區關系,也包括超社區關系。不同階層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它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及在階層關系中的行為取向。
1.管理者階層
管理者階層是由直接或間接掌握村莊權力和再分配權力的人組成,包括現任村兩委干部、退休村干部、村民小組長、黨小組負責人、黨員、村民代表、協管員等,以及接近村莊權力的那部分人,主要是與村兩委干部關系較好的農戶。管理者階層有以下特點:一是掌握或接近村莊權力,是村莊資源再分配的主持者和參加者;二是通過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獲得了較廣的利益關系和較多的經濟發展機會,并且擁有一定規模的土地(20—30畝),經濟收入在村莊中屬于中上水平(3萬—5萬元/年);三是他們的社區關系和超社區關系質量都較高,并擁有體制性關系⑥,因此對其他農戶的關系依賴程度較低。管理者階層占農戶的10%左右。
2.精英階層
精英階層是指村莊中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等資源上都較為優厚和獨立的農戶,他們對其他階層的依賴程度較低。這個階層包括富人群體、鄉村混混、鄉村教師、鄉村醫生、在外闖蕩者、退伍軍人、技術人員、家族頭人等。富人群體是指通過經商或辦實業,擁有較大規模的資產且年收入在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的那部分農戶。鄉村混混是指農村中不從事正當職業,專以暴力或欺騙手段謀取利益的群體。精英階層中的不同群體在某些方面擁有其他群體無可比擬的優勢,如擁有財富、知識、技術、暴力等,并因此整體上提升了他們的階層身份和地位。他們一般擁有一定規模的土地(20—30畝),自己耕種或轉出,并且擁有農業之外的收入和利益機會,經濟水平在中等偏上。他們之間關系較為密切,除少部分是村兩委干部的反對派外,一般都與村兩委關系良好并支持其工作,從而接近村莊再分配權力。他們的超社區關系網絡質量較高。這個階層占農戶的10%左右。
3.中上階層
這部分農戶主要包括舉家外出經商和以兼業為主、農業為輔的農戶,是農村經商或兼業農戶中的較為成功者,經濟資源較為豐厚,年收入在5萬至十幾萬不等,占農戶數的20%左右。這個階層的主要特點是:一是他們占有一定規模的土地(20—30畝),自己耕種或轉出;二是他們主要的利益關系和社會關系在村外,擁有較高質量的超社區關系,對村莊內部關系的依賴程度較低;三是與村莊其他階層的交往較為淡薄,即便生活在村莊中也不熟悉農村的情況,與其他階層來往較少;四是見識較廣,容易獲取相關知識和政策信息;五是他們與村干部接觸不緊密,甚至經常不配合村組干部的工作,等等。這個階層在經濟上和社會關系上都較為獨立。
4.普通農戶階層
這部分農戶包括純農業戶、半工半農戶和貧弱農戶。其中,純農業戶耕種中等規模土地(30—50畝),收入在3萬—4萬元,屬于中等水平;半工半農戶耕種20畝左右的土地,并外出務工或兼業,收入在中等偏下;貧弱農戶耕種較少土地(5—15畝),因鰥寡孤獨、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勞動力、常年有病號等緣故,家庭經濟較為困難。普通農戶階層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等資源占有上都一般或較低,他們在權力上依賴于管理者階層,在經濟和社會關系上不獨立于精英階層和中上階層,往往受其他階層的支配和排斥。這個階層占農戶的60%左右,是農村中最大的群體。
(二)征地拆遷中的利益博弈與再分配
對農戶而言,征地拆遷實質上是對土地增值收益及相關利益機會的再分配過程。土地增值收益中對農戶的再分配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與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構成。⑦與征地拆遷相關的利益機會包括拆遷、丈量、平整土地、修路、建筑、小區管理等工程的承包與務工。在這兩部分再分配過程中,除了國家和地方嚴格規定的標準外,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皆有較大的彈性,這就為階層間、尤其是各階層與管理者階層之間的利益博弈提供了空間。在階層的利益博弈中,不同階層的討價還價能力和策略取決于他們的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資源占有的多少,特別是取決于他們相對于管理者階層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上的獨立程度。獨立程度越高,討價還價的能力就越強,占有再分配的份額就越多;反之占的份額就越少。⑧
1.管理者階層通過再分配權力使自身財富猛增
在荊門市城郊純農業型村莊,管理者階層在征地拆遷前與一般農戶的經濟收入水平相差無幾,甚至不及中上階層的經濟水平,他們較多的經濟機會與跨體制身份并未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征地拆遷使他們得到補償等實在的利益,同時,征地拆遷本身也是他們跨體制身份轉化為經濟利益的機會,因此他們積極主動地介入征地拆遷,成為農村征地拆遷和利益再分配的主體。管理者階層利用他們的跨體制身份以及與體制的密切關系,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可以得到以下利益:使自己的征地拆遷補償不需要博弈便可以巨額增加;協助和介入征地拆遷過程并得到犒賞;組建建筑隊承包工程;管理征地拆遷的中間過程等。管理者階層通過征地拆遷得到巨額收入后,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收入購買挖掘機、組建建筑隊參與后續或其他村的征地拆遷,或者利用其他的經濟機會(如小區建設),使其財富得到大幅度穩定增長,迅速成為村莊中的富人。
2.精英階層通過依附管理者階層大幅擴大財富
在荊門市城郊村莊,精英階層屬于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上都獨立于其他階層的農戶群體,同時他們又是普通農戶階層在經濟和社會關系上的主要依賴對象,管理者階層通常也是通過他們與普通農戶階層建立溝通關系。精英階層的主要收入在農業之外,征地拆遷不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同時,這部分群體見識較廣,信息靈通,對征地拆遷的相關政策比較熟悉。因此,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農村管理者階層首先要籠絡精英階層,防止他們成為“釘子戶”⑨。一般情況下,精英階層中的大部分農戶都會積極配合管理者階層和基層組織的征地拆遷工作,并成為做其他農戶工作的主力軍。精英階層在征地拆遷中獲得了以下利益:獲取超出補償標準之上的巨額補償;參與做工作得到犒賞;富人群體和鄉村混混與管理者階層結成聯盟關系,壟斷征地拆遷中的各項工程承包以獲取巨額利潤;參與征地拆遷中的管理工作獲取利益;鄉村混混還通過暴力威脅被征地拆遷戶接受拆遷協議并從中獲取報酬;等等。
3.中上階層通過做“釘子戶”擴大了財富
由于中上階層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等方面獨立于管理者階層,在征地拆遷利益博弈過程中,他們能夠理直氣壯地抗征抗拆,不給管理者階層和來做工作的精英階層農戶“面子”,也不講熟人社會的人情情誼,在征地拆遷中漫天要價。在和諧征地拆遷背景下,管理者階層和基層組織毫無辦法,只能軟磨硬泡,將所有能動用的關系都動用過來做工作,最終不得不步步妥協,滿足他們的大部分要求。中上階層通過做“釘子戶”獲取超過補償標準以上的超額利益。由于他們有經濟頭腦,在外邊也有一定的社會關系,他們在征地拆遷后不僅可以擴大自己的經商兼業規模,還可以投資其他行業,實現財富的再增值。
4.普通農戶階層暫時獲得了一定財富,緩解了家庭困難,但整體利益受損
普通農戶階層在征地拆遷利益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既與再分配權力無緣,又無法當“釘子戶”獲取利益,他們在管理者階層和精英階層的輪番攻勢或威脅下很快屈服,他們最先簽訂“征地拆遷協議”,獲得標準的補償。如果說他們還有博弈空間的話,那就是在征地拆遷前在自家耕地上突擊種樹、在禾場上搭建附屋等,這些能使他們的利益有較大增長。但這些相對于管理者階層、精英階層和中上階層獲取的巨額利益來說是微乎其微。根據土地耕種的差異,普通農戶階層中的純農業農戶可以得到50—100萬元的補償款,半工半農戶可以得到15—50萬的補償款,貧弱農戶的補償款一般在8—15萬。這些補償能夠解決普通農戶階層的子女結婚、裝修房子、生病醫治、養老送終等急需,但不能使他們的財富增加,因為他們既無技術又無社會關系可以將這筆錢用于投資。由于沒有了土地收入,這部分農戶住進小區后,家庭生活向城市靠攏,所需物品都得購買,家庭開支猛增,他們的家庭生活愈發拮據,這更增加了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的焦慮感。
三、農村征地拆遷中的階層沖突
在上述征地拆遷的一般性利益博弈和再分配中,形成或加劇了兩對對立的階層關系:一是加劇了中上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對立關系;二是形成了普通農戶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對立關系。這兩對對立的階層關系很容易發展成劇烈的階層對抗和沖突。
(一)中上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沖突
中上階層的生活面向朝外,他們與其他階層的關系較為淡薄,尤其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上獨立于管理者階層。所以,他們往往是管理者階層的反對派,在村莊事務上為難村干部。中上階層是針對管理者階層的主要上訪群體,他們有時間、經濟能力和知識,又熟知政治體制的運作邏輯,因此能夠通過上訪這一渠道來參政議政、反映村組干部的問題以及達到其他目的,給村組干部出了不少難題。在征地拆遷中,中上階層是農村管理者階層想方設法要防止“搗蛋”的對象。征地拆遷伊始,管理者階層就會產生對中上階層的“包保”責任⑩,即幾個村組干部負責某些經商兼業農戶,將他們看好和穩住,防止其鬧事、上訪或做其他破壞性活動,以保證征地拆遷順利進行。盡管如此,中上階層依然是征地拆遷工作中常常出現的“釘子戶”和“上訪戶”。[11]
要在村莊征地拆遷中做“釘子戶”和“上訪戶”,尤其是做謀利型“釘子戶”和“上訪戶”,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是不在乎村莊的評價。與學界和媒體渲染的“維權抗爭”形象相反,“釘子戶”和“上訪戶”在村莊中的評價仍較為負面,其行為認可度較低。二是在權力、經濟和社會關系上獨立于管理者階層和精英階層。若不獨立,則要受這兩個階層的支配和約束,他們出面做工作就得給面子、賣人情,就做不成“釘子戶”和“上訪戶”。三是熟知征地拆遷的相關政策及基層政治體制的運作邏輯。做“釘子戶”和“上訪戶”不是胡攪蠻纏,要懂得相關政策和知識,能夠援引相關“話語”來論證自己行為的合理性,同時也能夠洞察管理者階層在征地拆遷中的違法違規行為,在上訪過程中要懂得相關程序和掌握各級政府對上訪的態度,主要是要抓住基層政府維穩心態,等等。這些知識和認識不是普通農民可以掌握的。在村莊的四個階層中,滿足這三個條件的只有中上階層。
中上階層做“釘子戶”和“上訪戶”,一般基于兩個理由:一是維護權益,為維護自身權益而與管理者階層對抗。二是謀取利益,為在征地拆遷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再分配份額。這兩個理由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中上階層做“釘子戶”和“上訪戶”對于征地拆遷而言,會帶來兩種效應:拖延征地拆遷時間和抬高征地拆遷成本。這兩點對地方政府和農村管理者階層來說是致命的。因為城市化擴張及城市GDP增長、城市固定資產投資是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或晉升的主要指標,而地方官員又有任期限制和地方財政約束,因此地方官員為顯示政績,希望克服地方財政約束而在任期內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征地拆遷以加快城市化發展。地方官員的這一征地拆遷期望,與中上階層做“釘子戶”和“上訪戶”拖延時間且抬高成本的現實發生碰撞,從而產生了劇烈的沖突。在征地拆遷現場,這種沖突就表現為中上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沖突。
1.個體對抗式沖突
此類沖突指的是中上階層中的個體農戶通過做“釘子戶”與管理者群體產生對抗而引發的沖突。做“釘子戶”是個體式的,一般不會出現“釘子戶”的聯合現象,這既與中上階層做“釘子戶”是為維護或獲得個體利益相關,也與征地拆遷中做工作的方式是先易后難、一家一戶分化瓦解(先從較容易做通工作的農戶開始,最后拔掉最硬的“釘子戶”)相關。在每次征地拆遷中,最后剩下最難纏、最難做工作的“釘子戶”一般只有一兩戶,這一兩戶的征地拆遷往往要驚動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由他們批準實施“強征強拆”,這個過程可能會出現暴力事件。
在征地拆遷過程中,中上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對抗與沖突集中在簽訂協議、領取補償和交付土地三個階段(拆遷中含房屋拆遷)。在簽訂協議階段,管理者階層主要通過中上階層農戶的親朋好友上門做工作,有時管理者階層和上級征地拆遷單位人員也陪同參加,而中上階層主要通過各種理由拒絕或拖延簽字。不同農戶會有不同的理由,這些理由既有合理合法的,也有不合理合法的,有的甚至漫天要價,但都是管理者階層無法完全滿足或一時難以滿足的,從而使得管理者階層的工作做不下去。這一階段的沖突一般是言語沖突,也可能出現冷漠對峙的情況。有時管理者階層會突破“和諧征拆”而引鄉村混混介入,則可能造成雙方肢體沖突。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后,雙方會簽訂“秘密協議”,中上階層從中獲取標準補償之外的巨大利益。在領取補償階段,中上階層農戶亦可能以某些理由拒絕領取補償,不在補償清單上簽字畫押,這也可能造成雙方的對峙。雙方會重復前一階段的博弈而最后達成協議,中上階層又可從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在交付土地階段,中上階層還可能故伎重演,在現場向管理者階層提出新的要求,不滿足就不讓動工,這很可能出現“釘子戶”與管理者階層發生肢體對抗和暴力沖突,也可能使雙方的私下交易公之于眾,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損害管理者階層的公正公平形象。征地拆遷中“強征強拆”事件也往往出現在第三階段。由于管理者階層和上級征地拆遷單位無法滿足“釘子戶”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巨額補償要求,因此市縣主管領導最后決策強征強拆往往不可避免。強征強拆過程也是中上階層與管理者階層沖突最劇烈的過程。
個體對抗式沖突的最大特點是,中上階層提出的要求是多樣化和個性化的,但滿足要求的方式卻具有同一性,即許諾更大利益。征地拆遷不會對中上階層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只能使他們的財富大幅增長,因此他們做“釘子戶”并不是不愿意征地拆遷,而是為了維護征地拆遷中個體的權益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管理者階層及其上級征地拆遷單位則是為了使征地拆遷更快、更順利,不是追求補償的公平公正,而是“用人民幣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使得利益博弈有利于中上階層,并在某種意義上認可和鼓勵了“釘子戶”的行為。
2.個體上訪式沖突
在征地拆遷中,上訪也是中上階層與管理者階層沖突的重要形式。前文已提及,中上階層既有征地拆遷相關政策法規的知識,也熟稔基層政治體制的運作邏輯,因此他們在征地拆遷中針對管理者階層的上訪總是輕車熟路,且志在必得。中上階層針對管理者階層的上訪主要有以下兩個理由:一是管理者階層在征地拆遷中違法違規操作和非法攫取利益問題;二是管理者階層對中上階層權利和利益的侵犯問題。前一個理由具有公共性,屬于公共維權,后一個理由是維護自身權益,兩個理由都具有維權性質。當然也不排除某些中上階層農戶以維權為幌子謀利。
當前我國信訪體制在調整利益分配、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和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我國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信訪作用越發突顯,各級政府的信訪壓力也越來越大。尤其是新的信訪條例出臺后,信訪“一票否決制”成為懸在各級政府頭上的一把利劍,信訪壓力型體制逐漸形成,全防全控越級上訪和進京上訪成為各級政府的中心工作,甚至是一線工作。在信訪壓力型體制下,信訪案件和信訪壓力一級級往下壓,到鄉鎮和村一級則無法再往下壓,只能自己解決問題,因此鄉村基層組織承擔了最大的信訪壓力。在征地拆遷中,中上階層掌握了鄉村干部害怕越級上訪的心理,偏偏越級到省市、乃至中央上訪“狀告”村組干部,最后信訪案件由中央、省市批轉至鄉村兩級,鄉鎮只能要求村一級配合說明情況或解決問題。為了平息中上階層的上訪事件,緩解自己和縣鄉對越級上訪的壓力,村干部往往用錢來解決問題。調查發現,凡是上訪的中上階層農戶都得到了巨額利益。這樣,上訪中所反映的問題不但一概沒有解決,反而原來的問題被掩蓋并得以強化。
個體上訪式沖突的特點是沖突始于中上階層的維權型上訪而止于管理者階層給予利益。利益的交換非但沒有終結兩者的沖突,反而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用錢來擺平上訪的方式激發了中上階層的某些農戶在征地拆遷后繼續通過上訪來謀取利益,其上訪的謀利性凸顯。[12]在這個意義上,信訪體制也成為村莊利益的再分配機制。
(二)普通農戶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沖突
在征地拆遷前,普通農戶階層與管理者階層的關系屬于相互隔離的關系,雙方較少直接發生聯系,而是通過與雙方關系都較好的精英階層作為溝通的橋梁。在征地拆遷過程中,普通農戶階層屬于村莊的下層農戶,缺乏知識和見識,對政策規范和制度運轉不熟悉,不了解自己的權益范圍,他們無法像中上階層那樣做“釘子戶”和“上訪戶”來維權和謀利。他們與管理者階層的沖突主要源于征地拆遷補償中出現的嚴重不公平現象:管理者階層通過權力直接攫取巨額財富,精英階層依附管理者階層獲得巨額財富,中上階層通過抗征抗拆獲得巨額財富。普通農戶發現,同樣面積的土地、同樣質地的房屋,其賠償的數額卻相差數倍甚至數十倍;村里給管理者階層、精英階層和中上階層購買養老保險,而普通農戶階層的養老保險卻久拖不辦。諸如此類的事實打破了他們的公平觀念,使他們產生極大的被剝奪感,并將此歸咎于管理者階層的“貪污腐敗”[13],矛盾的矛頭也就對準管理者階層乃至基層政府。征地拆遷再分配的差距越大,普通農戶階層的不公平感就越強,他們維護公平觀念、平衡公平感的方式也就越具有群體性和政治效應。一般表現為群體性事件和群體性上訪。
1.群體性事件
征地拆遷中的群體性事件是指由征地拆遷過程直接或間接引發的,相關利益群眾、個別團體與組織為了實現利益訴求,而通過集會、靜坐、圍堵、游行等方式力求解決問題,并造成一定政治社會影響的突發事件。[14]既有的群體性事件的研究,一般將事件主體籠統地概括為農民,其實真正的主體是農民中的普通農戶階層,其針對的對象是農村管理者階層以及基層政府。在征地拆遷群體性事件中,普通農戶階層的訴求一般有兩個:一是要求管理者階層和基層政府糾正征地拆遷中不公平、不公正的政策和做法,懲治管理者階層的貪污腐敗行為;二是純粹為了“出氣”、“解氣”,通過群體性事件的方式釋放對管理者階層以及基層政府的“氣”。
根據其規模和破壞性程度不同,征地拆遷中的群體性事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較為緩和的群體性事件,表現為普通農戶階層集體找管理者階層爭辯吵鬧、威脅群體上訪、靜坐抗議、圍攻指摘村干部、圍堵村辦公樓等;其次是較為激烈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有堵塞交通要道、在鄉鎮辦公大樓門口或主要街道游行示威、群體阻止征地拆遷施工、與管理者階層及施工人員發生肢體沖突和械斗等;最后是劇烈的群體性事件,包括攻擊政府執法人員、圍堵圍攻黨政機關并伴隨打、砸、搶、燒等行為,具有較強的暴力性和破壞性。
據調查,當前農村征地拆遷中的群體性事件有兩個發展趨勢:一是暴力化傾向加劇,二是組織化程度提高。前者主要是由于征地拆遷引發的不公平感和對管理者階層“貪污腐敗”的憎惡在普通農戶階層中極易產生共鳴,積聚了一股龐大的民怨之氣,許多普通農戶積極參與事件中。由于村莊的結構易得性,參與者相互熟識和信任,他們之間的互動頻率高、信息傳遞快,因而很容易群情激憤而使行為不受理智控制,卷入其中的農民自我意識明顯下降,普遍產生無法自制的興奮、狂熱、憤怒、失望等情緒,最終出現一系列破壞行為。[15]如果管理者階層和基層政府處理不當,甚至采取壓制打擊措施,那么就容易觸發暴力突發性事件。組織化程度提高是指與之前征地拆遷群體性事件無組織狀態相比,當前征地拆遷群體性事件具有明顯的醞釀、組織和策劃過程,組織性程度明顯增強。[16]其組織者和策劃者一般是中上階層農戶和精英階層中現任村干部的反對派,他們介入其中的目的不同[17],但他們作為骨干分子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對征地拆遷的各項政策有所了解,因而具有較大的抗爭能量,對普通農戶階層的心理和行為產生較大影響,這加大了群體性事件處理的難度。征地拆遷群體性事件的暴力化和組織化發展,增強了它的政治性和社會效應,更容易引起上級黨委政府的重視,也使普通農戶階層的訴求更有可能得到滿足。
2.群體性上訪
群體性上訪又稱群體訪、集訪,是5人以上的上訪類型,它是組織性最強的群體性事件。通過階層分化的視角來看農村的群體訪,會發現群體訪的主要人群是普通農戶階層。由于群體性上訪既需要熟知基層政治體制運作邏輯,又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規范,因此就需要有信訪經驗豐富的組織者,其充任者一般也是中上階層或現任村干部的反對派。群體訪花費較高,包括生活、住宿、交通、誤工等開銷,還包括高昂的組織成本,因此群體訪的訴求對象一般是縣鄉兩級政府,再往上走就只能派代表,進京群體訪極少。在征地拆遷過程中,普通農戶階層群體訪的直接針對對象是管理者階層,但由于它涉及到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問題,且上訪的人數越多、層級越高,它的政治性就越強,給縣鄉主要領導施加的政治壓力也就越大,因此在信訪壓力型體制之下,群體訪就成為縣鄉主要領導亟待處理的政治事件。一旦縣鄉主要領導介入征地拆遷事件,普通農戶階層提出的問題一般都會得到解決或部分解決。在這個意義上,當前我國的信訪體制也成為農村普通農戶階層在村莊利益再分配結構中的救濟渠道。
四、化解農村征地拆遷中階層沖突的策略
綜合以上分析,征地拆遷中的階層沖突和對抗成為農村規模最大、頻率最高、影響最大的社會矛盾,極大沖擊了農村階層關系的整合和農村政治社會穩定,影響了村級組織和基層政府的合法性。然而,沖突并非一無是處,沖突是一個社會過程,它對于社會結構的形成、統一和維持能夠起到一種手段作用,可以激勵社會革新,觸發社會變革。其前提是在沖突發生時社會管理者要真正認識到利益被剝奪階層的處境,了解“他們的憤怒和所遭受的苦難”,并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從而處理好沖突,發揮沖突的積極功能。[18]為此,為了緩解征地拆遷中的沖突,使其向積極方向發展,應該在以下幾方面努力。
1.進一步完善農村征地拆遷補償制度
應進一步擴大征地拆遷補償范圍,將征地拆遷后的殘余地和相鄰地以及經營損失、租金損失及其他附帶損失納入補償范圍。應進一步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使其適應市場經濟和不斷發展的經濟社會生活的要求。應進一步探索補償方式,逐漸建立有效實現農民土地發展權的補償方式,如留地安置。應進一步規范補償分配,提高對土地使用權的補償份額,限制村集體和地方政府對補償款的截留、挪用和拖欠。這些措施的實施可以將大部分利益留給農民,從而使占農村多數的普通農戶階層不再需要通過博弈而獲得征地拆遷的收益。
2.規范和限制村莊利益再分配的博弈空間
要限制管理者階層與精英階層利用權勢在農村征地拆遷及其他利益再分配過程中謀取暴利,進一步規范征地拆遷及其他利益再分配的標準與范圍,縮小和規范博弈空間,打擊非法牟利階層,使農村征地拆遷及其他利益再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維護社會基本的和諧與正義。
3.建立農村社會沖突的安全閥制度
社會安全閥制度是一種機制,它通過潛在的社會沖突來維持階層的和諧。在農村征地拆遷社會沖突中,應該建立各階層間的溝通機制,破除管理者階層和精英階層的壓制、威脅和“一言堂”,暢通農民意愿的表達渠道和情緒宣泄渠道,化解階層間的敵對情緒、誤會與矛盾。在征地拆遷過程中,管理者階層和基層政府應充分調動普通農戶階層的積極性,讓各階層都參與征地拆遷的過程、分享征地拆遷利益以及利益機會,讓他們都享有平等的表達權、知情權和決定權。征地拆遷利益的再分配份額和利益機會應向普通農戶階層傾斜,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建立有保障的生活、消除他們因征地拆遷而帶來的焦慮。只有建立農村安全閥制度并使之發揮作用,才能將社會沖突引向良性發展。
注釋
①劉易斯·科塞:《社會沖突的功能》,孫立平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2頁。②孟宏斌:《資源動員中的問題化建構:農村征地沖突的內在化形成機制》,《當代經濟科學》2010年第5期。③楊華:《農村土地流轉與社會階層的重構》,《重慶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④譚術魁、齊睿:《快速城市擴張中的征地沖突》,《中國土地科學》2011年3期;譚術魁:《中國土地沖突的概念、特征與觸發因素研究》,《中國土地科學》2008年第4期。⑤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⑥歐陽靜:《村級組織的官僚化及其邏輯》,《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⑦賀雪峰:《論土地性質與土地征收》,《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⑧楊華:《“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⑨本文所涉及的“釘子戶”、“上訪戶”概念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援用農村本稱為的是更形象地描述這類群體。⑩田先紅:《基層信訪治理中的“包保責任制”》,《社會》2012年第4期。[11]參見呂德文:《媒體動員、釘子戶與抗爭政治——宜黃事件再分析》,《社會》2012年第3期;陳柏峰:《傳媒監督權行使如何法治——從“宜黃事件”切入》,《法學家》2012年第1期。[12]田先紅:《當前農村謀利型上訪凸顯的原因及對策分析——基于湖北省江華市橋鎮的調查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13]劉燕舞:《當前農村基層組織演變的四種現象》,《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14]盧文剛:《征地群體性事件應急管理探討——以廣州市S鎮為例》,《中國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15]譚崢嶸:《征地沖突與征地制度的完善》,《求實》2011年第1期。[16]梅祥、時顯群:《新時期我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原因及對策》,《中國行政管理》2010年第6期。[17]如維權、謀利或其他的村莊政治目的。[18]蒿婉姝等:《農村征地過程中的階層沖突研究》,《中國土地科學》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