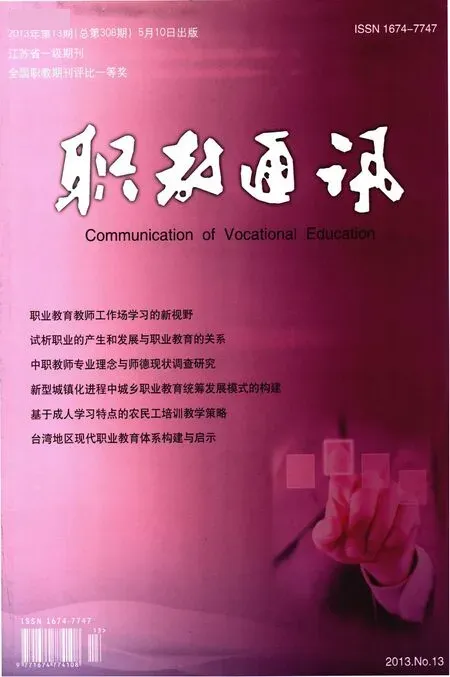“靜音模式”、葛蘭西和職業教育(下)
臧志軍
顯然,富士康是最理想的消滅“人“的場域:在區區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十數萬精力充沛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各異的年輕人,他們被要求按同樣的生產過程、同樣的生產標準從事相似的勞動,他們的日常工作、人際交往、業余生活甚至個人思維無不受到大規模生產方式的規訓以確保生產的流暢。就像所穿著的工作服一樣,他們無需、無法也不能表現任何個人的特性,或者說,對于十數萬的年經人來講,個人在這個場所中是不存在的。也許,正是這種可怕的非存在感才激發了那些消滅自身肉體的沖動。但富士康遠不是唯一一個制造這種現代化非存在感的場所,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中國大概就是一個巨型富士康,哪個企業、哪個機構不在試圖規訓它的員工?不在把那些不“適合于新的生產和勞動形式的人”淘汰或消滅?又有多少中國人真地感覺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把握著自己生活的方向?
這當中還是有悖論的。如果工業化的本質就是消滅“人”,那么,富士康十幾連跳應該發生在工業化的整個過程中,中國因為工業化而死去的人大概可以組成另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了,不應該直到今天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吧!實際上,在有些論者看來,三年自然災害以及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都可以算在工業化或現代化的賬上的。我們當然不必做如是論,還是要就事論事。富士康事件成為關注的焦點,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信息時代讓這類以前被屏蔽的事件無所遁形;工業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把生產與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放大了;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馴服”了,不愿再逆來順受,在反抗無果的情況下就采取了極端方法。
從一個教育者的角度出發,我傾向于認為“人變了”。他們正在形成新一代人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這些新人類從小是家中的“小皇帝”,長大后主動參與了信息時代的構建。這一代人所掌握的學校課本以外的知識的深度與廣度是他們的父母和老師們無法想像的,我甚至相信這一代人之所以陽光、向上、有愛心,不是家長或學校教育的成果,而是他們自我教育或相互教育的偉大成就。他們相信自己應該成為世界的中心,是自己生活的主宰,積累、低調、儉樸之類的詞在他們的詞典里只存在于最少翻動的幾頁上,長輩們的諄諄教誨在他們看來只是《大話西游》里唐僧那句“悟空,亂扔東西是不對的”。
這一代人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了,他們是世界人,他們唱的歌、看的電影、讀的新聞與全球同步,但他們偏偏生活在中國,在這個發展水平離世界水準仍有相當差距的中國。他們是在用信息化時代的身軀做著工業化時代的工作,在用后現代的眼光審視著現代的生活。當他們從網絡、從同伴的世界來到真實的“錫安城”(電影《黑客帝國》中的真正的人類生活的城市),產生失落、恐懼之類的情緒當然是不可避免的,極端的情況就是會懷疑自己在這樣一個現實的世界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我相信,個人世界觀、價值觀以及所掌握的知識的超前與工業生產管理方式的相對落后所造成的對個人價值的否定應該是富士康之類的企業面臨的困境的根源。
有沒有辦法擺脫這種困境?至少有兩種方法:一是改造工業生產管理方式,讓生產與生活不再“異化”,二是改造這些新人類,讓他們重新認同工業化時代的價值觀。就前者而言,我們很遺憾地發現,很少有人主動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更常見的情況是,不同企業、機構不斷強化工業化的管理方式,使那些管理更加精致,就像富士康的“靜音模式”一樣。對于后者,我們更加遺憾地發現,這幾乎已經成為職業教育的通行做法。
想想那些搞軍事化的職業學校、那些沒收學生手機的職業學校、那些禁止學生吃零食的職業學校,無一不是在試圖讓學校回歸到幾十年前曾經成功的教育管理模式,無一不是在試圖復制一個曾經成功的工業化教育形態。實踐者們當然有無數理由證明這些做法的合理性,但教育者還是應該跳出現有的班級、校園甚至這個社會,站在一個超然的高度思考一下“我們的做法真的合理嗎?”
葛蘭西曾認為:“直到現在,每次生活方式的改換,都是通過殘酷的強制,通過樹立一個社會集團對社會一切生產力量的統治而實現的。”這段話放在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都應該是適用的,但在比特化的今天,情況似乎正在發生變化,那個所謂的“社會集團”不再是單向地對個人發生作用,個人也開始通過信息的彌漫對“社會集團”或生產方式施加影響。或者說,個人正在與“社會集團”爭奪對生活與生產方式的控制權。因此,在我們這個社會,盡管有巨大的力量試圖恢復工業化管理方式的強勢地位(就像富士康正在做的),但參與社會生產的人已經變了,隨著這批人逐步成為社會的中堅,傳統的集成化、規范化的管理方式必然發生變化。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職業教育仍然堅持原有的工業化時代的教育方式,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生產方式的阻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