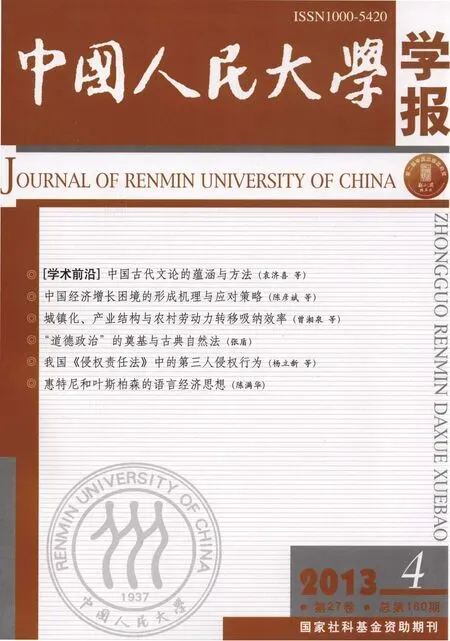學術史視野下的近世反孔運動研究
閆潤魚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鮮明特征是將抨擊的矛頭一步一步指向孔學,延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打到孔家店”儼然成為最具穿透力的呼喊。之后,學界持續不斷的所謂 “五四”研究,非儒反孔自然成為不變的主題。關于五四反孔思潮的興起,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肇始于民初的復辟逆流以及西方列強的刺激。不過,從筆者接觸到的相關著述看,晚明以來的學術變遷已經預示著一場徹底的反孔運動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這個視野下,所謂復辟潮流、西方的刺激等因素,只是發揮了提速和助力的作用罷了。
一、“沖擊”、“回應”與“復古”、“解放”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由于這場運動最鮮明的特征是反對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因此,學界對五四運動的相關研究也大體適用于對反孔問題的解說。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原因,梁啟超在1923年2月撰寫的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是這樣解說的:“古語說得好:‘學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約二十年的中間,政治界雖變遷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個色彩。簡單說,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的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1](P833-834)類似的觀察也出現在陳獨秀的筆下,他在1916年9月1 日發表的《吾人最后之覺悟》一文中稱:“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使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2](P41)
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和學術變遷,描述為由器物 (言技)到制度 (言政)再到文化(言教)這樣三個相繼推展的過程,不僅在親歷這個變遷的人們中比較普遍,就是后世對這段歷史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者也大體認同。如美籍華裔學者周策縱在其 《五四運動史》中就認為: “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經歷了三個階段。起初,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中國只需學習西方之物質文明;但不久,就很清楚,中國的制度與法律也必須要進行改革。到了五四時期,人們又清楚地看到,必須研究構成西方技術與制度的基礎的那些思想與原則,諸如哲學、倫理、科學、文學和藝術等等,都要研究。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新知識分子們猛烈攻擊儒家學說和傳統文化。”[3](P458)
不論是梁啟超借古語表達的 “學然后知不足”的道理,還是陳獨秀的 “西洋文明……促使吾人之覺悟者”、周策縱的 “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之說,均表明推動近世中國變遷的力量無不來自西方世界的刺激。在這種呈 “階段”性演進的邏輯中,致力于 “全人格的覺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樣,都是西方世界 “沖擊”的產物,確切地說,是對西方 “沖擊”的更有力、更全面的 “回應”。
不過,我們若把對反孔問題的討論由西學大規模侵入的晚清上溯到晚明開始,即把該問題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那么,情形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同樣以梁啟超為例,他的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是應五十整壽的 “館翁申老先生”(上海 《申報》館)之邀而作的。五十年即19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所受西方的沖擊已呈愈加深重之勢,這種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他對這個時段中國 “進化”的闡釋,使其論說無意中暗合了日后相當流行的 “沖擊/回應”模式。但在梁氏討論更長時段學術問題的著述中,我們卻能從中發現,按照中國社會和學術自身的發展理路,也完全可以走上 “從文化根本上”覺悟或堅決反孔的路子。在 《清代學術概論》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兩姊妹篇中,梁氏將明末以來近三百年的學術特征概括為 “以復古為解放”。具體而言: “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不止于此,他還進而斷言:“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P6)與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樣,這兩部著作完成的時間也是在20年代前半期,它們所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特別是《清代學術概論》,原本就是為蔣方震撰寫的 《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而成的。在這部論著中,不僅出現了 “文藝復興”等新鮮字眼,甚至還以歐洲的發展模式來闡釋中國的歷史變遷,所謂以“復古”“為其職志者”的清代思潮,“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 ‘文藝復興’絕相類”[5](P3)之類的說法即為明證。不過,由于這些著述探究的是近三百年的學術,其始點是西方大規模侵入之前,即西方的沖擊還未形成氣候的明末,因此,不論作者使用過什么樣的新概念或新方法,其具體論說也只能在中國自身的發展脈絡中展開。盡管在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梁啟超做出了類如 “沖擊/回應”的解釋,但在有關清學史的研究中,斷定 “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的口氣則表明,已趨尾聲的這場以反孔為重要特征的新文化運動,即使沒有西方的沖擊,按照明末以來中國學術自身的變遷也是早晚會發生的,因為非 “反動”孔孟不足以徹底 “解放”學術和思想。
對于梁啟超的 “以復古為解放”說,學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如錢穆在九一八事變后撰寫的與梁啟超同名的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反對以漢學涵蓋整個清學史。與梁啟超強調清學對宋明理學的 “反動”不同,錢著著意強調清學對宋明理學的繼承性,認為宋學是清學一以貫之的主線,研究這個時期的學術 “必始于宋”。究其原因,可以概括為四:一是因為漢學與宋學為敵是近世學術的鮮明特征,如果不了解宋學,自然“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二是漢學雖與宋學為敵,但其思想淵源卻與宋學脫不了干系,那些對漢學的形成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思想大家,或 “靡不寢饋于宋學”,或 “皆于宋學有甚深契旨”;三是判斷漢學各家的高下深淺, “亦往往視其所得于宋學之高下深淺以為判”;四是道咸以來,學術風氣漸變,“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綜之,“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6](P1)我們這里無意對這兩部著作的孰是孰非做進一步討論,相信各自的說法都有成立的依據。況且,在筆者看來,關于近三百年的學術,看重 “反動”的梁啟超并不一定否認某種意義上的繼承,同樣,看重繼承的錢穆也不拒絕承認某種程度上的 “反動”。只是,由于梁啟超的“反動”說直接啟發了筆者對近世反孔問題的思考,故打算以此為參照來梳理明末以來的學術變遷,目的是為闡釋近代反孔運動的興起提供一種偏于學術史的新視角。
二、由“擴充”步入“反動”的儒學
中國一向號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夏以前(包括夏)的歷史,不僅真假難辨,也太過簡略。因此,學界多以周代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起點。周代學術的大興,是在東遷以后的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之所以在這個時期勃興,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二是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7](P2)“天下無道”、 “禮崩樂壞”正是這個時期社會政治環境的真實寫照。這種狀況意味著往昔用以維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風俗制度一一失去效用,一些有識之士因此不得不認真探究這種亂象叢生的原因,并借此尋得補救之方。此外,像孔、孟、莊、韓等天資卓絕的思想家也恰逢此時而生。于是,在時代與思想家的交互影響下,德國哲人雅斯貝爾斯所謂的 “軸心時代”、梁啟超所謂的 “全盛時代”宣告誕生。
這個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百家爭鳴的時代,但其中真正 “卓然自樹壁壘”的,則主要有儒、墨、道、法四家。就其影響而言,初期以儒家為大,后期則以法家為著。因為周代學術的勃興,就是以 “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8](P1)為標志的,而伴隨著秦統一六國進程的展開,法家的影響便逐步突顯出來: “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9](P55)
西漢初年的特殊歷史環境,使儒、道、法等各派又有了用武之地,這些學派之間雖不免有爭論發生,但卻因各自適應了社會的需求,而在客觀上呈現出一種逐步走向合流的趨勢。漢初統治者奉行的學說雖被稱為黃老之學或 “新道學”,但其中卻混雜了多家學派的思想,呈現出 “道表法里”的特點。所謂 “法”,與申不害、韓非、商鞅等人已有明顯不同,其表現形態看上去像是道家一樣的守靜、柔弱。而所謂 “道”,則是與儒交織在一起的, “因為陸賈所把握的是活的五經六藝,而其目的是在解決現實上的問題,所以他把儒家的仁義與道家無為之教結合在一起,開兩漢儒道并行互用的學風”。[10](P63)
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到漢武帝時,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以主張清靜無為為特征的黃老思想,逐漸顯現出其無法滿足現實需要的弊端,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以及君臣倫理等觀念,則因與漢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最終在思想領域取代黃老學說占得統治地位。完成這種學說建構的就是治春秋公羊學的著名學者董仲舒。他在針對漢武帝的征問而連上的 “天人三策”中,根據 《公羊傳》的 “大一統”義,明確提出了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的建議: “臣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建議得到了漢武帝的采納:“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11](P2、525)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 一項基本國策的推行,營造出兩漢異常熱鬧的經學研究氛圍,并形成今文經和古文經兩個分歧日趨明顯的學術派別。
東漢末年,隨著環境的改變,經學逐步走向衰落。繼經學而起的是玄學思潮的興起。玄學上承先秦兩漢道家思想,并將儒道糅合在一起,既克服了漢代經學煩瑣的弊病,又影響了隋、唐佛學,以至宋明理學。北宋時期最有影響的思潮是道學,該思潮 “是由印度佛教傳入與本土道教興起對儒家思想的沖擊,而引發的一場復興儒學的思想運動”。[12](P204)道學內部,人才輩出,學派林立,到南宋中后期,以朱熹為代表的一派逐步在思想界取得獨尊地位。但推演到明朝末期,其獨尊地位又被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取而代之。
由以上對儒學發展史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雖然不同時代的學術宗旨總在回復先秦儒家學說的本來精神,但為了有效地應對各種挑戰,儒學實際上是在不斷地擴展著自己的內涵。董仲舒建議統治者獨尊的儒術,已經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學派的一些思想,顯現出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的某些不同特征。宋代道學雖以儒學為核心,卻大量地吸收了外來的佛教思想和本土的道家思想。但到了明末,儒學過往的發展路徑開始轉向,即思想家們不再以 “擴充”儒學為努力方向,而是要 “以復古為解放”。他們所謂的 “復古”,不啻是在為儒學 “瘦身”,即把后儒填充在儒學肌體中的某些背離原始儒家的思想成分 “剔除”出去。
王學是當時的顯學,所謂解放, “第一步”便是 “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之后,則有第二步、第三步,直至第四步 “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13](P2)梁 啟 超 曾 將學術思潮分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在他看來,學派的發展總是循環的: “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14](P6)以學術演進的這種 “公例”來檢驗近代反孔運動發生的必然性,則可謂 “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
若就具體情形進行分析的話,筆者以為走向“反動”孔孟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學術發展的慣性使然,二是孔孟或原始儒家神秘性褪去的結果。就前者言,中國的學術發展既然步上了 “以復古為解放”的軌道,那么,在總結、概括和繼承夏商周三代文化基礎上而形成的所謂原始儒家,顯然不是 “復古”的終點。在學術發展的慣性作用下,原始儒家早晚都會遭遇被 “反動”的厄運。就后者言,對儒學一步一步地 “反動”,實際上是在為徹底清算孔孟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做著準備工作。因為,不論是心學還是理學、是宋學還是漢學、是嫡出還是庶出,都是孔子后學。他們之間的相互攻訐,最終會殃及原始儒家。以今文經學者廖平為例,其秉承 “先攻之……后救之”[15](P720)、“為學 須善變”[16](P721)宗旨而進行的學術活動,就隱含著對孔子的大不敬。他使讀者“迷惘不得其要領”[17](P724),即使 “從事漢、宋工深者”,也 “轉多迷罔”。[18](P785)學術思想一旦被徹底攪亂,真孔假孔一旦辨識不清,徹底反孔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梁啟超的 “以復古為解放”說,與清代學術史的演進情形基本吻合。正因為如此,持 “復古”說的也就不止任公一人。比如清末的皮錫瑞,他在 《經學歷史》中雖無意揭出有清一代經學變遷的 “解放”意蘊,卻也劃出了明確的 “復古”輪廓: “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尟。說經者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19](P376)有些學者,雖然在經學流派的歸屬上有所不同,但對 “復古”趨勢的觀察卻無歧見,比如相對偏于經古文學的葉德輝認為: “學既有變,爭亦無已……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20](P20)而相對偏于今文學的蒙文通在 《經學導言》中也有類似的議論:“近三百年來的學術,可以說全是復古運動,愈講愈精,也愈復愈古,恰似拾級而登的樣子……到了王陽明以后,學問的前進,便是復古。從明末到現在,只是把從王陽明起直到孔子時候的學術,依次的回溯一番便了。”[21](P10)再比如,五四時期有相當影響的青 年啟蒙思想家傅斯年,早在梁啟超論清學史的那兩部著述問世之前,就表達了類如學派循環的觀點,并揭示出反孔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在他看來,康有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學問的結束期,而 “中國人的思想到了這時期,已經把 ‘孔子即真理’一條信條搖動了,已經臨于絕境,必須有急轉直下的趨向了。古文學、今文學已經成就了精密的系統,不能有大體的增加了,又當西洋學問漸漸入中國,相逢之下,此消彼長的時機已經成熟了”。[22](P230)這些議論不僅解釋了過往的歷史,也預測了反孔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
三、“復古”資源與“反孔”力度
事實上,不論是就中國學術走上 “以復古為解放”的歷史看,還是考察更長的歷史時段,反孔都非始于五四時期。在 “百家爭鳴”的先秦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也像任何一個學派一樣,曾是其他學派攻訐的對象,甚至其內部還分化為八個流派。即使是在實施 “獨尊儒術”的國策后,誹孔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不過,在經歷了一步又一步的 “以復古為解放”的學術變遷后,對孔子孔教表示不滿的人很明顯地呈增加之勢。比如,一生思想學說復雜多變的章太炎,在1902年撰寫的 《訂孔》一文中,就曾借日本人遠藤隆吉之口激憤地指出: “孔子之出于支那,實支那之禍本也。”[23](P179)而五四時期的反孔健將吳虞,也早于 《新青年》之前就有批孔的文字面世,其1910年9月撰寫的 《辨孟子辟楊墨之非》中就有這樣的議論: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專制,曰教主之專制……教主之專制,極于孔子之誅少正卯,孟子之距楊、墨。”[24](P13)
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學術界的反孔之路已由像吳虞這樣的 “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25](P2)開辟出來。由是,在多種因素的刺激下,反孔很快演變為激進思想界的一種群體性反應。除急先鋒吳虞發表 《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吃人與禮教》以及 《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文繼續 “反對孔丘”外,被錢玄同認作 “可以做打真正老牌的孔家店的打手”有 “胡適、顧頡剛之流”; “配做” “冒牌的孔家店”“打手”的有 “陳獨秀、易白沙、胡適、吳敬恒、魯迅、周作人諸公之流”。[26]這些 “思想很清楚的”打手們,將孔家店里的 “貨物”一一盤點出來,予以清算。諸如陳獨秀的 《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孔教研究》等;易白沙的《述墨》、《我》、《戰云中之青年》、《孔子平議》、《諸子無鬼論》等;魯迅的 《狂人日記》、 《我之節烈觀》、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很顯然,“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的學術 “反動”,已推演為學術的主流。
當時,賦予 “對……學而得解放”的理由大體有二:一是認為孔孟要為當下令人難堪的現狀負責;二是認為孔孟之道不適應現代生活。這種論證方式與之前的 “復古”情形頗為相似。比如, “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就是因為步入衰落期的程朱之學給學術和政治社會帶來太多的災難。學術方面, “晚明理學之弊,恰如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之景教。其極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閉塞不用,獨立創造之精神,銷蝕達于零度。夫人類之有 ‘學問欲’,其天性也。 ‘學問饑餓’至于此極,則反動其安得不起?”[27](P7)政治社會方面,“晚明政治和社會所以潰爛到那種程度,最大罪惡,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巴結太監,魚肉人民。我們一點不能為他們饒恕。卻是和他們反對的,也不過一群上流無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幾句 ‘致知格物’的口頭禪做幌子,和別人鬧意見鬧過不休……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28](P94-95)同樣,在五四新文化者的眼中,孔孟也像晚明的理學一樣,嚴重地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如吳虞借李卓吾的說法所表達的:“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二千年以來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為是非,此其所以無是非也。”[29](P6)不僅近三百年的文化衰頹,就是近三百年的國勢破敗,也無不為尊奉儒教所致。 “向使無儒教之束縛拘攣,則國內之學分歧發展,骎骎演進,未必無歐美煒曄燦爛之觀……由此觀之,儒教之影響于亡國亡種實大矣。”正因為儒家思想不僅 “禍國殃民,為禍之烈,百倍于洪水猛獸也”[30](P64),也與進入共和時代的需求不相適應, “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貴賤不平等之義當然劣敗而歸于淘汰”[31](P5),所以,中國欲改變衰敗現狀,就必須下狠心打倒“孔家店”。
至于 “復……之古”方面,情況與前相比則有了明顯的不同。前四步,每 “解放”一步就有更 “古”一些的儒學流派成為 “復”的對象。但“對于孔孟而得解放”這一步,由于儒學的內核已在價值層面被棄之,所謂 “復古”,就不可能也沒必要從業已走到盡頭的儒學資源庫中挖掘。本來, “復”的對象通常也是用以實現 “解放”的憑借。而當孔孟成為避之不及的邪惡代名詞時,實現 “解放”的武器便只能從儒學外部去獲取。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與反孔或重新評價孔子相伴的學術現象,一方面是對子學的提振,另一方面則是對西學的大量引進。比如章太炎,他的 “訂孔”雖然承接了傳統儒學的統緒,卻以匯子學入儒學或以子學證經學、攝取佛學、 “旁采遠西”為其著力點。而為中國政治改革獻身的譚嗣同,其所思所想也與他所宗奉的墨家俠義精神及學術思想有密切關系。在 “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子學矯正儒學偏頗甚或否定儒學價值的做法繼續沿用。以圍繞著《禮運》“大同”說的爭論為例,當時有尊孔者提出, “大同”說合于共和政制,而吳虞則認為“儒家大同之義本于老子說”, “《禮運》‘大同’之說,乃竊道家之余緒”。[32](P39)陳 獨 秀 也 否認 《禮運》“大同”說本于孔子,認為 “古之孔教徒鄙棄”該說。他還進一步指出,即使 《禮運》出于孔子,但 “若據此以為合于今之共和民選政制,是完全不識共和為何物,曷足與辨哉?”[33](P120)話語中流露出試圖將共和民選價值與孔子剝離開來的意向。當然,包括陳獨秀在內,他們對于不同的子學或子學的不同方面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大體看來,一些與儒學價值相通的子學思想成分也成為被駁斥的對象。比如,陳獨秀在分析造成國民的退讓、茍且、無所作為的性格特征時,就曾指出: “吾國舊說,最多莫如孔老,一則崇封建禮教,尚謙讓以弱民性;二則雌退柔弱為教,不為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為之風于焉以斬。” “魏晉以還,佛法流入,生事日毀,民性益偷,由厭世而消極,由消極而墮落,一切向上有為,字曰妄想,出世無期,而世法大壞。”[34](P626)
與有條件地提振子學相比,作為解決 “對于孔孟而得解放”使命過程中武器短缺困境的嘗試,新文化派重在旗幟鮮明地引進以德先生、賽先生為代表的西學,并據此來評判或重新估價儒學的是非得失。“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我們都不推辭。”[35](P243)“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36](P9)依據西方的經驗事實,“德賽兩先生”被確立為衡量一切社會現象的價值準則。易白沙在否認中國古代文明、古文奇字出自孔子的說法時,也要參照西方的做法:“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煥發,睿思幽渺,靈耀精光,非一時一人之力所能備;文字為一切文化之結晶,尤難專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臘、羅馬文字者,不詳始作之人。中國文字,亦復如是。”[37](P92)
當然,上述情形并不能否認新文化運動發動前社會政治現實對于學術 “刺激”的影響。事實上,正是這個時期政治生活方面發生的一些變化,不僅為反孔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理由,也在客觀上推動了反孔的進程、增強了反孔的力度。其中的因素,突出者至少有三:一是復辟思潮的興起。儒學原本是為帝制統治服務的,帝制的結束已使其影響日漸式微。面對帝制結束后不久發生的復辟思潮,那些信奉民主共和價值的人們很快意識到 “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38](P71),反孔的政治色彩遂愈加濃郁起來。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告終。 “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39](P834)三是西學的大量涌入。外來的新文化不僅充實了走在 “對于孔孟而得解放”路上的新文化人士的頭腦,也使其有條件在比較“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的東西兩種文化的基礎上做出取舍。 “使今猶在閉關時代,而無西洋獨立平等之人權說以相較,必無人能議孔教之非。”[40](P78)“吾人生于二十世紀之世界,取二十世紀之學說思想文化,對于數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較的批判,以求真理之發見,學術之擴張,不可不謂今世當務之急。”[41](P660)西學無疑為反孔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這些新增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五四新文化運動 “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的步伐邁得更加決絕,言辭更加尖刻。誠如范樸齋評論吳虞的反孔時所言:“自尊孔黜百家而后,后漢王充始著文問孔,歷二千年而有明李贄之誹孔,后贄三百年,先生再起而斥孔。其斥之也,至呼孔子為盜丘,謂其罪浮于跖。噫,是何惡之深也!蓋先生之所以斥孔,已不止于是非之論間,舉倫理、政教諸說,盡斥之,并托古改制之說,亦斥之。以其阻進化、弱國家、害人群,大不合于時宜也。”[42](P488)雖然在吳虞是否配做 “孔家店打手”的問題上,學界有不同看法①胡適認為吳虞是 “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和陳獨秀是當時 “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參見胡適:《〈吳虞文錄〉序》,載 《吳虞文錄》,1~4頁,合肥,黃山書社,2008。錢玄同則認為吳虞既沒資格 “做打真正老牌的孔家店的打手”,也不配做 “冒牌的孔家店”的打手,他充其量是 “孔家店里的老伙計”。參見XY: 《孔家店里的老伙計》,載 《晨報附刊》,1924-04-29。,但五四時期反孔較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激烈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當然,其激烈的程度也是隨著社會政治事態的變化而不斷加劇的。陳獨秀在 《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 《敬告青年》中雖以諸如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句式,表達了他崇尚西學的文化價值觀。但與后來的文字相比,則遠遠算不上尖刻、犀利。“儒”和 “孔”在全文各出現過一次,在“實利的而非虛文的”部分中,他以批評的口吻稱: “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而在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部分中,則非但不以孔子為退隱的代表,反以其為 “進取”的楷模,表示 “吾愿青年之為孔、墨,而不愿其為巢、由”。[43](P3-9)但伴隨著尊孔復辟逆流的上演,陳獨秀對待孔子儒教的態度明顯地激進起來,不僅 “孔”、“教”并用,還宣布不作真假孔子之分,一律予以打擊。
當時的反孔派人士并非不懂原始儒學與變異后的儒學之間的區別,但他們的這種意識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徹底反孔的態度與立場。以易白沙的 《孔子平議》為例,文章雖然在一開頭就對“天下論孔子”的種種 “瞽說”提出批評,明確反對把事關風俗人心的問題交由孔子負責: “孔子未嘗設保險公司,豈能替我負此重大之責?”他也承認 “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悖孔子之精神”,因為 “孔子宏愿,誠欲統一學術、統一政治”。不過,整篇文章的核心部分卻在從 “孔子之自身”尋找 “以何因緣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的原因。他所列的原因有四個方面:一是 “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二是 “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三是 “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藉口”。四是 “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這些原因足以讓易白沙宣布:野心家之所以利用孔子, “是不能不歸咎孔子之自身矣”。[44](P85-97)陳獨秀反對區分真假孔子的理由也大體相同: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為二,且謂孔教為后人所壞。愚今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不依傍道法楊、墨,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為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45](P640-641)關 于 五 四 時 期 反 孔 派不分真假孔子一律打倒的態度,胡適在向中國少年介紹 “‘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時,做了最為淺近的說明:“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46](P4)
西學或近世西方的快速發展之于五四新文化者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影響的發揮卻是緣于中國自身的學術 “反動”。如果歷史的發展沒有進到西學大規模東漸的時代, “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或許只能在子學或前孔孟的時代尋找。當西學豐富或更新了中國人的 “復古”資源庫時,假近世西方發展優勢的西學便逐漸取代子學,成為新文化界的寵兒, “復古”必然地演變為 “崇西”,孔家店作為西學的對立物,不可逃匿地成為被搗毀的對象。
自明末中國學術步上 “以復古為解放”之路后,到清末民初,已然走到 “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一步。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派人士接過學術“反動”的接力棒,以搗毀孔家店為目標,將“對于……解放”的事業轟轟烈烈地推展開來,使社會人心最大限度地從孔孟的思想束縛中 “解放”出來。在 “復……之古”方面,子學的影響隨著全盤性反傳統熱潮的涌動,呈現出愈來愈弱之勢,中國學術的發展無可奈何地進入了后經學、后子學的時代。
[1][39] 梁啟超:《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34][35][36][38][40][41][43][45] 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長沙,岳麓出版社,1999。
[4][5][13][14][27][28]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6][15][16][17][1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7][8]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9] 桓寬:《鹽鐵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0]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11] 班固:《漢書·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12] 周山主編:《中國學術思潮史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
[19]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20] 葉德輝:《郋園書札·與戴宣翹校官書》,民國觀古堂本。
[21] 蒙文通:《經學導言》,《蒙文通文集》,第三卷,成都,巴蜀書社,1995。
[22]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3] 章炳麟:《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24][42] 吳虞:《吳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5][46] 胡適:《〈吳虞文錄〉序》,載吳虞:《吳虞文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
[26] XY:《孔家店里的老伙計》,載 《晨報附刊》,1924-04-29。
[29][30][31][32][33] 吳虞:《吳虞文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
[37][44] 陳先初:《易白沙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