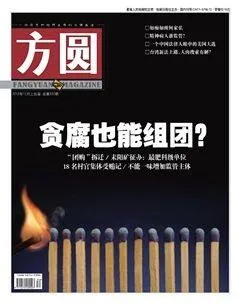18名村官集體受賄記
【√】利用職權制造不公平的社干部們,在收受賄金時卻十分講究“公平”,必須人手一份,數(shù)額一樣。這種“公平”如同一條麻繩,將社委們?nèi)缥涷埔话憷υ谝黄穑嚼υ骄o,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2009年9月的一天,梁國錦在飯桌上習慣地接過李亞金遞上的一個信封,厚實的手感讓他不用看也知道信封里是什么,有多少。和他一樣收到信封的還有和他同村的其余8個人,飯桌上的觥籌交錯沒有因此而被打斷,仿佛這一動作沒有發(fā)生過。
多個類似的情景在2012年8月間統(tǒng)統(tǒng)定格。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批準逮捕廣州市白云區(qū)棠景街棠溪村第一經(jīng)濟合作社社長梁國錦和第一、第十三、第十四經(jīng)濟合作社,崗貝片經(jīng)濟合作聯(lián)社等社委11人及5名行賄人(另有若干村干部在逃、1名被取保候?qū)彛?br/> 村干部在飯桌上收受上百萬元賄金,18名“村官”涉嫌集體受賄647萬……棠溪村這種收“好處費”的習慣由來已久,至該案案發(fā)前已持續(xù)多年。10月25日,該案在廣州市白云區(qū)法院開庭審理,被告席上的村干部大多認為收“茶水費”不過是一種行規(guī)罷了,就類似買入場券,你來我的地盤兒承租承建,就得買票進場,僅此而已,所以他們收錢時也不遮掩,更沒想到收“茶水費”竟然算是受賄,屬于違法犯罪的行為。
酒桌上的投票
棠溪村共設有十四個經(jīng)濟合作社,村子的部分集體財產(chǎn)由幾個經(jīng)濟合作社共同所有,所以這個村子又分別由幾個經(jīng)濟合作社成立了崗貝片聯(lián)社、趙家片聯(lián)社、黃家片聯(lián)社、梁家片聯(lián)社以及長崗片聯(lián)社。
“每個社經(jīng)濟都是獨立的。片聯(lián)社由其所屬的經(jīng)濟合作社共同管理,片聯(lián)社的財產(chǎn)和開支都歸所屬經(jīng)濟合作社支配。”梁國錦說,每個經(jīng)濟合作社設有包括社長、副社長、會計、出納等5名管理成員,而片聯(lián)社則由其所屬的經(jīng)濟合作社分別推選一人形成領導班子進行管理。
崗貝片聯(lián)社由第一經(jīng)濟合作社(下文簡稱一社)、第十三經(jīng)濟合作社(下文簡稱十三社)和第十四經(jīng)濟合作社(下文簡稱十四社)組成,由三名社委共同管理。
村子的土地、集體財產(chǎn)大部分由合作社集中管理,掌握著“經(jīng)濟大權”的社長,說話有時比村長更有分量。
“我國法律并沒有要求鄉(xiāng)一級行政單位對工程項目進行公開招投標,所以一個項目給誰不給誰完全是由他們自己做主的。”該案承辦人、廣州市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處李健文告訴《方圓》記者,村干部們在土地承建、公用物業(yè)出租方面掌握著“說一不二”的權力,他們相互之間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即使有上級單位來檢查也不會發(fā)現(xiàn)任何問題,因為表面上的程序都是合法的。
2009年上半年,棠溪村崗貝片聯(lián)社村民集資的崗貝路拆舊建新(金光廣場)項目招投標,化州工程隊負責人李亞金便找到一社社長梁國錦,希望梁能幫忙“活動”一下,讓他接到這個項目。
為此,李亞金特地請梁國錦等人到酒店吃飯。在席間,李亞金仔細數(shù)了一下,來吃飯的有一社、十三社、十四社和崗貝片聯(lián)社的18名社委以及一個包工頭,私下了解,這個包工頭原來是棠溪村黨總支書記介紹來的,在這之前,書記和18名社委就和這個包工頭談過合同、預算等問題。金光廣場項目的承建商也將在他和這個包工頭中誕生。
上菜前,社長梁國錦開始主持投票,“大家在小紙條上寫下同意誰來承建金光廣場項目,無記名投票。”不久,這個集資兩千多萬的項目承建招標就在這18張小紙條上有了定論。
除了一兩張反對票之外,李亞金高票獲得承建資格,他對此并不意外,事先找到梁國錦談這個項目的時候,梁國錦已經(jīng)承諾與社委們討論一下。
棠溪村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村里物業(yè)如果是整棟樓承租、租賃金額達1000萬元以上或承租期限十年以上的大合同都必須由負責管理的合作社全部社委共同簽名。有梁國錦的支持,與競爭對手比起來,李亞金的勝算更大。
拿到了金光廣場項目的承建資格,高興之余,李亞金也沒忘了“規(guī)矩”,他掏出一摞尚未拆封的現(xiàn)金,在場的社委都拿到了5萬元。“即使是投了反對票的社委,我也會給他一份好處費,這邊的習慣一直都是這樣的。”
在飯桌上花了18萬
2009年8月,棠溪村一社辦公樓下的公布欄上貼出一張A4紙,由一社村民集資的農(nóng)民公寓建設項目對外招投標。李亞金又撥通了梁國錦的電話。
幾天后,李亞金讓女婿在花都區(qū)的一家大酒店開了個包間。到了午飯時間,一社社長梁國錦、副社長梁國深和梁兆文、出納梁志成、會計梁國榮五人先后來到,五六個人在飯桌上談工程合同、預算、工程材料等事宜。
經(jīng)過幾次商談,各種事項雙方都談得比較滿意。在審核完工程圖紙后,一社的五名社委們集體同意由李亞金來承建,李亞金認為,自己該有所表示了。
2009年中秋節(jié),廣州已經(jīng)進入微涼的金秋,李亞金約上梁國錦等五個社委一起去80公里外的從化市泡溫泉,同行的還有4個一社村民代表。趁著還沒上菜的空當,李亞金從身旁的袋子中掏出9個用信封包好的東西,逐一派給在場的5名社委和4個村民代表,他沒有說包的是什么,也沒有人問。這頓飯,還未結(jié)賬,李亞金就已在飯桌上花了18萬。
2011年,農(nóng)民公寓項目竣工,由棠溪一社社委、股東代表、社員代表負責驗收。為了順利驗收,李亞金又把這9個人聚到一塊兒“敘舊”,這一次,李亞金給每個人塞了1萬元。“錢應該都是直接從銀行里取出來的,很新,還沒開封,李亞金還用黑色塑料袋一萬塊錢一沓這樣子包好。”梁志成回憶起當時拿到的好處費說。
拿到項目就得給紅包、給“好處費”,行賄的和受賄的雙方對此早已心照不宣。“按照經(jīng)濟社的規(guī)矩,要拿到工程就必須給每個社干部派紅包,李亞金拿到這個項目也是(因為)派了紅包的,這是潛規(guī)則。”崗貝聯(lián)社社長梁應祥在供述中交代,“這些工程回扣也是不該拿的錢,是不合法的錢,但這些都是潛規(guī)則。”這樣的默契,使得現(xiàn)在形形色色的行賄方式、各種復雜隱秘的手段在他們之間都顯得累贅。
行賄者與受賄者的默契
有不少落馬的貪官在懺悔時總會說,很多人為了求他們辦事,一定會想方設法地塞錢給他們,很多時候收錢都是身不由己。而棠溪村的社委們,在這一方面則更顯“主動”。
2009年5月左右,李亞金接到一社社委的電話,對方要求他“今天過來一社這邊,有些事要商量。”帶著疑問,李亞金來到一社辦公點,等著他的還是五名社委。
梁國錦主動以“最近急著用錢”做了個開場,六個人商量決定把工程造價提高一點,讓社委們賺點“水錢”,于是,該項目工程由12層改為16層,面積由2.1萬平方米增加到2.9萬平方米,還提高了工程單價,這一改就產(chǎn)生了500萬元差價。
2011年8月29日,一社社長梁國錦、副社長梁國深和梁兆文、出納梁志成與李亞金再次約定在一社辦公點見面。按照5月份商量的結(jié)果,社委們讓李亞金以“工程款”的名義填了一張面額為250萬元人民幣的收據(jù),然后李亞金和梁國錦、梁兆文、梁國深在收據(jù)上簽字確認,梁志成當場做了一份提取大額資金申請表,并從保密柜里拿出公章蓋在申請表上,拿著這份申請表,李亞金來到廣州農(nóng)商銀行蕭崗支行從棠溪村一社的賬戶上提取了250萬元人民幣現(xiàn)金。
剛提完現(xiàn)金,社委便來電話“你開車去云城西路,我們在那兒等你”。在這條車水馬龍車道的邊上,梁兆文和梁國深從李亞金車里拿走了這筆已“支付”給李亞金的“工程款”。
梁國錦、梁兆文、梁國深、梁志成以及未參與商量的會計梁國榮平分了這筆錢,每人分得50萬。
“這已經(jīng)成了他們的土規(guī)矩,承包工程必須給村干部好處,而拿到好處的村干部也必須如實地與其他人平分。”李健文說,行賄者與受賄者之間的默契由來已久,這樣的平衡亦從未被打破過,它游走于法律背面。在這種默契的支配下,雙方已絲毫不費心思遮掩自己的欲望。赤裸的意圖,直白的方式,使法律形同虛設。
“一直都是每人一份的”
位于廣州三元里大道1183號的商業(yè)樓是棠溪村一社的物業(yè)之一,2007年,嚴家誠想做七天連鎖酒店,于是找到梁嘉良,看有沒有合適的地方,梁嘉良是棠溪五社的副社長,梁嘉良想了一會兒,告訴嚴:“一社有一個合適的地方,地址在三元里大道1183號,你租那棟樓挺合適的,我們合伙成立一間公司,把三元里大道1183號整棟租下來再轉(zhuǎn)租出去。”
嚴家誠同意了,隨后在白云區(qū)工商分局注冊成立成社物業(yè)管理有限公司,股東是嚴家誠、梁業(yè)潮、黃國偉。梁嘉良不掛名為股東,也沒有出資。嚴家誠和梁嘉良兩人商量分工,由嚴家誠談七天連鎖酒店的業(yè)務,梁嘉良則負責與一社方面聯(lián)系租地的事情。
2008年,梁嘉良找到一社社長梁國錦,提出整棟承租1183號商業(yè)樓的想法,雙方就租金價格和租用期限等事宜談了兩個多月。
嚴家誠好不容易與七天連鎖酒店談妥業(yè)務簽約的時候,梁嘉良卻帶來一個讓他左右為難的消息:要與一社租賃三元里大道1183號,就必須給每個社委20萬。
這邊已與七天連鎖酒店簽好約,那邊卻要給好處費才能繼續(xù)談下去,如果不花錢打點,就要遭受違約的巨額損失。權衡之下,嚴家誠無奈地答應了梁嘉良的要求。2007年12月31日,嚴家誠的公司與一社簽訂了租用三元里大道1183號的協(xié)議。2008年,嚴家誠與梁國深先后見了三次面,并給一社五名社委送去了100萬元人民幣。拿到錢后的梁國深,將錢平分成五份,梁國錦、梁兆文、梁志成和梁國榮每人20萬元。
“這些錢是我向朋友借來的,我知道我送錢給一社社委的行為是違法的,但當時我如果不能把三元里大道1183號租下來,要虧很多錢,走投無路了,我只能給他們好處費。”對此,嚴家誠說,雖然這100萬是給一社社委們的好處費,但他租賃這棟大樓并沒有得到任何優(yōu)惠,相反,嚴家誠租賃該物業(yè)還比當時的市場價格要高。
從幾個社委們的供述看,每個人收好處費的心態(tài)各異,社長梁國錦一直矢口否認收受賄金,而一些社委收好處費時的心情卻非常矛盾,梁國深第三次從嚴家誠手里取走錢的半小時后,梁志成給嚴家誠打來電話:“你為什么叫梁國深拿錢給我?我不要,你現(xiàn)在過來把錢拿回去。”嚴家誠只好來到梁志成家樓下。
“你這樣把錢退給我我很難做,一直都是每人一份的。你要是不要這筆錢的話,要不就讓你女兒在我的公司里擔任股東吧。她掛名擔任股東,也可以有收入的。”梁志成考慮了一會兒,答應了嚴家誠這個折中的辦法。
當法律遭遇宗族
從片聯(lián)社的名稱不難看出,棠溪村主要有幾個大姓,而合作社社委又是由社員投票選舉出來的本地人。簡單直白的賄賂背后,宗族因素不容小覷。
“要不是有群眾舉報,這樣的案件我們一般很難發(fā)現(xiàn)。”有18年辦案經(jīng)驗的廣州市檢察院檢察官坦言,“在這些村子里,有時候宗族關系的力量比法律更有作用。”
這種規(guī)范模仿著國家法律的機構和符號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著法律的記號和功效。它們同樣是一種“法”,至少是一種“準法”,是一種具有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準法”,主要依靠血緣、情感來維持。
村里的村民大多同姓,之間多少都有點沾親帶故,這種宗族關系把村民們聯(lián)系得十分緊密。在這宗案件中就有所體現(xiàn),辦案人員告訴《方圓》記者,因為涉案的社委在村內(nèi)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家族成員眾多,彼此相互維護,就像一個碉堡,從外部深入到村民當中了解案情絕對是一個棘手的工作。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移送起訴后發(fā)現(xiàn)一些我們沒有辦法取得的證據(jù),犯罪嫌疑人的律師那里都有。”李健文告訴記者,這個案件中有一個嫌疑人需要村委出具他是成員的證明,但是村委始終沒有出具,最后只能請街道辦事處出面協(xié)調(diào),類似的情況很多很多。只要集體經(jīng)濟發(fā)展良好,村民年底能分得滿意的紅利,就不會有人對村干部受賄的行為提出異議,村(社)務公開制度形同虛設。社委們和村民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他們更習慣遵循自己定下來的“規(guī)矩”。在這種狀態(tài)下,村民對村干部的工作幾乎沒有起到監(jiān)督作用,在他們看來:反正,村官都是各大家族輪流坐莊的,只要自己該拿的錢能拿到手就行了。
2009年年中,由于經(jīng)濟社在建設金光廣場過程中資金短缺,為了籌集建設資金,崗貝片聯(lián)社社委梁樹潮提出將該物業(yè)提前由一個叫陳飛躍的老板承租,并要求陳飛躍支付400萬元作為承租的定金。一天,梁樹潮、梁國錦、梁偉東就召集所有副社長以上的社干部和梁應祥、梁兆星、梁應軍在聯(lián)社的辦公室開會,討論承租事項,還帶來了由陳飛躍承租該項目的合同。
參加會議的社干部討論通過了這個事項,梁應祥在供述中提到“我認為該合同不合理,期限太長,且租金遞增慢,在會上我一直都不同意將該廣場以這個合同形式租給陳飛躍,還拒絕在該會議記錄上簽名。但是我在承租合同上簽了名,因為這件事情不是我一個人能改變討論結(jié)果的,在其他社干部都同意該合同的情況下我只能簽名”。參加會議的社干部在現(xiàn)場都簽了名,會后,梁應祥會逐一上門找未參加會議的社干部,讓他們補簽名。
簽完合同后,梁樹潮就從汽車尾箱拿出幾個塑料袋子裝好的現(xiàn)金到聯(lián)社辦公室分錢,“總共有100萬元,每個社干部分5萬元,剩下的要給推薦人。”梁樹潮向在場的社干部解釋。這次會議沒有所有人到齊,一社、十三社、十四社和片聯(lián)社的社長們按照各自社里人數(shù)瓜分了這筆“紅包”。
“利用職權制造不公平的社干部們,在收受賄金時卻十分講究‘公平’,必須人手一份,數(shù)額一樣,即便是投反對票的社干部、即便是沒在受賄現(xiàn)場的社干部,也會為他留有一份。”李健文告訴記者,這種所謂的“公平”如同一條麻繩一般,將社委們?nèi)缥涷埔话憷υ谝黄穑嚼υ骄o,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tài),這樣的狀態(tài)讓他們感到安全,也讓這個“土規(guī)矩”得以“名正言順”
就正如在庭審現(xiàn)場,有的村干部為自己辯解說的那樣:“大家都是一起收錢的,別人都拿了錢,就我一個人不拿的話,等于和所有人對著干,大家都是村子里的人,平日低頭不見抬頭見,這樣做的話以后在這個領導班子里、這個圈子里、這個村子里都沒法混下去,況且大家都這么做,我也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