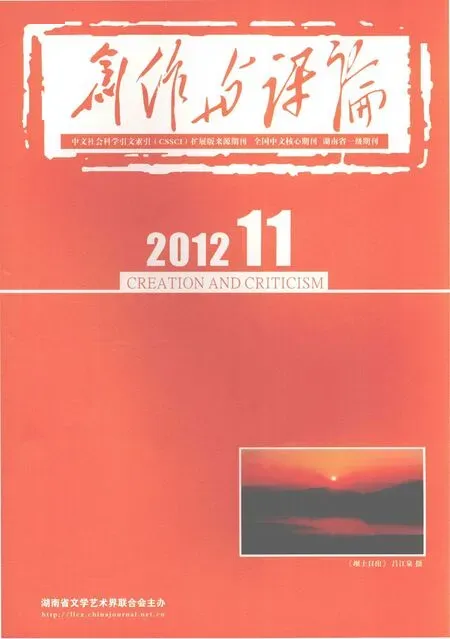“大江東去”與“尋常巷陌”——彭國梁散文論
■ 周荷初
一
彭國梁稱得上一位持之以恒的散文家。不過,他很少寫純粹的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而是多年來致力于“大散文”的創作。我稱其為“大”,首先是題材所涉甚廣,歷史、文化、民俗、風物、藝術乃至街頭小景,在在皆有;其次是文體不拘格套,舉凡叢書、日記、隨筆、雜記、序跋,皆可釀制出散文佳作。正應了魯迅先生那句話:“散文的體載,其實是大可隨便的。”再者,他那結集的文化隨筆,視野寬闊,體現出一種大境界大氣象。以上恐怕是我們探測彭國梁散文創作的基本前提。
其實,在各種文學樣式中,散文是最難藏拙的,因為其中最易于辯識出作者的才情、稟賦和各方面的修養。因此,清人為文很講求“學”與“文”的綜合,首先是好的學者,然后才是好的詩人、文章家。像顧炎武、黃宗羲、姚鼐,乃至駢文圣手汪中,誰不是第一流的學者?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五四”以來的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散文大家,你讀他們那些佳作,無不是揉合作者的文化積養、國學根基、藝術感覺及生活體驗才形成獨自風貌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只有廣采多識,綜學博觀,才能獲得更廣闊地反映生活的創作活力與源泉,才能促進作家對社會、人生更深層次的體悟與思考。
彭國梁自然不乏作為優秀散文作家必備的學養、素質和生活體驗。他雖不以學者自命,但實際上是一位“學者型”的作家。他藏書近三萬冊,從那本記書人書事的《書蟲日記》中便不難領略:買書、藏書、讀書、編書、寫書,已成為他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你讀他那本由隨筆聯綴而成的著述《中秋》,其中鉤沉史實,廣征傳說,對中秋節的由來、變遷、內容,各地中秋節俗的異同,皆有精到的闡釋,所引錄的典籍包括歲時風土,詩文書畫,野史雜記等等,其獵涉之廣,可見一斑。從彭國梁的個人簡歷中便可得知,他著書二十多本,主編各類書籍一百余種。其中與楊里昂先生合作主編的“中國傳統節日系列”就有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陽等八種;《跟魯迅評圖品畫》等魯迅系列五種。他如果沒有廣泛的閱讀,是不可能編那么多書的。他既然編著了那么多的書,而且不少都是極有分量的好書,說他是“學者型”的作家自然也就是名至實歸了。
然而,知識結構層次固然是寫散文的一種優勢,問題在于,并非書讀得越多散文就寫得越好。事實上,有些學者恰巧因讀書甚多,眼界過高,下筆過于矜持,寫出的文章反而情趣稍遜。清人黃宗羲在《思舊錄》中曾批評一代文宗錢謙益的文章“不能入情”,乃此之謂也。在黃氏看來,有了學問,還要深于情而工于文,才能寫出好的散文。用今天的話說,即作家的感覺、才氣。彭國梁早年是以詩人名世,他屬于那種自我意識強烈,率性豁達,具有浪漫氣息的性情中人。他與江堤、陳惠芳發起的新鄉土詩派,是一個圍繞“城鄉兩棲”和“精神家園”而寫作的主題性詩派。這對他后來寫作文化隨筆和城市散文皆不無影響,或者說,后者的某些命題,即是對前者的回應。更重要的是,這段寫詩的經歷,磨礪了他良好的創作素質與敏悅、精微的藝術感悟力。同時,他又當過報社記者,有著豐富的底層生活的深入體驗。這些潛在的優勢,也體現在他的散文創作中。比如,他收入《繁華的背影》、《書蟲日記》、《感謝從前》、《寫作真的很好玩》等文集中的不少耐讀的作品,語言在無色彩處見功夫,感情凝聚,筆觸含蓄,情韻幽遠,讀者能明顯地體驗到其中的“空白”。或者說,形式上雖是散文,骨子里卻貯蘊著詩的素質。
二
當今,文化隨筆已成為散文的大項。但如何寫每每因人而異。彭國梁的文化隨筆是以長沙為中軸,而兼涉其它地域的(如永州等地)。他較早就發表過一些與長沙文化相關的零散文字,后來與楊里昂先生合寫過一本《消逝的長沙風景》,繼而乘興而為,以《長沙沙水水無沙》一書,為文化界所矚目。此書主要記述晚清至民國這一時期,在長沙古城留下文學作品及深淺足跡的文化名人,并將其與長沙的名勝古跡,民俗風習和歷史變遷結合起來,以揭示“屈、賈之鄉”深厚的文化涵蘊。眾所周知,近、現代是中國社會文化急遽轉型的時期,而知識分子既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又是現代意識的媒介,在此背景下去審視他們與長沙文化的精神關聯,顯然更具有歷史深度和文化價值。所以說,作者截取這一歷史時段去考察長沙文化,恐怕不是出于純粹的個人興趣,它本身即是一種文化選擇,一種文化創意。該著在結構上采用了分題聯綴的體式,即:每篇獨立成章,并有標題,你可當作單篇隨筆散文來欣賞,而合擾起來卻又渾然一體,體示出作者對長沙文化宏闊的視野。故爾,此書列入南京師大的“城市文化叢書”之一。
這本書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史著作。作者的意圖,借用陳平原先生《老北大的故事》中的話說:“更希望溝通文與史、雅與俗、專家與大眾、論著與隨筆。”所以,彭國梁在此書自序中說:“我決不從宏大敘事入手,我得把口子盡量開小一些。”而且,他從一篇《新舊南門口》的民間說唱文學中受到啟發,于是采取了“大題小作”的敘事策略,即在大量鉤沉新的史料的基礎上,把不被史家看重而未曾進入歷史敘述的“故事”作為解讀對象,并以風物名勝為聚焦,藉此找到眾多文化名人與地域文化的契合點,以闡釋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遺傳、文化精神。
該書涉筆的內容十分廣泛。下面只能就其體現特色的方面窺測一二。
古人寫“列傳”有一個訣竅,即“每寫一二無關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彭國梁也借鑒了這種史筆。就是說,借一二件小事,與潛藏在文字背后而眾所周知的生平大事呼應,以凸現人物的個性特點和精神風貌。例如,對曾國藩這位中國近代最后一位集傳統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作者便采用了“常事不書”的手法,不寫他一生的輝煌業績和精深學問,只記敘他死后由朝廷在長沙所建專祠后面的“浩園”,由此牽引出湘軍團隊的中堅人物劉坤一、彭玉麟、郭嵩燾等在浩園詩酒從容的興會,不過重心仍落在曾氏身上,即通過這些人的相關詩文,誘引出曾氏幾件軼聞:如他與幕僚們相聚,因聯語“同進士”(即與進士不同)觸動其一塊心病,使聚會不歡而散;再如他違規在轄區娶民女為妾,遭到彭玉麟指責而輕松化解;還有他無法參劾臨陣脫逃的將領等。文章煞尾則補寫曾氏后代在浩園舊址創辦藝芳女子中學及募捐賑災等公益活動,以與前面呼應。于中我們不難窺見曾國藩的人脈關系、文化困惑及長沙文化對其家族的滋潤。此外,對于八指頭陀這位思想和經歷都十分復雜的人物,無論從哪個角度去寫他都可下筆千言,而作者只抉出其易為人們忽視的幾則舊聞軼事加以引申。如他在長沙新河開福寺的碧浪湖與王闿運等在湘名土飲酒賦詩的雅集,他之所以在此寫下很多詩篇,是為了酬答王闿運的知遇之恩。行文順此插入王氏在碧浪湖建亭背上冤枉,以及后來陳寶箴疏浚“新河”的善舉。而作者真正關注的則是隱藏在文人雅事背后的人間情懷和文化情緒。
本書各篇的基本敘述方法雖說是常見的夾敘夾議的隨筆體式,但其特點是盡量回避對人與事的直接評述和抒情。作者的感受和看法,往往寓于所引征的詩文和史料之中,只用簡短的文字聯綴或關鍵處略加評點,類如周作人當年所看重的“抄書體”。《坡子街上葉德輝》一文最能代表這一特色。文章從葉德輝被農會所殺談起,以史料為據,對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言表示存疑,繼而圍繞題旨,摭取大量文獻資料,詳盡描述了坡子街的小吃,福祿宮的老字號,以及神會、廟會等民俗活動,然后借文史專家陳先樞先生的話,肯定了葉德輝對坡子街繁榮發展的貢獻:一是建造藏書名樓,二是為湘劇改建固定舞臺,三是掌管火宮殿使之興盛一時。今天看來,葉德輝在政治上的確極端保守,他惡意攻擊維新運動,且與當時風起云涌的大革命運動對立,對此,我們不應曲為之諱,但他作為一位古籍收藏家、版本目錄學家,其整理、保存祖國文化遺產的貢獻,豈能一筆抹煞?至于葉氏該不該殺,此文借著名史學家尹達先生的話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革命群眾運動要估計恰當,不能說群眾運動中每一件都是正確合理的,只有實事求是地寫,才是一個具體的人。”
文章當然是多添幾套拳腳,多一點套路為好。彭國梁此集的隨筆,也有女性視角下的敘述話語和情調。作者記敘了與長沙結下不解之緣的有三位才女,即秋瑾、林徽因和謝冰瑩。三人的共同特點是: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富有激情的心靈,及其報效祖國的雄心壯志。由于作者的視角不同,寫法上路數也有異。寫鑒湖女俠在長沙憑吊賈誼,乃隔代感應,為的是表現其獨立的人格和建功立業的豪情。而敘林徽因,是以她在韭菜園教廠坪的租房為聚焦點,敘寫共赴國難的文人在此說文談藝、縱談時局,且長歌當哭,用救亡的歌聲,發抒內心的苦悶與仇恨,租房被日寇炸毀后,他們仍然經常相聚,以尋求溫暖與力量,充分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在風云劇變的時代心靈的激蕩。至于“女兵作家”謝冰瑩,則以她涉筆過的岳麓山、愛晚亭、云麓宮、古稻田、妙高峰等人文景觀為中心,或探幽紀勝、考釋名物,以掘發其深藏的文化意蘊,或引用詩文對聯來“情事曲傳”,抑或介紹烈士公墓中的黃興、蔡鍔等英雄人物的業績,可謂漫筆成文,枝蔓橫生,以自由表達作者的深微寄托為主。其中還穿插了一則笑話,某官吏把城南書院的匾額中題寫的“張浚”二字,誤以為是殺害岳飛的奸臣“張俊”,致使此匾被毀,看來,這并非是可有可無的“閑”筆。
教育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故作者也涉筆古代與現代教育,無論是岳麓書院的樹木亭臺,名碑聯匾,或城南書院的“朱張會講”和歷史興廢,都有說不盡的話題,它的鮮活處在于賦予了傳統教育明義理修養、倡躬行實踐的學風,及其個人自學與集體答疑相結合的教育方式。誠如作者所云:“因為岳麓書院的亭、臺、樓、閣、廊、軒、甚至庭院中的一塊石頭一顆樹,都是文化的結晶。”而《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一文,則通過講述抗戰期間長沙“臨大”的創建,展現了一道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景觀。作為學校主要負責人的蔣夢麟,曾任北大校長十五年。這位在政治與教育之間依違兩難的職業教育家,由于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制、延聘過大批留學生,反對學生無休止的罷課,解放后一度成為有爭議的人物。此文對蔣氏雖著墨不多,但不無深意。一寫他帶病堅持工作,二是他評價長沙人尚武好斗而行動遲緩,而對長沙人個性剛強直爽卻十分稱贊。“臨大”在長沙僅三個月,學生的主要活動是聽演講與演劇,并積極參與抗日救亡活動,你能說蔣夢麟治校有什么“不良居心”?
所謂“地域文化”,不單是以空間來劃分,更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態為依據。因此,彭國梁的文化隨筆,對社會時尚、風俗物產、民間傳說、飲食居住的細膩描繪中,都透出長沙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氛圍。在他筆下,有“陶公爭坐”的民間故事,有銅官窯的瓷器,有反映風土民情的長沙竹枝詞,還有銅官鎮和撈刀河得名的傳說。讓讀者品嘗到未經商業文化“污染”、處于自在狀態的民間文化本身的特殊魅力,體現出作者對地域文化特征的凝視和關注。其中《長沙李合盛》一文,通過寫百年老店具有地方風味的“牛百頁”小吃,串聯著兩位文學巨匠,記敘了田漢與郭沫若在李合盛的聚會,雖說只是歷史的小插曲,但記事言情,其狀依依,頗為感人。
《長沙沙水水無沙》一書,還真實記敘了抗戰時期的《文學月報》、《抗戰日報》的創刊;電影明星胡萍在長沙的生活片斷;湖南報界先驅嚴怪愚對社會低層生活的新聞報導;以及王魯彥、趙景深等才彥之士的文教活動等等。其中旁征博引,談古論今,使文本平添了一派淵深之美。作家何立偉曾在《胡子的書》一文中談到《長沙沙水水無沙》一書讓他很吃了一驚:“這書里寫了與長沙有關的那么多的人跟事,那么多的歷史掌故與文化細節,那么多的風云際會與白云蒼狗,其中不少是我作為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長沙本土人亦未必了解的。胡子從故紙堆里枝枝葉葉地尋來,把它們編織成了馬王堆漢墓古帛畫一樣的千年長沙的絢爛文化織錦。可以說,在此之前,我還沒有從哪一本關于長沙的書中見過如許之多的文化細節、歷史人物、鄉風民俗,見過如許之多的老照片、老畫圖、老文史。而且,這是一本寫得非常之好的書,單篇來看,也篇篇皆是激越飛揚氣場不小的地域文化散文。胡子做的是功德事,了不得。但凡以后研究長沙的歷史文化,我估計會繞不過胡子的這本書。”總之,該書以廣闊的文化視野,獨特的審美視角,揮灑自如、饒有興味的表達方式,展現出古城長沙的文化圖景,傳導出中華民族歷史積淀的文化心理;使讀者通過點點滴滴的歷史記錄和文化細節,不僅領略到長沙文化那永具魅力的歷史智慧,而且能從較深層上理解近、現代知識分子與長沙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精神關聯。不待說,其中的文化涵蘊又超越了單純的地域性。
三
案頭擺著的這本《繁華的背影》,是彭國梁“城市散文”的代表作。不難看出,題目便體現了他對城市觀照的基本視角。即把筆觸伸入糾葛重重的社會低層,浸淫著他對大世界中小人物的入微觀照和相關思考。其實,寫“尋常巷陌”并不比“大江東去”來得容易,因為受到題材基點、時空范圍、及其攝象畫面等自然形態的約制,筆力稍有不逮,就會變得淺切平庸。完全可以說,經過多年的探索,彭國梁在這塊世俗化的園地,已經找到了穩固而扎實的藝術支點。
那么,作者以什么樣的眼光去打量他熟悉的底層生活,并撩開它的面紗,一窺其面目呢?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樣竭力塑造自己莊嚴而慈善的形象,而骨子里卻對市井小民采取一種鄙視和把玩的態度,從而導致矯飾與做作。作為一個具體的人,彭國梁一開始就以一個“弱者”的角度,去諦視市井社會乃至身邊發生的一切。城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賴以生存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無處不充滿物化的痕跡,難免使人產生無以適從的煩惱與沉重。即以《垃圾》一文為例,由于種種“規則”和趨利的世風,作者窗前那堆使人寢食不安的發臭垃圾,始終無法清除,“我感到一種恐懼,垃圾的力量為何如此強大?”《路燈》一文寫馬路的開通帶來一個轉折,所有的路燈都熄滅了,“這個地方的人又開始陰沉著臉,一到黃昏,我早早緊閉家門,荒郊繼續野外,黑燈依舊瞎火,那馬路雖然寬敞了,但缺少一種盎然生氣”。此中實流露出作者的失望和無奈。其實,在城市的每一角落,類此的尷尬都存在,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不僅要寫出自己的切膚之感,而且應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不僅是自己的,也是更多人乃至人類的。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彭國梁的城市散文,透示出對人的生存境遇與精神空間的深切關注和沉重思考。感于現代文明把人類從大自然中疏離出來,《白沙井》一文,傳遞出在古文化陶冶下的天人合一、物我和諧的審美理想。那位“泉癡”般的老人,像一位勇敢的戰士一樣守護著白沙古井,但白天周圍機器轟鳴、淘水者擁擠狂躁的環境,使他感到隔膜,唯其夜晚,冥然兀坐,在寂靜的境界中才能享受寧靜中的從容。在喧囂熙攘的鬧市,你展讀此文,或許可以獲得一方清涼、一點寧靜,使浮躁的心得以平和。應當說,這正是作者向往的境界。彭國梁曾在《彭胡子的日常生活》一文中,即表達了“與繁華和喧囂保持一點距離”的生活態度。然而,作者的生命意識尚不止于此。須知,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正以不可逆轉的姿態迅速發展,要返回那種田園牧歌式的融樂已不可能。《殘局》一文,可從不同視角去解讀。但我以為,作者是通過提煉一個核心細節來拓展寓意的。那位悠閑吸煙喝茶的長者,在一座大樓前放置棋盤,設一殘局,雖說他感到“一股豪氣油然而生”,但“對面那張小凳仍然一直空著。”盡管他口頭以“心靈的平安”自慰,內心卻彌漫著一種帶有懷舊意識的孤獨感。作者通過這一細節,溝通了今天與昨天的內在聯系,概括了時代驟變中許多普通人無可奈何的精神困頓,其中“包孕”的社會內容極為深廣。極平常的細節用來最大限度地透示生活,這正是作者藝術手腕的高妙,也是該文的耐讀之處。
在作者筆底,城市的絕大部分人都在極為普通的狀態下生存。他們雖然只是偉大歷史進程中的蕓蕓眾生,但仍然積極、倔強而艱難地生活著。無論是背著蛇皮袋,“像一只無頭蒼蠅,在城市的夾縫中盲目前行”的“垃圾王”,還是“一見皮鞋就肅然起敬”,為練擦鞋,曾經把大石頭都擦融的老人,或是靠“一口酒”撐著修單車的下崗工人,還有那懸于高層清掃摩天大樓的“蜘蛛俠”等。這些底層小人物,在現實生活的催迫下,生存著,掙扎著,誰也不屑于叫喚他們的姓名,他們也不在乎什么名份。不是么,“垃圾王”只能夜半三更起來,自問自答姓名。但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歡樂著,“垃圾王”的樂趣是在廢報紙上看征婚啟事,而拉煤者抽煙提神后可以偷看幾眼過路的女人。這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市民,思想性格明顯地秉承了傳統的道德準繩,勤儉寬厚而忍讓,甚或近于麻木,對于他們的生活命運,作者筆下觸發出真切的理解、同情與人性的光芒。正如彭國梁在《雜文選刊》記者對他的訪談中所說:“我工作單位旁邊有一條小街,十多年來,我長期穿行其中。在這條街上,開飯店的、理發的、賣菜的、拖煤的、擦皮鞋的、賣水果的、開日雜店的,大都成了我筆下的人物。我熟悉他們,我知道他們的辛酸苦辣。我看見他們長年累月地賣菜賣出來一部摩托或一間小門面;我看見一個‘拆’字寫在某一家的墻上時,那一家人的恐慌。我看見一線幾萬元一平米的門面一直在關閉著,可那個位置的拆遷戶至今工作還沒有著落。我知道一個城市如果離開了這些人,將是怎樣的沒有生氣,怎樣的黯淡無光。”
同時,彭國梁也描繪了現代都市因變態而瘋狂表演的女人,他們無論經濟地位或居住條件都遠勝于下層市民,但過得并不開心。所謂“變態”,多半是由某種心理落差造成,當她們不具備超凡的業績和品格時,通常都是畸人,其實也是庸人,不過被賦予某種偏執的倫理品格而已。《泡電話的女人》,講述一位離婚的女子,當她獲得“自由”后,又被另一種原先沒有時間去關注的孤獨與寂寞所折磨,于是她選擇不斷地與陌生人泡電話來尋求新鮮刺激。《女人醉酒》中,那位愛慕虛榮的女子,由于某個場面握手的鏡頭被別人搶了,她心存不甘,于是在一家酒樓趁著酒興,與每桌的顧客一一握手。還有一位臺灣來的富婆,酒醉后給周圍帥男一人一張百元美鈔,條件是都進大包廂陪她喝酒唱歌,因為其夫在大陸包了二奶。對于這些人性的弱點,盡管作者給予了帶有幽默的嘲諷,但并未以此當作笑柄,而是以其本真的態度,冷靜地剖析了導致這樣“畸形”的深層原因,揭示出社會文化轉型時期價值觀和人際關系的痛點:倫理讓位于物質,愛情讓位于欲望,作者藉此在城市生活中,找到明察“世道”與“人心”的契合點,向世人召喚回歸與理解。
彭國梁不是一位政治意識很強或善于胡編亂造的作家,而是擅長于常態氛圍中樸實無華地再現生活的風貌,使讀者獲得一種生活質感和天然之趣。你讀《底層細節》中那尋常小巷的生活速寫:
張家長,李家短的,從街的這頭飛到街的那頭。過不了多久,張家短,李家長的,又從街的那頭跑到街的這頭。
吃飯了,端著個飯碗到處跑。有時候,一雙筷子,可以伸到五六張飯桌上去。有時候一個噴嚏,打得滿街都落小雨。再看《送煤的》中主人公拖煤的艱窘之狀:
送煤的個子不高。可他那拖煤的板車卻不小。他拖著一車煤,在小巷里走。他的背弓著。你要是從后面看,那就只能看到煤,而看不見人了。
煤就像一座黑色的山,在移動著。
還有《耳光》中與一辦假證的女子對話:
某一次,又是在小吳門,一個女人攔住了我的去路,問:辦證啵?我說:你能辦什么證?她說:什么證都辦!我說:那我問你:賣淫啵?那女人說:不辦就不辦,憑什么問我賣淫啵?我說:我走我的路,那你憑什么問我辦證啵?那女人說:別看你夾著個公文包,好多要我辦證的都夾著個公文包哩!再說了,好多當官的到大學里搞的什么碩士博士的什么證,未必就比我們這證干凈?我本想扇她一記耳光,但她后面這句話一說,我伸出去的手便又縮了回來。
大致相似的情境還有:菜市場的嘈雜和斤兩計較;超市人流恰似搬東西的螞蟻;被車輛行人“堵得嚴嚴實實”的小巷等等,作者通過提煉這些從街頭巷尾拾得的“雞零狗碎”的素材,窮形極相地描繪了現代城市的色彩、聲音、速率和氣氛。這些情境,誰又沒見過呢?由于作者善于運用短峭質樸而略帶幽默的藝術筆致,對世俗化的情態進行絲絲入扣的精微刻畫,使人感受到細膩的思維內容和濃厚的人生況味。作者無意賣弄,卻能以情動人。
有論者指出,這組散文“是彭國梁通過細致的觀察寫出的心靈之聲,其描寫當代社會的眾生相,幽默中拌進了嘲諷,點出了正面的發展中負面的雜質”。此言不謬。如寄生爛尾樓混進賓館白吃白睡的“蛀蟲”;閑得無聊的紀念館館長加入麻將協會;橫穿馬路翻越欄桿的悲劇時有發生;城市干凈的墻上到處都有張牙舞爪的標語等,這都是社會發展中尚未得到治理的亂象,更有甚者,在似乎合理的“規則”掩蓋下的假公濟私、弄虛作假,如借抽樣檢查為名白拿白占的工商稅務人員,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居然在城市廣場種麥子的奇思妙想等。作者把病態的世相撕破給人看,嚴肅而又冷峻,尖刻而不失熱情,大抵正如魯迅所說,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
四
散文是一種側重于抒發主觀情志和體驗的文學體裁,作者的感情無疑是重要的內驅力。彭國梁的散文無論是文化隨筆或城市小品,都有明確的地域性,即生于斯長于斯的古城長沙。他在《長沙沙水水無沙》的后記中說:“長沙在我眼中變得越來越親切”。《繁華的背影》的后記也有類似的表達:“我每天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走……我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然后變成文字,躍然紙上。”不消說,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心理結構特別強韌的方面,即是其與鄉土的那重聯系與那份情感。彭國梁之所以能持續不斷地寫作文化隨筆和城市散文,恐怕也是緣于他對故鄉那種摯愛之情,即使寫“孤獨”寫“陌生感”,也是從“我”與鄉土的不可分離的前提下來思考“自我”的。無怪乎他寫到岳麓書院“半學齋”時,竟花了那么多篇幅插寫文化學者江堤。江堤十多年致力于湖湘文化的研究,岳麓書院已融入他的血脈,哪怕院中一顆大樹枯死他也會傷心至極。聰明的讀者不難發現,彭國梁寫江堤,實際上也傳達了自己真醇的鄉土情懷和文化情結。應當說,以上正是他散文創作的堅實基礎和不盡源泉。
有論者說:《繁華的背影》“將雜文和小說元素融合得非常好。”確為知文之論。雜文是一種曲折而堅定的表達方式,一種以剖析事理為主的帶有論辯性、諷刺性的文體。在彭的散文中,如《誰最有名》:寫三人爭論誰的名氣大,最后只得在街上表演鉆圈一決勝負;《三大寶》中寫善于品頭論足的理論寶與檳榔寶、鉆褲檔寶三人的爭吵,都揉入了雜文筆法,夸大其辭,正話反說,旁敲側擊,嬉笑怒罵,顯得格式特別。彭國梁不少文章對社會人群中某種“劣根”進行揄挪,往往帶有雜文色彩。至于他的散文融入小說元素,實不難理解,即有些精短散文與微型小說相似,有簡單的人物和情節,在簡單的篇幅中有情節變化的過程。實際上,散文本身就有“兩棲性”的特點,可謂左鄰詩歌右鄰小說。中國古代的小說把那些半虛半實的筆記雜談也涵括在內,《聊齋志異》中即有四分之一的篇什可歸入小品文,汪曾祺、何立偉、阿城等的小說,有些也可當散文讀。
這里我想補充兩點:
一是彭國梁那些抒寫性情、發表見解或雜記見聞的小品文,采取了近乎“無結構”的隨筆體式,無拘無束,漫筆成文,總以自由表現真純的意緒為主,且綿里藏針,機鋒特出,幽默詼諧,似乎受到明清小品文與“禪宗語錄”的濡染。如《垃圾王》中寫拾荒者在報上看到征婚啟事,要求男方有文化,還有素養,“他曾經養過豬,養豬怕的是瘦,瘦養,素養。怪不得這些女人嫁不出去。”《女人醉酒》寫五個離異了的女人一塊喝酒,喝了酒便抱頭痛苦:“在一起集中孤獨,回了家各自孤獨。”這些帶有冷幽默的機鋒語隨手拈來,使散文趣味橫生。
二是為適應當代生活的閱讀審美趣味和感知方式,較之傳統的小品散文,彭國梁的作品加強了外物心靈化的內容,把內心的感覺意緒寫得若隱現,蘊含著某種難以說清、耐人尋味的情韻。如《幻覺》、《底層細節》等都體現這一特點。
彭國梁的散文是值得認真研究和探討的。我這篇文章還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最后,我想借用彭國梁贈我的一疊藏書票小套盒上的兩句詩作為本文的結尾:“無須表白/只把手緊緊一握/握住這美好的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