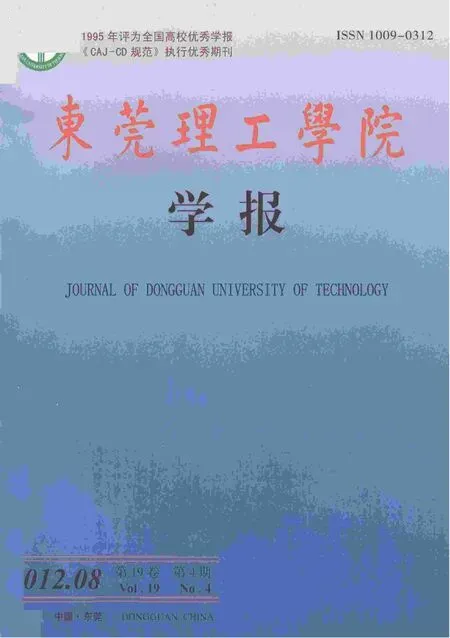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對現代高校德育的啟示
王賀
(東莞理工學院 學院辦公室,廣東東莞 523808)
面對當今社會眾說紛紜的道德現象和莫衷一是的道德觀念,如何才能使高校德育卓有成效?這是21世紀的高等教育關注的焦點。高校德育除要具有系統性、邏輯性和科學性之外,還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符合道德教育規律的理路架構。作為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儒家道德教育思想,探討它的內在邏輯理路,將對現代高校德育的發展提供許多可以借鑒的觀點與方法。
一
人性 (humanity)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質品性[1]121,自古以來,由于儒家道德教育中厚生愛民的傳統,關于人性問題的討論始終是儒學理論家學術探討中的熱門話題。但是,儒家先賢孔子卻對人性問題只是偶爾談及,因此使得他的弟子常有“不可得而聞”(《論語·公冶長》)的嘆息。
從發展淵源上考察,人性問題之起源最早始于戰國初期的世碩對人們之間善惡關系的思考。世碩的理論是“性有善有惡”,他曾說“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論衡·本性》)在他的論域中,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如果發掘人的善良本性,通過后天的正確培養、引導,那么人好的品行 (善)就會生長出來;如果發掘人的惡劣本性,再加以培養、引導的話,那么壞的品行(惡)也會迅速發展下去。概而言之,世碩認為人性的善或惡,關鍵在于后天的培養方向。但是,在戰國中期,告子卻對世碩后天培養的人性論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否定,他反其道行之提出了“性無善無不善”的自然人性論觀點。
隨后的孟子主張人性本善,提出了“四心”說①“四心”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分別體現出人的仁、義、禮、智。《孟子》四心說的內容詳見《公孫丑上》第六章。。他曾比喻說“人之性善,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并進一步深入論述“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這大體構成了孟子的“性善論”學說體系。在他看來,人性之善是人獨異于禽獸的根本特征,善使人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道德意識。這“四心”孟子給他概稱為“本心 (良心)”②《孟子·告子上》第八章、第十章依次提及良心、本心兩個詞。,本心是人生而有之的,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由外鑠的,從本心發端可以成就人的仁、義、禮、智四端,它們的重要作用體現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上》)進一步說,仁義禮智雖然為天性,卻僅是“善端”,只是一種向善的可能性,只有通過后天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才能使先天的德性得以擴充,才能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否則就會失去它們應有“善”的功能,因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
另一儒家先賢孟子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篇》),即人性本惡。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惡的,偽是后天教化的結果,為善,即“虛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荀子·正名》)同時他還認為人天生是好利而多欲的,“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惡篇》)所以對待先天惡的人性必須要進行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惡的本性轉向善的向度。
儒家人性善惡之爭的歷史考察表明,人性是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辯證統一。人性之辯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論題,儒家人性之辨,總是圍繞著一個“善”字生發開來。在儒家道德教育的實踐中,人性被作為善的預設進行設置,盡管人性在不同的道德個體中呈現出不同的差異性,但是人性本善確是儒家道德教育不變的命題,因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的,后天的不善是社會造成的,人性可以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日臻完善,人格也會日趨健全。總之,人性善的同一性保證了儒家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而同時個體道德行為的差異性也提出了儒家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這種人性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共同構成了儒家道德教育的邏輯起點。
二
“義”是儒家傳統的重要義法之一,儒家歷代圣賢都非常重視義利問題,首先,“義”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種基本價值,一種根本精神和理念。孔子曰: “君子義以為質”。這里, “質”是與“文”相對舉的, “質”為內容,為精神,為理念,為價值; “文”為表象,為形式。其次,“義”是一種社會行為規范和取舍標準。《中庸》曰: “義者,宜也”,韓愈說: “行而宜之之謂義”,這里的“宜”字是“應該”的意思,“義”就是一種行為規范和取舍標準,強調的是人的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要求人們在決策時要充分反省和思考“應不應該”的問題。第三,“義”是一種途徑,一種上達天道和下貫人事的途徑。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孟子則把“義”視為 “人之正路”。[2]32
儒家著重于仁和義,并把它們當作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在這里不得不說“義利之辨”,中國的義利之辨,不知起始;儒家的義利之辨,自孔子始。所謂“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就此便能看出,孔子把義作為取舍的道德標準。在義利關系上,孔子將“義”的概念引入對人的道德評價體系,把重義還是重利作為區別君子與小人的標準,他提出“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的觀點。
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義利觀,強調“惟義所在”。“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也就是說通達的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結果不可,只要合乎道義就行。他一再強調:“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孟子主張“居仁由義”(《孟子·盡心上》),這里說的義,是指大道,是道德和義理的內在根據,有“理義”、“禮義”、“仁義”等意思。孟子堅持著孔子的義利之說,把義看成道德的內在根據,看作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仁義之心、是非之心。他是把義和仁聯系起來,當作人類普遍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規范,在這一點上,孟子將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深化了[3]156。
荀子比孔子與孟子更重視義,他將義視為求取社會公利和個人正當利益的惟一正確的手段,主張“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他指出: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矣。”(《荀子·勸學》)他認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荀子·勸學》)就是說,人人都要求利,但求利的方法不同。正確的方法就是將義放在第一位,以義取利。
漢代儒者董仲舒繼承了孔孟重義輕利的基本思想,提出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命題。他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故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人,大于利。……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春秋繁露·身之養莫重于義》)董仲舒分析了義和利的功用,肯定了義和利各自的功能,每一個生命個體都不可能缺如。養身是每一生命個體的本能,凡動物都有這一本能,所以“利”是不用人去引導,謀利是無師自通的;養心之事則不是所有動物都能夠自覺為之的,人之所以為人,他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知曉并用行動去養心。在董仲舒看來,義是滋潤心田的唯一養分,心貴于身,故義大于利,義重于利。為人處世當舍利取義,能夠堅持這一原則,雖貧而能樂;反之,忘義殉利,雖富足必罹于憂患。
事實上,儒家所言“輕利”,并非不重視利,儒家先哲都不否認“利”客觀存在,都承認利對于人生存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荀子所說的“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歇,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韓非子·榮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此之后,歷代儒家先哲們對義利之辨命題均有豐富的論述,但基本都是在重義輕利的層面展開討論[4]132。這樣一來,儒家重義輕利的道德價值觀就發展為重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公),而輕個人利益 (私)的道德價值判斷,雖然在“義和利”的關系問題上,儒家道德學說具有某些禁欲主義因素,具有輕利的傾向,但其所倡導的以義取利,無疑可以成為當今社會人們道德活動可資借鑒的價值資源。
從儒家思想家對于義利問題的論述中不難看出,義則是和諧的,大家都言義,都自覺將義作為自己言行舉止的標準,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就是一個講信修睦、禮讓的社會;利是必須的,如果不講利,人們就失去了業已存在的生存基礎。儒家這種道德價值觀直接要求建立新的時代精神所要求的現代義利觀,誠然,市場經濟和傳統社會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等等,只要精神文明建設稍稍放松,就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無疑,這正需要用正確的義利觀作為導向,用儒家的義利觀來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
三
圣王人格源于儒家“內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內圣”表現為:“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圣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莊子·天下篇》)。“外王”表現為:“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莊子·天下篇》)。圣王人格的內涵通俗地講,“圣”就是修身養德,要求人做一個有德性的人;“王”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圣王人格是儒家道德教育的價值歸依,可以從兩方面講,在“圣”方面,孔子主張,“為仁由己”。他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品德高尚的仁人,關鍵在于自己。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在“王”方面,儒家以“修己”為起點,而以“治人”為終點。子曰:“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在儒家道德教育的邏輯理路中,圣和王是相互統一的,圣是基礎,王是目的,只有內心的不斷修養,才能成為“仁人” “君子”,才能達到內圣,也只有在內圣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安邦治國,達到外王的目的。[5]183孔子曾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就是說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也要滿足他人的需要,兩者都滿足了,才是一個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內圣外王之道”。
孔子之后,孟子堅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主張在道德教育中追尋一種堯舜般的圣王理想人格,讓世人修身養性以成為內圣外王的“大丈夫”。他給“大丈夫”的人格定位畫了個很好的坐標:“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這種人格在孟子看來,是道德領域中社會生活和理性思維在內心的結晶,是人處理道德問題時特有的心理境況和境界,它指引著每個人的航標,給人以自然向上的力量[6]343。它強調主體的自覺與超越,激勵人們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講求修身養性,培養氣節,鍛煉意志,重視道德操守,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執著追求真善美;這也主要是用來對抗和改變當時“圣王不作,諸侯橫恣,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滕文公下》)的凄涼社會道德現實。
四
概而言之,儒家道德教育思想是我國高校德育中取之不竭的價值之源。面對一定意義上的傳統社會道德的“禮樂崩壞”(孔子語),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傳統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為此,我們必須調整對于社會文化傳統的態度,從“集體記憶”上重新反思關于傳統的合理理念。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道德教育不是服從某個外在的目的,不止于某種道德規范原則的授受,道德教育是一種道德信念的確立。道德信念一經形成就會成為人們進行道德判斷的標準,個體一般不會輕易改變在道德行為中所表現的堅定性和一貫性。今天高校的大學生,已經處于具有獨立思考和進行自我教育能力的青年時期,目前的高校德育中如何利用課堂的教育、教學網絡平臺的討論等方式啟發、調動大學生進行自我教育的積極性,能夠精誠反省自己的道德動機和行為,確立正確的堅定的道德信念,仍然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討的問題。
從儒家道德教育實施內化接受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啟示:現代大學生的道德推理、遷移、判斷和選擇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過程中,強烈的道德情感體驗和反復的道德實踐驗證后所確立的道德信念是最牢固的。因此,現代高校德育應該把大學生道德信念的培養與抓好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為結合起來。譬如一次熱心的公益活動,同學間的一次無私關愛,生活中那些一次又一次的舉手之勞,這些強化的是一種教育,形成的是一種思想,鞏固的是一種信念。在恒久的道德踐行中,高校德育的時效性會得到不斷加強。
[1]朱義祿.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2]黃書光.理學教育思想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3]翟廷晉.孟子思想評析與探源[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4]宋紅霞,張凌云.孟子的人格意識與士節[J].齊魯學刊,2006(4):27-29.
[5]林語堂.孔子的智慧[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6]楊澤波.孟子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魏琳,朱文華.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培育中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研究[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