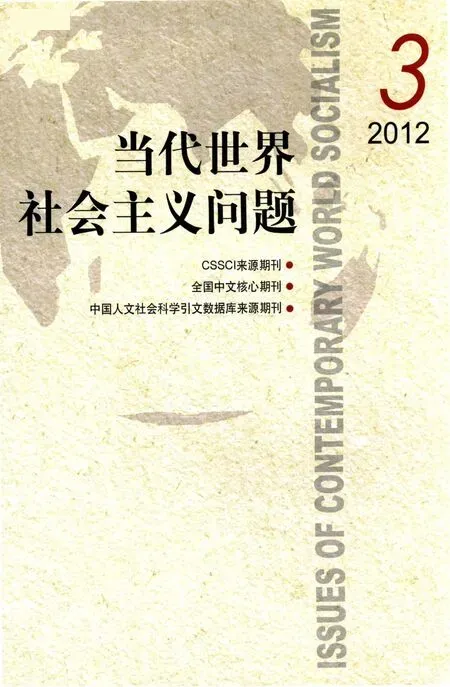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與傳統均貧富思想的關系*
魯法芹
對西方工人運動的關注是社會主義思潮傳入中國的契機。西方工人運動尤其是工人罷工的表面訴求,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工作環境等,使人們很容易將其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思想相聯系。隨著人們對歐美資本主義弊端的認知以及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這種聯系得到了強化。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義被很多人界定為公有制基礎上的均貧富學說。本文嘗試對辛亥革命前中國社會主義思潮傳播史上的這種現象作一評述。
一、中國傳統的均貧富思想
“均貧富”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范疇,最早的明確記載見于《晏子春秋》。在該書《內篇·問上第三》中,齊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答曰:“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這里所說的“均貧富”,即“取財于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①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世界書局1935年版,第81頁。。其實,均貧富思想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并不鮮見,不過大多并不是指在各階級、階層之間平等地分配財富,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治者之術”,建議統治者通過政治權力來調節貧富差距,限制兩極分化的進一步惡化。秦漢以后,隨著土地買賣和兼并的不斷發展,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形成了富家大姓對國家賦稅的威脅,于是統治者開始采取措施限制地主勢力的膨脹,限田、均田、均稅等方法應時勢而生,繼之被廣泛運用,目的只是“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均調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②賴炎元注譯:《春秋繁露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06頁。。
與此相比,肇始于秦漢農民戰爭中的農民階級的“均貧富”思想則激進得多,這種思想也被后人稱為“農業共產主義”思想。例如《太平經》對理想“天國”的描述:“皆食天倉,衣司農,寒溫易服”,“粗細靡物金銀彩帛珠玉之寶,各令平均。”③王明編:《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79頁。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領袖張魯、張角借用《太平經》的言論,宣稱“太平”就是在“大如天”的廣泛范圍內普遍實現人人平等的“太平均”④楊寄林:《太平經今注今譯》(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頁。。據《三國志》記載,在張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期間,曾實行“義舍”、“義米肉”等措施,以便“行路者量腹取足”用之⑤陳壽:《三國志》(上),吳金華校點,岳麓書社2002年版,第180頁。。唐末農民起義軍則首次公開打出“均平”的旗幟,王仙芝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黃巢率起義軍入主長安后則定國號為“大齊”,意思是天下均平,這對后來的農民起義產生了巨大影響。五代南唐時期,農民起義軍提出了“使富者貧,貧者富”的口號,反映了農民階級企圖打破貧富對立、實現絕對均平的要求。北宋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明確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⑥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李之亮校點,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頁。;繼起的李順則“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⑦沈括:《夢溪筆談》,侯真平校點,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214頁。;方臘把反對“剝削”納入起義軍的行動綱領,高呼“東南之民,苦于剝削久矣”⑧方勺:《泊宅編》附錄《清溪寇軌》,許沛藻、楊立揚點校,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12頁。。南宋時,鐘相領導的起義軍不僅要“均貧富”,還要“等貴賤”:“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明確“謂劫財為均平”⑨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6頁。。元末紅巾軍把“均平”的主張與“推富益貧”的強制手段結合在一起,奪取富人之財分給窮人,力圖改變“人物貧富不均”的現實⑩葉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51頁。。明末李自成起義軍提出了“貴賤均田之制”和“均田免糧”的口號,超越了以往農民起義只著眼于剝奪和均分富人“浮財”的做法,提出了均分土地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地主土地所有制。
晚清以降,中國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1753年,全國人口18369萬人,人均土地4.25畝,超出當時的溫飽線(人均4畝);到1850年,全國人口達41449萬人,人均土地降為1.78畝,遠在溫飽線以下①參見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另一方面,隨著國門的打開,大量外國廉價商品涌入,造成白銀大量外流,農民和手工業者大批破產,土地兼并現象愈演愈烈,再加上清政府為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和軍費開支而不得不增加新稅捐,致使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終于引發了震撼中華大地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洪秀全從農民革命的需要出發,借鑒和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所宣揚的平等思想,并將《禮記·禮運》篇中有關大同理想的描述抄錄于《原道醒世訓》中,作為其“原道”的佐證。這是歷代農民起義中首次運用大同學說來指導實際斗爭,意在追求“公平正直”、“各自相安享太平”的理想盛世。洪秀全已意識到私有制是產生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恨,一出于私”②《洪秀全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頁。,故在起義軍中建立“圣庫”制度,“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圣庫,逆者議罪”③《洪秀全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頁。。1853年入主南京以后,他又將“圣庫”制度推廣到社會生活中,使之成為一項法律。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提出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公有,按口計田,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社會生產和經營,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保暖”的新社會。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洪秀全在這方面走得更遠、更荒唐。在天京城內,他拆散家庭,將居民分編為男館、女館和牌尾館,并把各種手工業作坊及手工業者按技藝分門別類進行集中,稱之為“諸匠營”和“百工衙”,試圖取消個體手工業和私營商業,使人民的日常生活由政府統一供給;在農村,他大力普及“圣庫”制度,規定“凡二十五家設一國庫”,將農民剩余的農副產品和銀錢均收歸“國庫”所有,而“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④《洪秀全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172頁。。顯然,這是一種把傳統“均貧富”思想推向極端的實踐,試圖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一個“軍事共產主義”社會,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二、早期外交人員和來華人士對社會主義的“均貧富”解說
據現有史料,對歐洲工人運動最早進行記述的是中國早期外交人員張德彝,他在《再述奇》和《三述奇》中分別記錄了拿破侖三世統治時期的法國工人運動和巴黎公社起義的情況。但這兩部游記在當時并未刊行,影響微不足道。1873年由中華印務總局刻印發行的王韜《普法戰紀》一書影響甚大。在卷十二中,王韜指出,巴黎工人起義的原因在于“法國廷臣之轉為自主之國也,民間囂然,皆以為自此可得自由,不復歸統轄,受征徭,從役使,畫疆自理,各無相制”,當與政府發生矛盾時,人民便揭竿而起,討伐當權者,且將“所有產業一概歸公”①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頁。。郭嵩燾在《倫敦與巴黎日記》中也多處記載了19世紀70年代末歐洲工人罷工運動及俄國民意黨人的活動情況,并且已經注意到了其一些基本特點:“通貧富上下,養欲給求通為一家,不立界限”,“統貧富無分,金帛皆公用之”②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岳麓書社1984年版,第886、698頁。。黎庶昌的《西洋雜志》和李鳳苞的《使德日記》是最早明確提及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中文文獻,是國人首次對Socialist、Social Democracy、Communist等詞匯進行中文音譯,二人均將社會民主黨意譯為“平會”③黎庶昌:《西洋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8頁;李鳳苞:《使德日記》,見《使西日記(外一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1—52頁。。黎庶昌認為,“平會”的目的是“冀盡除各國之君使國無主宰,然后富貴者無所恃,而貧賤者乃得以自伸”;李鳳苞認為,“平會”的目的在于“欲天下一切平等,無貴賤貧富之分”。
同一時期,西方來華人士通過其主辦的報刊雜志,也向中國傳遞了西方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學說的零星信息。巴黎公社失敗后,美國傳教士主辦的《中國教會新報》從歐洲報紙上摘譯了所謂“法京民變”的新聞,但沒有引起太大反響。江南制造局編譯的《西國近事匯編》則影響頗大。正是在這份刊物上,他們將社會主義學說解釋為“主歐羅巴大同”、“貧富適均”“貧富均財之說”等,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欲藉其本境殷富,奪其資材,以予貧乏”,并將工人罷工的目的解釋為“藉富室私產而公晰之”,“以贍貧困、以均有無”④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9—10頁。。這與中國早期外交人員的理解頗為相似。
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陸續出現了一些涉及歐美各社會主義流派的譯作。京師同文館副教習汪鳳藻1880年翻譯的英國經濟學家Henry Fawcett的《富國策》一書,在“論制產主義與均富之說”一節詳細介紹了歐文和傅立葉的學說,稱歐文首創了“革除私產”的“均富之說”:“因思不去私產之制,必無以均民財,遂創議立策,革除私產,使人共享其利,此均富之說所由來也。”書中還將歐文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組織形式(即合作社)解釋為:“其法令若干家聯絡一氣,通力合作,計利均分,相功相濟,如然一家。”而對于傅立葉所設想的“法郎吉”,作者則認為相較于歐文的合作社來說是一種“變通”⑤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9頁。。這本書對中國思想界產生了較大影響。例如袁宗濂和晏志清在1902年編輯的《用材總論》中,介紹歐文“均富之說”和傅立葉“變通其意”的內容,就基本取自《富國策》,并且認為:“是均財之法,使各保其私產,即可以分濟貧人,則取為我者不得笑其迂,主兼愛者不得譏其忍。”①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頁。后來,康有為也對傅立葉關于“法郎吉”經濟制度的設想明確表示贊同,稱之為“均民授田”或“大井田”:“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②康有為:《孟子微·中庸注·禮運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9頁。;“欲以十里養千人為大井田,其義仁甚”③康有為:《大同書》,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頁。。1885年傅蘭雅翻譯的《佐治芻言》一書中,把法國社會主義者的主張闡釋為:“一國產業,必與一國人平分,令各人皆得等分,方為公道。”④傅蘭雅譯、應祖錫述:《佐治芻言》,上海書店2002年版,第71頁。由日文翻譯而來的《萬國史記》中,將社會主義解釋為:“等男女之權,廢世襲財產之法”;“主張四海兄弟,人民等同之說”;“欲使全世界為一大勞動公會,以廢政府律法習慣等”;“平俸給,齊貧富”。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中,將社會主義解釋為:“其蓋謂他人有何財物,我亦可以取用”;“如共有財物亦可任人通用,無稍吝惜”⑤轉引自《張艷國自選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頁。。此外,在李提摩太翻譯的《大同學》一書中,不僅介紹了馬克思其人及其學說,還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各流派進行了介紹,認為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主于資本者”,為“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亨利·喬治的單稅社會主義“主于救貧者也”;貝拉米的空想社會主義“主于均富者也”;費邊社會主義“皆言人隸律法之下,雖皆平等,人得操舉官之權,亦皆平等(君主之國無此權也),獨至貧富之相去竟若天淵”⑥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20—621頁。。總之,在這些早期譯作中,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思想始終是聯系在一起的。
三、改良派對社會主義的“均貧富”解說
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認為,歐美資本家所以能夠“巨富”,原因就在于“眾工人胼胝辛勤所致”,因此他對工人運動持有同情心,認為工人組織工會以及以罷工手段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日,只不過是工人階級“求工資饒裕”而“以資養息”,并非與資本家階級“為難”⑦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364頁。。1896年,嚴復和譚嗣同幾乎同時從限制壟斷資本所造成的資本主義流弊出發,把社會主義政黨解釋為“均貧富之黨”。嚴復認為,伴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歐美社會生產力得到大發展,但也導致了私人資本的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于是“均貧富之黨興”⑧王木式主編:《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4頁。。譚嗣同對西方“均貧富之黨”崛起原因的闡釋,與嚴復的見解大同小異(見《報唐佛塵書》)。值得一提的是,嚴復在《天演論》中還將赫胥黎原文中“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學說,意譯為“財之不均,亂之本也”的“均富言治之說”①參見宋啟林等譯《進化論與倫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66頁。。
1898年,梁啟超在《讀〈孟子〉界說》中首次提到西方的社會主義學說。在“界說八”一節中,他指出,孔子立井田之制是為了“均貧富”,井田乃“均之至”、“平等之極則”,而“西國近頗唱貧富均財之說,惜未得其道耳”。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在出逃日本的船上翻譯了日人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借“老偉人”之口描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貧富兩極分化而形成的社會主義運動:“于是天賦貧富平均說,社會黨論,乘勢而起,氣焰日張,以與富者反對”。1900年7月26日,在他主編的《清議報》上曾刊登過日人加藤弘之的《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一文,文章明確提及:“所謂社會思想者,即關于貧富問題者耳”,而以謀救濟貧富不平而起之社會思想,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②梁啟超主編:《清議報全編》(第5集)卷二十,第70—71頁。。1901年梁啟超撰文指出,“泰西社會主義,原于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經18世紀圣西門、康德等人進一步發展之后,“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勢力”,并認為其師康有為之哲學乃“社會主義派哲學也”,《大同書》所設想的理想社會乃將“國家家族盡融納于社會而已”③《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492頁。。實際上,康有為在《大同書》中的確把社會主義學說稱為“均產之說”、“合群均產之說”或“共產之法”、“共產之說”。1902年,梁啟超在文章中把馬克思稱為“社會主義之泰斗”的同時,也把Socialism譯為“人群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④《梁啟超全集》(第3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8頁。。在《二十世紀之巨靈托拉斯》一文中,他把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解釋為“變私財以作公財”。在《外資輸入問題》一文中,他借“當代社會主義家”之口指出,社會主義“必以資本歸公為救時弊第一著手者”,或提倡“資本歸公(即資本國有之說)”,并認為國有政策“自今以往,日益占勢力矣”。不過,他認為社會主義所奉行的公有制原則并不適合中國,中國只能采用社會主義之精神而不能“師其法”,只能在不觸動現存產權制度的前提下實行以國有資本經營為主的“國家社會主義”,來糾正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社會主義若能實行,則“分配極均,而世界將底于大同”,是“將來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義”⑤陳書良選編:《梁啟超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頁。。可見,在梁啟超的社會主義觀中,仍透露出中國傳統均貧富思想的影響。
四、革命派對社會主義的“均貧富”解說
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孫中山于1903年首次明確提及社會主義,并把它與“平均地權”的主張聯系起來,認為中國農業生產尚未使用機器,故“作生財之力尚恃人功,而不盡操于業主之手”,與歐美“地主之權直與國家相埒”所造成的“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的嚴重社會積弊相比,平均地權“當較彼為易”,是“為吾國今日可以切實施行之事”①《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8頁。。后來,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社會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會上貧富太不均”②《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71頁。,國民黨民生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③《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8、394頁。。
在《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期間,革命派人士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胡漢民在《“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中指出,歐美社會主義的產生不是起因于政治上的等級差別,而是起因于經濟上的貧富懸殊,其“學說雖繁”,但宗旨不外乎“皆以平經濟的階級為主”④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377頁。。馮自由在《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中亦認為,就其綱領來看,民生主義之所以發達,是“以救正貧富不均,而圖最大多數之幸福故”,此乃民生主義之“精髓”⑤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419頁。。正是從這一“精髓”出發,胡漢民指責梁啟超的社會主義思想混亂:“梁氏重視生產問題,而輕分配問題,又以二者為不相容也。故于其論分配問題時,崇拜社會主義,而于其論生產問題時,則反對之,此其所以為大矛盾也。”⑥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680頁。章太炎在區分“農耕”和“商工百技”的基礎上,建議平均“農耕”的土地,而不平均“商工百技”的財富,并且建議:“今夏民并兼,視他國為最少,又以商工百技方興,因勢調度,其均則易,后王以是正社會主義者。”⑦章炳麟:《訄書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頁。也就是說,在他看來,中國兼并問題尚輕,近代工商業剛剛興起,易采取社會主義的調度措施,以防蹈歐美社會貧富不均之覆轍。秦力山則把“貧富平等,可以免經濟上之逼迫”作為“社會主義暢行”的標志之一。至于“貧富何以能平等”,他認為此事在歐美“已難望之”,只有中國“尚有此資格”,其辦法是:“他日舉全國之地,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為烏有”,再將無主土地分配給有公民權的成年男女,作為耕種或制造之用,土地收獲國家取十之三四,剩余歸農民所有,如是,“智識與貧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⑧彭國興、劉晴波編:《秦力山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8—90頁。。
五、無政府主義派對社會主義的“絕對均平”解說
20世紀初年,無政府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1907年6月,《天義》報和《新世紀》公開打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旗幟,標志著這一思潮在中國的正式登場。劉師培等人組織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打著研究和普及“社會主義”的旗號,但實質是在公開鼓吹無政府主義。在無政府主義派對社會主義的解說中,也與中國傳統的均貧富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
“天義派”從人類完全平等的觀念出發,認為“自社會主義明,然后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為羞”;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為人民天賦之權”,而民生主義者由于“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革命取得功成,“亦恐以暴易暴”。鑒于此,劉師培等人組建“社會主義講習會”,以研究社會問題為主旨,搜羅西方社會主義學說,以“參互考核,發揮廣大,以餉我國民”①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廣陵書社2008年版,第652、661、699頁。。在《社會革命大風潮》一文中,他們認為,“今日言社會主義者,當以勞動者為主體行社會革命”,而“欲行社會革命,不僅恃罷工已也,必合世界勞動者為一大團體,取資本家所有之財,悉占為已有”;革命成功后,“為農者自有其田,為工者自有其廠,自為自用,不復認資本家之產”,“土地財產均可收為公有,豈非世界之一大創舉耶”②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906—907頁。。劉師培還從權利與義務絕對平等的觀點出發,修正共產主義者關于“人人做工,人人勞動”的說法,提出“人類均力說”,主張在打破國界、沒有政府、土地資本公有的條件下,按照統一的區劃和模式把所有人培訓為“以一人而兼眾藝”或“萬能畢具一身”的全才,以消滅社會分工,實現“絕對均平”③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廣陵書社2008年版,第704—706頁。。在《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一文中,他將“平等”界定為“權利義務無復差別之謂也”,認為“平等之權必合人類全體而后見,故為人類全體謀幸福,當以平等之權為尤重”。在此基礎上,劉師培闡釋了人類不平等的原因、表現和救治方法:“至于近世,學者嫉富民之壓制,競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或依宗教、或依哲理、或依科學作為立論基礎,“然推其立說之旨,大抵謂生產機關,均宜易私有為公有,依共同之勞動,蓄積共同之資本,即以此資本為社會共同之產業,以分配全部之民”。他還對第二國際大多數社會黨的社會主義主張進行了批評,認為它們“或欲運動政府,或欲擴張本黨權力于國家”,即便達到了目的,“政體悉改為民主,然掌握分配機關之人必有特權”,“支配之權仍操于上,則人人失其平等之權,一切資材悉受國家之支配,則人人又失其自由之權”。所以,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能顛覆資本家之財,而不能消滅國家之權也,且將擴張國家之權”,因而不能實現“人類完全之平等”;只有無政府主義才能“實行人類天然的平等,消滅人為的不平等,顛覆一切統治之機關,破除一切階級社會及分業社會,合全世界之民為一大群,以謀人類完全之幸福”④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廣陵書社2008年版,第719—732頁。。
“新世紀派”也堅決反對“世界種種之不平等者”⑤高軍等主編:《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頁。,將巴黎公社革命視為“將來社會革命之先導”,盛贊公社下令接管資本家的工廠交給“工作者協合組織”管理經營是“社會主義之方策”①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978頁。。他們借西方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經濟革命的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之要”,認為社會革命不是少數人聚世界所有之財而分之,而是“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貧富也,一言以蔽之,使大眾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②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999頁。。他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就是要“削去等等階級”,或曰“平等級”,是“平經濟的組織,以絕貧富,尚共產”③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1008頁。;只有“財產廢而為公共”,才能斷絕“貧富之別,饑寒之憂”,達到“同作同樂,同息同游”的理想圣境④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1027頁。。因此,社會主義“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以冀大同;無貧富,無尊卑,無貴賤,以冀平等;無政府,無法律,無綱常,以冀自由”,總之,“社會主義者,無自私自利也”⑤張木丹、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1008頁。。很顯然,這實際上是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兜售無政府主義。
有趣的是,“新世紀派”的李石曾在翻譯“和孟”的《社會主義釋義》一文時,還試圖從概念上來區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譯文認為,若專從經濟上言,社會主義的確切含義是“以生財之物與所生之財皆屬之于社會”,這是各地“政治社會黨”、“革命社會黨”和“共產無政府黨”的一致主張,最接近社會主義的“本意”。若“分而言之”,社會主義還可以細分為“集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前者主張“產業為眾所集有”,其大旨是“各取其所值”;后者主張“產業為眾所共有”,其大旨是“各取所需”。所以從“本意”看,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亦非反背”,沒有根本沖突,前者是就“經濟上”言,后者是就“政治道德上”言,故二者可合稱為“無政府的社會主義”。譯文認為,只有這樣,“社會主義之意乃明晰”,才能使“人聞而明之”、“無誤會”和“名實相符”。譯者李石曾建言:主張無政府主義者,一是常以社會黨或社會主義冠名,“殊覺寬泛”,因而才有“無政府”這一專有名詞誕生;二是鑒于“無政府黨未有非社會黨者,而社會黨未必皆無政府黨”,因而主張無政府主義者與其自稱社會黨,倒不如干脆自稱“無政府黨”,這乃是化解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確有沖突之時”的良方⑥林代昭,潘國華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上),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46頁。。
六、早期日譯著作中對社會主義的“均貧富”解說
據統計,中國各書局、譯書社僅在1902—1903年就翻譯出版了十四本介紹社會主義的日文著作⑦楊漢鷹:《西方社會主義的輸入與中國傳統的均平思想》,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可以說,20世紀初期很多有代表性的關于社會主義學說的中譯本,幾乎都來自日文著作。
1900—1901年連載于《譯書匯編》上的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據說是“中國報刊上第一次使用‘社會主義’一詞,并把馬克思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①林代昭、潘國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介紹到傳播》,載《世界政治資料》1983年第1期。。不過,有賀長雄認為馬克思是“均富之說”、“均產之說”的首倡者,卻是嚴重的誤讀。該書對社會主義的解釋是:“西國學者,憫貧富之不等,而為傭工者,往往受資本家之壓制,遂有倡均貧富、制恒產之說者,謂之社會主義”,并且認為“中國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謂社會主義”②高軍等編:《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頁。。
1903年出版的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中譯本,在“緒論”部分簡要介紹了社會主義產生的原因、社會黨內部不同派別的主張及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由來、定義、目的等。書中指出,歐美社會黨“最后之目的”在于“均一之分配”,從這一目的出發,社會黨內的“共產主義派”主張“生產機關之全部,全然國家而握其主權”,“以其所得之利益,均一而分配于各勞動者之間,以止不法之競爭”;“無政府主義派”屬“過激之論者”,主張“一掃現社會之制度”而達到所謂“真平等”;“公有主義派”或“共有主義派”主張“以財產之絕對的平等為目的”,但不主張廢除生活資料私有制,“乃任許一部之財產私有制,悉委任于國家而為生產機關之全部,各以其勞力勤勉之功果,而受國家應分之報酬”;“講壇社會主義派”或“國家社會主義派”主張“以政府之力,調和于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總之,社會黨“議論之根底,必置于經濟上之主義”,力圖改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采取“均一之制”以“分配其利益,而變更其不平等”。所以,“要求貧富之平均,以改革社會之組織”是社會主義的“定論”③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6、90頁。。
同樣出版于1903年的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中譯本,在第四章“社會主義之主張”中寫道: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生產機關”不得假手于私人,必須“公共而管理之”或“公選代表者而經營之”;社會全體人民都是“業主”,也都是勞動者,“全社會皆勞動,屬于公共的產業之下,無所謂利息,無所謂地主,且兼無徒手游食者,以掠奪勞動之結果”;社會產品“唯以給社會全體之需用,決不使為市場之交換也”,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分配制度,所以“公共的生產之收入”在做了必要扣除后,“余則概分配于社會全體”,此乃“公正之分配”,是“社會主義所以組織產業之必要目的也”④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296頁。。該書對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僅民國時期就有四個中文版本。據吳玉章回憶說,1903年在東京讀《社會主義神髓》以后,感到社會主義“這種學說很新鮮”,書中所描繪的那種“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鼓舞了他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頁。。
在同年連載于上海《新世界學報》上的久松義典的《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一書中,作者指出,社會主義一詞源自英文Socialism,其義“專欲以救藥社會之不平,故名之曰社會主義”。對此,譯者杜士珍在“譯者案”和“感言”中寫道:“社會主義,‘索西亞利士謨’者,其宗旨專在廢私有財產,而為社會財產,為共有財產”,“欲均貧富為一體,合資本為公有”,此乃“公之至,仁之盡”之義舉也②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245頁。。
總起來看,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日譯社會主義著作中,大都把貧富兩極分化以及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努力作為西方社會主義學說和運動產生的原因,并把“均貧富”視為社會主義的精髓或目的。除前面提及的著作外,1899年村井知至在《社會主義》一書中也把“以協和而營業,以平允而分財”視為“社會主義之本領”③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頁。;1901年島田三郎在《社會主義概評》中寫道:“社會主義之主眼,在于論究對勞動者報酬之當否,以救財產不平均之患。”④轉引自談敏著《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上),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頁。應該說,日本學者對社會主義的上述解說,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大,比如《新民叢報》在為《社會黨》一書的中譯本所做的廣告中,就明確稱社會主義學說為“均產之說”⑤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