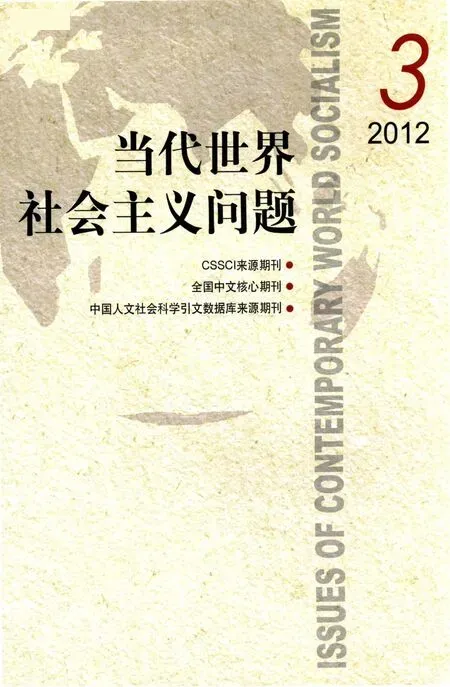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眼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概念》一書簡介*
童建挺 秦 琥
在國內學術界,民主社會主義雖談不上是理論熱點問題,但有關于它的討論卻不時泛起漣漪。然而,民主社會主義自身所信奉的多元化價值觀、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在綱領上的不同側重以及實踐中形成的不同模式,使相關理論概念異常龐雜混亂,國內對其討論中也常常出現某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認真研究和討論民主社會主義,前提在于對其理論和概念的系統把握,而日前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概念》一書對此所作的闡明,至少為我們研究和討論德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概念基礎。
該書是一本專業性的理論詞典,之所以說它體現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眼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因為其編者和詞條的撰寫者絕大多數是德國社民黨的學者、理論家或政治家:主編托馬斯·邁爾長期擔任德國社民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副主席、艾伯特基金會政治教育學院院長,在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方面著述頗豐;卡爾—海因茨·克萊爾擔任過社民黨理事會政策、研究和計劃部主任和歐盟地區委員會社民黨黨團主席,同時對第二國際史頗有研究;蘇珊·米勒曾任社民黨理事會歷史委員會主席,她與書中“工會—概念”等詞條的撰寫者、另一位社民黨學者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合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一版再版,公認是德國社民黨歷史的官方權威讀本。詞條的撰寫者更不乏大名鼎鼎的社民黨政治家:長期擔任該黨主席和聯邦德國總理的勃蘭特撰寫“民主社會主義”詞條,《哥德斯堡綱領》經濟部分的撰稿人、曾任德國聯邦經濟合作部部長的艾哈德·埃普勒撰寫“增長的極限”、“生活質量”,時任德國社民黨理事會環境委員會委員的約·萊內恩撰寫“環境政策”,擔任過慕尼黑和柏林市長、后來接替勃蘭特擔任德國社民黨主席的漢斯—約亨·福格爾撰寫“市鎮(自治)政策”,從自民黨轉投社民黨并擔任過《前進》雜志主編的貢特·費爾霍根撰寫“自由主義”,等等。
正是因為編者和作者的身份,詞條從選擇以至解釋都帶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即鮮明的民主社會主義立場。這首先體現在詞條的選擇上。原書名為《社會主義辭典》,出版于上世紀80年代中,被稱為德語區的第一部社會主義詞典和民主社會主義詞典。它收入六百多個詞條,囊括了在政治和學術討論中與社會主義有關的常用語、基本概念、理論概念、政策、運動、組織機構、人物和事件。它們不是德國社民黨認為有必要闡明的概念,就是認為必須對其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看法的組織、人物、事件和政策主張。對此,本書德文版的前言表述得非常清楚:“‘社會主義’一詞涉及從19世紀工人運動中發展出來的全部努力”,盡管“這些流派從那時開始就相互疏遠”,但有必要“從民主社會主義的角度出發從整體上來考察它們”。中文版譯者從這六百多個詞條中挑選出166個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較為直接的關聯的詞條,加上邁爾新撰寫的幾個詞條,形成了這本辭典,這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完整性,但更加突出了它的系統性。
而在概念的釋義上,這種立場表現得更為清楚。勃蘭特撰寫的核心詞條“民主社會主義”,如果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或許更像一篇政治講話,而不是一個概念解釋。事實上,時任德國社民黨主席的勃蘭特在這個詞條中也確實不是在解釋一個學術概念,他是在代表德國社民黨闡述該黨自身對于民主社會主義的認識。因此,詞條只是概述了民主社會主義在德國的起源,德國社民黨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它的看法,它對于該黨的意義,當前面臨的問題以及未來的前景,既沒有提到這種“主義”的特征,也沒有說明它在歐洲各國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模式。這顯然不是一種學術論證,但它凸顯了德國社民黨的觀點,代表了社民黨官方對于民主社會主義的看法。類似的詞條還有很多,比如福格爾撰寫的“市鎮(自治)政策”,埃普勒撰寫的“增長的極限”、“生活質量”,萊內恩撰寫的“環境政策”,邁爾撰寫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等等。它們無一例外代表了德國社民黨的官方觀點,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從對概念本身進行學術考察的角度看,這樣的解釋不免有失偏頗。然而,如果人們要研究德國社民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研究社民黨的自我定位,它們就是非常權威的解讀,而這正是本書的一個價值所在。
全書圍繞民主社會主義選出的詞條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可以稱為基本概念,即那些在社會主義討論中常常出現,不是直接與民主社會主義相聯系的概念——如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市政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流派,就是與其有重大的立場區別或對立的概念——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等。通過對這些概念的辨析,民主社會主義與這些主義的相似、相同或不同又或對立之處從政治立場上和學術上得到闡明。第二類可以稱為理論概念,既包括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相關的概念,如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啟蒙、理性、古典哲學、天主教社會教義等,也包括早期社會主義、費邊社、米勒蘭主義、中派主義等歷史概念。通過對這些概念的解釋,德國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源泉——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等理論,它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公正、團結、博愛等基本價值,其歷史淵源、理論淵源以及社民黨本身對它們的理解得到系統的說明。第三類則可以稱為政治概念,即與德國社民黨的現實政治活動相關的概念。既有與黨的工作相關的概念,如德國社民黨綱領、宣傳、爭取信任的工作、基層群眾動員、罷工等,也有與黨的政策主張相關的概念,如福利國家、輔助性原則、計劃化、結構政策、競爭政策、結構政策等。這些概念涉及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層面,闡明了社民黨的工作方法以及在各個領域的政策主張。三類概念互為補充,相互加深,從概念、理論和實踐三個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份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系統而整體的解釋。即使對民主社會主義知之不多的讀者難以看出這些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但通過本書,至少也可以清楚地明了德國社民黨在日常的政治和學術討論中常用的這些概念的具體指涉,而研究者更可以把本書所界定的這些理論概念作為共同的討論基礎,不用再在基本的理論概念上作過多的糾纏。這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所在。
不過,在原書出版十多年之后,德國社民黨在全球化、歐洲一體化的沖擊和本國經濟、政治、社會、價值結構變化的影響下,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認識已經有所改變,詞典中對它的解釋是否已經過時了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取決于社民黨的認識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變化無疑不少:就在冷戰結束之后不久,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就已經為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所取代,德國社民黨先后通過了《柏林綱領》和《漢堡綱領》,在其執政期間走上“新中間道路”的嘗試,目前又在大張旗鼓地進行組織改革。不過,用社會民主主義取代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并不涉及這個概念的內涵或者說社民黨本身理念的改變,正如邁爾在本書中所說的那樣,主要是為了“減少由于后共產主義國家或政黨令人眼花繚亂地濫用民主社會主義概念而引起的誤解”。而《柏林綱領》對單方面的進步思想和增長思想的告別,實際上在埃普勒撰寫的“增長的極限”和萊內恩撰寫的“環境政策”中已經有所預兆。至于第三條道路對社民黨傳統立場的“綱領性的和政策的修正”,至少從《漢堡綱領》的內容和社民黨當前的主張看,都沒有涉及社民黨根本價值和理念的變化,當前的社民黨不過是在繼續強調其傳統的同時,采納了施羅德“新中間道路”的一些元素:在經濟政策方面主張“質的經濟增長”,在社會政策方面提出激活性福利國家的理念,強調教育對保障生活機會平等和社會整合的作用,主張政府更多地投資教育事業。就此來看,除了對待福利國家的立場有了較大的調整,社民黨的變化主要出現在經濟、社會、環境等具體的政策領域。它的價值、目標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只不過實現這些價值和目標的工具或手段根據新形勢進行了調整。因此,本書的詞條對民主社會主義基本概念和理論概念的解釋,至今仍然在極大程度上體現了德國社民黨當前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