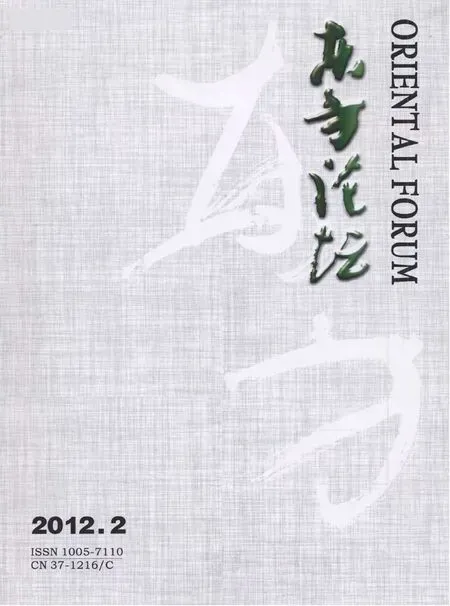論史鐵生對(duì)生命之路的探尋
論史鐵生對(duì)生命之路的探尋
戚 國(guó) 華
(廣東科學(xué)技術(shù)職業(yè)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廣東 珠海510640)
“路”在史鐵生的人生歷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含義。由于雙腿癱瘓,他無(wú)法走路;將近四十年,他不斷地探尋人的生命困境的緣由與終極希望之出路。從荒誕的命運(yùn)謎路走向“愛(ài)命運(yùn)”的審美與藝術(shù)之路,他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求索之路;至終他坦然認(rèn)同并走在仰望與奉獻(xiàn)的愛(ài)愿之路上,完成了他的“過(guò)程即目的”的人生突圍之路。
史鐵生;生命;命運(yùn);荒誕;愛(ài)愿;審美;過(guò)程
史鐵生在他21歲時(shí)因病雙腿癱瘓,后他選擇寫(xiě)作,將寫(xiě)作視為“為心魂尋一條活路”。他曾多次闡述過(guò)自己的寫(xiě)作動(dòng)機(jī):先是為了謀生,然后看見(jiàn)價(jià)值、虛榮和荒唐。他以筆為腿,終生探索擺脫人間困境的道路,慢慢地“一顆世間最為躁動(dòng)的心走向?qū)庫(kù)o”。他的后期寫(xiě)作不再過(guò)多的描述人生外在生活的真實(shí),更主要的是揭示自身內(nèi)在真實(shí)的心路歷程,他一生都在尋找超越困境的道路。
一、“人間戲劇”——走出偶然與荒誕命運(yùn)的精神之路
在對(duì)人生的原生態(tài)進(jìn)行了種種抽絲剝繭的分析后,史鐵生在代表作《病隙碎筆》中得出了人類的命運(yùn)是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并由上帝設(shè)置了精彩紛呈的情節(jié),并且每個(gè)人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diào)換。因此,具有“粒子樣位置”的人就有了“波樣的命定之路”,并由“生日”這天被固定為個(gè)人永遠(yuǎn)的命運(yùn)。他認(rèn)為這種“偶存性”的荒誕與神秘卻要看重并善待它,因?yàn)椤氨囟际腔恼Q領(lǐng)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難”,[1](P9)他在《一種謎語(yǔ)的幾種簡(jiǎn)單的猜法》中說(shuō):萬(wàn)事萬(wàn)物,你若預(yù)測(cè)它的未來(lái),你就會(huì)說(shuō)它有無(wú)數(shù)種可能,可你若回過(guò)頭去看它的以往,你就會(huì)知道其實(shí)只有一條命定的路。
他的作品充滿著對(duì)人類命運(yùn)的思考:人為什么要活著?生存的意義到底是什么?誰(shuí)能把這個(gè)世界想明白呢?我們真的已無(wú)路可走了嗎?在對(duì)人類難解之謎的追問(wèn)與求解的過(guò)程中史鐵生走過(guò)了十多年痛苦的心路歷程,終于明白了:無(wú)緣無(wú)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處境。他早期作品的內(nèi)容與主題常常充滿著命運(yùn)的偶然性與荒誕性,并流露出憤激的情緒。如《山頂上的傳說(shuō)》那個(gè)小伙子因?yàn)榈揭婚g八面漏風(fēng)的潮濕的小屋睡覺(jué)而終生殘疾;《來(lái)到人間》一對(duì)健康的夫妻生下一個(gè)先天性的侏儒,純粹出于偶然;《邊緣》中老頭凍死在自以為床的石頭上。《原罪·宿命》最具代表性,前途光明的青年莫非即將出國(guó)留學(xué),卻忽然“因一秒鐘的變故”被汽車(chē)撞斷了腰椎而好運(yùn)告罄,而悲劇的原因?qū)じ鶈?wèn)底竟是一聲很響但是發(fā)悶的“狗屁”!中期作品《務(wù)虛筆記》中,為了展現(xiàn)命運(yùn)的偶然與荒誕,他更是將同樣的事情讓不同的人都經(jīng)歷,并將我一分為“我”與“史鐵生”兩個(gè)人,時(shí)空界限也被打亂。MR因?yàn)椴豢蛇x擇的出身問(wèn)題而失去了上大學(xué)的機(jī)會(huì),多年的奮斗化為泡影;畫(huà)家Z由于自小家境貧困,受到歧視,而終生走不出屈辱的陰影。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他竟讓靈魂陪同肉身“丁一”一同經(jīng)歷人生的酸甜苦辣,將“我”拆成三個(gè)人:“我”、史鐵生、丁一,他們同時(shí)或交叉出現(xiàn)于作品之中,他一生的思考都濃縮在迷宮般的文體中,讀者若沒(méi)有足夠的耐心很難讀完全篇。仿佛冥冥之中有命定,一個(gè)偶然的非選擇性的原因,就決定一種生命形態(tài)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人生充滿了荒誕和虛無(wú)。他肯定命運(yùn)是“難以捉摸、微妙莫測(cè)和不肯定性”的“黑夜”,而陷入謎團(tuán)之中。他甚至認(rèn)為:人生就是一場(chǎng)苦難,從根本上說(shuō)就是荒誕的(曾被譽(yù)為“中國(guó)的加繆”)。“就命運(yùn)而言,休論公道”這是人類的局限、痛苦與深刻的絕望。經(jīng)過(guò)迷茫、掙扎、困惑后他找到了“一切不幸命運(yùn)的救贖之路”——“生命的意義本不在向外的尋取,而在內(nèi)向的建立。那意義本非與生俱來(lái),生理的人無(wú)緣與之相遇。那意義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實(shí)現(xiàn),那便是神性對(duì)人性的要求。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無(wú)邊的生命意義重又聚攏起來(lái),迷失于命運(yùn)之無(wú)常的生命意義重又聰慧起來(lái),受困于人之殘缺的生命意義終于看見(jiàn)了路。”[2](P97)“在科學(xué)的迷茫之處,在命運(yùn)的混沌之點(diǎn),人唯有乞靈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么,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dǎo)。”[3](P308)史鐵生終于說(shuō)服了自己,把對(duì)苦難命運(yùn)無(wú)法理性解釋的強(qiáng)烈生命意識(shí)轉(zhuǎn)化為精神信念。于是,他由對(duì)個(gè)人無(wú)定命運(yùn)的拒絕與憤怒轉(zhuǎn)變?yōu)樘谷慌c平和的接受,并升華為整個(gè)人類生存本相的擔(dān)當(dāng),還原了人生的悲劇性并具備了崇高的悲劇意識(shí),使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有了自己的空靈、美麗而又詩(shī)意的靈魂之舞,就像史鐵生在作品中一再寫(xiě)到的那只悠然飛翔的白色大鳥(niǎo),純潔、高貴、美麗。他的寫(xiě)作也因著涉及了一個(gè)獨(dú)特而縱深的領(lǐng)域——人的精神和形而上的生命而得到提升,在中國(guó)作家少涉足的區(qū)域開(kāi)出了“一朵朵藝術(shù)奇葩”。在此意義上史鐵生也超越了自己“沉重的肉身”而開(kāi)始走上獨(dú)吟“精神”之路,找到了一條超越人性普遍困境的救贖之路,成為他實(shí)踐人生的第一條突圍之路!為人與為文融為一體,他的人生及寫(xiě)作歷程在與人類困境與個(gè)人宿命較量的過(guò)程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在缺少內(nèi)在精神信仰和心魂建設(shè)的時(shí)代,史鐵生的獨(dú)特寫(xiě)作引發(fā)了我們對(duì)人生意義更深層次的注視。
二、“愛(ài)命運(yùn)”——仰望與奉獻(xiàn)的愛(ài)愿之路
史鐵生的人生態(tài)度在創(chuàng)作后期雜文集《扶輪問(wèn)路》里得到了高度的總結(jié)與概括。開(kāi)篇他就說(shuō):要愛(ài)命運(yùn),愛(ài)命運(yùn)才是至愛(ài)的境界。愛(ài)命運(yùn),既是愛(ài)上帝——上帝創(chuàng)造了無(wú)限種命運(yùn),要是你碰上的這種不可心,你就恨他嗎?愛(ài)命運(yùn),也是愛(ài)眾生——假設(shè)那一種不可心的命運(yùn)輪到別人身上,你就會(huì)松一口氣怎的嗎?在他看來(lái),人置身苦難命運(yùn)中,有兩種基本心態(tài):一是怨恨,一是愛(ài)愿。怨恨使人走向孤苦、爭(zhēng)競(jìng)和虛榮,愛(ài)愿使人走向信仰、尊嚴(yán)和獻(xiàn)身。在《放下與執(zhí)著》中寫(xiě)道:由衷感到,尼采那一句“愛(ài)命運(yùn)”,真是對(duì)人生態(tài)度之最英明的指引。不僅愛(ài)好的命運(yùn),對(duì)一切命運(yùn)都要持愛(ài)的態(tài)度,愛(ài)是人類唯一的救助。愛(ài)命運(yùn)就是與上帝和好,接納上帝給予的一切。愛(ài)命運(yùn)是一個(gè)意志堅(jiān)強(qiáng)的人敢于承擔(dān)非他意志所能支配的一切,是一個(gè)強(qiáng)者正面的人生態(tài)度和積極的人生選擇。“尼采說(shuō),偉大的人是愛(ài)命運(yùn)的。是呀,既不屈從它,也不怨恨它,把一條冷漠的宿命之途走得激情澎湃、妙趣橫生,人才可能不是玩偶。那是什么?又如尼采所說(shuō):既是藝術(shù)品,又是能夠創(chuàng)造并欣賞藝術(shù)品的藝術(shù)家。”[4](P66)“拯救,即在有限向著無(wú)限的詢問(wèn)中、人向著神秘之音的諦聽(tīng)中;而大道不言,大道以其不言驚醒了人間的智慧——唔,那原是一條無(wú)休無(wú)止地鋪向圓滿與善美的神性之路!從而你接受宿命又不囿于宿命,從一個(gè)被動(dòng)的玩偶轉(zhuǎn)變成自由的藝術(shù)家,尊重原著又確信它提供了無(wú)限可能。圣靈即于此刻降臨。所以,拯救必定是‘道成肉身’。”[4](P67)而《欲在》更是一首愛(ài)的贊歌:愛(ài)是對(duì)他者的渴望,對(duì)意義的構(gòu)筑。愛(ài)是拯救,既拯救了當(dāng)下又成就著永恒;愛(ài)是受命于上帝的一份責(zé)任,愛(ài)是主旋律;不管什么樣的生命你都要以愛(ài)的態(tài)度來(lái)對(duì)待,這不單是受造者對(duì)創(chuàng)造者的承諾,更是上帝拯救人于魔掌的根本方略。愛(ài)命運(yùn),不等于喜歡命運(yùn)。喜歡意味著占有;愛(ài),則是愿付出。在生命的戲劇中并沒(méi)有純粹的觀眾。所以,上帝并非是讓你喜歡存在,而是要你熱愛(ài)存在。(創(chuàng)世主)在人四顧迷茫而不見(jiàn)歸途之際,他以其愛(ài)愿,溫暖了這宇宙無(wú)邊的冷漠。真正的神恩,恰是那冷漠的物界為生命開(kāi)啟的善美之門(mén),是那無(wú)限時(shí)空為精神鋪就的一條永不衰減的熱情之路。在《理想的危險(xiǎn)》中總結(jié)為:“人類的一切精神向往,無(wú)不始于一個(gè)愛(ài)字”。在《門(mén)外有路》指出人生的意義“是要把一條困頓頻仍的人生之真路,轉(zhuǎn)變?yōu)橐粭l愛(ài)愿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條無(wú)盡無(wú)休、頗具荒誕的人生之實(shí)路,轉(zhuǎn)變?yōu)樾坳P(guān)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4](P95)只有這樣才能達(dá)到“心靈的完善”。到了生命的晚期,史鐵生仰望“神啟”,做到了豁達(dá)與甘愿。他生前多次表達(dá)過(guò)想把自己的遺體捐獻(xiàn)的愿望,當(dāng)他的呼吸一停止,肝臟就被摘取給急需的患者。史鐵生的寫(xiě)作與他的生命實(shí)踐完全同構(gòu)在了一起。確實(shí),他的腿雖不能站起來(lái),卻比我們有腿的人看得更高更遠(yuǎn);他不能用腳走路,卻比很多走遍世界的人擁有更開(kāi)闊的心,他比我們?cè)S多人都健康!無(wú)論為人還是為文,他都具有著非凡的地位與高度。他設(shè)計(jì)并實(shí)踐的人生突圍的第二條路——愛(ài)愿之路,將鼓舞更多的人加入愛(ài)與奉獻(xiàn)的路。
三、“永恒回歸”——永遠(yuǎn)在過(guò)程中的藝術(shù)與審美之路
史鐵生在《人間智慧必在某處匯合》一文中說(shuō):“永恒回歸”又譯為“永恒再現(xiàn)”或“永恒復(fù)返”,意思是:“一切事物一遍又一遍地發(fā)生”[4](P51),“像你現(xiàn)在正生活著的或已經(jīng)生活過(guò)的生活,你將不得不再生活一次,再生活無(wú)數(shù)次。而且其中沒(méi)有任何事物是新的”,[4](P51)生命的前赴后繼是無(wú)窮無(wú)盡的。但生命的內(nèi)容,或生命中的事件,無(wú)論怎樣繁雜多變也是有限的。有限對(duì)峙于無(wú)限,致使回歸(復(fù)返、再現(xiàn))必定發(fā)生。那是出于人的根本處境,或生命中不可消滅的疑難。“永恒回歸”指的是生命的主旋律,精神的大曲線,根本的路途、困境與期盼是不變的;根本的喜悅、哀傷和思索也不變。生命是沒(méi)有意義的,“永恒回歸”是無(wú)窮路,只能是無(wú)窮地與困苦相伴的路;沒(méi)頭,都得在一條狹窄的道路上做無(wú)限的行走。“永恒回歸完全發(fā)生在這個(gè)世界中:沒(méi)有另一個(gè)世界,沒(méi)有一個(gè)更好的世界(天堂),也沒(méi)有一個(gè)更壞的世界(地獄)。這個(gè)世界就是全部”。[4](P51)人間的智慧——尼采、玻爾、老子、愛(ài)因斯坦、歌德……他們既知虛無(wú)之苦,又懂得怎樣應(yīng)對(duì)一條永無(wú)終止的路。
人生中的過(guò)程與目的是一個(gè)永恒的課題。史鐵生在多篇散文中談到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思索,他說(shuō):痛苦和幸福都沒(méi)有一個(gè)客觀標(biāo)準(zhǔn),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生命就是這樣一個(gè)過(guò)程,一個(gè)不斷超越自身局限的過(guò)程,這就是命運(yùn),任何人都是一樣,在這過(guò)程中我們?cè)庥鐾纯唷⒊骄窒蕖亩惺苄腋#ㄓ羞^(guò)程可以變得十分精彩、美好,值得體驗(yàn)和享受。因此“過(guò)程就是目的”。他說(shuō)到:向美向善是一條永遠(yuǎn)也走不完的路,再怎樣走,月亮走我也走,它也還是可望不可及。只有過(guò)程才是“人類唯一具有終極意義的精神寄托”。史鐵生由開(kāi)始寫(xiě)作關(guān)注目的轉(zhuǎn)向了后期寫(xiě)作的體驗(yàn)過(guò)程,他似乎看開(kāi)了自己的命運(yùn),認(rèn)為也許“上帝讓我終生截癱就是為了讓我從目的轉(zhuǎn)向過(guò)程”,他思想的轉(zhuǎn)變?yōu)槿祟惱Ь秤謱ふ业搅说谌N出路。因?yàn)椤耙粋€(gè)只想使過(guò)程精彩的人是無(wú)法被剝奪的,因?yàn)樗郎褚矡o(wú)法把一個(gè)精彩的過(guò)程變成不精彩的過(guò)程,因?yàn)閴倪\(yùn)也無(wú)法阻擋你去創(chuàng)造一個(gè)精彩的過(guò)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變成一個(gè)精彩的過(guò)程。相反壞運(yùn)更利于你去創(chuàng)造精彩的過(guò)程,于是絕境崩潰了,它必然潰敗。你立足于目的的絕境卻實(shí)現(xiàn)著、欣賞著、飽嘗著過(guò)程的精彩,你便把絕境送上了絕境”。[3](P294)他也多次說(shuō)過(guò):我還是相信西緒福斯的歡樂(lè)之路是最好的救贖之路。他看到了那個(gè)永恒的無(wú)窮動(dòng)才是存在的根本,如尼采所說(shuō)的那樣,以自己的勞頓為一件藝術(shù)品,以勞頓的自己為一個(gè)藝術(shù)欣賞家,把這無(wú)窮的過(guò)程全盤(pán)接受下來(lái)再把它點(diǎn)化成藝術(shù)。人生百般奮斗不斷超越的意義不在于去實(shí)現(xiàn)一個(gè)具體現(xiàn)實(shí)的功利“目的”,而在于不懈追求的“過(guò)程”本身之中,過(guò)程就是目的。西西弗斯就是在滾動(dòng)巨石的過(guò)程中戰(zhàn)勝了絕望,成為壯美的生命過(guò)程的象征。
《命若琴弦》、《對(duì)話四則》是他的過(guò)程哲學(xué)的最形象詮釋:人生一世其實(shí)活得都是一張無(wú)字的白紙,人生的目的是虛幻的、自造的。只有那過(guò)程中滿懷希望彈斷的琴弦才是真正的、實(shí)實(shí)在在擁有的快樂(lè),彈出最優(yōu)美的旋律就會(huì)給人帶來(lái)歡樂(lè),自己的生命的意義也就在這里了。即使一場(chǎng)足球比賽的結(jié)果是0 : 0,但球迷們自始至終保持狂熱的興致。因?yàn)樵诒荣惖倪^(guò)程中球迷們欣賞到了球員的生命的矯健、堅(jiān)強(qiáng)、智慧和優(yōu)美,在輸贏難定的過(guò)程中享受了激情、驚險(xiǎn)、渴望和著迷。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就是美,這就是生活的目的。人生難道不是上帝安排的一場(chǎng)球賽?所有的人都在場(chǎng)上摸爬滾打,企望射中目標(biāo)。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有好運(yùn),每次都能達(dá)到目的,如果只注重目的的實(shí)現(xiàn),人永遠(yuǎn)也不能得到滿足,一生處在無(wú)涯的痛苦之中。所以,人只有把關(guān)注的重心放在過(guò)程之上,在上帝設(shè)置的困境之中不斷超越,人的生活才會(huì)充滿激情,人生才會(huì)獲得快樂(lè)。當(dāng)生命以美的形式證明價(jià)值的時(shí)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藝術(shù)正如愛(ài)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無(wú)盡頭,比如‘詩(shī)意的棲居’可不是獨(dú)享逍遙,而是永遠(yuǎn)的尋覓與投奔,并且總在黑夜中。”[2](P116)
從思想淵源看,史鐵生的命運(yùn)觀與永恒回歸思想都深受尼采影響,而尼采又受古希臘悲劇命運(yùn)觀與佛教輪回的強(qiáng)烈影響。“說(shuō)他與存在主義相通,根本原因在于他對(duì)苦難,對(duì)困境的理解和感悟,正是這些把他引向‘存在的意味’。”[5]作為一種積極的、肯定的命運(yùn)觀,“愛(ài)命運(yùn)”思想是希臘悲劇命運(yùn)、英雄行為和主體意識(shí)的高度升華和綜合。尼采認(rèn)為最高的善是源于創(chuàng)造的善,誰(shuí)要?jiǎng)?chuàng)造,誰(shuí)就要愛(ài)命運(yùn),愛(ài)生命的過(guò)程,而不去追究它的實(shí)質(zhì)和歸宿,從生命的絕對(duì)無(wú)意義性中獲得藝術(shù)快感和審美陶醉。人類既是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者和欣賞者,本身又是藝術(shù)品,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軀殼,在一旁作著美的欣賞。就算人生是個(gè)夢(mèng),要有滋有味地做,不要失掉了夢(mèng)的情趣;就算人生是幕悲劇,也要有聲有色地演,不要失掉了悲劇的壯美。這種審美的人生不計(jì)較任何功利目的得失,而只注重過(guò)程的精彩,不再管坦途還是困境,樂(lè)觀還是悲觀,幸運(yùn)還是不幸,只關(guān)心這一切美還是不美,人便在審美的意義上獲得了超越。史鐵生以自身和整個(gè)人類的生命狀態(tài)為審美對(duì)象,以哲思和寫(xiě)作為自己的審美方式,以博愛(ài)為自己的審美追求,孤獨(dú)而又執(zhí)著地建立起自己的審美世界,他所開(kāi)出的人生困境突圍的第三條路——審美的藝術(shù)之路真的能救贖人類永恒的困境嗎?
綜上所述,可以比較清晰地梳理出史鐵生人生突圍之路的三條路——前兩條即精神與愛(ài)愿之路雖具有一定的超越意味,但還是缺乏神圣的根基,他所言的精神最終并非承載苦難而還是解釋了苦難,走向了自我超脫;他所認(rèn)為的愛(ài)愿的生發(fā)即信仰的過(guò)程,因缺乏具體的信仰對(duì)象而有懸空之感,連他自己也承認(rèn)是證明了神性而否認(rèn)了神。他以愛(ài)愿取代了信仰,以精神取代了上帝,信仰精神既深刻又虛妄。第三條審美之路更使其走了后退的路而回到了原點(diǎn),因?yàn)檫@實(shí)際是一條沒(méi)有盼望、沒(méi)有終點(diǎn)的封閉式的無(wú)效徒勞之路。正如他在《叩與問(wèn)》中所說(shuō):“生生相繼,連突圍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話是永遠(yuǎn)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遠(yuǎn)要存在的。”“對(duì)于永遠(yuǎn)的游魂,危難并不在于旅途的崎嶇坎坷,而在于歸心昭昭然而卻歸路昏昏!‘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6](135)所以在史鐵生的哲學(xué)思索中,盡管存在著一些形而上的追求,但人本主義還是占了主導(dǎo)地位,對(duì)人的主動(dòng)性和創(chuàng)造性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尋找的每條路還是理性、自明之路,他窮其一生所艱難探索出的心靈跋涉之路依然是一條人間的路——沒(méi)有確據(jù)的路——沉浸在人性幽暗的深淵里發(fā)出絕望的呼告和禱愿的路,他是在封閉系統(tǒng)內(nèi)的突圍,其實(shí)是走向了死胡同,沒(méi)有找到活潑的有盼望的開(kāi)放系統(tǒng)的活路。正如齊宏偉所說(shuō):他在寫(xiě)作中把苦難轉(zhuǎn)化為一種信念,沒(méi)有強(qiáng)大的信仰支撐單單依靠自我設(shè)置、自我生發(fā)的神性能否支撐著語(yǔ)言成為存在的家園?信念畢竟不過(guò)是信念,還沒(méi)有凝鑄成完整而有生命活力的信仰,還沒(méi)有超越理性推演和批判反思層面,還沒(méi)有展示出真正有原創(chuàng)力和超越力的精神資源,也還沒(méi)有解決自我信仰與信仰自我等等這些最為內(nèi)在的矛盾和沖突,這致使史鐵生的寫(xiě)作顯得精致有余而大氣不足,解釋過(guò)多而聆聽(tīng)過(guò)少。也正如史鐵生自己所言:“確實(shí),人一直是在解釋的路上,且無(wú)盡頭。事實(shí)上,未必是我們?cè)谧呗罚锹吩谧呶覀儭!盵7](P97-198)其實(shí)在命運(yùn)面前,重要的是承載而不是解釋。
對(duì)人生意義的終極追問(wèn)是古今中外擁有“人間智慧”的哲學(xué)家與思想家們都無(wú)法突破的致命瓶頸。哲學(xué)的盡頭正是神的起頭。生命的困境,只能靠超生命的神去解套。史鐵生雖也多次談到神,但是“說(shuō)神,道主,怕又要惹人疑忌。其實(shí)呢,‘名可名,非常名’,姑且名之罷了。你叫它‘大爆炸’也行,謂之‘太初有道’或‘第一推動(dòng)’也可;名者,不過(guò)為著言說(shuō)之變。”[4](P86)“其作者無(wú)論叫‘上帝’,還是叫‘大爆炸’,一樣都是永不可及的謎。”[4](P136)雖然他信有神,但不是人格的神,也不是自己的救主。他由殘疾走向愛(ài)情,沒(méi)有由苦難走向信仰,正如羅丹的雕塑《行走的人》:無(wú)頭,無(wú)臂,只剩下結(jié)實(shí)的軀干和跨開(kāi)的大步,很盲目地走向前方。他失去了大地,但也沒(méi)得到完全的天空,他只是個(gè)朝圣者,“未來(lái)的路途一樣還是無(wú)限之問(wèn)”。[4](P10)
[1] 史鐵生.寫(xiě)作之夜[M].沈陽(yáng):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2002.
[2] 史鐵生.病隙碎筆[M].北京:中國(guó)盲文出版社,2007.
[3] 史鐵生.別人[M].武漢: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01.
[4] 史鐵生.扶輪問(wèn)路[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0.
[5] 胡山林.苦難把你引向存在的意味[J].南陽(yáng)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4).
[6] 史鐵生.我的丁一之旅[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
[7] 史鐵生.活著的事[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責(zé)任編輯:馮濟(jì)平
On Shi Tiesheng’s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Life
QI Guo-hua
(Faculty of Arts,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Road” had a very special meaning in Shi Tiesheng’s life experience. Paralyzed, he was confined to a wheelchair. The helplessness and pain forced him to take up writing, which was his way of living and where his value lay. During some forty years of “road quest on the wheelchair", he kept on seeking the reasons for the trapped life and the ultimate way out for himself as an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s. It took him a long time to shift from the puzzlement of absurd fate to the aesthetic and artistic road of “l(fā)oving his fate”. Finally, he was reconciled to his fate and was happy on his road of faith and dedication, thus completing his breakthroughs in life with the theory that “process is purpose”.
road;fate; absurd;desire for love;aesthetic appreciation;process
I207
A
1005-7110(2012)02-0070-04
2011-11-27
戚國(guó)華(1962-),女,山東黃縣人,廣東科學(xué)技術(shù)職業(yè)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