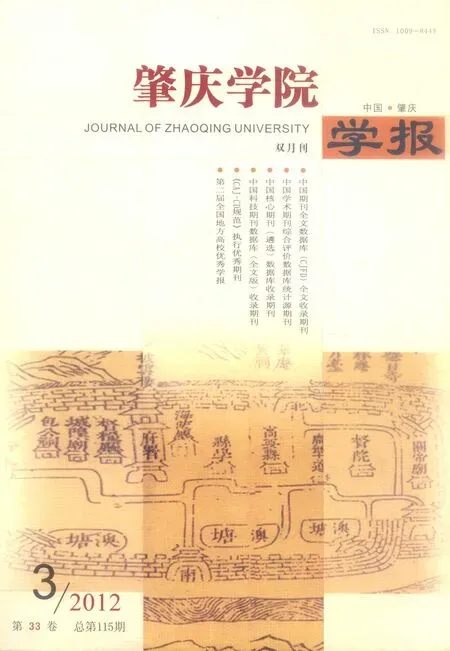利瑪竇與中西醫學交流
何凱文
(肇慶學院政法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利瑪竇與中西醫學交流
何凱文
(肇慶學院政法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利瑪竇是第一個將西方中古醫學理論(四體液說)以及近代生理學(腦的結構和功能理論)介紹進中國的人,同時也是最早向西方社會介紹中醫的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從自然哲學、生理學和醫學方法論等層面系統地與傳統中醫進行理論交流的先河。此外,本文從科學哲學和醫學史的視角,重新評價利瑪竇在中國醫學發展史和中西醫學爭論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遠影響。
四體液;四元素;五行;實體性;醫學觀念革命
當今廣受關注的中西醫爭論和廢止中醫的舉動,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西醫文化交流的當代表現形式。人們一般把中西醫爭論的歷史追溯到清末有“廢醫第一人”之稱的俞樾及其徒子徒孫民國時期的章太炎、余云岫等人。章、余受到近代西方醫學以及日本廢醫運動的影響這已經眾所周知的,而“始祖”俞樾的“廢醫論”被認為是個人原因——出于至親的生命一再被中醫里的庸醫所誤,乃至遷怒于中醫體系。另有王清任氏重視經驗觀察,觀察死刑犯的尸體,發現了傳統中醫論述“臟腑”的位置與自己所觀察到的事實嚴重不當,遂于1830年著《醫林改錯》,試圖指正中醫幾千年的所謂的“流弊”,從而“自發、自覺”地“開創”了中國醫界近代生理解剖學的新風。今日學界似乎普遍認為俞樾、王清任二人質疑中醫理論乃是基于自身的經驗認識,兩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近現代醫學開創者,似乎沒有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但在中醫發展兩千年的歷史上,有他們兩人這樣的經驗的人肯定不少,但為什么直到清朝后期才出現這種“背經離道”的事情呢?僅僅把他們的質疑中醫理論的舉動視為基于經驗認識的觀點并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
學術界有一個由美國當代科學哲學家漢森提出的、得到廣泛認同的命題——“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經驗觀察并不是純粹的客觀、中立的,而是受到觀察者固有的觀念或理論的影響的。據此,我們可以推測,俞、王等人的認識不僅來源他們自身的經驗,還有一定的觀念或理論背景。
他們除了中國傳統的學問之外,還有什么知識觀念背景呢?事實表明,西方醫學和生理解剖學,如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說概》、《人身圖說》等,已經在清朝社會上廣為流傳。有理由相信,相對于傳統的學問,西方的生理解剖學思想更有可能成為俞樾和王清任質疑中醫的觀念和理論背景。
西方的生理解剖學在中國的傳播,自然會與中國的相關的學科,特別是中醫,發生交流和沖撞。因此,中西醫的理論爭論歷史,似乎可以追溯到比余云岫,乃至俞樾、王清任更早的耶穌會傳教士。本文正是基于這個認識,試圖揭示和論述早在四百多年前,作為耶穌會傳教士的利瑪竇已經開展了中西醫理論對話,而且將中西醫理論的對話深入到自然哲學領域,影響了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同時,正是在利瑪竇的影響下,其他的耶穌會士陸續著述和翻譯醫學和生理解剖學書籍,進而擴大和加深了西方醫學對中國學界的影響。故此,本文認為,利瑪竇是真正的開創中西醫理論交流與對話的先驅。
眾所周知,利瑪竇在促進西方的數學、天文歷法、地理學、地圖制作、機械、音樂、繪畫等方面的知識向中國傳播和交流的貢獻很大。但他在中西醫學交流方面的作為和影響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其影響遠被低估。
誠然,利瑪竇的西方醫學思想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醫學思想,但現代醫學的理論根基仍然是利瑪竇所在中古時期的西方傳統醫學的繼承和發展,西方傳統的還原論和構成論的醫學觀和方法論,以及相應的醫學倫理原則,仍然保留下來。而利瑪竇時期的歐洲醫學,正是承上啟下的時期。一方面這個時期還保留著古希臘的醫學傳統;另一方面,近代醫學的萌芽已經通過近代的生理學和解剖學體現出來了。因此,追根溯源,重新認識利瑪竇在四百年前開啟的中西醫平等的對話和交流,或許能夠得到某種啟發。
本文將首先考察利瑪竇在中西醫交流過程中所持的基本立場和醫學觀,進而具體分析利瑪竇在不同層面與中醫的交流的事實,以期更全面、深入地認識和評價利瑪竇在中西醫學文化交流方面的影響和意義。
一、利瑪竇的醫學觀
只有知道了利瑪竇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才能深入地理解他是如何處理現實和理論中的醫學問題的。那么,利瑪竇是如何看待醫學的?可以相信的是,作為一個由耶穌會學校精心培養多年的虔誠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的態度和立場顯然會與耶穌會保持一致。因此,首先要了解耶穌會對待醫學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會認為疾病是上帝對人的罪惡的懲罰,不主張積極對患者進行醫學上的治療,而主張引導病人進行懺悔和禱告,以獲得上帝的寬恕。故教會曾禁止神職人員行醫,特別是外科。直到1576年2月,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開始允許所有精通醫學的耶穌會士在會長的允許下,在任何難以找到世俗醫生的地方行醫,不過外科仍然不在允許的范圍之內。
在1540年成立的耶穌會在其《耶穌會會憲》中規定,耶穌會的大學不設立醫學和法學的科目,起碼耶穌會是不會參與這類事物的[1]38-40。但事實上,耶穌會并不反對醫學,而是在有利于傳教事業的前提下,將行醫和傳教結合起來,將行醫和照顧病患之人視為修行和傳播教義的一種方式和手段。醫學,與科學和技術一樣,耶穌會士們看來,都是通向上帝之路。它們成了耶穌會傳教的工具,可以被利用來引導人們“沿著自然顯示的合理性,即科學規律的道路,可以認識人格化的上帝”[2]62。
由此可見,耶穌會的醫學立場和觀點可以簡要表達為:基督教信仰優先,允許醫學有限度地存在和發展,利用醫學為信仰服務。
事實表明,利瑪竇信奉和實踐了這一立場。在面對疾病時,他不是積極地醫治疾病,而是優先選擇傳播教義和奉教修行——在面對其他病人的時候是傳播教義為優先;在面對自身的疾病的時候是奉教修行。以下兩個實例可以證明這點:
其一,據《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第一個公開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就是一個來自肇慶本地社會底層的病人[3]170。本地的醫生斷定他得了不治之癥,家人已經無力負擔其醫療費用,因而將他拋棄在大路邊。耶穌會的神父們出去找到這個病人,讓他住進干凈的房子里,并讓他成為第一個自愿接受洗禮的“大帝國”的臣民。這里雖然沒有直接記錄神父們在這個救治和救贖病人的過程中是否運用了在歐洲所學的醫學知識,但從這個相對簡潔的記錄中可以判斷:利瑪竇作出了“治療肉體疾病已無希望”的判斷。這當然是一個醫學判斷,能作出這一判斷說明他具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和醫學經驗;利瑪竇認為,盡管“治療肉體疾病已無希望”,但可以“照顧他的靈魂,”讓他回到上帝懷抱,獲得極樂。這說明利瑪竇堅持“宗教正確”之立場,他始終是以宗教關懷為主照顧病人,而不是醫藥治療。
其二,《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了利瑪竇的同事麥安東神父之死,面對疾病的折磨,沒有記載醫治的記載,只有神父們的祈禱、彌撒、圣禮的安慰[3]256-257。
利瑪竇在傳教事業上,在傳播科學、技術(自鳴鐘、地圖制作等)和翻譯《幾何原本》上都很積極,但這不是意味著利瑪竇冷落醫學。這可能與利瑪竇在歐洲所受到的教育有關。一方面,利瑪竇在來華之前并沒有受到多少醫學方面的教育。除了宗教教義的學習之外,利瑪竇其它的學習時間主要花在哲學、法律、數學、天文等方面。另一方面,也與基督教教會對醫學的保守立場有關。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學,神學、哲學、法律和醫學是四個傳統的學科,但醫學排名最后,內容最少,但基督教不排斥醫學,而是認為,醫學研究是基督智慧中的一個完整部分[4]118。
在客觀上,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向外(包括東亞)傳播了西方包括醫學知識在內的自然知識和相關技術,其作用相對于殖民者和商人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耶穌會士中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較高的西方文化修養的人才比比皆是。正是利瑪竇和其他的傳教士如鄧玉函、卜彌格等人也是在將醫學作為傳教工具的過程中,成全了中西方醫學的早期的交流和對話。
二、利瑪竇的醫學交流活動
(一)利瑪竇與中醫生的交往以及對中醫醫技的評價
利瑪竇在中國的二十八年間,結交了一些中醫生,其中儒醫代表人物王肯堂(1549—1613),為醫學百科全書《六科診治準繩》的作者[5]603。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利瑪竇多次提到的王姓醫生(意大利文稱名為Guanchileu,音譯為“王繼樓”)。王在南昌傳教過程中把利瑪竇引薦給上流社會,對利瑪竇的幫助很大[3]294-295。
利瑪竇長期與王繼樓交往,甚至在他家里住過三個星期,把王醫生發展成為一個基督教徒。王醫生用了很多時間陪同他一起討論各種問題,包括自然哲學和神學問題[3]349。而哲學問題必然會涉及到中醫的理論基礎——陰陽五行說。
正如本文后面將要論及的那樣,利瑪竇在理論層面質疑作為中醫理論基礎的陰陽五行說,但在臨床實踐層面,他對中醫有較高的評價。利瑪竇是最早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醫學的人之一。他說:“中國的醫療技術的方法與我們所習慣的大為不同。他們按脈的方法和我們的一樣,治病也相當成功。”除此之外,他還介紹了中國的草藥、醫學教育、醫學在社會和學術領域的受重視的程度等[3]34。
利瑪竇本人還接受中醫生對他進行的中醫治療。例如,利瑪竇在蘇州患病近一個月,曾得到瞿太素的精心照顧,但瞿太素不是醫生,自然少不了請中醫來為他診治,使利瑪竇完全恢復了健康,甚至感覺恢復得比病前還要健康[3]339。另有記載,利瑪竇臨終前幾天,李之藻曾派自己的私人醫生來給他看病。而后,耶穌會神父們也先后找了六位醫生來給他診治[3]612。無疑,這七位給利瑪竇看病的醫生都是中醫。這是利瑪竇和照顧他的神父們與中醫生交往的歷史事實,也是傳教士們不排斥中醫治療的明證。
(二)基于生理解剖學層次的理論交流
當然,利瑪竇所接觸到的醫學理論,主要還是希波克拉底傳統的蓋倫醫學。這也是中世紀的歐洲的主流醫學。利瑪竇來到中國大陸的時候(1583年),正是西方醫學經歷從中古代蓋倫醫學轉型和發展到近代醫學的時期。近代解剖學的奠基之作、比利時醫學家維薩里(A.Vesalius)的《人體的構造》已經出版整整四十年了,以此為基礎,歐洲的近代醫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醫學基礎也會受到以人體解剖學為基礎的歐洲近代醫學的影響。
1599年,利瑪竇在南昌刻印出版了顯然受近代生理學影響的《西國記法》。《西國記法》分原本、明用、設法、立象、定識、廣資等六篇,介紹了記憶方法和人腦的生理結構和功能理論。
《西國記法·原本篇》簡要講述了西方的腦的結構和功能,即腦與記憶的關系:“記含有所在腦囊,蓋顱囟后、枕骨下為記含之室。故人追憶所記之事驟不可得,其手不覺搔腦后,若索物令之出者,雖兒童亦如是。或人腦后有患則多遺忘。”[5]279
《西國記法》如此分析腦在記憶過程中的功能:“人之記含有難有易,有多有寡,有久有暫,何故?蓋凡記識必自目耳口鼻四體而入。當其入也,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均似以印腦。其腦剛柔得宜、豐潤完足則受印深而明藏象多而久;其腦反是者,其記亦反是。”“如幼稚其腦大柔,譬如水,印之無痕,故難記;如成童其腦稍剛,譬如泥,印之雖有跡,不能常存,故易記亦易忘;至壯年其腦充實,不剛不柔,譬如衤者帛,印之易而跡完具,故易記而難忘;及衰老,其腦干硬大剛,譬如金石,印之難入,入亦不深故難記,即強記亦易忘。……博學強記之士,人以石擊破其頭,傷腦后盡忘其所學,一字不復能記。又有人墮樓者遂忘其親,知不能復識。”[5]279
利瑪竇的以上分析運用了類比論證,切合人的基本經驗,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受到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上層知識分子的贊賞。
傳統中醫本來就缺乏對腦的結構的研究,而且在功能方面,心腦的區分是不嚴格的。中醫在功能意義上講,腦是屬于內涵豐富的“心”這一范疇的。因此,利瑪竇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通常認為人的記憶是由“心”來主導的。因此,“記含有所在腦囊”的觀點對中醫來說幾乎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利瑪竇傳入這些觀點和理論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包括醫學界影響很大。這客觀地鼓勵了其他傳教士進一步把西方的醫學和生理學傳入中國,為隨后的生理解剖學傳播奠定了基礎,開啟了中西醫對話的濫觴。1623年,艾儒略著的《性學粗述》在杭州出版,介紹了西方的人體生理知識。鄧玉函翻譯的《泰西人身說概》以及與人合撰的《人身圖說》,在利瑪竇的基礎上更系統地介紹了西方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知識。
(三)利瑪竇的醫學方法論之“四體液”說
四體液說是歐洲傳統的病因學說,即關于引發疾病的原因的學說。古希臘的“醫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約公元前460—前360)提出了關于疾病的本質的學說——四體液說。他認為,疾病乃是人體內部的四體液(血液、黏液、黑膽汁、黃膽汁)失去平衡。四體液說被蓋倫(公元130—公元200或210)繼承下來。中世紀歐洲乃至文藝復興時期,四體液說仍然是主流醫學,蓋倫被稱為“醫學教皇”以及解剖學和生理學家的“導師”[4]101。
利瑪竇把四種體液(血液、黏液、黑膽汁、黃膽汁)翻譯為血、白痰、黑痰、黃痰。盡管四體液說是一種整體論,但這種整體論是可分解的,因為任一體液都是最終的不變的實體性存在(利瑪竇謂之“恒性”)。這一人體之整體性乃是基于四種可分解的體液要素之間的數量加減,故是一種構成整體論①在本文中,“構成”與“生成”是一對哲學范疇。“生成”指的是世界萬物是由一個整體生出另一個新的整體,其終極因乃是無。而“構成”則是指世界萬物由實體聚合而成,構成的終極因乃是不可再分的微粒實體。主張整體是生成的理論,及時生成整體論,而主張整體是構成的理論,就是構成整體論。與四體液說的構成整體論不同,中醫的病因學說乃是一種基于陰陽五行生克平衡的生成整體方法論。五行的每一行同時具有生和克(勝)兩種功能,生是目的,克亦是為了生生不已的目的終成。木火土金水之間“比相生而間相勝(克)”,形成生克兩個完整的循環。五行每一行都是一個連續生克過程的一部分,任何一行的屬性依賴于其在整體中的功能和關系來定義,不能離開其它行而存在。五行模型可謂是關于系統生成演變的最簡單模型,一個完整的五行生克循環即是最小的生成單位。整體不是由更小的部分構成的,而是由更小的整體生成的。傳統中醫學認為,人是一個有機的生成整體。陰陽五行生成的過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中醫稱為“平人”,即是健康的人。當陰陽五行生成的動態平衡因某種原因而遭到破壞而未能及時恢復時,即為疾病。破壞平衡,引發疾病的原因就是病因。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中醫的陰陽五行說是一種生成整體論。。利瑪竇認為,人發生疾病乃是因為四種體液的比例不調和(“人發病疾,蓋四液不調耳”)[6]。有學者考證,利瑪竇是最早把歐洲醫學理論的四體液說介紹給中國的人[1]325。
利瑪竇試圖以四體液說來否定陰陽五行說的病因解釋。利瑪竇之所以有足夠的信心祭出四體液說來否定中醫,不是因為臨床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對四元素說有信心。四體液說作為一般的醫學方法,其賴以成立的哲學基礎乃是四元素說。利瑪竇認為四元素說足以否定五行說,故四體液說比中醫的病因說更能夠解釋疾病形成的原因。
(四)利瑪竇的醫學哲學層次的四元素說
在利瑪竇之前,耶穌會士羅明堅曾向中國簡要介紹西方傳統的自然哲學中的四元素說。而利瑪竇在與王繼樓等醫生的討論后,在南京以漢語撰寫《四元行論》,并印刷分發,系統地向中國介紹了四元素說,以駁斥中醫的理論基礎,包括氣論和陰陽五行說[1]324。這引起中國知識階層很大興趣,為利瑪竇獲得很大的影響[3]350。
四元素說乃是古希臘的恩培多克勒(Empe docles,約公元前500—前430)開創的一種形而上學理論,被亞里士多德繼承和發揚,成為西方近代之前的科技醫史上的重要的自然哲學基礎。四元素說認為,所有的物質均由四種基本的、永恒的元素構成:氣、土、水和火。四種基本元素始終保持自身的性質和獨立平等,不能轉化為同類元素和其它元素,乃基本而永恒的有形實體。宇宙和人類的存在和變化無非就是這四者的混合和分離而已。四種元素按比例的混合體而展現為具有整體功能的有機體,包括人與自然萬物。
利瑪竇是如何利用四元素說來批駁五行說的呢?
1.將非實體性的“行”化為實體性的“元行”
利瑪竇的《四元行論》首先將中醫的過程性的、非實體性的“行”翻譯為“元行”,賦予“行”以“元素”之純粹的、最終實體性存在的內涵(所謂行者,乃萬象之所出。則行為元行,乃至純也,宜無相雜,無相有矣)[6]。但是,五行之“行”是不是如利瑪竇所理解的“實體性的、純粹的物質存在”——元素或元行?據東漢《說文解字》云:行,人之步趨也。在現代漢語里,“行”的基本義是邁步往前走,進而引申為運行,運動。五行,即是五個運動過程。
受利瑪竇影響,傳教士高一志在其《空際格致》一書中也是把過程性的、非實體性的“行”與實體性的“元素”概念混淆,并認為“五行”的劃分不合理,因為“五行”之“五元素”僅僅是四元素而已。高一志認為:“元素乃純物質,概因分解而不能成任意他物,唯能成諸元素混合之物。何謂純物質?此乃無他混合元素之單性物。世間萬物由此皆可據純混區分。純者有土、水、空氣、火四元素,混者呈五態:雨、露、雷、光等為一,金、石為一,花草、樹木、五谷為一,飛禽走獸為一,人為一,此五態皆由四元素混合而成。”[7]27
可見,利瑪竇等人僅僅是拘泥于文字字面含義,并沒有深入充分理解五行說的內涵。在比較過程中,站在西方自然哲學的立場上,強行格義。
因此,利瑪竇將非實體性之“五行”具體化為生活經驗中的"五材"的做法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古代曾經將“金,木,水,火,土”理解為器物層次的、實體性的“五材”。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又如《周禮·考工記·總目》記載:“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五材”指的是形而下之器物。但是,“五行”不是“五材”。五行具有超越于“五材”之形而下內涵的、更深層次的意義。而利瑪竇在《四元行論》中將“五行”理解為實體性的形而下器物——“五材”,借以否定五行。他認為,木(材)的生長同時有賴于土(材)的培植和火(太陽)的溫煦作用,不能夠單獨歸結為由水(材)來生[6]。
正如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史研究所的滿晰駁(Manfred Porkert)教授所指出,利瑪竇等基督教傳教士們將“五行”理解為實體性的"五個要素"是不當的。滿晰駁發現,一直以來,包括當代的一部分中國人最能接受這種解釋,因為這些中國人從中看到了對五行說的一個“唯物主義”的解釋。他意識到這是中國人的自我損害的決定,就像西方科學家決定頒布一條在實現定量表述和數據的無歧解中不再使用米突制或者任何別的定量標準的禁令一樣荒謬,因為這種喪失自身文化判斷標準的決定阻擋了人們對中醫傳統的理性探討和對中醫傳統的興趣,并且使它的實踐應用變得毫無意義和效用[8]546。
2.以四元素的線性關系來否定五行的非線性關系
由于“四元素”乃是一種永不變性的純粹實體,所以,四元素之間的關系選擇一種簡單的數量加減,而質疑五行之河圖數,即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這五個數來自儒家經典《尚書大傳·五行傳》,其中記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利瑪竇認為:一二三四五這些數字應該依次序相生,而五行說的生成次序是混亂的,或反轉,或間位;因此,五行說是不合理的[6]。可見,利瑪竇試圖以四元素之間的線性關系來否定五行之間的非線性關系①線性,指量與量之間按比例、成直線的關系,在空間和時間上代表規則和光滑的運動;而非線性則指不按比例、不成直線的關系,代表不規則的運動和突變。“線性”與“非線性”常用于區別函數y=f(x)對自變量x的依賴關系。線性函數即一次函數,其圖像為一條直線。其它函數則為非線性函數,其圖像不是直線。。
3.將五行說、氣論與四元素說錯位比較
利瑪竇將具有宇宙論意蘊的四元素說比照方法論層面的五行說,將物質實體的氣元素比照宇宙論的“氣論”,可謂是錯位的比較。本來應該是“四元素說”之宇宙論與“氣論”之宇宙比較,“四性情說”和“四體液說”之方法論對“五行說”之方法論的比較。結果成了“四元素說”對比“陰陽五行說”。
實際上,四元素說是中古時期歐洲的一種自然觀和宇宙論。利瑪竇告訴他的中國論辯對手:只有四種元素,它們具有相反的特性;天空之下火占有基本土地的一大部分。彗星和流星也燃燒著在地上所看到的那種同樣的火。四元素之由輕至重,由上到下分布為火、氣、水、土[6]。
而中醫與之可比的、帶有宇宙論內涵的乃是“元氣論”,或曰“氣論”。氣是貫穿于天地人宇宙各個層次的非實體性的、無時不在運動的物質存在。五行是非實體性、動態的氣運行的五種狀態,而且這五種狀態是一種生成關系,乃是一種生成整體論的宇宙論,而四元素說論述的是不變實體之元素的按比例的組合和分離的關系,乃是一種構成整體論的宇宙論。利瑪竇不理解“氣論”的真實內涵,反而認為這是奇談怪論,并驚訝于中國人一點也不知道作為實體性的、純物質的元素——“(空)氣”[3]350。
本文認為,真正應該拿來與五行說比較的四元素說衍生出來的“四性情”(熱干冷濕)[6]和四體液說,因為“四性情”和四體液說是方法論層次的理論。如果這樣的話,可以發現兩種方法論的差異在于,五行說是立于(生命)實踐基礎的方法論,而“四性情”說和四體液說是基于理論思辨和概念知解上的方法論,限于篇幅,此處不欲詳論。
可見,利瑪竇是歷史上第一個將“五行”之“行”翻譯和理解為“元行”或“元素”的人。他的這一缺乏深度了解基礎上的比較和會通行為乃是一個不具足夠理論依據、非等價性比較的做法,誤導中西學界四百年,至今很多的研究仍然囿于利瑪竇開拓的思路不能超出。利瑪竇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對陰陽五行說進行理解和格義的。從比較的技術、方法上來看,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奇怪的是,這一方法似乎為后世比較“四元素說”與“陰陽五行說”立下了規范和視域,至今仍然陷在肇始于利瑪竇的窠臼中者比比皆是。
值得指出的是,“陰陽五行說”兼具“陰陽之道”本體論,這是氣、萬物存在的依據,乃至中醫的價值之源。故“陰陽五行說”實際上可以開出道本體論說來對比利瑪竇從神學里搬出來充當“元行”和萬物之本體的“造物主”[6]。
中國傳統中醫沒有把心物截然分開。“氣”乃是既貫穿天地人,也貫穿精、氣、神等范疇。實際上就是貫穿西方文化中的“精神和物質”世界的非實體性的動態存在。利瑪竇的世界是“精神和物質”兩分的。四元素是物質世界的存在。他認為“精神世界之靈魂”另有本體(造物主)存在,于是他將中醫的“氣”理解為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四種純物質)中的“空氣”,沒有把氣論與陰陽五行說區分開來。利瑪竇之后的傳教士高一志也認為中國人沒有意識到“氣”是一種純物質——元素。
4.否定五行存在的本體論依據
中醫是以陰陽五行說和氣論為理論基礎的。陰陽五行學說不僅是中醫方法論原則,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哲學基礎,上可通達形而上本體之“道”,下可為形而下之“器”立可效法之“象”,也就是說,陰陽五行說具有“形而上”之超越意義,也可為具體的學科和技術層面的方法論之原則。例如,中醫的經絡、腧穴、藏象、治則、本草等具體的方法論乃是以氣論和陰陽五行說為基礎的。因此,批駁倒了陰陽五行說,中醫的具體的防病治病方法就成了一些沒有理論根基的經驗之談,沒有有效的、理性的因果解釋的神秘主義,成為近乎巫術的“原始醫學”。
從理論邏輯上講,人們還可以追問四元素存在的依據。這涉及到終極存在問題。作為傳教士的利瑪竇將之歸結為造物主。在與中國學者的討論過程中,利瑪竇等人發現,“中國學者除了遵古而外,并沒有別的信仰依據,所以他們教導說有五種不同的原素(即“元素”——本文作者)。他們沒有一個對此懷疑,或者想加以疑問。這些原素是一一派生的。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有空氣,因為他們看不到它。對他們來說,空氣所占的空間只是虛空而已。然而當他們推論錯誤的時候,他們卻并不頑固堅持錯誤的結論。利瑪竇神父很少管或者根本不管他們對古代權威的信仰”[3]349-350。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在這里,利瑪竇等人為元素或者原素之存在立下“信仰的依據”。利瑪竇等人認為“五行”、“氣”存在和成立的依據乃是基于中國學者的“尊古”,這是不可靠的;而西方四元素說則是從“造物主”那里找到了存在的依據,這是可靠的。信仰是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的,這是人類理性的界限。在利瑪竇看來,因為這已經把源于方法論的問題引申到本體論層面,而利瑪竇的本體論依據自然只能追溯到上帝(造物主)。到了這步已經沒理可講了,利瑪竇只能訴諸信仰。所以,利瑪竇“很少管或者根本不管他們(中國學者)對古代權威的信仰”,而只管自己的信仰,這是必然的。
三、利瑪竇對中西醫交流和發展的影響
(一)利瑪竇直接改變某些中國知識分子醫學觀念
利瑪竇把《西國記法》、《四元行論》等文章裝訂成精美的書籍送給明朝的宗室貴族和官員,借助他們的影響力在中國上層社會中流傳[3]301。通過各種手段的交流,利瑪竇的自然哲學、醫學和生理學知識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一大批人。從醫學及其相關方面受利瑪竇影響的人有兩類:
一是上層知識分子。在中國上層知識分子中,利瑪竇已經種下了西方醫學和生理學的種子。除了王繼堂這樣交往密切的知識分子外,連崇禎時期進士出身的金正希都知道:“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小兒漸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凡人外見一物,必有一形留于腦中。”這種說法明顯受到利瑪竇的影響。明末清初著名的中醫學者汪昂著有一本流傳甚廣的《本草備要》,其中認為“人之記性,皆在腦中”(《本草備要·辛夷》)。另外,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方以智也受利瑪竇的影響,將人的聰明、記憶能力歸之于腦髓[1]393。
二是先后來華的傳教士。這些人往往都是受過良好的西方醫學和生理解剖學的教育,如金尼閣、鄧玉函等人。金尼閣是利瑪竇的朋友,也是《利瑪竇中國札記》的整理者和作者之一。1618年,金尼閣把知識淵博的學者鄧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及其他新招募的傳教士帶到中國。鄧玉函其后在中國著有《泰西人身說概》,以及與羅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合作的《人身圖說》,一并成為最早傳入的西洋生理解剖學著作,對中國學界,特別是醫學界的醫學觀念影響巨大而深遠。
值得指出的是,與后世的中西醫交流相比,利瑪竇在中西醫之間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及其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主要在醫學觀念上,具有更純粹的學術意義①在19中后期以后的中西醫交流,逐漸摻雜進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現實利益,如經濟、政治、軍事等的因素,使得中西醫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復雜。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在華的醫學活動與其它社會活動,如經濟、政治、宗教,甚至軍事方面的結合越來越緊密。茲舉幾例證:其一,中國近代史上,美國基督教會的牧師彼得·伯駕(1804-1888,Peter Parker)來華初期,傳教兼行醫,后升任美國駐華公使一職,并成功建立了著名的廣州教會醫院(后改名廣濟醫院)。其二,美國在華的教會協會曾經有這些主張:“欲介紹基督教于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藥;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教士。醫藥是基督的先鋒,而基督教又是推銷商品的先鋒。”其三,裨治文牧師曾經放言:“我等在中國的傳教之人,與其說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舉例證參見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M].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18.)。盡管利瑪竇的學術交流難免摻雜宗教因素。畢竟,對利瑪竇等耶穌會士而言,醫學是為傳教服務的,是傳教的一個主要的知識工具。不過,宗教因素在醫學交流過程中也并非完全的消極。從另一方面來看,正是宗教的因素,使得中西醫的交流能夠超越“形而下”之現實功利因素,深入到醫學后面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層次,即探討中西醫的自然哲學基礎,這使得利瑪竇的在醫學方面的對話與交流具有更豐富的理論內涵。
(二)利瑪竇引發的“蝴蝶效應”②1963年,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Lorenz)曾經詩意地描述了非線性系統或混沌性系統演化的一個特征:一只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能在兩周后在美國德克薩斯引起一場龍卷風。后被稱為蝴蝶效應,這成為混沌學的重要概念。它揭示了,事物發展對初始條件具有極為敏感的依賴性,初始條件的極小偏差,將會引起結果的極大差異。不唯自然系統,就在各種社會系統中,蝴蝶效應也是比比皆是。往往一個微小的改變,可能會給社會系統帶來非常大的影響。例如:橫過深谷的吊橋,常從一根細線拴個小石頭開始;一國宣布試射導彈的消息,便可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大動蕩。個人的事件,可以引發全國甚至世界性的大事件。暨王清任的局部的“醫學觀念革命”
當代著名的科學史學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席文(Nathan Sivin)教授認為,耶穌會士帶來的科學導致了18世紀的中國發生了科學革命,主要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人們的科學觀念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即使得中國當時的天文學家逐漸相信“數學模型能夠解釋并預測天象”[9]509-510。當然這僅僅是“觀念”或概念(concept)意義上的科學革命,中國天文學家的文化價值并沒有改變,特別是社會建制意義上的革命需要到19世紀末期才形成。席文從科學史角度解讀的中國“科學革命”,實際上是一種有限的“科學觀念革命”。
耶穌會士可謂是一個具有“科學革命傳統”的基督教教會組織。在近代歐洲的科學革命過程中曾經起過促進作用。以色列學者菲爾德海(Rivka Feldhay)發現,耶穌會士突破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傳統觀點,認為救贖靈魂的道路除了默禱敬神修行之外,還要通過學習知識來實現。而在知識觀上,耶穌會士又突破了傳統的托馬斯主義的局限,他們指出,從假設出發,通過數學和邏輯得到的結論,是能夠與觀察到的現象保持一致的。因此說真正知識或認識的對象,除了實體性的客體之外,還有理論上假設的實體(如托勒密天文學理論中的本論、均輪等)。耶穌會的新的知識觀,為數學在物理學中的應用鋪平了道路,在傳統的經院哲學與近代物理學之間架起了過渡的橋梁[10]208-209。
自從耶穌會來到中國發展以后,在幾十年的經營過程中,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很大。耶穌會士不僅引發了天文學和數學的“觀念革命”,實際上對中國醫學領域也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醫學在19世紀前期發生了有限度的“醫學觀念革命”,具體表現是對中國的醫學觀念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有一個明顯的前所未有的現象出現在中國歷史上,即在利瑪竇等傳教士將西醫及相關理論傳入中國以后,19世紀的中國先后出現了一些批評中醫甚至要求廢止中醫的人,其中尤其以王清任和俞樾為有名,這是中醫幾千年發展史上從未有的新事。
王清任是清朝乾嘉時期的名醫,他曾親自觀察三十余具小兒尸體和犯人尸體,以近乎300前近代西方生理學奠基人維薩里的精神,“前后訪驗四十二年,據所實睹者繪成的臟腑全圖而為之記”,發現了中醫經典書中所繪臟腑多不符人體實際。1830年撰成的《醫林改錯》兩卷,一版再版,開一代新風,被譽為中國近代醫學史上一件大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他有科學實證精神,“誠中國醫界極大膽之革命論”者。
《醫林改錯》開篇即表明該書是解剖學著作,其自序云:“余著《醫林改錯》,非治病全書,乃記臟腑之書也”[11]1。《醫林改錯》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倡新的臟腑觀念。他是這樣批評中醫經典中的臟腑理論的:“其言仿佛是真,其實臟腑末見,以無憑之談作欺人之事,利己不過虛名,損人卻屬實禍。竊財猶謂之賊,偷名豈不為賊!千百年后豈無知者?”[11]6
臟腑論不過是中醫學方法論層次的道理。過去評論王清任及其醫書,大抵視其為方法論的革命,但本文認為,《醫林改錯》并非停留在此。王清任有意無意地把臟腑論提升為方法論的原則——“前人創著醫書臟腑錯誤,后人道行立論,病本先失。……病情與臟腑絕不相符,此醫道無全入之由來也。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11]3
王清任這樣做,實際上否定了傳統中醫一貫的治病原則。在傳統中醫中,陰陽說是本體論,也是作為治病的方法論原則。《內經·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可見,王氏并非如前人所說的局限于醫學方法論,而是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否定了中醫的方法論原則——陰陽之道本體論。王氏將實體性的臟腑用以反對中醫的治病的方法和方法論原則,與利瑪竇以實體性的四體液——四元素來反對中醫的方法和方法論原則可謂異曲同工。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激發了王清任的“醫學觀念革命”?或許多少會受乾嘉樸學考據精神的直接影響。有學者將王清任視為徹底的先覺者,將他比作中國的維薩里,斷言“即使沒有近代西方醫學的傳入,中醫學也距重解剖、由實驗而求醫理的時代不遠了”[12]46。這是一種李約瑟式的人類文化一元進化的歷史觀,即將近代科學視為人類各文明科學文化的唯一的歸屬,謂之“百川歸海”。還在李約瑟在世的時候,這種觀點就廣受質疑。現在國際科學史界信奉這樣的科學史觀的人已經很少了,主流觀點是文化多元的史觀,即各文明有其自身的科學文化傳統,西方近現代的科技醫文化并不能普遍代表其他文明的科學文化。
將王清任視為中醫史上自行產生的“革新家”[12]42的理由之一,是認為利瑪竇與王清任的時間間隔達到200余年之久。特別是歷經滿清朝廷與基督教之間的“禮儀之爭”之后,中西方文化正常交流中斷一百多年,傳教士的思想似乎難以影響王清任。
眾所周知,在“禮儀之爭”之后,傳教士的宗教活動在中國大陸被停止了。但在學術領域,包括數學,醫學,天文,繪畫,地圖制作以及機械制造等技術領域,并沒有停止。清朝朝廷和康熙本人對西方數學、天文、醫術方面一直保持很高的興致。西方的哲學、科學、技術以及數學思想仍然保留在正規的出版物(如《四庫全書》)以及私人的筆記當中。
再者,兩個事件相隔時間長久并不能成為否證它們之間沒有因果關系的理由,特別是帶有信息特征的人類思想。它們仍然會以各種方式保留在一定的載體中。作為信息的思想,是能夠跨越時空發生“長程相干”作用,在另一段時空中引發中醫史上的“蝴蝶效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生理解剖學思想之于王清任的臟腑新觀念,以及王清任引發的“醫學觀念革命”,正是信息的跨越時空傳播的結果。
王清任的先知先覺的說法并沒有多少說服力。在《醫林改錯·腦髓說》中,王清任講述了“記性不在心在腦”之新腦髓說[11]23-24,這個思想就是單憑王氏觀察死尸,絕無可能發現的思想。可見,王清任的思想并非原創,乃是外來,因中國古典以及同時期的學者并無如此思想,最大可能是源于耶穌會傳教士的西方醫學生理學的觀念。由此可以推斷,王清任直接或者間接受到利瑪竇的《西國記法》或者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說概》、《人身圖說》等西方生理解剖學的影響。
王清任的出現,使得清末時期西方近代醫學的傳入減少了很多障礙,人們更容易接受西方醫學。王清任的《醫林改錯》自1830年至1950年,再版近40次,關于該書的評注一直不斷,進入21世紀仍然有新的評注出版。中醫發展的歷次社會化運動,如民國的廢止中醫運動,乃至新中國的中西醫結合運動甚至21世紀的網絡簽名廢止中醫的過程中,王清任及其著述都一次次祭出。王清任及其著述影響之巨大深遠可見一斑。
由王清任生前200年的利瑪竇肇始的西方醫學思想的傳入,導致中國的醫學觀念特別是臟腑觀念的轉換,將傳統中醫的功能整體性的、非實體性的臟腑,轉換為結構還原性的、實體性的臟腑。這可謂是一種“醫學觀念革命”。不可否認,王清任在醫療實踐臨床方面也有諸多探索,但在思想層面,王清任已然承接繼續了傳教士們的基本醫學思想,骨子里已是西方醫學的精神附體。而且王清任這種現場觀察尸體的研究方法,“背離”中醫傳統的“觀物取象”和“比類取象”的方法,而是訴諸于直接經驗的實證方法,儼然是西方近代科學研究方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在遙遠的歷史時空中的醫學交流活動,對中國醫學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甚至在后世圍繞中醫的種種爭論中仍然可以從利瑪竇開展的醫學交流中找到爭論的“原型”。利瑪竇等人的中西醫交流活動鼓蕩了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的一次次的“蝴蝶效應”。
[1]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李文潮,H.波塞爾.萊布尼茲與中國[C].李文潮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3]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M].何高濟等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4]洛伊斯·N·瑪格納.醫學史[M].劉學禮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馬伯英.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M].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
[6]利瑪竇.四元行論[M].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之《乾坤體義·卷上》.
[7]本杰明·艾爾曼.中國近代科學的文化史[M].王紅霞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李國豪等.中國科技史探索(中文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席文.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是否沒有發生?[M]∥劉鈍,王揚宗主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10]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11]王敬蘭等.《醫林改錯》評注與臨床應用[M].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12]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M].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M atteo Ricci:the Pioneer of Chinese-W estern M edicine Communication
HE Kaiw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Matteo Ricci was the pioneer in the medicin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theories, including natural philosophy, physiology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introducedthe theory of body-fluids of four kinds, and the theory of brain function into China. And he was thefirst person who introduc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Europe. In addition,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of philosophy and medical history, re-evaluates Matteo Ricci’s prominent position an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in bo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roversial history of Western and 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
four-body-fluid; four-element; wu-xing; substantiality; concept revolution in medicine
book=7,ebook=1
B913
A
1009-8445(2012)03-0007-09
(責任編輯: 姚 英)
2012-01-03
廣東省哲學和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GD10DL04)
何凱文(1971-),湖南汝城人,肇慶學院政法學院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