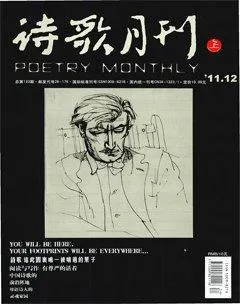孫友民的詩(5首)
解放大道我走過一條河流岸柳、陽光和血管一樣鼓脹的支流滋潤著林立的高樓和人性頭頂是日,月,星辰、更深更深的藍兩岸飄浮著麥香、書香芝麻油的清香和豫南話的濃香許多年前,它還是一條細細的溪流迷途的孔丘,搜神的干寶、顏體的夫子、秦相李斯從這里趟過打濕過他們的褲腳風,吹起大地上的土落滿了史書也吹得家鄉的大道如此寬闊一條路,每天都在新生的樹葉下敘述流水的故事——魚一般涉水而過的火紅少女北岸高級中學里飄向彼岸的誦書聲比風更快的鋼鐵邏輯的紅色黃色藍色的精靈……成為這個永無止境的故事中新生的感性詞匯和最為明亮的部分我走過一條河流——它深陷于豫南平原和時光深處東端起于京廣鐵路的一個叫駐馬店的小站一座座城池,以及城池以遠的北方的寒流和南方的細雨有關西端起于村莊,田野,田野上的阡陌以及村莊里一顆顆散淡的心現在是一個新時代了不知村莊是車站的終點還是車站是村莊的終點?不知是該從家鄉的麥場,順著解放大道走上匆忙的站臺乘著汽笛,暮靄漸漸遠去叫做解放還是該從一枚車票中跳下來,順著解放大道回到我們世世代代的村莊才叫解放?
給母親打電話昨夜我看見你額頭上渾濁的河流越來越近河水,和整整一個秋天的光明覆蓋了我破
碎的夢1962年晚秋池塘邊的烏桕樹,和今天你稀疏長發的黑白畫面就那么一直地飄呀直至霜打的紅葉失卻了顏色我知道,流水沖積的病灶深沉地凝結在你的心口今天一早,我急忙推開面向家鄉的窗戶一陣風,頓時,吹上了我的頭頂這電一般的打擊,讓我坐在客棧一樣的房間里沉默不語一你漫游多年的兒子有了憂傷
給死于1966年的一位農民當你的簡約之心和你精神里的那些濃血在我的體內形成年幼的河流我初知了痛的力量你走了。帶著熟透玉米的沉默,太平原的
沉默帶著黑鐵之鋤落地時的光芒和身體深處的病灶二十世紀上半葉人問悲傷和歡樂的持有者走過家園戰亂的胸腔和大地餓殍的骨殖檢校過著名的蝗蟲大軍在倒伏的麥子旁手捧水形的陶罐這就是我的爺爺——死于1966年的一個農民作為往昔的葬送者和被往昔所葬送的人他渾濁的眼瞳再不能映現我幼年的池塘和天空西天熔金時分豫南后孫莊的路口上一個四歲的孩子在尚未出現的星辰下哭喊那是因為一只溫暖面具的突然消失
春節我看見大地上寒氣的影子從老家的窗外走過母親不滅的爐火跟隨靜穆的風水冉冉升空歸來兒子蒼白的容顏被什么映得通紅沒有雪。清晨過后誰見到了神——他在有門的地方寫遍祝福我看見天空如此洗練高高的云像一條條白練從西向東輕輕擺動天黑了,守夜的小歌之坐在長明燈下一邊聆聽從誰的手指上發出的青色歌聲一邊夢見奶奶梧桐樹的褐色枝條靜靜地指向黎明子夜時分,好事的人燃起爆竹模仿天庭里的一陣陣鼓聲我看見——人間的煙火在上升流向天空的桃花三月的一個早上從遙遠春節的一個雷聲
和冬天里孩子的夢中走來的一場細雨悄無聲息地消失了晚報的頭版上說雨已經潛入了農家門楹那正在褪色的春聯上這個早上陽光像洪水一樣咆哮而來讓村莊里那些就著寒氣咳嗽的老者猝不及防陽光沖走了大路上冬天零亂的腳步轟地一聲推開了春天門楣上銹跡斑斑的
鐵鎖推開了桃園水木構件的大門碎金撒落的聲音以及在其撒落的瞬間
進濺的光芒將那些濕漉漉的褐色枝條一一點燃噼噼啪啪的粉紅火焰
借著風勢流向大地流向澄明澄明的天空恣意的映亮村莊映亮桃園里一個彎腰勞作的老婦人緩緩張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