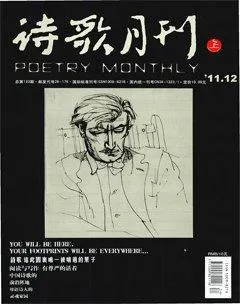“歧路花園”的一千零一夜
寫作本文的初衷是想嘗試著梳理兩岸出生于1970年代詩(shī)人的寫作征候,但是限于龐大的詩(shī)人數(shù)量和難以想見(jiàn)的文本閱讀量,我最終不得不“投機(jī)取巧”地選擇了“70后”女性詩(shī)歌這一更小的視閩作為考察的起點(diǎn)。本文為了論說(shuō)的方便在論述兩岸出生于1970年代女性詩(shī)歌詩(shī)學(xué)稟賦和精神征候時(shí)并未采用臺(tái)灣“新新世代”或“新新人類”(相當(dāng)于“六年級(jí)”)。的概念,而是采用了大陸所普遍使用的“70后”概念。盡管“70后”這種代際劃分至今仍有異議者,但我覺(jué)得有其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的言說(shuō)的便利。需要再次強(qiáng)調(diào),我所說(shuō)的“70后”從來(lái)都不會(huì)指涉什么“運(yùn)動(dòng)”的“70后”,而是指涉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人。而臺(tái)灣所指稱的“新世代”和“新新世代”所攜帶的“追新逐后”性的指稱有一定的“進(jìn)化論”色調(diào),也可能有意或無(wú)意地?cái)U(kuò)大了代際之間的差異。而關(guān)于世代(代際)的詩(shī)歌概念以及相應(yīng)的新詩(shī)研究已經(jīng)是一個(gè)久遠(yuǎn)的傳統(tǒng)。無(wú)論是韋勒克還是沃倫以及眾多研究者都對(duì)文學(xué)代際興趣濃厚。而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歌尤其是從“第三代”
(新生代)詩(shī)歌開(kāi)始,代際的詩(shī)歌史現(xiàn)象和研究就成為顯豁的事實(shí)。而在海峽的對(duì)岸,臺(tái)灣的代際研究尤其是中生代、新世代、新新世代或者說(shuō)以“年級(jí)”來(lái)劃分顯然已經(jīng)成為值得研究的文學(xué)史現(xiàn)象。
毫無(wú)疑問(wèn),在經(jīng)歷長(zhǎng)期的社會(huì)、政治和文學(xué)中女性被“無(wú)性化”和“男性化”的噩夢(mèng)之后,在女性的文學(xué)和身份革命被長(zhǎng)期“淘洗”和延宕之后,當(dāng)“無(wú)性”敘述的性別場(chǎng)景(這在大陸的女性詩(shī)歌那里要更為顯豁)逐漸隱退、消匿,放逐身體和欲望的克己及禁欲的動(dòng)力結(jié)構(gòu)一去不回,女性詩(shī)歌在經(jīng)歷了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狂躁的性別風(fēng)暴和權(quán)力話語(yǔ)突起的尖銳景觀之后,近年來(lái)的“70后”女性詩(shī)歌寫作在整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視閥和姿態(tài)更為寬廣、更為繁復(fù)的美學(xué)趨向。實(shí)際上不管我們?cè)诤畏N意義上來(lái)談?wù)摗?0后”女性詩(shī)歌以及1990年代后期以來(lái)的女性詩(shī)歌,我們都應(yīng)該認(rèn)識(shí)到女l性寫詩(shī)有著巨大難度,甚至在特殊的時(shí)期女性寫詩(shī)不亞于一場(chǎng)殘酷的戰(zhàn)爭(zhēng),
“你將要進(jìn)行一場(chǎng)戰(zhàn)斗,以便證明在你豐滿健康的身體內(nèi)存在著一種呼喊著要求被人們聽(tīng)到的才智……對(duì)你來(lái)說(shuō),要把這種情況大聲講出來(lái)將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你會(huì)經(jīng)常吃虧,幾乎總是吃虧。但你卻不敢失去勇氣”。而由兩岸的“70后”女性詩(shī)歌寫作,我一直試圖尋找相同或相通的質(zhì)素,而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其“想象的共同體”的背后卻看到了不盡相同的面影和差異。“內(nèi)心的迷津”仍然通過(guò)深深的海峽映射出當(dāng)代女性波瀾繁復(fù)的精神圖景,而在共性和差異性的精神地理學(xué)上,我看到了一個(gè)別致而充滿歧路的花園。花園里每夜都有人在講著故事,而這些故事盡管有雷同、有重復(fù),但更多的故事卻具有個(gè)人性、隱秘性和差異性。在一千零一夜般的“歧路花園”里,我們的傾聽(tīng)也許才剛剛開(kāi)始。當(dāng)我在2011年的4月,在臺(tái)北的一個(gè)路邊酒吧里拿到林維甫(1974年出生于高雄,臺(tái)北長(zhǎng)大,畢業(yè)于臺(tái)灣大學(xué)歷史系)的被稱為臺(tái)灣第一本鑄鉛活字印刷的抒情詩(shī)集《歧路花園》(該詩(shī)集名與JorgeLuis Borges的小說(shuō)集The Garden of ForMng Paths同名,又譯作《交叉小徑的花園》,但如詩(shī)人林維甫自己所陳并無(wú)直接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時(shí),我強(qiáng)烈感受到“歧路花園”正在成為當(dāng)下青年詩(shī)歌寫作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的最為準(zhǔn)確的命名。當(dāng)林維甫在暗淡的燈影中在書的扉頁(yè)上寫下“永遠(yuǎn)在歧路”時(shí),我想這可能真正隱喻了詩(shī)人和詩(shī)歌的某種難以規(guī)約的命運(yùn)甚至宿命。試想,如果詩(shī)人都走在同一條道路上該是如何可怕的景象!詩(shī)人與“未選擇的路”之間應(yīng)該是互相發(fā)現(xiàn)和勘問(wèn)的過(guò)程。
我們一直在近些年排斥庸俗社會(huì)學(xué)方法對(duì)文學(xué)的介入,確實(shí)在歷時(shí)性的向度考量各個(gè)時(shí)代的很多優(yōu)秀詩(shī)人都是在“我行我素”、“自鑄偉詞”的追索精神世界的高迥與差異,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從詩(shī)人作為生命個(gè)體而言其存在狀態(tài)不是真空的,而是注定與身邊之外甚至一個(gè)時(shí)代的整體語(yǔ)境和精神氛圍發(fā)生或顯或隱的關(guān)系。而談?wù)撆_(tái)灣的“70后”女性詩(shī)歌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要注意到這些女性的精神成長(zhǎng)期恰好是臺(tái)灣社會(huì)發(fā)生重大變更的時(shí)期,相對(duì)穩(wěn)定和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以及緊隨而來(lái)的城市文化、后工業(yè)文明以及新媒體的席卷都對(duì)她們的精神成長(zhǎng)和詩(shī)歌成長(zhǎng)起到了某種生態(tài)的調(diào)節(jié)和影響作用。可以肯定地說(shuō),前代詩(shī)人尤其是出生于1930-1950年間的詩(shī)人其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集體焦慮以及“鄉(xiāng)愁”情結(jié)基本上在這些“70后”的臺(tái)灣女性詩(shī)人那里已經(jīng)不那么明顯(并不是不存在),相反一種“美麗島”上的個(gè)人化寫作的稟賦卻日益顯豁。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大陸甚至臺(tái)灣本土的詩(shī)歌研究者在研究女性詩(shī)歌時(shí)往往容易犯同樣的錯(cuò)誤,這就是易將一些男性詩(shī)人誤認(rèn)為是女性。這一方面在于確實(shí)有些臺(tái)灣的男性詩(shī)人的名字(更多是筆名)更像女性,而且在閱讀過(guò)程中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些男性詩(shī)人的寫作一定程度上具有“陰性”特征。
本文所涉及到的臺(tái)灣“70后”女性詩(shī)人主要有:林怡翠、林婉瑜、林岸、林思涵、楊佳嫻、吳苑菱、侯馨婷、何雅雯、潘寧馨、廖之韻、葉惠芳。、江月英等。這里基本上沒(méi)有涉及臺(tái)灣本土的原住民族的詩(shī)歌寫作,此外“臺(tái)語(yǔ)詩(shī)”由于筆者在語(yǔ)言上的差異也未予涉及。而鑒于言說(shuō)的方便以及必須的詩(shī)歌學(xué)比較,本文也會(huì)涉及一部分‘七年級(jí)女生”,也即“80后”女性詩(shī)人,比如臺(tái)灣的廖亮羽、林禹碹、崔舜華以及大陸的鄭小瓊等。
隨著兩岸“泛政治”時(shí)代的遠(yuǎn)去,女性詩(shī)歌寫作在多元的維度中又不約而同地呈現(xiàn)出對(duì)日常和無(wú)“詩(shī)意”場(chǎng)景的關(guān)注和重新“發(fā)現(xiàn)”。當(dāng)下的女性詩(shī)歌在很大程度上呈現(xiàn)了一種“日常化詩(shī)學(xué)”。具體言之就是無(wú)限提速的時(shí)代使得目前的各種身份和階層、經(jīng)歷的女性詩(shī)人面對(duì)的最大現(xiàn)實(shí)就是日復(fù)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暈的生存語(yǔ)境,這些日常化語(yǔ)境為女性詩(shī)人的日常體驗(yàn)和想象提供了自白或?qū)υ挼目臻g。所以無(wú)論是從題材、主題還是從語(yǔ)言和想象方式上女性詩(shī)歌越來(lái)越走向了“日常化”和“一己化”。在都市化、消費(fèi)化和電子化的“后工業(yè)時(shí)代”的語(yǔ)境之下,臺(tái)灣的這些女性詩(shī)歌真正復(fù)原了個(gè)體意義上的詩(shī)學(xué)努力,平面、個(gè)人、碎片,日常的低語(yǔ)或自白成為基本語(yǔ)型。正如何雅雯所說(shuō)的“現(xiàn)在寫詩(shī)等于夢(mèng)囈”,“好日子過(guò)多了就不太寫”,換言之她們的寫作更多指向了身邊之物和日常經(jīng)驗(yàn)。比如江月英的《曬衣繩上》就在景物素描般的場(chǎng)景中呈現(xiàn)出個(gè)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言說(shuō)方式:
“曬衣繩上
吵鬧鬧地/一群剝光身體的衣服/在日光屋里
蒸氣/大紅胸罩?jǐn)[著蕾絲粉碧
呵風(fēng)/發(fā)白BOX牛仔褲追著長(zhǎng)年風(fēng)濕/旋高旋低泡泡襪嘆著/人情淡薄/和經(jīng)濟(jì)不景氣。”我也在“70后”女性詩(shī)歌中看到了從詩(shī)人活生生的社會(huì)生活、個(gè)體生存和現(xiàn)實(shí)場(chǎng)域中生發(fā)出來(lái)的平靜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這些詩(shī)歌呈現(xiàn)出一個(gè)個(gè)女性在日常生存現(xiàn)場(chǎng)中宿命般的時(shí)光感和生命的多種疼痛與憂傷,以及帶有與詩(shī)人的經(jīng)驗(yàn)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陣痛與流連。當(dāng)我們看到女性詩(shī)歌的限囿和存在問(wèn)題的同時(shí)也應(yīng)該注意到女性詩(shī)歌廣闊的寫作和閱讀、交流的新的空間和可能性前景。為數(shù)不少的女性詩(shī)人使記憶的火光,生命的悲歡,時(shí)間的無(wú)常,個(gè)人化的想象力以及現(xiàn)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無(wú)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詩(shī)歌在年輕一代女性這里更大程度上體現(xiàn)為個(gè)人化的言說(shuō),女性幽微細(xì)膩的情感體驗(yàn)與抽絲剝繭般的詩(shī)歌方式天然融合在一起。甚至在后起的臺(tái)灣“80后”女性詩(shī)人廖亮羽、林禹碹、崔舜華那里,一種類似于古代柔軟、婉轉(zhuǎn)、清新、細(xì)膩的“小令”式的詩(shī)歌寫作已經(jīng)出現(xiàn)。詩(shī)人的敏感甚至偏頭痛是與生俱來(lái)的,女性詩(shī)人就更是如此。而這種敏感對(duì)于女性詩(shī)人而言顯然是相當(dāng)重要的,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刺激詩(shī)人的神經(jīng)和想象,能夠讓詩(shī)人在司空見(jiàn)慣的事物和季節(jié)輪回中時(shí)時(shí)發(fā)現(xiàn)落英的新蕊,發(fā)現(xiàn)麻木的我們?nèi)杖账?jiàn)事物的另外一面;也因此呈現(xiàn)出一番與常人有些差異和距離的內(nèi)心圖景甚至精神風(fēng)暴。她們特有的幽微而深入、敏感而脆弱、遲疑而執(zhí)拗的對(duì)生命、愛(ài)情、性、命運(yùn)的持續(xù)的思考與檢視,斑駁的時(shí)光影像中的火車滿載著并不輕松的夢(mèng)想、記憶和塵世的繁雜。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下的女性詩(shī)歌更大程度上表現(xiàn)出女性與自然之物間天然的接近,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工業(yè)化、城市化飛奔道路之上自然和人所經(jīng)歷的前所未有的孤獨(dú)與惆悵,從而生命的本能和哲學(xué)、文化、語(yǔ)言上的“返鄉(xiāng)”的沖動(dòng)才愈益顯豁。由于海洋文化和地形學(xué)的影響,臺(tái)灣的“70后”女性詩(shī)歌中的植物意象更多帶有熱帶海澤性特征,而大陸的“70后”女性的植物抒寫則帶有明顯的“多土性”。詩(shī)歌寫作尤其是關(guān)注自然萬(wàn)有的詩(shī)歌寫作能夠成為消除時(shí)間的焦慮、生存的痛苦、死亡的宿命的抗?fàn)幨侄巍Q言之在植物這些卑微的生命身上,女性詩(shī)人得以不斷的確證自身、返觀自我。強(qiáng)烈的時(shí)間體驗(yàn)和生命的焦慮在自然物象面前得以喚醒和抒發(fā),當(dāng)然這種抒發(fā)很大程度上是低郁的、沉緩的、憂傷的。自然事物尤其植物紛紛闖進(jìn)當(dāng)下女性詩(shī)人的現(xiàn)實(shí)和詩(shī)歌的夢(mèng)想視野之中,在這些植物身上投注了這些女性特有的童年體驗(yàn)、女,陛經(jīng)驗(yàn)以及時(shí)光的折痕。在這些女性詩(shī)歌中植物意象往往是和生存片斷中的某個(gè)細(xì)節(jié)同時(shí)呈現(xiàn)的,換言之這些植物意象是和詩(shī)人的真切的本原性質(zhì)的生存體驗(yàn)的見(jiàn)證或客觀對(duì)應(yīng)物。在這些植物的身上我們能夠返觀普遍意義上的這個(gè)時(shí)代和女性整體的時(shí)代面影和內(nèi)心靈魂。
據(jù)此,如果我們?nèi)匀粡奈膶W(xué)的社會(huì)功能和詩(shī)人“神圣”身份來(lái)衡估這新一代的女性寫作顯然有些不切實(shí)際。也不夠“明智”,因?yàn)閷?duì)于這些臺(tái)灣的“70后”“新新世代”而言,她們的詩(shī)歌除了承擔(dān)個(gè)人和語(yǔ)言之外似乎其余的都無(wú)須談?wù)摗_@早在1996年12月《雙子星人文詩(shī)刊》推出的出生于1970年代的“新新詩(shī)人專輯”就刻意強(qiáng)調(diào)了這些被冠以“新新”一代人的獨(dú)特甚至叛逆之處:“出生于七十年代的新世代詩(shī)人,他們的骨肉、血液、食物、糞便都和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先人們迥然不同。他們兼或作怪、兼或尖銳、兼或平庸、兼或不知所云,但無(wú)妨于真實(shí)”,“詩(shī)壇的先人們,新世代寫詩(shī)更多是玩票性質(zhì),何況他們也沒(méi)有地方上臺(tái)亮相,誰(shuí)稀罕再繼續(xù)堅(jiān)持下去呢?”。這里所強(qiáng)調(diào)的代際之間的巨大鴻溝和差異也不一定能夠完全代表“70后”一代女性的寫作觀念和初衷,她們的寫作也并非完全是不負(fù)任何責(zé)任和道義的“玩票”,這更多也是一代青年人急于“上位”的策略化噱頭。正如當(dāng)時(shí)的一個(gè)詩(shī)人所高聲吁求的——“他們的出現(xiàn),宣告了新時(shí)代的來(lái)臨”,“他們終將占領(lǐng)未來(lái)的版圖和全世界”。這種“PASS”前輩詩(shī)人的情結(jié)以及占山頭、跑馬圈地的心理在詩(shī)歌界并不顯見(jiàn)。實(shí)際上,時(shí)隔三年之后,北京的一些“70后”詩(shī)人便同樣以策略化、噱頭式但更為激進(jìn)的“下半身”的方式搶灘登陸詩(shī)壇。當(dāng)時(shí)詩(shī)壇為之嘩然的程度是今天的詩(shī)人們難以想象的。
當(dāng)然除了這種“日常”的個(gè)人詩(shī)學(xué)的圖景之外,也有一部分的女性詩(shī)人葆有了可貴的歷史想象力和文化重構(gòu)能力,以及介入當(dāng)下的具有“現(xiàn)實(shí)感”的質(zhì)素。在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林怡翠。林怡翠(著有詩(shī)集《被月光抓傷得背》,麥田出版社,2002年)在《被月光抓傷的背——寫給帶著“慰安婦”傷痛活著的臺(tái)灣阿嬤》等詩(shī)作中則體現(xiàn)了與個(gè)人和精神地理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個(gè)人化的歷史想象能力與記憶重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被月光抓傷得背》一詩(shī)前面的一段文字:“夜半,在公視看見(jiàn)臺(tái)籍慰安婦阿嬤的紀(jì)錄片。在貞操潔癖的世界里,她們哭著或笑著說(shuō)起自己的故事,多半是不甘心,是青春不再。她們很老很老了,像這段戰(zhàn)爭(zhēng)和婦女受難的日子一樣,在鏡頭前蒼老得有些難堪。可是,我感覺(jué)到了那種疼痛卻不輕易叫出來(lái)的勇敢,當(dāng)她們低頭,在滿身的傷口中看見(jiàn)自己的時(shí)候,我不由得尊敬起這些生命來(lái)了,然后才有詩(shī)。”顯然,詩(shī)歌不是社會(huì)學(xué),也不是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知識(shí)的翻版,當(dāng)歷史甚至現(xiàn)實(shí)進(jìn)入到詩(shī)歌語(yǔ)境之后一種被“想象”和“修辭”的現(xiàn)實(shí)就產(chǎn)生了。顯然,這種更具“現(xiàn)實(shí)感”和象征意味的修辭化的歷史、現(xiàn)實(shí)與實(shí)有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之間就必然產(chǎn)生了距離和差異。非常可貴和值得注意的是林怡翠以個(gè)人化的視角進(jìn)入到歷史煙云的深處,以更具體溫和的知冷知熱的細(xì)微方式和濃重的情感色彩的敘事語(yǔ)調(diào)試圖和另一個(gè)時(shí)代的女性命運(yùn)發(fā)生意味深長(zhǎng)的對(duì)話關(guān)系。那一場(chǎng)場(chǎng)通天的大火就這樣無(wú)情焚燒著卑微如螻蟻的女性,而曾經(jīng)潔白勝雪的流蘇樹(shù)一樣的美麗生命和“沒(méi)入遠(yuǎn)煙的十六歲”最終被一場(chǎng)場(chǎng)烈火過(guò)后的寒冷和無(wú)邊無(wú)際的灰燼所覆蓋——“天已被焚化,灰燼是無(wú)處攀爬的/螻蟻,我們馱伏著沉重過(guò)自己數(shù)倍的命運(yùn)/那時(shí)流蘇花還飄飛滿天/怎么會(huì)就下了一場(chǎng)大火?”當(dāng)青春的女性被戰(zhàn)爭(zhēng)和死亡的威脅蹂躪,當(dāng)麻木與疼痛日夜糾纏,一個(gè)島嶼上的女性命運(yùn)的屈辱史如何能夠用唏噓感嘆和沉重足以描述,“一顆子彈穿過(guò)我的下體/競(jìng)像一片枯葉輕輕地飛過(guò)庭院/我已忘卻的疼痛如一排一排的落花/不知黏在哪一雙軍靴跟底,一步/踩爛一個(gè)少女的春天”。更為重要的是女性詩(shī)人以女性特有的體驗(yàn)和想象更為本真地呈現(xiàn)了歷史圖景中女性命運(yùn)的真實(shí)存在和個(gè)體命運(yùn)。
臺(tái)灣“70后”女性詩(shī)歌再次證明了女性寫作的自白性質(zhì)素,再次呈現(xiàn)了女性與“愛(ài)情詩(shī)”之間的天然關(guān)系。當(dāng)然在一些更為年輕的女性寫作那里,“愛(ài)情詩(shī)”已經(jīng)被置換為“情詩(shī)”、“性詩(shī)”甚至“無(wú)愛(ài)詩(shī)”、“同志詩(shī)”。而對(duì)于臺(tái)灣“70后”這些在穩(wěn)定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中幾乎普遍有著大學(xué)教育的一代女性而言,她們?cè)缙诘脑?shī)歌都帶有“青春期”階段“小女人”情感的投影,具有程度不同的“童話”氛圍。但是當(dāng)2000年左右經(jīng)過(guò)人生和文學(xué)觀念的雙重淬煉,她們的詩(shī)歌文本呈現(xiàn)出愈益的復(fù)雜性甚至某些分裂性特征。當(dāng)然也有為數(shù)不少的女性通過(guò)詩(shī)歌的修辭練習(xí)繼續(xù)反思著女性命運(yùn)、內(nèi)心體驗(yàn)、身體感知的特殊性。其中林婉瑜的詩(shī)集《索愛(ài)練習(xí)》(爾雅出版社,2001)就集中而具有代表性地呈現(xiàn)了女性與“愛(ài)”之間的膠著狀態(tài),而其中的代表作《抗憂郁劑》更是呈現(xiàn)了青年女性無(wú)可療救的精神癥候。在“病人”和“醫(yī)生”的對(duì)話與疑問(wèn)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呈現(xiàn)了難以消弭的“病態(tài)”。這種“憂郁”甚至“變態(tài)”的精神問(wèn)詢和“毫無(wú)出路”的結(jié)局是否凸顯了“新世紀(jì)”以來(lái)女性命運(yùn)仍然是問(wèn)題重重——“每個(gè)禮拜,我前去/扣問(wèn)我靈魂的神/洗凈我吧/赦免我/他白袍筆挺/仿佛纖塵不染的真理//讓我描述/我內(nèi)部正在發(fā)生的戰(zhàn)爭(zhēng)/金邊眼鏡透露冷靜的眼神/醫(yī)生——/你相信柏拉圖所說(shuō)的嗎?/我們?cè)诙囱▋?nèi)/火光的倒映舞影中生活?/你也犯錯(cuò)嗎?/你有一雙探進(jìn)護(hù)士裙的手?/你逃稅嗎?/你想像病人的身體,一邊手淫?/你比較想和男人做愛(ài)嗎?/你為自己寫下處方?/你心平氣和看完新聞?/你娶了你愛(ài)的女人?”當(dāng)“憂郁”的女性祈求“神”的療救時(shí),“神”(“醫(yī)生”)卻被還原為世俗、淫惡、齷齪、病態(tài)的“男人”,這重新呈現(xiàn)了性別之間的沖突以及女性自身的焦慮癥狀。詩(shī)歌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黑暗“洞穴”不僅意指精神被囚禁的居所或者暗室,也是女性身體體驗(yàn)和情欲想象的憑依。而“柏拉圖”在詩(shī)歌中的出現(xiàn)顯然帶有女性對(duì)精神之愛(ài)的虛無(wú)與詰問(wèn),也呈現(xiàn)了“洞穴”牢籠的巨大規(guī)訓(xùn)力量。而“洞穴”中倒映的火焰呈現(xiàn)的是真實(shí)還是幻想,這都成為女性詩(shī)人的白日夢(mèng)或日天鵝絨監(jiān)獄一般的詩(shī)性體驗(yàn)與想象。女性的高燒仍將無(wú)可避免的持續(xù)…一而這種特屬于女性“偏頭痛”般的“精神疾病”氣息和“自省”姿態(tài)的詩(shī)歌寫作在臺(tái)灣“80后”女性一代那里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比較罕見(jiàn)。盡管一些“80后”女性文本中也出現(xiàn)了病人、病房、疾病等意象和場(chǎng)景,但是它們?cè)诟蟪潭壬铣尸F(xiàn)為詩(shī)人個(gè)體主體性的想象,更多指向了時(shí)間、生命和憂戚甚至悲劇性的體驗(yàn)。比如林禹碹的《夜中病房》,盡管詩(shī)中出現(xiàn)了男性人稱“他”,也可以視為兩性之間的“低燒”而“平靜”狀態(tài)的對(duì)話和低語(yǔ),但是這個(gè)“他”是“虛化”的。整首詩(shī)的情感基調(diào)是徐緩和平靜的,盡管略帶憂傷,而“他”實(shí)際上更近于一個(gè)詩(shī)人設(shè)置的關(guān)涉時(shí)間和愛(ài)情“病人”的傾聽(tīng)者與撫慰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詩(shī)人的身體、心境和情感投影的另一種呈現(xiàn)方式。
“在夜里傾聽(tīng)你的鼻息,仿佛/一列火車自遠(yuǎn)而近,輪軌摩擦/時(shí)間發(fā)出金屬的高音/然后淡去,如同為你熬煮的草葉/在滾水中慢慢舒開(kāi)蜷曲的肢體/點(diǎn)一盞燈,讓寂靜擁有溫度/讓光淌進(jìn)門縫,滲過(guò)你的指尖、夢(mèng)境/和體內(nèi)日形廣闊的角隅/疾病的陰影緩緩攤開(kāi)、爬行/我正聆聽(tīng)”。
值得注意的是楊佳嫻(著有詩(shī)集《屏息的文明》,木馬出版社,2003年)主持的個(gè)人新聞臺(tái)“女鯨學(xué)園”(http://mypaperl,ttimes,corn,tw/user/chekhov/index,html)已經(jīng)是重要的女性和女性寫作的平臺(tái)與窗口。而由楊佳嫻的詩(shī)需要提請(qǐng)注意的是女性詩(shī)歌的互文性特征。在臺(tái)灣的青年女性寫作中,與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詩(shī)詞對(duì)接、仿寫和改寫的現(xiàn)象大量存在,例如夏宇、曾淑美、顏艾琳、楊佳嫻等人。甚至曾淑美、夏宇等人都寫過(guò)與漢樂(lè)府民歌《上邪》互文的文本,比如曾淑美的《上邪》、夏宇的《上邪》。其中楊佳嫻的《木瓜詩(sh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首《木瓜詩(shī)》顯然與《詩(shī)經(jīng)》中的《木瓜》具有互相打開(kāi)的性質(zhì)。這種帶有互文甚至“寄生性”的詩(shī)歌文本顯然對(duì)于詩(shī)人而言更具有挑戰(zhàn)性和寫作的難度。而楊佳嫻的《木瓜詩(shī)》更為幽微而深入地展現(xiàn)出現(xiàn)代女性的靈魂波瀾和內(nèi)心體驗(yàn)的小小“閃電”,相當(dāng)細(xì)膩而從容地呈現(xiàn)出女性深沉而熾烈的內(nèi)心的膂力,“我呢焦躁難安地徘徊此岸/拉扯相思樹(shù)遮掩赤裸的思維/感覺(jué)身體里充滿鱗片/波浪向我移植骨髓/風(fēng)刺刺地來(lái)了/線條洶涌,山也有海的基因//木瓜已經(jīng)向你擲去了//此刻我神情鮮艷/億萬(wàn)條微血管都酗了酒/等待你游牧著緘默而孤獨(dú)的螢火/向這里徐徐而來(lái)”。
四
伴隨著以“網(wǎng)路”(大陸稱為“網(wǎng)絡(luò)”)尤其是部落格(大陸稱為“博客”)等新媒體為主體的數(shù)子時(shí)代和電子化語(yǔ)境對(duì)女性詩(shī)人的影響,而詩(shī)歌的敘事性、戲劇化、碎片化、拼貼化的綜合性和“后現(xiàn)代性”特征愈益明顯,其中吳菀菱的《左右漆黑,一○○一演出新解》就通過(guò)43個(gè)看似零碎實(shí)則關(guān)聯(lián)的戲劇性片斷呈現(xiàn)了女性與性別、政治、宗教、哲學(xué)、時(shí)代、
“民間”的諸多復(fù)雜關(guān)系以及激素化、狂歡化,怪誕性的體驗(yàn),“11.肛門與陰道雙重孔欲,異性戀與同性戀的糾葛。12.帶上沙德墨鏡(sade)才能出現(xiàn)端倪的演出。13.心眼與色眼窺淫之欲望。14.突破兩點(diǎn)禁忌,爭(zhēng)取乳房與睪丸的裸露權(quán)。15.夜行高速公路主道與干道的雙重快感狀態(tài)。16.杠與糊的麻將術(shù)語(yǔ)”。這種“大尺度”的詩(shī)歌話語(yǔ)在大陸即使目益開(kāi)化的紙質(zhì)媒體上仍會(huì)有道德的禁忌和發(fā)表的障礙,從中也可以看出兩地文化和文學(xué)語(yǔ)境共通之外的一些差異。
每一個(gè)時(shí)代的性別抒寫與想象甚至“創(chuàng)設(shè)”都不能不與動(dòng)態(tài)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有關(guān)。在21世紀(jì)的第一個(gè)十年已經(jīng)結(jié)束的時(shí)候我們?cè)絹?lái)越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尤其是博客成了最為普遍、自由、迅捷,也最為重要的詩(shī)歌生產(chǎn)和傳播的重要媒介。我們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shuō)我們的詩(shī)歌已經(jīng)進(jìn)入了一個(gè)博客時(shí)代,而博客與“70后”甚至更為年代一代的女性在詩(shī)歌寫作之間的關(guān)系似乎更值得我們關(guān)注。博客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甚至成了新世紀(jì)以來(lái)最為激動(dòng)人心的文學(xué)現(xiàn)象,無(wú)論是已經(jīng)成名立腕的,還是幾乎還沒(méi)有在正式紙刊上發(fā)表詩(shī)作的青澀寫手都可以在博客上一展身手,而更為重要的是女性的詩(shī)歌博客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和相關(guān)問(wèn)題。博客無(wú)疑已經(jīng)成為女性詩(shī)人們必須面對(duì)的特殊“房間”和靈魂“自留地”
(當(dāng)然這個(gè)“房間”和“自留地”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公開(kāi)。公共化了),對(duì)話、絮語(yǔ)、獨(dú)白甚至夢(mèng)囈、尖叫、呻吟、歌唱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容身之所;更為重要的在于女性詩(shī)歌寫作與博客之間的關(guān)系為研究女性寫作又提出了一個(gè)新的話題。在新世紀(jì)以來(lái)的新媒體神話和狂飆突進(jìn)的城市化的后工業(yè)時(shí)代的景觀中博客似乎為“個(gè)人”的自由,尤其是寫作的“個(gè)體主體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博客和自媒體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似乎像上個(gè)世紀(jì)1980年代一樣,自由、開(kāi)放的詩(shī)歌話語(yǔ)空間空前激發(fā)了女性詩(shī)人,尤其是年輕的女性詩(shī)人的寫作欲望和“發(fā)表渴求”,博客之間的“互文性”關(guān)系尤其是省略了以前紙質(zhì)傳媒時(shí)代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shī)歌投稿、發(fā)表、編輯、修改、審查的繁冗環(huán)節(jié)和周期,更使得詩(shī)歌寫作、傳播和閱讀、接受都顯得過(guò)于“容易”和“自由”隨便,這都使得女性詩(shī)歌寫作人口的日益壯大。網(wǎng)絡(luò)和博客的話語(yǔ)場(chǎng)域無(wú)形中起到了祛除詩(shī)歌精英化和詩(shī)人知識(shí)分子化的作用。而博客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寫作也同時(shí)帶來(lái)另外一個(gè)問(wèn)題,較之以前少得可憐的女性詩(shī)歌群體,當(dāng)下龐大的博客女性詩(shī)歌群體的涌現(xiàn)以及大量的數(shù)字化的詩(shī)歌文本給閱讀制造了眩暈和障礙。但可以肯定地說(shuō)面對(duì)著當(dāng)下女性詩(shī)人在博客上的無(wú)比豐富甚至繁雜的詩(shī)歌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女性詩(shī)歌的寫作視閡已經(jīng)相當(dāng)寬遠(yuǎn),面對(duì)她們更具內(nèi)力也更為繁復(fù)、精深、個(gè)性的詩(shī)歌,當(dāng)年的詩(shī)歌關(guān)鍵詞,如“鏡子”、“身體”、“黑色意識(shí)”、“房間”、“手指”,“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自白”等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予以調(diào)整和重新審視,這些詞語(yǔ)已經(jīng)不能完壘準(zhǔn)確概括當(dāng)下的個(gè)人博客時(shí)代女性詩(shī)歌新的質(zhì)素和征候。可是兩岸“70后”女性詩(shī)人的博客詩(shī)歌似乎仍然呈現(xiàn)了一種悖論性特征。按照常理來(lái)說(shuō)博客的發(fā)表和傳播的“交互性”和“及時(shí)性”、“公開(kāi)性”會(huì)使得女性詩(shī)人會(huì)盡量維護(hù)自己的“隱私”和“秘密”,但我們看到的是除了一部分博客上的女性詩(shī)歌在情感、經(jīng)驗(yàn)和想象的言說(shuō)上確實(shí)維持了更為隱幽、細(xì)膩和“晦澀”的方式,在一些日常化的場(chǎng)景和細(xì)節(jié)中能不斷生發(fā)出詩(shī)人情思的顫動(dòng)和靈魂的探問(wèn)之外,我同時(shí)也注意到深有意味的一面。即為數(shù)不少的女性詩(shī)人將博客看成了是發(fā)表甚至宣泄自己的情感的一個(gè)“良方”,一定程度在她們這里詩(shī)歌代替了日記,以公開(kāi)化的方式袒露自己的情感甚至更為隱秘的幽思和體驗(yàn),比如癖好、性愛(ài)、自慰、經(jīng)期體驗(yàn)、婚外戀、秘密的約會(huì)、精神世界的柏拉圖交往等等。尤其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博客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在看似極大的提供了寫作自由和開(kāi)放的廣闊空間的同時(shí)也無(wú)形中設(shè)置了天鵝絨一般的監(jiān)獄。漂亮的、華麗的、溫暖的、可人的包裹之下的個(gè)體和“發(fā)聲者”實(shí)則被限囿其中,個(gè)人的烏托邦想象和修辭、言說(shuō)方式不能不隨之發(fā)生變形甚至變質(zhì)。當(dāng)政治烏托邦解體,個(gè)人烏托邦的想象、沖動(dòng)和話語(yǔ)方式似乎在網(wǎng)絡(luò)和博客上找到了最為恰切的土壤和環(huán)境,似乎個(gè)人的世界成了最大的自由和現(xiàn)實(shí)。但是這種個(gè)人化的烏托邦是有著很大的局限性的。一定程度上與網(wǎng)絡(luò)和鏈接尤其是與大眾閱讀、娛樂(lè)消費(fèi)緊密聯(lián)系,甚至膠著在一起的博客女性詩(shī)歌成了消費(fèi)時(shí)代、娛樂(lè)時(shí)代取悅讀者的“讀圖”、“讀屏”時(shí)代的參與者;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共謀者”。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后期純文學(xué)刊物為了適應(yīng)市場(chǎng)而紛紛改版,這從一個(gè)側(cè)面凸現(xiàn)了商業(yè)時(shí)代的閱讀期待以及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對(duì)傳統(tǒng)文學(xué)機(jī)制和觀念的沖擊與挑戰(zhàn)。值得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2011年的臺(tái)北書展上,楊小濱主辦的刊物《無(wú)情詩(shī)》以其大膽、情色、時(shí)尚的刺激性封面和內(nèi)頁(yè)大量的女性和身體彩照受到了包括馬英九先生在內(nèi)的眾多讀者的關(guān)注。這也在另一個(gè)層面呈現(xiàn)了紙質(zhì)媒體的尷尬,甚至美國(guó)已經(jīng)聲稱到2017年紙質(zhì)報(bào)紙將全面退出。很明顯在全球化語(yǔ)境之下,文學(xué)市場(chǎng)和大眾文化顯然也是一種隱性的政治。我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新傳媒尤其是網(wǎng)絡(luò)、博客和市場(chǎng)文化的能量和它們無(wú)所不在的巨大影響。市場(chǎng)文化最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shī)蕵?lè)精神和狂歡為旨?xì)w的大眾化和商業(yè)化,而博客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寫作勢(shì)必在文學(xué)觀念、作家的身份、職責(zé)和態(tài)度上發(fā)生變化。一切都無(wú)形中以市場(chǎng)和點(diǎn)擊率為圭臬。很多女性詩(shī)人為了提高自己的博客點(diǎn)擊率而與娛樂(lè)和消費(fèi)“媾和”。實(shí)際上這不只是發(fā)生于女性詩(shī)人和女性詩(shī)歌,這是博客時(shí)代的消費(fèi)法則、娛樂(lè)精神和市場(chǎng)文化的必然趨向。在女性詩(shī)歌的博客上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女詩(shī)人的精彩紛呈甚至是“誘人”的工作照、生活照和閨房照。在無(wú)限提速的時(shí)代以及詩(shī)歌會(huì)議和活動(dòng)鋪天蓋地的今天,有些女性詩(shī)人將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風(fēng)景照,與名人的“會(huì)見(jiàn)照”,以及更為吸引受眾的寫真照甚至不無(wú)性感、暴露的圖片隨心所欲且更新頻率極高地貼在個(gè)人的博客上。這在博客好友以及訪友的跟帖留言中可以看到閱讀者對(duì)女性詩(shī)人博客的關(guān)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窺視”和“意淫”的心理。當(dāng)然我說(shuō)的是一些個(gè)別現(xiàn)象,我的說(shuō)法也可能有些過(guò)于尖銳。博客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到底在何種程度和哪些方面會(huì)改變?cè)姼璧纳鷳B(tài)還有待隨著寫作現(xiàn)象的發(fā)展而做出結(jié)論,而最為重要的還在于面對(duì)博客興起以來(lái)的大量女性詩(shī)歌群體和寫作現(xiàn)象需要研究者及時(shí)發(fā)現(xiàn)一些詩(shī)學(xué)問(wèn)題。就個(gè)人博客時(shí)代的女性詩(shī)歌寫作,還沒(méi)有到下“結(jié)論”甚至“定論”的時(shí)候,討論仍會(huì)繼續(xù)下去,這可能就是“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命運(yùn)!
五
談?wù)撆詫懽魉坪跻粋€(gè)避不開(kāi)的話題就是“身體修辭”。而在那些出生于1950和1960年代女性詩(shī)人那里曾經(jīng)相當(dāng)激烈甚至極端的帶有雅羅米爾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無(wú)”的精神疾病氣息的性別話語(yǔ)仍然一定程度上延續(xù)在“70后”的一部分女性寫作群體當(dāng)中。相反在我有限的閱讀中臺(tái)灣的“80后”女性詩(shī)人即使也有為數(shù)不少的身體修辭,但是整體上而言已經(jīng)不像此前女性的那樣激烈和尖銳,而是將身體甚至性都還原為日常化經(jīng)驗(yàn)的一部分。即使是在自認(rèn)為擅長(zhǎng)“細(xì)節(jié)敘寫和身體抒寫”的“不成熟的女權(quán)主義傾向”的崔舜華這里,“身體”抒寫也是較為平靜、日常和舒緩的,如“將久病的肌膚寫成了字/嵌入淺眠的掌紋/若你觸碰我,便可閱讀/從謐凝的晚嵐/到杜鵑的蕊心/我就是六月最棘手的隱喻”
(《六月》),“命名你為:我的國(guó)土。/在我身體虛弱時(shí)/難以順利地術(shù)馭/一套窗簾,一張床,一把扁梳/我的權(quán)位由這些構(gòu)成”(《所有的邊疆都存在矛盾》),“——或許并不是喜歡你/我躺在床上,吸著煙/夕陽(yáng)的顏色偏向一種淫靡橘/我的肌膚熟爛而柔軟/心在深處,產(chǎn)生動(dòng)搖”(《沉默》)。這是否也說(shuō)明隨著時(shí)代文化語(yǔ)境的轉(zhuǎn)換,曾經(jīng)如此激烈白熱化的兩性對(duì)抗和性別抒寫已經(jīng)成為明日黃花,對(duì)于更為年輕也更為開(kāi)放的“80后”甚至“90后”女性而言,身體和性已經(jīng)和飲食一樣沒(méi)有多少值得大肆渲染和作秀之處?值得強(qiáng)調(diào)的是很多人批評(píng)“70后”女性詩(shī)歌時(shí)都是戴著有色的眼鏡放大和歪曲了其詩(shī)歌中的身體與欲望。不容否認(rèn)的是對(duì)于“70后”女性詩(shī)歌寫作而言“身體”和“欲望”確實(shí)也成為了繞不開(kāi)的重要的關(guān)鍵詞之一。但是在近幾年仍用這些詞匯來(lái)限定“70后”女,陛詩(shī)歌寫作就未免太過(guò)單一、武斷、庸俗了,這對(duì)詩(shī)歌和評(píng)論都是不負(fù)責(zé)任的表征。但是我看到的卻是大量的詩(shī)人和批評(píng)者在近年的一些所謂的“權(quán)威”詩(shī)歌年選中仍然“我行我素”地用“身體”和“性”來(lái)評(píng)價(jià)包括“70后”在內(nèi)的女性詩(shī)歌。這有很大的不合時(shí)宜的“脫鉤閱讀”的慣性勢(shì)能導(dǎo)致的誤區(qū),因?yàn)樗麄冞@些讀者、批評(píng)者幾乎無(wú)視“70后”女性詩(shī)歌寫作在近年來(lái)的新的發(fā)展趨向和更為繁復(fù)的運(yùn)動(dòng)軌跡。陳仲義在一篇文章中就談到了對(duì)臺(tái)灣的“軀體性”詩(shī)歌的認(rèn)識(shí),當(dāng)然陳仲義的態(tài)度和論述是較為嚴(yán)密和富于學(xué)理性的,這與一些掄著道德和道學(xué)的大棒的人或嬉皮笑臉的應(yīng)和者形成了強(qiáng)大的反差。
從《下半身》等民刊,叫人聯(lián)想起彼岸臺(tái)灣,類同的寫作風(fēng)氣,早先有始作俑者夏字,第二本詩(shī)集《腹語(yǔ)術(shù)》,充分施展身體優(yōu)勢(shì),極盡女性軀體“以暴抗暴”的奇譎。晚近則有江文瑜、顏艾琳等。《男人的乳頭》(江文瑜著),渾身使出肉欲殺手锏,青出于藍(lán)而勝于藍(lán)。卷一《愛(ài)情經(jīng)濟(jì)學(xué)》,把情欲之想象發(fā)揮到極致。卷二《憤怒的玫瑰》,戲劇性顛覆性中心暴力,濃稠的肉身氣叫人窒息。卷三《巫師與無(wú)詩(shī)》,展演生育全過(guò)程,即使借此論詩(shī),也充滿令人咋舌的轉(zhuǎn)喻。整部詩(shī)集采用或局部或特寫或整體的裸像對(duì)讀,變形、直呈、提喻。文類駁嫁轉(zhuǎn)鏈,赤裸裸穿行于子宮、陰蒂、乳頭,免不了膜臊之味!哪怕干凈地拼貼“胸罩”與“兇兆”,粘連“精液”與“驚異”(“每夜用你親手撫慰的最高敬意/冥想創(chuàng)造/精益/求精…每日用你喉嚨尖聲喃喃的勁囈/冥想創(chuàng)造/精液/求驚”。)即使高明文字的游走和文化穿透,要想得到多數(shù)受眾認(rèn)同,恐怕尚須耐心等待。
換言之談到詩(shī)歌中的“身體”,談到女性詩(shī)人的“身體”敘事,更多的人是將之狹隘化、倫理道德化,忽視了“身體”在文學(xué)和詩(shī)歌寫作中的重要性。更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的是似乎一談到那些從1990年代開(kāi)始詩(shī)歌寫作的“70后”的女詩(shī)人,一些研究者就煞有介事的提起“身體”、“欲望”、“情色”、“性”等這些語(yǔ)詞,似乎這些詩(shī)人除了這之外空無(wú)一物。如果說(shuō)身體修辭和欲望抒寫是詩(shī)歌和文學(xué)寫作的合理性依據(jù)甚至基本質(zhì)素,那么身體和欲望的表現(xiàn)和抒寫就是合理的。但是女性的身體體驗(yàn)包括性愛(ài)體驗(yàn)只有在具有了更多融合的視閩和提升的能力才有可能在另一種向度上抵達(dá)自身、靈魂和詩(shī)歌的內(nèi)核。“70后”女性詩(shī)歌寫作不能離開(kāi)女性意識(shí),又不能將之極端化、偏執(zhí)化,應(yīng)該在一定程度上在更寬更深的超越性別意識(shí)的視閡進(jìn)行寫作、探詢、辯難和挖掘。也許一個(gè)詩(shī)人的一句話宣告了一個(gè)恰切和合理的姿勢(shì)——“我首先是一個(gè)詩(shī)人,其次才是一個(gè)女人”
(張燁)。不可否認(rèn)在女性詩(shī)歌中尤其是1970年代出生的更為年輕的女性詩(shī)歌文本中似乎身體的感知、經(jīng)驗(yàn)、欲望要更為顯豁。除了大陸“下半身詩(shī)歌”的尹麗川、巫昂等詩(shī)人的欲望化敘事引起了很大的爭(zhēng)議外,臺(tái)灣的一些生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女性詩(shī)人也同樣遭受到了非議。
顯然,臺(tái)灣女性的“身體詩(shī)”(或日“情色詩(shī)”、“性愛(ài)詩(shī)”,還有特殊的“同志詩(shī)”)寫作顯然要比大陸的女性來(lái)得更刺激、更大膽、更感官化,也更尖銳化。實(shí)際上臺(tái)灣的一些男性作家關(guān)于身體和性的抒寫也一直作為一種“小傳統(tǒng)”而存在,而這在大陸要遲至1980年代后期才出現(xiàn)。陳黎等人的《忽必烈汗》、焦桐的《完全壯陽(yáng)食譜*、陳克華的《在A片流行的年代》和《下班后看A片》以及題目更為生猛刺激化的詩(shī)歌《女人的隱形陽(yáng)具》、《男人的陰道慶典》都呈現(xiàn)了男性視角下的身體觀和占有女性身體的殖民欲。而一些女性的身體和兩性抒寫顯然在于反撥這種男權(quán)觀照下的身體與欲望。說(shuō)臺(tái)灣的詩(shī)歌界自1980年代以來(lái)--g在上演著“身體爭(zhēng)霸戰(zhàn)”也許并不為過(guò),而“蕾絲與鞭子的狂歡”似乎也點(diǎn)出了臺(tái)灣情色文學(xué)的一些狀況。針對(duì)著主導(dǎo)性的男性身體政治學(xué),出生于1961年的江文瑜和出生于1 968年的顏艾琳通過(guò)兩部詩(shī)集《男人的乳頭》和《骨皮肉》表達(dá)了屬于女性這一“第二性”的話語(yǔ)突圍和反叛。而這些同樣感官化甚至更具有挑逗性的性別話語(yǔ)在一定程度上表達(dá)出女性獨(dú)立和身體平等的時(shí)代和詩(shī)學(xué)意義的同時(shí),也再次陷入到“女性展示——男性窺視”的圈套之中。在顏艾琳和江文瑜詩(shī)歌中大量出現(xiàn)的“乳頭”、“乳液”、“精液”、“生殖器”、“勃起”、“潮濕”、“挺進(jìn)”、“舔舐”、“呻吟”以及更為讓一般讀者難以接受的“成人化”“段子式”甚至“A片鏡頭lHIb9fA6ayzHDL3Yb1rAixbo4A7rNJ7mT8EGexqVZec=化”的詞語(yǔ)譜系其過(guò)于明顯的對(duì)立性、姿態(tài)性,甚至性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詩(shī)歌。
而中國(guó)自1980年代肇始的先鋒文學(xué)中出現(xiàn)的林白、陳染以及詩(shī)歌界的伊蕾、翟永明和唐亞平的身體敘事也許并不比海峽對(duì)岸的臺(tái)灣女性作家遜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臺(tái)灣的1960年代出生的詩(shī)人之后,那些“70后”女性的身體抒寫并沒(méi)有比前輩弱化甚至有“趕超”的傾向,而這在大陸的“70后”女性這里卻十分罕見(jiàn)。除了2000年左右以“下半身”詩(shī)派出現(xiàn)的尹麗川和巫昂、春樹(shù)曾經(jīng)在短時(shí)期內(nèi)大張旗鼓的上演“身體”修辭秀之后,也很快偃旗息鼓。更多的大陸的“70后”女性詩(shī)人也許不乏關(guān)于身體的想象和性的修辭,但更多是呈現(xiàn)了個(gè)人化、細(xì)膩化、情感化和私密化的狀態(tài),從而與此前女性詩(shī)人“戰(zhàn)爭(zhēng)般”的性別表達(dá)具有不小的差異。而再次反觀臺(tái)灣的“70后”女性的身體抒寫,包括吳菀菱、潘寧馨、葉惠芳在內(nèi)的詩(shī)人其性別和身體的情色表達(dá)要更為突出和刺激,也更挑戰(zhàn)讀者和男性詩(shī)人的閱讀極限。吳菀菱甚至宣稱“女性是個(gè)被分解的尸體”,她在詩(shī)歌中宣稱必須反對(duì)男性身體的奴役,而是應(yīng)該相反女性去“使勁的挑逗男人的肛門,以陰唇或手指”。
相應(yīng)的提到大陸的“70后”女性詩(shī)歌的身體敘事人們馬上就會(huì)想到尹麗川,眾多專業(yè)研究者和一般閱讀者首先會(huì)自然而然地將其和“下半身”直接聯(lián)系起來(lái)。確實(shí)尹麗川的一些詩(shī)作所處理的題材是“身體”,甚至是“下半身”,早期的詩(shī)作也帶有明顯的精神疾病、過(guò)度的“身體修辭”的揮霍,但是尹麗川不能完全被判定為一個(gè)簡(jiǎn)單化的、欲望化的身體寫作者,尹麗川的詩(shī)歌寫作是豐富的多棱體。但是尹麗川詩(shī)歌文本的豐富性卻被巨大的公論陰影所籠罩。單就詩(shī)歌趣味而言可能有人對(duì)尹麗川的詩(shī)極其贊賞,但也會(huì)有人極其反感,尤其是對(duì)其涉及“身體”、
“性”的詩(shī)歌更是如此。但是我們是否注意到了尹麗川詩(shī)歌寫作的“嚴(yán)肅性”的一面,也正如先鋒批評(píng)家陳超所說(shuō)的從詩(shī)歌趣味上而言,我們或許對(duì)一些詩(shī)人更為認(rèn)同,而對(duì)某些詩(shī)人則不太適應(yīng),但是“我同樣看到他們面對(duì)寫作的嚴(yán)肅性的一面以及各自的可信賴的才能”。實(shí)際上尹麗川的身體敘事更多是一種以瘋癲狀態(tài)呈現(xiàn)出的另一種“失語(yǔ)癥”。讀尹麗川的詩(shī)有時(shí)很困惑,尹麗川更像是一個(gè)吉普賽女郎,在遷徙與流浪中,在都市與鄉(xiāng)村中間,在世間萬(wàn)象和內(nèi)心潮汐之間,她所牽扯出的正像是炫目而暖昧的萬(wàn)花筒,而尹麗川在更多時(shí)候是被指認(rèn)為“下半身”的詩(shī)人,《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就被認(rèn)為是“經(jīng)典”的“下半身”之作。。
哎 再往上一點(diǎn)再往下一點(diǎn)再往左一點(diǎn)再往右一點(diǎn)
這不是做愛(ài)這是釘釘子
噢再快一點(diǎn)再慢一點(diǎn)再松一點(diǎn)再緊一點(diǎn)
這不是做愛(ài)這是掃黃或系鞋帶
喔再深一點(diǎn)再淺一點(diǎn)再輕一點(diǎn)再重一點(diǎn)
這不是做愛(ài)這是按摩、寫詩(shī)、洗頭或洗腳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溫柔一點(diǎn)再潑辣一點(diǎn)再知識(shí)分子一點(diǎn)再民問(wèn)一點(diǎn)
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這首詩(shī)你可以說(shuō)它暖昧、色情、下流、骯臟,或者說(shuō)它根本就不是詩(shī)歌而是“淫詞浪語(yǔ)”的葷段子,但是尹麗川的意圖可能更多是出自激憤和反諷,她所想反撥和挑戰(zhàn)的正是積習(xí)的男性化的閱讀“意淫”,而詩(shī)中的“再知識(shí)分子一點(diǎn)”、“再民間一點(diǎn)”顯然是“70后”詩(shī)人對(duì)當(dāng)年盤峰論爭(zhēng)的認(rèn)識(shí)與批評(píng)。“70后”詩(shī)歌包括“下半身”詩(shī)歌正是在1999年的那場(chǎng)世紀(jì)末的“知識(shí)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縫隙中沖殺出來(lái)的。正如不同的人面對(duì)同一部《紅樓夢(mèng)》會(huì)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而尹麗川《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最終所折射的是不同身份角色的靈魂,或高或低,或雅或俗,或善或惡……但是,眾多的閱讀者在以快感或憤怒讀這首詩(shī)的時(shí)候,可能忽略了這首詩(shī)最為重要的部分,當(dāng)尹麗川有意或無(wú)意地將生活中的日常舉動(dòng)和性暗示放置在一起之后,就別有用心的出現(xiàn)了這樣的詩(shī)句:“再知識(shí)分子一點(diǎn)再民間一點(diǎn)。”這肯定不是可有可無(wú)的句子,甚至說(shuō)相當(dāng)富有意味的句子。當(dāng)“知識(shí)分子”、“民間”和暖昧的場(chǎng)面混雜在一起的時(shí)候,尹麗川所想表達(dá)的遠(yuǎn)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簡(jiǎn)單或低下。而如何正確體認(rèn)女性與身體抒寫之間的關(guān)系,我想巫昂的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我一向只能用女人的眼睛去看東西,它們給我的震撼和我的反應(yīng)肯定也都是陰性的,每個(gè)女人的一生,都要被郁悶、慌張、惱怒和難以言表所困擾,但我決不是想當(dāng)這個(gè)性別的代言人,因?yàn)椋乙呀?jīng)遭遇了很多來(lái)自同性的攻擊,我無(wú)法不僅僅代表自己發(fā)言。”(巫昂:《我為什么寫性》)巫昂的詩(shī)歌寫作在2000年之后多少顯出關(guān)于身體和性的取向,寫性,女性的性,可能有很多人誤讀了巫昂和她的這些“敏感”的詩(shī)作。而在我看來(lái)巫昂的詩(shī)歌中這些“性”的場(chǎng)景的出現(xiàn)都是和實(shí)實(shí)在在的生存感受和生命認(rèn)知直接相關(guān)的。巫昂的詩(shī)歌中幾乎很少有赤裸裸的對(duì)性和欲望的宣泄。透過(guò)巫昂詩(shī)歌中的性的元素所折射的是更為尖銳的女性生存的悖論、憤怒、陰郁甚至質(zhì)疑。巫昂以特有的女性視角和個(gè)性化的抒寫方式呈現(xiàn)了一個(gè)蜘蛛般的憂郁天氣,“打開(kāi)了又一瓶啤酒/這是德國(guó)老娘們開(kāi)的酒吧/以前我們?cè)谶@里/親嘴、亂摸、倒頭大睡/她在柜臺(tái)后面看電視/她的床在墻后面發(fā)餿/后來(lái)。酒味變薄/我們?cè)阶冊(cè)叫?小到接近腐爛/有人開(kāi)始搶/靠窗的位置”(《好東西總是容易壞掉》)。換言之巫昂關(guān)注的不是單純的性,而是與之相關(guān)的令人唏噓感嘆的黑色質(zhì)地的沉重區(qū)域,“需要性來(lái)讓我軟弱/需要堅(jiān)定的交往/你的生殖器無(wú)人可以替代/需要你覆蓋我/如國(guó)旗和棺木”(《需要性》)。按照巫昂自己的說(shuō)法就是“作為女人,我關(guān)心性交帶來(lái)的那些副產(chǎn)品,幼年到少年,我在母親的產(chǎn)房里混,生產(chǎn)的血、引產(chǎn)嬰兒滿地躺著、生過(guò)八胎以上的癟了的小老女人,14歲的小姑娘懷著老師的孩子,這些記憶太深了,好像沒(méi)有什么比那更加動(dòng)物、更不人性。相比之下,我覺(jué)得性交不算什么觸目驚心的事,性交不是性的全部”(巫昂:《我為什么寫性》)。但是在更多的“70后”女性詩(shī)人那里關(guān)于身體的詩(shī)歌敘事顯然并沒(méi)有像當(dāng)年的尹麗川和巫昂那樣如此強(qiáng)烈、如此集中,而是將身體更多地還原為個(gè)體生存權(quán)利,身體、靈魂和那些卑微的事物一樣,只是詩(shī)人面對(duì)世界、面對(duì)自我的一個(gè)言說(shuō)的手段而已。或者說(shuō)對(duì)身體的命名和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不再是1980年代中國(guó)女性詩(shī)人的空前激烈的自白狀態(tài),而是上升為一種日常化的撫慰與感知,“身體有它受過(guò)的愛(ài)撫,薔薇色的時(shí)刻/身體有它的寂寞/它的哀傷、痛楚、顫栗/身體有它的夜晚、一個(gè)唯一的夜、從未/到來(lái)的夜/(一雙唯一的眼睛)——/身體有它的相認(rèn)/它的拒絕、潔癖/它固執(zhí)的、不被看見(jiàn)的美麗/身體有它的柔情/有它的幻想、破滅、潦倒、衰敗/它終生不愈的殘缺……/身體有它的記憶,不向任何人道及”(扶桑:《身體有它受過(guò)的愛(ài)撫》)。即使是在身體和欲望在青春年少燃燒的年代,在寫于1994年的早期詩(shī)作中扶桑的關(guān)于身體的敘事也呈現(xiàn)出少有的知性的色彩,“在我的背后解開(kāi)那顆細(xì)小的紐扣/你的手握著我的 乳房/仿佛兩只溫順的鴿子棲落你的手掌//寂靜的屋頂上,有薄雪似的霜……”(扶桑:《霜》)。
六
就筆者近些年對(duì)兩岸“70后”女性詩(shī)歌的閱讀觀感而言,其寫作變得更為廣闊舒展,其視閡與題材都呈現(xiàn)了令人贊嘆的豐富性、復(fù)雜性。她們?cè)谳嵊行碌呐元?dú)有體驗(yàn)的同時(shí)又向著更為廣闊的精神維度伸展。面對(duì)這種更有內(nèi)力也更為繁復(fù)、精深、尷尬的詩(shī)歌,我們僅用一句“女性意識(shí)”來(lái)概括肯定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如李小洛的《省下我》不僅以反諷的方式呈現(xiàn)了一個(gè)時(shí)代尷尬的生存氛圍,而且凸現(xiàn)了“70后”女性基本的精神維度和價(jià)值取向,“省下我吃的蔬菜、糧食和水果/省下我用的書本、稿紙和筆墨。/省下我穿的絲綢,我用的口紅、香水/省下我撥打的電話,佩戴的首飾。/省下我坐的車輛,讓道路寬暢/省下我住的房子,收留父親。/省下我的戀愛(ài),節(jié)省玫瑰和戒指/省下我的淚水,去澆灌麥子和中國(guó)。/省下我對(duì)這個(gè)世界無(wú)休無(wú)止的愿望和要求吧/省下我對(duì)這個(gè)世界一切的罪罰和折磨。/然后,請(qǐng)把我拿走。/拿走一個(gè)多余的人,一個(gè)/這樣多余的活著/多余的用著姓名的人”。
“70后”女性詩(shī)人開(kāi)始關(guān)注和打量生存的細(xì)部,體驗(yàn)著更為廣大的群體的艱辛,同時(shí)也表達(dá)了新一代知識(shí)女性靈魂和生命體驗(yàn)的扎實(shí)可靠。但是這種無(wú)限開(kāi)闊的“70后”女性詩(shī)歌的寫作傾向也在另一個(gè)向度上印證了其尷尬和兩難性的特征。與大陸的“70后”女性詩(shī)人相比,臺(tái)灣的女性詩(shī)人在“鄉(xiāng)土寫作”、“家族譜系”甚至個(gè)人與歷史關(guān)系的抒寫上顯得不夠明顯和突出。當(dāng)我在2011年的春天在臺(tái)灣三個(gè)多月的交流考察中,曾經(jīng)在1970年代余光中等詩(shī)人的詩(shī)作中大量出現(xiàn)的“鄉(xiāng)土”意象,比如香蕉林、芒果園、鳳梨地等在“70后”詩(shī)人這里幾乎已經(jīng)難覓影像。而隨著臺(tái)灣本土的日益城市化,更多的年輕詩(shī)人在投身城市化的激烈競(jìng)爭(zhēng)的同時(shí),盡管多少還保留著自己曾經(jīng)的“鄉(xiāng)下”人的某些“口音”和慣性“鄉(xiāng)愁”情結(jié),但是更多的是個(gè)人與城市在詩(shī)歌中的交相叩問(wèn),雖然城市在這些女性詩(shī)人那里呈現(xiàn)為被質(zhì)疑、顛覆甚至戲謔的客觀對(duì)應(yīng)物。限囿臺(tái)灣島悠閑的空間距離以及高速發(fā)展的交通,即使是所謂的“鄉(xiāng)下”已經(jīng)日益被城市化和去地方化,一代女性的“精神地理學(xué)”正在從“鄉(xiāng)愁”的層面轉(zhuǎn)換為“都市現(xiàn)代人”的繁復(fù)經(jīng)驗(yàn)。與此同時(shí),倫理化和社會(huì)化的寫作在臺(tái)灣的這些女性詩(shī)人這里也較為鮮見(jiàn),家國(guó)意識(shí)、擔(dān)當(dāng)精神、介入姿態(tài)和使命感盡管偶爾在一些詩(shī)人那里有著稍縱即逝的顯現(xiàn),但更多的時(shí)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gè)個(gè)女性、一個(gè)個(gè)個(gè)體在寫作日常的、個(gè)人的詩(shī)。
原型甚至是弗洛伊德思想體系參照下的“俄爾浦斯”和“那喀索斯”形象曾在中國(guó)的先鋒文學(xué)中得到了互文性的呈現(xiàn)和闡釋,而更具詩(shī)學(xué)和歷史意義的普泛層面的家族敘事則在女性文學(xué),尤其是女性詩(shī)歌中得到了越來(lái)越廣泛和深入的體現(xiàn)。在很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中國(guó)女性詩(shī)人的家族敘寫更多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這些傳統(tǒng)的家族形象成為詩(shī)人們追蹤、描述和認(rèn)同的主體,“她生來(lái)就是這樣造就的,絕沒(méi)有屬于她自己的什么意見(jiàn)或者愿望,而總是寧愿贊同別人的意見(jiàn)和愿望。最要緊的是——我其實(shí)不用說(shuō)出來(lái)——她很純潔。她的純潔被視為首要的美”。而值得注意的是臺(tái)灣的“70后”女性詩(shī)人由于“鄉(xiāng)土”經(jīng)驗(yàn)的普遍缺乏,顯然缺少一種對(duì)來(lái)自于“土地”和“家族”的譜系性抒寫。而相應(yīng)的,這些出生于大陸的“70后”女性詩(shī)人由于普遍具有“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農(nóng)村經(jīng)驗(yàn)和古典農(nóng)耕情懷的遺留以及理想主義情緒的少量沉淀,她們的詩(shī)歌更多體現(xiàn)為“還鄉(xiāng)”意識(shí)和個(gè)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下對(duì)家族的不無(wú)沉重和多樣化的抒寫。當(dāng)然對(duì)于其中那些來(lái)自于城市的“70后”女性而言,她們的家族抒寫更多帶有反諷和顛覆的意味。據(jù)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女性詩(shī)人是持著尊敬、懷念、贊頌之情將家族敘事在失落的農(nóng)耕文明和強(qiáng)勢(shì)的城市背景之下展開(kāi),但也有女性詩(shī)人對(duì)待家族敘事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反思、背離和批判、顛覆的態(tài)度。
上個(gè)世紀(jì)的70年代末,女性詩(shī)歌中的家族敘事更多是政治和社會(huì)學(xué)層面的,而到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詩(shī)人更多意義上成了西方自白派詩(shī)歌和伍爾莢、杜拉斯的追隨者,更多是像伍爾芙在《一間自己的屋子》、《瓊’馬丁太太的日記》里所做的那樣試圖通過(guò)分析家族中的“母親”形象來(lái)尋找女性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生命的傳統(tǒng)與困境并進(jìn),而對(duì)抗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男權(quán)文化霸權(quán)。這在伊蕾、翟永明、唐亞平、陸憶敏等女性詩(shī)人關(guān)于“母親”的敘事那里得到了最為直接的帶有“傷痕”性的疼痛式印證與母女關(guān)系的疏離,“歲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讓我親眼看著自己被碾碎/呵,母親,當(dāng)我終于變得沉默,你是否為之欣喜/,沒(méi)有人知道我是怎樣不著痕跡地愛(ài)你,這秘密/來(lái)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兩個(gè)傷口痛苦地望著你”
(翟永明:《母親》)。女性詩(shī)人對(duì)“母親”的家族抒寫無(wú)疑經(jīng)歷了由血緣和人格的“鏡像”式認(rèn)同到剝離和反思的艱難過(guò)程,這一時(shí)期的女性詩(shī)歌的家族敘寫帶有強(qiáng)烈的對(duì)抗性和道德色彩,表現(xiàn)出強(qiáng)大的對(duì)父權(quán)規(guī)訓(xùn)的反叛與挑戰(zhàn)。而在筆者看來(lái)新世紀(jì)十年以來(lái)的大陸女性詩(shī)歌寫作顯然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不同于此前詩(shī)歌的新的特質(zhì),其中最為顯著的征候就是女性詩(shī)人在家族敘事上的新變,而這種變化無(wú)論是在詩(shī)歌美學(xué)還是在社會(huì)學(xué)的層面上都值得進(jìn)行切片式的研究和關(guān)注。盡管這些“70后”女性詩(shī)人不乏強(qiáng)烈而又帶有智性色彩的女性意識(shí),但是這與“第三代”女性詩(shī)歌自白式的言說(shuō)方式和一定程度上偏激的女權(quán)立場(chǎng)有著很大的區(qū)別。女性意識(shí)不等同于女權(quán)主義,由于這些青年女性詩(shī)人差異較大的生活背景、成長(zhǎng)經(jīng)驗(yàn),這就使得這些女性詩(shī)人詩(shī)歌文本中同時(shí)出現(xiàn)了差異很大的甚至相互齟齬的家族譜系,同時(shí)呈現(xiàn)出對(duì)家族譜系的歷史敘事和現(xiàn)實(shí)抒寫中的贊頌性情感和背離性反叛精神,“那個(gè)瘦小的女人最后離去/我們家醉心紙牌的女人終于離去/你看不到這一切:在沿河地帶/丟失貍貓的少年又失去母親//在半夜流著血/在半夜尋找鄉(xiāng)村巫師/符咒和草藥相煎的氣味彌漫在這些手稿中間/自殺者沉著、堅(jiān)定,蔑視死神”(白瑪:《家族史:靜靜的陰影》)。這種不無(wú)尷尬的家族譜系的建構(gòu)甚至拆解不能不呈現(xiàn)出近年來(lái)女性詩(shī)歌最為重要的尷尬性特征以及個(gè)人化的歷史感和自省精神。當(dāng)這一時(shí)期的女性詩(shī)歌中同時(shí)出現(xiàn)惡父、惡母、慈父、慈母甚至是不偏不倚的不帶感情色彩的家族的形象時(shí),傳統(tǒng)的家族譜系敘事在這些女性詩(shī)人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重新清洗和審視,當(dāng)然也程度不同地仍然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家族印象和一代人特有的集體記憶。在尹麗川的詩(shī)作中其彰顯的女性意識(shí)有時(shí)候是相當(dāng)強(qiáng)烈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尹麗川的很多詩(shī)作中都出現(xiàn)了年邁的母親和老婦人的形象。這些年邁的女人形象無(wú)不扭曲、平常、灰暗,這也從另一維度呈現(xiàn)了女性命運(yùn)的尷尬,年長(zhǎng)色衰、為人妻為人母的多重身份的重壓,抑或詩(shī)人對(duì)女性身份的焦慮。當(dāng)光陰陰暗的鏡子中一個(gè)個(gè)容顏老去的時(shí)候,一種自戀、自問(wèn)、懷疑和怨憤的情結(jié)就不能不空前強(qiáng)烈的凝聚和爆發(fā)出來(lái)。曾經(jīng)的文學(xué)寫作中“愛(ài)女慈母”的經(jīng)典模式在尹麗川等“70后”和“80后”女性詩(shī)人這里遭到了解構(gòu)與顛覆,“惡母”的形象在女性文學(xué)中一再閃現(xiàn),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有張愛(ài)玲的影響。對(duì)母女關(guān)系的重新認(rèn)知成了包括尹麗川在內(nèi)的“70后”女性詩(shī)人的一種近于天生的家族譜系審視。在《媽媽》這首詩(shī)中血緣層面的母女關(guān)系被置換為女人和女人,年輕的女人和年老的女人的關(guān)系,熟悉與陌生,倫常與悖論,生命與符號(hào)所呈現(xiàn)的是男性讀者非常陌生的經(jīng)驗(yàn)和場(chǎng)景。“老女人”形象鮮明地揭示了尹麗川作為女性的性別焦慮和身份隱憂,這種焦慮和隱憂在《郊區(qū)公廁即景》的“不潔”場(chǎng)景和細(xì)節(jié)中被還原為年輕女人和老女人的錯(cuò)位的對(duì)話以及挑戰(zhàn)性的否定。而作為一個(gè)女性詩(shī)人,尹麗川的詩(shī)歌文本中的“父親”無(wú)疑是一個(gè)重要的、敏感的形象。在伊格爾頓看來(lái)“父親”是政治統(tǒng)治與國(guó)家權(quán)力的化身,而在尹麗川的詩(shī)歌中“父親”還沒(méi)有被提升或夸大到政治甚至國(guó)家的象征體系上,而是更為真切的與個(gè)體的生存體驗(yàn)甚至現(xiàn)實(shí)世界直接關(guān)聯(lián)。而詩(shī)人與“父親”的關(guān)系則是尷尬的狀態(tài),既想回到本真性的親切又不能不面對(duì)強(qiáng)大的血統(tǒng)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和隔膜。與尹麗川在城市背景下更多的對(duì)家族譜系的反思性甚至質(zhì)疑性的姿態(tài)不同,李小洛則更多是在鄉(xiāng)土化的背景中呈現(xiàn)了沉重而不乏溫情的家族敘事。在《大事件》這首敘事性的深情繾綣的詩(shī)作中李小洛選取了相當(dāng)具有震撼性的歷時(shí)性的日常生活的“大事件”和戲劇性的場(chǎng)景,以及個(gè)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從而呈現(xiàn)出真切的父親生活史和情感履歷以及其間詩(shī)人的反思、自責(zé),痛苦、難以言說(shuō)的深厚情感和生命無(wú)常的無(wú)奈與喟嘆。實(shí)際上在很多有著鄉(xiāng)村背景甚至像鄭小瓊這樣不僅有著鄉(xiāng)村背景而且同時(shí)具有“打工”和“底層”身份的“80后”女性詩(shī)人那里同樣呈現(xiàn)了李小洛一樣的沉重而尷尬的家族敘事,家族敘事的背后有著詩(shī)人對(duì)后工業(yè)時(shí)代的生存場(chǎng)景和農(nóng)耕文明失落的憂思和痛苦的家族記憶。鄭小瓊呈現(xiàn)了一個(gè)加速度前進(jìn)的后工業(yè)時(shí)代詩(shī)人身份的多重性和寫作經(jīng)驗(yàn)以及想象力的無(wú)限可能的空間。在關(guān)于家族的詩(shī)歌敘寫中鄭小瓊從活生生的社會(huì)生活、個(gè)體生存和歷史場(chǎng)閡中生發(fā)出平靜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更為可貴的是這些詩(shī)作閃現(xiàn)出在個(gè)體生命的旅程上時(shí)光的草線和死亡的灰燼以及對(duì)鄉(xiāng)土、生命、往事、歷史、家族的追憶。這些詩(shī)歌帶有強(qiáng)烈的挽歌性質(zhì),更帶有與詩(shī)人的經(jīng)驗(yàn)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陣痛與流連。女性詩(shī)歌的家族敘事凸顯了這些年代女性詩(shī)人艱難的生存背景,據(jù)此早期的過(guò)于對(duì)抗性和封閉性的女性欲望和身體敘事在這些更為年輕的女性詩(shī)人這里得到了轉(zhuǎn)向,轉(zhuǎn)向了更為值得文化反思和詩(shī)學(xué)呈現(xiàn)的視野,也更為寬廣的家族譜系的抒寫。新世紀(jì)以來(lái)的女性詩(shī)人關(guān)于父親、母親的家族敘事大體是放在鄉(xiāng)村和城市相交織的背景之下,沉寂,蒼涼,孤獨(dú)成為基本意緒。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shí)期的女性詩(shī)人在家族敘寫上不僅對(duì)現(xiàn)實(shí)、身體體驗(yàn)和男性文化進(jìn)行了相當(dāng)富有深度的省思與反問(wèn),更為重要的是她們普遍的具有歷史意識(shí)觀照下的沉重的家族敘事所呈現(xiàn)的社會(huì)景觀以及更為駁雜的內(nèi)心圖景。換言之這些女性詩(shī)人不乏個(gè)人化的歷史想象力,這種關(guān)于歷史的個(gè)性化表述不是來(lái)自于單純的想象而是與一代人的生存背景和對(duì)文化、歷史、政治的態(tài)度相當(dāng)密切的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中張揚(yáng)出個(gè)體和女性的雙重光輝。
贅述了這么多,也注定是浮光掠影甚至是言不及義的個(gè)人表述和碎片化觀感。兩岸的“70后”女性詩(shī)歌的諸多共性和不可消弭的差異性都值得我們反復(fù)深入追問(wèn)和研究。當(dāng)這些女性已經(jīng)不再年輕,當(dāng)她們現(xiàn)在的詩(shī)歌精神地理已經(jīng)和她們剛出道時(shí)候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小的差異時(shí),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自信來(lái)面對(duì)一個(gè)寫作數(shù)量日益激增,博客、微博、手機(jī)等自媒體日益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只能說(shuō),對(duì)于仍然深不見(jiàn)底的海峽,對(duì)于更為多元和個(gè)性化的詩(shī)歌寫作而言,兩岸女性都以各自知冷知熱的方式以及不可消弭的個(gè)性,呈現(xiàn)出一個(gè)“歧路的花園”般的精神地理學(xué)。而漫步在歧路和迷津的花園里正在上演著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傾聽(tīng),還需要繼續(xù)下去。
①當(dāng)然也有臺(tái)灣的學(xué)者對(duì)采用民國(guó)紀(jì)年的“年級(jí)說(shuō)”持異議,如評(píng)論家楊宗翰在《臺(tái)灣“崛起中的七字頭后期女詩(shī)人”》(《詩(shī)歌月刊》,201 1年第7期)中就認(rèn)為“最近臺(tái)灣文化圄內(nèi)/外蠱行‘幾年級(jí)’說(shuō),我一來(lái)實(shí)在看不出此詞究竟有何種文學(xué)史意義;二來(lái)總覺(jué)得這些采‘民國(guó)’紀(jì)年、斷代者頗類于時(shí)風(fēng)俗潮下的又一場(chǎng)流行性感冒——吾既身強(qiáng)體健、又厭隨俗從眾,何必取之?”據(jù)此,楊宗翰在2001年發(fā)表的《新浪襲岸》中提出擬仿中學(xué)時(shí)期的學(xué)號(hào)即以入學(xué)年份而生來(lái)劃分世代,即“字頭”斷代法,如“六字頭”、“七字頭”等。同時(shí)感謝在寫作此文的過(guò)程當(dāng)中,臺(tái)灣著名學(xué)者楊宗翰所提供的關(guān)于“七字頭后期女性詩(shī)人”的一些代表性文本。
②(德)E·M-溫德?tīng)枺骸杜灾髁x神學(xué)景觀》,刁承俊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第62頁(yè)。
③葉惠芳,女,1976年出生于臺(tái)北,主修戲劇,為“摩羯劇場(chǎng)”成員。值得注意的是與其名字相近的另一位詩(shī)人葉蕙芳卻是一位男性詩(shī)人。葉蕙芳,本名林群盞,1969年出生。連臺(tái)灣本土的研究者也誤將葉蕙芳判定為女性詩(shī)人,例如李元貞的《女性詩(shī)學(xué)》。
④《編輯前言》,《雙子星人文詩(shī)刊》,1996年,第4期。
⑤2007年11月1日到2日,在海口召開(kāi)的21世紀(jì)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研討會(huì)上,與會(huì)者重新提起了“70后”詩(shī)歌并且以沈浩波和尹麗川的“身體”性詩(shī)歌為例。非常有意思的是,與會(huì)者分成兩派,一部分批評(píng)家對(duì)尹麗川和沈浩波口誅筆伐,另一部分人卻對(duì)沈浩波和尹麗川大加贊賞。筆者在大會(huì)發(fā)言和討論中集中談?wù)摿恕?0后”詩(shī)歌寫作的特征,以及目前文學(xué)界對(duì)“70后”詩(shī)歌普遍的誤解與歪曲。
⑥弗吉尼亞·伍爾莢:《伍爾芙隨筆》,伍厚凱、王曉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