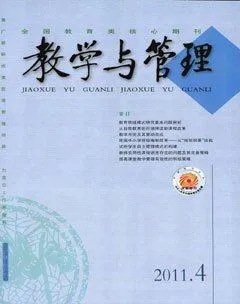從自我教育的內涵釋讀新課程改革
新課程改革說到底就是中國面向新世紀預設的,應變未來各種挑戰的一種文化構建。這一構建指向的目標就是“智慧”,在學生身上,生成一種基于他個人的生存智慧,在國家、民族層次,生成一種自主創新的復興大智慧。但“真正的智慧是不可能被教會的”,它不僅要“以道觀之”,還必須“以我觀之”,無“我”則無智慧。a以此觀照過去幾年新課程改革的實施,會發現一些教師并沒有深深吃透新課程改革的本義,因而在相關教育教學環境越來越多彌漫的是“應景”式的技術、技能、技藝的復制、表演和轉借,于是導致學習者的學習,更多脫離了他們最深層的有血有肉的人性,而建構在人為的、強制的、外控的布景上,致使“偽智慧”層出不窮。毫無疑問,決定這次課程改革成敗的就是第一線的教師,他們的觀念、靈感、激情、乃至最深層的有血有肉的人性,能被他們主動地、自主地、獨立地挖掘出來幾分,學生的創造性、主體性、批判性就能達到幾分。換句話說,教師的自我教育能達到什么程度和廣度,學生的自我教育就能達到什么程度和廣度,與此同時,新課程改革就能成功到什么程度和廣度。這里的自我教育不僅指學校環境中圍繞著學科文化的“狹義自我教育”,更包括在廣大的社會生活中,承載著無限豐富的文化傳承的“廣義自我教育”。它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個體通過把自我作為對象所進行的一切教育過程,反映的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學習模式”。這些模式的進行大多數并不像在學校教育中那么目的明確、計劃周密、控制有致,相反是在極端紛繁復雜的家庭、社區、單位、偶然社會環境等等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地展開的。在其中,每個人時時刻刻身浸體感在周圍生存環境、情境、情景的價值和意義的運動變化中,在對這些環境、情境的價值和意義的審視、認識、理解、判斷中,在對特定(職業、學業等)生存環境認識和行為方式的融通與超越中,從而顯現出了每個人對知識主動的“深”加工,獨立的“精致”加工,自覺的“超越性”加工中“轉識成智”的一條條通途。
一、課程資源挖掘中的自我教育
如果把這樣一個自我教育界定投入到新課程改革中,則教師的生涯發展未免顯得苛責和悲壯。一些研究者曾把全國特級教師孫維剛,還有像李吉林、劉可欽等的教學過程進行了總結,得出了一整套的教學方法模式,意圖向全國推廣。筆者大膽猜想推廣的結果,大多數都是東施效顰,因為總結出來的都是這些特級教師表面化的皮毛特征。翻看他們的教學歷程會發現,他們的所言所行是其他任何教師都可以做得到,之所以后者沒有做到,是因為后者缺乏一種自覺的主體智慧。居于這種智慧核心的就是一個詞——學生,在這些最優秀教師的血肉、骨髓乃至靈魂深處,這個詞是最神圣的,也因此孫維剛上了八次手術臺,第八次終于沒有下來,李吉林幾種疾病纏身,無怨無悔,應該說,這種狀況就是他們生命能量全部“超越性”地投入到課程資源挖掘中的結果。
2006年教育部委托幾所師范院校對新課程改革數年來的實施,做一追蹤調研發現,課程資源的匱乏已嚴重影響了新課程的順利實施,突出表現是:盡管經過大規模教師培訓,教師對新課程理念及基礎教育的現實問題有了了解,但是怎樣把這些理念在教學中呈現出來卻有很大的難度與差異度,因為“找不到和教材有關的資料”。是真找不到嗎?《綱要》及其《解讀》明確表達了本次課程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入地投入到學生的生存環境中,去挖掘和建構圍繞著他們生活興趣、體驗和情意的一個感受、感知和感應系統,以使靜態的認知過程活化、靈化和自由化,從而極大地推動學生最底層身心狀態的全面開放。從中可知,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環境就是教師取之不竭、展開新課程改革的資源寶庫。
關鍵在于教師的精神世界有沒有一個自主建構起來的,隨時隨地、臨場即時的“心向”,它表現為大腦皮層一組活躍的“興奮灶”,里面的內容包括三類:一是有關學生的包羅萬象的人格特點;二是種種課程的認知點;三是如何把前兩者結合起來的種種“?”。其中的第三點幾乎構成了教師全部生活的“當下意識”,內隱的暗示性語言經常是:“這個現象(生活中碰到的)會不會有助于學生理解‘慣性’”、“這個鏡頭(電視中看到的)我是不是可以讓學生看看,他們看到了會怎么想,和我想的一樣嗎,社會是怎樣看待這種現象的,我應該怎樣尊重性地啟發、引導他們”、“這個事件(來自媒體、網絡甚至偶然聊天)應該拿到班里讓學生討論一下,肯定比教材的效果更好”、“這種情況要是王小明白,一定會更加清晰地知道什么是新陳代謝”等等等等,整個過程折射著全身心投入的敏感性、敏銳性甚至過敏性的教育使命意識,其推動著教師的自我系統總是在生成假設、解釋、預測及信息的加工組織中,持續地自我觀察、自我判斷、自我反應和自我強化,以最廣泛地洞察、搜尋、捕捉到那些切合于教育教學的復雜又微妙的課程資源。李吉林選擇與教學相關的最佳情境已到了癡迷的程度,為了趕在學生前面去觀察日出,夜不能寐,困頓中夢見太陽在黑云里翻騰,好久也跳不出來,一下子就急醒了,馬上翻身起床,立即出發。在黎明前的黑夜里,她獨自騎著車,飛奔在鄉間小路上。劉可欽始終認為“她自己”就是一個課程資源庫,一笑一顰,一促一急,無不牽引著學生們心緒、情感、想象的流離波瀾。因此,在每學期開學前的整個晚上,她都在對著鏡子練習一句話:“孩子們,你們好。”這句話已無數次在她腦海里涌動,但是她認為問題不在于這句話本身,而在于將用怎樣的語氣、怎樣的表情說這句話。在練習中,她總是對自己的表現不滿意,有時太嚴肅、死板,有時聲音太高,故意做作,有時在倉促中應付了事。直至第二天在去學校的路上,在路人驚詫的目光中,她還在練習和傾聽著這句話。她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在這樣一句溫情又自然的問候中,讓學生們在整個學期,成為一個完全樂于接受教育的、滿足和幸福的人[1]。
范梅南建議基礎教育的教師們,要深切“同情”學生,這種同情與其說是教師設身處地地生活在學生的世界中,還不如說是學生已經生活在教師的內心世界中[2]。后者凸顯著教師的自我系統持續不斷地運轉著“毋我”、“毋固”、“毋必”的專業化解放之路,這不啻有一種脫胎換骨的被改造之感,因為他將以謙恭的心態、甘當配角的“屈己力”及天文學家那樣精細的洞察力,去沉浸在對學生著迷般的極大興趣中,從而在精神世界衍生出一個如影隨行的“教育心向”,于是,周圍的社會環境自然而然成了他取之不竭的課程資源寶庫。
二、課程事件展開中的自我教育
課程事件觀認為,課程是指在某種具體情境下,讓學生作為主要參與者對人類生活進行的某種“復演”、表演。現行的語言體系對課程事件有三種理解:宏觀、中觀、微觀,本文更多地著眼于微觀課程事件的展開,即課堂上濃縮的人類歷程的變化及其存在的情境,通俗講就是各學科的課堂教學。
新課程改革用一個“三維目標(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概括了它要追求的課堂“生命活力”。應該說“情感態度”是其中居支撐地位的樞軸,諸如,物理學中對事物運行法則的內在景仰,數學中對數字變幻莫測的神奇膜拜,語言學中對奇巧精文的“如嘗甘飴”等等,歸為一句話,就是養成對科學、對人類的人文學科一種崇尚理性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表現為好奇、懷疑、不輕信,不盲從,崇尚真理,人格獨立,多元價值兼容等,實質就是批判性思維的生成,它與創新性作為一對孿生兄弟一起成為了學生智慧的首要表征,其典型行為就是層出不窮地提出問題,慣于四處尋找答案,常常自主地猜想、反思和得意于一些“異想天開”的主意中……但是有這樣行為的中國學生比例非常低。楊振寧不斷地說起“外國學生知道一些皮毛的問題,中國學生可能做過成千上百遍了,但中國學生膽子小,教師沒講過的不敢想,老師沒教過的不敢做”。問題是,中國學生為什么膽子小?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創新性往往是一個人最深層精神能量的外化,伴隨這一過程的更多是緊張、焦慮、惶恐甚至極大的不安,這時學生特別需要教師給予一個強大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如范梅南所講的,并不僅僅是“作為教師角色的社會支持,而是像父母樣的深切體懷性支持”[3],只有這樣,學生的最深層精神能量才能“肆無忌憚”地激情四射。劉可欽上課時要是有學生遲到,她會深情問:“你可來了,我們正為你擔心呢!”在她巡視學生做練習時,發現小飛寫錯了一個字,于是站在身后“小心地屏住氣說:‘這個字能不能再檢查一遍’”,這時見小飛驚恐地回頭瞥了她一眼,趕忙拿起了橡皮……這一瞥曾使劉可欽久久不能忘懷,她想自己已經是非常小心地注意了講話的語氣,學生都這么驚恐,那么平時他們是帶著多么大的緊張、慌恐和防衛感在接受教育。她進一步思考,要打消他們的慌恐和防衛感,不是要尊重他們,而是要極大地尊重他們。第一步就是無條件地把他們當成一個個非常獨特的個體,要經常把這樣的問題掛在嘴邊:“小明的學習風格是什么樣的”,“小紅對什么有興趣”,“小麗遇到的障礙在哪里”,“小華學習四則運算的敏感點是什么”。一次,劉可欽要學生們舉手回答一個問題,發現小青的手欲舉又放,猶豫不決,于是課間她問小青:“你是不是很想回答問題,但又沒有想好?”“就是”“那么咱們約定,你對問題很有把握時,就高高舉左手,還沒有想好時,就舉右手,怎么樣?”在師生間的這種心靈默契中,小青堅定又自信地舉左手的次數越來越多。全國特級教師斯霞一次講“笑嘻嘻”這個詞,她讓學生看她臉上的表情。學生們見斯霞咧著嘴,咪著眼(顯得夸張、搞笑),都說老師的臉上笑嘻嘻的。可以認為,這些最優秀的教師正在將來自成人世界的自尊感、自貴感、尊嚴感自覺地降到最低、最低,以充分地暴露、表達出自己最深層精神能量中稚氣、率真,甚至脆弱的一面,去精細地辨別學生的聲音、眼神、動作和神態的細微差異,配之以聆聽、揚眉、點頭、深情的注視、期待的凝望,以求得一個與學生共同在場的、共同遭遇的、共同開拓的互動、靈動、觸動、序動、跳動的課堂情境,進而換得學生最深層精神能量的大膽迸發,同時使自己成為一個不像教師的“教師”。
蘇霍姆林斯基始終認為,任何使學生沒有感覺到教育的教師,肯定是最好的教師。因為一種“放松的警覺狀態”會油然誕生在學生的心靈中,推動著他們生出一種社會主體間交往的美感來,這種美感會極大地激勵他們相信自己內在需要的真理性。于是敢于對自己負起責任,敢于與眾不同,敢于表現真實的自己,敢于欣賞自己的所作所為,敢于最充分地、生動地體驗社會生活的每個時刻。也就在這時,他們成了自己最好的教育者,從此,“學生式的教師教出了教師式的學生”,教師外部教育行為的終結點,成了學生自我教育行為的起始點,這是教學藝術最可貴的體現。這個起始點最顯著的表征就是,每個學生都是一個充滿了問題欲的“問題庫”,其中的問題就像是陶行知的八位好朋友,它們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時、何如、何地、何去,還有一個西洋派,姓名顛倒叫幾何。”
三、社會化成長中的自我教育
法布爾曾做過一個試驗,將一些蜜蜂和蒼蠅放入瓶中,瓶底朝向有陽光的窗戶,瓶口朝向屋子較黑的地方,一會兒發現所有蜜蜂都朝著有陽光的瓶底沖去,連綿不絕,矢志不渝,直到最后全部累死,沒有一只知道轉一個方向就安全脫險。而蒼蠅剛開始向有陽光的窗戶沖了幾次之后,馬上轉身向較黑的瓶口沖去。社會生活遠比學校科學知識描述的復雜得多,科學知識只是給學生了一些普遍性的準備,更多地需要學生面對各種最具體的社會情境,自己迸發出“蒼蠅式的智慧與勇氣”——冒險、即興發揮、迂回前進、混亂、隨機應變、非理性直覺、生命化體悟及邊緣化旁門左道等等,這些屬于學生的“個人知識”可以說是他們社會化真正的主導力。但是孫維剛不贊同“蒼蠅式的個人智慧”。他的學生是社區、學校圖書館以至區教育局最受歡迎的學生,因為請他的學生來幫忙勞動,干活干到了精細的程度,認真負責到了讓人感動的程度。在他的教室里赫然掛著“誠實,正派,正直;樹立遠大理想,為人民多作貢獻;做有豐富感情的人,是因為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使別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一系列條幅,更甚者,他規定了:不許留長頭發,不許穿皮鞋,不許唱庸俗的流行歌曲,男女生不許輕浮地說笑,不開生日晚會,不寄賀年卡等這樣一系列“恍若隔世”的班規。沒有一個學生有異議,相反全部主動、自律、自覺、自愿地遵守,任何一個新來者不用一天就會自主地融入到這些班規里。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的孫老師也是認真地這么做的。
“蒼蠅式的個人智慧”離開了生命最底層厚重的“利他”力量,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可能是危險的,這正是孫維剛憂慮之所在。他說:“外面的風氣我管不了,我能管的就是我自己和每天觸及的那片小天地。”正是融入著最深層的體驗、激情、靈性,投入到這片小天地的“去存在”、“去生成”的自然顯現、自我澄明、自身彰現的過程,凝結出了教師一系列教育教學最本真的理解——非判斷性理解、發展性理解、分析性理解及形成性理解。也正是這些理解一步步地喚起、推動、養成、構建、鑄造出了學生未來發展中,適應、完善、改革、超越社會的種種類型各異的自我教育系統,使他們在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民族恒久瞬息的長河中,獲得了自身生涯發展最節省能源的方法,那就是用自己心靈深處的能源,來照亮自己的精神世界。
有研究者認為,本次新課程改革已經走向了“泛人本化”,不是在釋放張揚學生的個性,而是在遷就放縱他們的劣性。筆者很不贊同這種看法,這不啻是教育者對過去以“他”為中心的單一、刻板、權威教育生活留戀心態的折射,學生的“無忌”、“坦言”、“鋒芒”甚至“放肆”,無疑開始深深觸及教育者多少年來固結下來的“教師尊嚴”。應該說,在當代面對這種“觸及”,教師所能做就是迎頭趕上,靜下心來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進行沉思、自思、反思,像劉可欽、孫維剛們那樣對多少年來固結下來的“自我系統”,進行大縱深的重組、破立、陣痛、致思、顛覆甚至革命,于是成百上千個劉可欽、孫維剛就會涌現出來,進而教育的本質“讓學”就會變得像外科手術一樣精細、精致、精妙絕倫,自然而然,新課程改革也就瓜熟蒂落。
參考文獻
[1] 教育部師范教育司.劉可欽與主體教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2] [加拿大]馬克斯·范梅.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李樹英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
[3] 胡東方.教育新思維.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4] 容中逵,劉要悟.論新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價值取向問題.現代教育論叢,2004(5).
(責任編輯關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