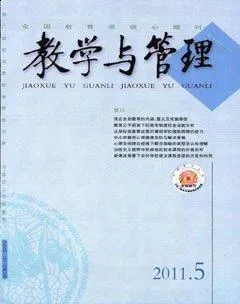研究性學習的歷史解讀
研究性學習是新課程的難點和亮點,也是小學綜合實踐課的核心問題。如果解決好研究性學習的問題,小學綜合實踐課的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研究性學習作為一種學習方式,是指學生圍繞一定的問題、文本或材料,在教師的幫助和支持下,自主尋求或自主建構答案意義,理解信息的活動、過程。
這個舶來品與我們習慣的接受性學習有很大的區別。所以在課改實踐中,有些人僅從技術操作層面來理解它,過于注重形式,將其視為具有普適意義的教育經驗直接照搬。以為上課時前后桌幾個學生討論幾分鐘就是合作學習;掂一掂物品的重量就是親身體驗;表演課文內容就是自主探究;讓學生走出教室就是創新實踐,等等。這樣理解研究性學習是因為有一個“文化適應”問題。這些真實的事例說明,了解并實踐研究性學習不能停留在“手段方法”的表面,而要深入到內部,從歷史的角度來認識它。
之所以有“文化適應”問題,是由于我們的文化傳統更傾向于接受性學習。經驗為知識,古書是經典,教科書中貫穿的是這個社會主流話語,否則不是被焚便是被黑出。教師把現成的結論“告訴”學生,學生記住、背誦即可。“天不變,道亦不變。”不用研究,無須創新。而研究性學習的文化背景和我們是有差異的。因為不同的民族在千年歷史的演進中必定會形成比較穩固的意識,思維程序和文化承諾,這些是學習方式形成的根據。中國位于東亞,大部分地區處在北溫帶,如此的生存位置使之成為世界農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農業生產有條不紊的季節規律性造就了農耕文明:生活雖然艱苦,卻有穩定的保證,因此民眾固守土地,囿于傳統,沒有變異,無須創新,求穩、求靜成為傳統的心理趨勢。這種生產方式下形成的哲學思想更是認為靜止是世界的根本,主張清凈無為,崇尚天人合一,物我相混。《尚書·大禹謨》中就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觀點。在這一思想中,似乎把所有經驗都安排妥當,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大系統中得以解決,不要求思維去做超越經驗的反思,也不用去探求事物的本質(漢語從來不曾創造出“本質”這個詞匯)。它更多地強調人與自然對立中的滲透與協調,而不是排斥與沖突,在自覺不自覺中賦予自然、宇宙帶有情感性的肯定——人們對天地產生親近、感恩和敬重,不是畏懼和抗爭。所以有人說中國哲學的特點不在其知識論,而在其價值論。西方文化兩大源頭之一的古希臘、羅馬(另一源頭是基督教文化)文化的生存之地,海上交通發達,促進了商業文明發展和人口的遷徙流動。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中,希臘人更關注對世界本質的探究和理解,因為他們必須認識自然才能改造甚至征服自然。其文化系統是從對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解釋開始的,求“真”的要求高于求“善”。所以西方哲學是愛智,中國哲學是聞道。智由探求而來,道是聆聽而得。“朝聞道,夕死足矣”是孔子的理想。
同樣,由哲學思想衍生出的思維方式,中西方也有不同。李澤厚先生曾清楚地指出:“中國古代哲學范疇(陰陽、五行、氣、道、神、理、心)無論是唯物論或唯心論,其特點大都是功能性的概念,而非實體性的概念。中國哲學重視的是事物的性質、功能、作用和關系,而不是事物構成的元素和實體。對物質世界的實體興趣遠遜于事物對人間生活關系的興趣。”其思維特點有直覺、倫理化傾向,大多通過“意會”來交流,連圖畫也講究寫意。表述概念多用比喻且很模糊——時間用“一頓飯功夫”,速度用“風馳電掣”,程度用“些微”等等。即便是科技文獻,大多是生產經驗的直接記載或對自然現象的描述,缺少準確的根據、原理和精密的論證分析。注重對認識對象直覺體悟和整體把握的思維方式非常講究務實(這大概源于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農業生產方式),器用之學相當發展。早于歐洲許多年就發明了灌溉系統、印刷、瓷器、指南針、水闡、測震儀等,卻沒有形成科學體系。更多的是各種“術”——醫術、技術、巫術、學術、美術、戰術、心術、權術、武術、數術……不重視似乎是無用的原理思考。重德輕智,重心輕物。如果有研究,也是研究事物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和自然的關系。以為天人合一,如此宏大的領域實在太復雜了,只能靠直覺獲得其合理性,只是追求那些極為具體的感覺印象。以簡單的觀察代替精密的實驗(如中醫的望、聞、問、切),以散漫的幻想代替嚴謹的推理。只是觀察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愿明其就理——我們崇尚生成法,道生一,一生二,宇宙萬物都是天然生成的,沒有揭示規律的必要。這種大而化之的思維方式,一元化整體思考的習慣,是籠統粗疏的,它重人生經驗、直觀感悟和綜合性的融會貫通。而古希臘境內由于山脈成分大,便于狩獵、放牧和貿易。相對而言更自我,不像農業生產那樣集群化,于是更關注物體本身而不是人際關系。當地居民經常遇到從世界各地與他們完全不同的人,不但能帶來許多他們未知的新鮮事和物,而且還要學會處理各種矛盾,由此促進了認知的發展。他們還經常召開市民集會討論公務,使得人們要憑借理性分析和嚴密的推理說服對方。蘇格拉底日常生活只做兩件事:沉思及與人辯論;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學生們邊散步邊討論,邊爭辯。他們一直保持一種對外界事物的好奇,對自由探索知識的熱情。其思維特點是注重構成法,對歸類有極強的興趣。有人做過一個試驗,把畫有猴子、牛羊和香蕉、干草的圖畫分別交給中美兩國兒童,請他們歸類。結果中國孩子把猴子和香蕉歸在一起——因為猴子吃香蕉,關注的是事物之間的關系。美國兒童把猴子和牛羊放在一處——因為他們關注的是它們都是動物。這大致反映了中西方思維的區別。其實確定屬性是物體分類的基礎,而歸類又是規律形成的前提。不僅如此,觀察和精確描述的結合使重復驗證成為可能,而且發展為有目的的實驗,使人們發現了更多的我們憑感覺經驗得不到的新事物,糾正我們曾經確信不疑的“真理”。如望遠鏡讓我們看到遙遠的天空是一些物質體而不是自古以來所相信的純精神的東西。由此奠定了伽利略——牛頓的天地共同遵守著同樣定律的力學體系。所以,西人既有提出問題的想象力,又有解決問題的求證能力,此傳統延續至今,自然就形成了在教學活動中研究性學習方式。
中西方社會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環境也對研究性學習有不同的影響。中國文化一開始就關注精神和人文領域。黃河流域良好的農業生產條件使得人們不用探究世界的本質問題就可以獲得生存資料,所以所有活動均以事功原則為最終根據。儒家思想的中心不在于發現真理而在于探索生存之道。玩味的是養花、蒔草、賞雪、聽雨、觀云、望月、吟詩、作畫……孔子欣賞的是曾點的志向——一次輕松愉快、富有詩意的春游。最理想的價值取向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人文環境是老者為尊,權威為重,經驗為上。諸葛亮出山時僅二十幾歲,但在舞臺上、繪畫中卻均帶有象征智慧、成熟和穩重威嚴的胡須。知識、真理來自年齡和權力的勢差,表現在教學中便是教師是知識的化身。所有問題都有既定的、標準的、統一的答案,不可懷疑,不用研究,學生從老師那里接受過來即可。連孔子都是“述而不作”。甚為極端的一例,有個小學生問老師做組合算式時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減時,老師喝道,這有什么好問的,國務院就是這么規定的。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是尋求真理,理解世界,它通過儀器和實驗,解釋自然界的秘密。理想境界是“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循著經驗——實驗——理驗(筆者命名,意為數理式的檢驗)的軌跡探究著萬物發展的規律。這里不囿于經驗,因為所有經驗都指向過去;不迷信權威,權威會被打破,“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正是這樣的人文環境,在18世紀前后近百年中,接連出現了影響人類社會進程的標志性事件:1687年,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宇宙空間的新觀念;1709年,英國的達比發明焦碳煉鐵技術;1764年,英國人發明珍妮紡織機;1769年,瓦特發明蒸汽機;1776年,北美獨立宣言發表;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而此時的中國正收拾著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以上所述絕無揚西貶中之意,也不是比較孰優孰劣,只是就不同文化底蘊對研究性學習方式的影響做一說明。結論是顯而易見的,要在文化素養的層面上做研究性學習的實踐,而不僅僅是模仿。其實從“五四”運動起,我們就已經有了民主、科學自覺地交融、匯合,只不過后來的國難中斷了這個進程。現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文化的對接,適應有了更加有利的條件。我們應以開放的心態了解、學習西方文化,為研究性學習找到良好的起點。否則就有可能是東施效顰。北京海淀區的一所中學給學生布置了一次閱讀作業,給學生們列出一些中國古詩詞的詩句,讓學生查出這些詩詞出自哪首詩,作者以及作者的年代。以為這就是研究性學習。同樣是閱讀,美國某小學的作業是讓學生列出自己身邊的一些日常用品的名稱,查出它們的化學成分構成,并寫出一些基本的化學元素的名稱。至于選擇了什么,并不做統一要求,只要有理有據即可。結果為此項作業,學生們紛紛選擇自己好奇的東西,然后去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既有興趣,又讀了大量的文章書籍(見1164期《南方周末》)。另外,要重新定位師生關系,學生也是真理的發現者和裁判員。應鼓勵和支持學生挑戰權威,質疑結論。有位學生對教師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時,老師說,這是書上說的。學生答曰,我說的終究會寫到書上的。這,正是本文的期待。
參考文獻
[1] 任長松.探究式學習.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2]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書店,1992.
[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4] [美]理查德·尼斯貝特.思維的版圖.北京:中信出版社.
[5] [英]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任洪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