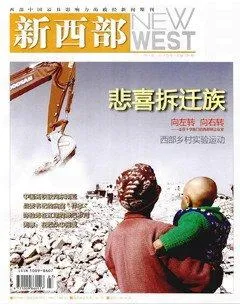陳獨秀在江津的最后歲月
江津,位于重慶西南長江之濱,因地處長江要津而得名。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輪在江津悄然靠岸。一塊接一塊的木條板上,顫悠悠地蠕動著一條長龍似的人流。人流中,一位滿臉疲憊的老者在一個年輕女子的攙扶下,緩緩地向前挪動著蹣跚的步子。
這位老者不是別人,正是一代風云人物陳獨秀。
此時的陳獨秀剛剛從國民黨監(jiān)獄釋放出來,又因抗戰(zhàn)爆發(fā)被迫出南京,奔武漢,過長沙,最后輾轉(zhuǎn)抵達重慶,落腳江津。
但是,當時沒有人會想到,江津竟會成為陳獨秀傳奇人生的最后一站。
流寓江津
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陳獨秀一直是閃耀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盞明燈,也是當時千千萬萬青年人心中崇拜的偶像。但是,因為右傾錯誤,他在擔任中國共產(chǎn)黨總書記6年后被撤銷職務(wù),隨后又被開除出黨。1932年,他又被國民黨逮捕入獄。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在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呼聲中,經(jīng)過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爭,蔣介石釋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包括已經(jīng)入獄5年的陳獨秀。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走出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住進了當年的北大學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機的轟炸,陳獨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學生陳鐘凡家里。但是,僅僅過了一個月,隨著國民政府一路西遷,陳獨秀又不得不踏上走走停停的逃亡之路。陪伴他的是小他30多歲的妻子潘蘭珍。
1938年7月,陳獨秀終于來到陪都重慶。
陳獨秀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再加上大半年的遷徙漂泊,讓他感到疲憊不堪。原以為到了重慶就能得到歇息,誰知山城高溫炎熱,日機頻繁空襲,而且還有多如蚊蠅的特務(wù),更讓他喘不過氣來。
就在陳獨秀不知所措的時候,卻意外收到同鄉(xiāng)好友鄧仲純從江津寄來的信。鄧仲純誠懇地邀請他去江津居住,并說“如果你及嫂夫人潘蘭珍愿來江津避難,我及家弟熱情歡迎,其住所和生活費用,均由我們兄弟二人承擔”。
在這樣一個進退兩難的時刻,有這么一個熱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啻于雪中送炭。
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陳獨秀抵達江津的情景。
鄧仲純等同鄉(xiāng)友人在碼頭接到陳獨秀夫婦后,便將他們安排到江津城關(guān)的黃荊街83號——鄧仲純開設(shè)的延年醫(yī)院居住。可是,鄧仲純的太太卻不同意,給了陳獨秀夫婦一個閉門羹。鄧仲純雖然十分尷尬,但他又是個懼內(nèi)的人.一時也沒有什么辦法。
此時的陳獨秀政治失意,夾在國共兩黨之間,又被誣陷為“日本間諜”、“漢奸”、“托匪”,處境艱難。鄧太太是將其當作“危險分子”避而遠之的。
另一種說法是,鄧太太是因為看不慣陳獨秀老夫少妻的做派才不愿接納的。
不管什么原因,初到江津遭遇被拒,確實讓陳獨秀感到狼狽不已。在給兒子陳松年的信中,他不無感慨地講述了這段遭遇:“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
幸好得到同鄉(xiāng)方孝遠一家的接待,陳獨秀才臨時住了下來。隨后,他們又搬到郭家公館,算是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
不過,這只是陳獨秀到江津后遭遇的第一個挫折。
1938年秋,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與其安徽同鄉(xiāng)決定把他們籌辦的國立九中設(shè)在江津。于是,陳松年帶著妻子和長女,陪同祖母謝氏來到了江津,與陳獨秀同住郭家公館。時至初冬,經(jīng)鄧仲純的再三懇求,鄧太太終于做出讓步,陳獨秀遂舉家移居延年醫(yī)院。
謝氏并非陳獨秀的生母。陳獨秀過繼給叔父陳衍庶后,謝氏就成為陳獨秀的嗣母。自1913年離開家鄉(xiāng)安慶,陳獨秀便投身革命,四處漂泊。謝氏用家族變故后所剩不多的財產(chǎn),養(yǎng)活著陳獨秀的發(fā)妻、4個子女及另外兩個侄孫,一家八口,艱難度日。
如今,分處天南地北幾十年的一家人在異鄉(xiāng)團聚,四世同堂,使晚年的陳獨秀上能侍奉母親,下能教導兒子,且有含飴弄孫之樂,加之老夫少妻伉儷情深,給陳獨秀寂寞的心田,注進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幸福的時刻總是那么短暫。1939年3月22日,在江津僅僅度過一個冬天的母親溘然長逝。陳獨秀俯身在母親的遺體前,失聲慟哭,老淚縱橫。
陳獨秀記得當年參加革命后,為了與舊官僚劃清界限,曾去宗祠辦理了“退繼”手續(xù)。當時,母親對著他驚惶地哭喊出一聲:“慶同啊(陳獨秀的家譜名),你不認爹娘了嗎?當皇帝的也要認啊!”
世事變遷,遠離黨政紛爭的陳獨秀重回平靜的生活,也有了給母親盡孝的時間,可母親卻這么快就離他而去,讓他怎能不傷心欲絕!
移居石墻院
陳獨秀母親逝世以后,兒子松年一家也搬到學校居住。屋子寬了,家務(wù)少了,陳獨秀便打算著手整理在獄中的文字學著述,并間或?qū)懶r事評論的文章。
但好景不長。1939年7月的一天,鄧太太一通指桑罵槐的刻薄話,讓潘蘭珍在臥室內(nèi)飲泣不已。陳獨秀一再追問,方知因鄧太太指責他們是“寄生蟲”之故。顯然,如此難堪的處境是無法呆下去了。經(jīng)過陳獨秀言辭懇切的堅決請求,鄧仲純只好答應(yīng)了陳獨秀的遷出。
鄧仲純通過時任九中校長的兄長鄧季宣和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關(guān)系,幫助陳獨秀搬遷到離城30里地的鶴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一中校長施懷清的居所。可是,那里孩子又太多,整日吵吵鬧鬧,讓陳獨秀不得清凈。不久,陳獨秀又遷到離施家大院兩里遠的石墻院——前清二甲進士楊魯承的舊居。
石墻院內(nèi)景致優(yōu)美,魚池假山,竹樹成蔭,院外視野開闊,阡陌縱橫,倒不失一處修心養(yǎng)身的佳地。惟一的不便是這里太偏僻,往返縣城一趟至少6個小時,不僅《江津日報》和重慶方面的報紙不能及時讀到,而且所有書信報刊,也要由鄧仲純?nèi)⑽迦丈踔烈恢芩蛠硪淮巍?br/> 陳獨秀的住所是石墻院的兩間偏房。盡管房主人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房子的條件還是非常有限,腳下的泥土地面既潮濕又不平,室內(nèi)僅有的一點兒用具也很破爛。不過,對于只想做做學問、寫寫東西的陳獨秀來說,這樣的條件已經(jīng)讓他很滿意了。
但是,偏僻的石墻院,卻無法割斷外界與陳獨秀的聯(lián)系。當?shù)厝穗m不知道這“陳先生”曾是中共最大的官,但看他穿長衫,戴眼鏡,說話斯文,又時常有乘船或坐轎的大人物來拜訪他,大家就猜想這不是個簡單的“陳先生”。
其實,陳獨秀出獄后,中國共產(chǎn)黨理論刊物《解放》就曾發(fā)表時評《陳獨秀到何處去》,歡迎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但是,王明、康生等人卻將陳獨秀誣為“日特漢奸”,并誣其拿人“津貼”。此舉令陳獨秀大為不滿,他曾于1938年3月17日致信《新華日報》,以公開信形式表明其心志立場。
蔣介石也曾派親信朱家驊來拉攏陳獨秀,希望他能組織一個與延安對著干的新共黨,除許諾給予10萬元活動經(jīng)費外,還給出5個“國民參政會”名額相誘。但在陳獨秀冷冷的笑聲中,朱家驊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被弄得下不了臺。
之后,蔣介石又托人請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他當即予以痛斥:“想拿我裝點門面,真是異想天開。”
蟄居江津后,陳獨秀已經(jīng)無意任何黨派,但上門游說者仍然不斷。當國民黨要員戴笠和胡宗南上門拜訪,陳獨秀便告訴他們,自己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不聞?wù)危辉腹_發(fā)表言論,引起喋喋不休之爭”。他還曾氣憤地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xiàn)在國共合作,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此后,陳獨秀又謝絕了胡適邀他去美國做傳記的盛情,還兩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請他去美國參加第四國際工作的“好意”……
周恩來等中共領(lǐng)導人也曾邀請陳獨秀去延安,也被他婉言謝絕。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中央里沒有可靠的人,“他們開會,我怎么辦呢?”
陳獨秀與中共的關(guān)系,至此畫上了句號。
白發(fā)老書生
陳獨秀晚年自稱“除卻文章無嗜好,依然白發(fā)老書生”。他在石墻院最大的樂趣,莫過于潛心于自己的文字學著述《小學識字課本》。
盛夏時節(jié),陳獨秀身上只穿短褲和背心,但渾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書桌邊用以揩汗的手巾總是濕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亂舞,陳獨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鋸木面與藥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煙霧繚繞中筆耕不輟。
隆冬之夜,書房里四面透風,潘蘭珍學著農(nóng)家的樣子,給陳獨秀弄一個外罩篾條、內(nèi)裝瓦缽木炭的“火籠”,讓他烘手烤腳。
當時雖然有不少朋友在經(jīng)濟上設(shè)法接濟陳獨秀,但這種接濟畢竟是有限的。為了節(jié)約開支,陳獨秀夫婦在石墻院親耕農(nóng)事,向農(nóng)人們學著種土豆。
一次,與陳獨秀相交頗深的老同盟會員、安徽老鄉(xiāng)朱蘊山提著幾只鴨子前來探望。當時,胃痛得在床上打滾的陳獨秀想起五代時流落蜀地的畫家貫休,聯(lián)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感慨萬千!他從床上硬撐著坐起身,將自己日前所作的詩謄抄給摯友。詩云:“貫休入蜀睢瓶缽,山中多病生死微,歲晚家家足豚鴨,老饞獨噬武榮碑。”
捧著陳獨秀的贈詩,朱蘊山似觸摸到老友窮且益堅的情懷。看到墻角邊那殘剩的幾顆干癟土豆,他禁不住喃喃自語:“可憐呵可憐,仲甫竟然沒有東西吃!”
曾參加辛亥革命并擔任過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與陳獨秀是同鄉(xiāng),也曾在一起共過事。1939年冬,他到重慶開會,便順路來探望陳獨秀。當他看到陳獨秀在大冬天里只穿著單薄的棉衣時,心中不禁泛起一陣酸楚,當即把身上的狐皮襖贈送給陳獨秀。可固執(zhí)的陳獨秀堅決不收。柏文蔚說:“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時便是生死與共的老朋友了!當年你年輕有為,不怕殺頭坐牢,豪氣沖天。現(xiàn)在你窮困到這個地步,作為老朋友送你一點東西難道也不行么?你再堅持,我就立即告辭!”見老朋友如此,陳獨秀只好收下。
但是,即使貧病交加,陳獨秀對于別人饋贈的錢物,也是十分有分寸地接受。國民黨政要羅家倫、傅斯年等出于尊師、同情與憐憫,親自送上錢物,他不收。朱家驊托張國燾轉(zhuǎn)寄來的5000元匯票,他原樣退還。周恩來、董必武知他生活艱難,送來一點錢,他也堅決不收,提出把這些錢用來營救獄中同志,照顧烈士遺孤。
為了《小學識字課本》的書名,陳獨秀跟時任國民黨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各持己見,僵持不下。陳立夫以為“小學”二字不妥,硬要陳獨秀更改書名后才準予出版。陳獨秀卻不同意,聲稱一個字也不能改。由于意見相左,陳獨秀便將國民政府教育部預支給他的兩萬元稿酬全部存入一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而朋友的接濟,陳獨秀雖以感激之心收納,內(nèi)心卻難免不安。據(jù)四川渠縣檔案館的資料,陳獨秀曾在晚年致信友人楊鵬升40封,這些信件多由“江津鶴山亭”寄出。最后一封信寫于1942年4月5日,信中表示,對楊鵬升多年的資助“內(nèi)心極度不安,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除此之外,“北大同學會”也每月定期資助陳獨秀300元,而且還委托羅漢具體照顧陳獨秀的生活。羅漢遇難后,該會又委托何之瑜繼續(xù)照顧。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陳獨秀的晚年生活將是不可想象的。
魂歸故鄉(xiāng)
光陰荏苒,冬去春來,陳獨秀在江津一晃呆到了第四個年頭。當時,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飛漲,已殃及所有百姓的生活,陳獨秀夫婦也時時處于饑餓的威脅之中。
陳獨秀身患多種疾病,但肚子都填不飽,哪還有多余的錢醫(yī)治病痛。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說胡豆花泡開水,可以治療高血壓,便想一試。孰料找來的胡豆花發(fā)霉變質(zhì),泡水飲用后中毒腹脹。次日,包惠僧來訪,陳獨秀作陪飲了小酒,過量食用四季豆燒肉,造成嘔吐不止,虛汗如浴。他立即叫回兒子陳松年。原準備外出的鄧仲純得到信息也立即取消行程,趕到石墻院日夜守護。
這一次,陳獨秀終于未能戰(zhàn)勝病魔。1942年5月27日晚9時,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在滿目凄涼中溘然辭世,享年64歲。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門外鼎山山麓鄧燮康家的塋地——康莊,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臨長江的墳冢。一代英豪,就這樣走完了他頗具爭議的一生。
陳獨秀逝世后,其遺作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后論文與書信》一書,靠朋友集資印刷。胡適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后對于民主政治的見解》,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并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jīng)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nèi)容”。
在陳獨秀的嫡親孫女陳長璞看來,祖父終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政治家。”她評價其祖父,“一生為信仰所驅(qū),不昧良知,不趨權(quán)貴。”
1947年6月,陳獨秀逝世5年之后,陳松年遵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江津原墓穴中遷出,雇木船沿江而下,運回故里安慶,與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安慶市北門外的十里鄉(xiāng)葉家沖。陳松年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陳獨秀”這個大名,而是用了他早年的名與字,“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如今看來,陳松年的這一做法,使父親的遺骸在此后幾十年躲過的豈是一劫!
1953年2月20日,毛澤東路過安慶,得知陳松年一家生活困難的情況后,對時任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后期他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他1937年出獄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爭取他參加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希望他發(fā)表個聲明承認錯誤,回到黨內(nèi)來,但他拒絕了。因此,對他這個人物要歷史地具體分析。對于他的家庭,地方上還是應(yīng)當予以照顧的。”從那時起,陳松年便得到了當?shù)亟y(tǒng)戰(zhàn)部門發(fā)放的每月30元的生活補貼。
改革開放后,陳獨秀墓園經(jīng)過數(shù)次修復,現(xiàn)已成為占地150畝的獨秀園,是“安徽省少先隊教育基地”和“安慶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陳獨秀當年在江津居住近3年的鶴山坪石墻院,如今也仍然完整地保存著。從江津市區(qū)到鶴山坪的交通已大大改善,一條盤山公路直達石墻院門前。革命先輩的舊居,清幽迷人的風景,外地人到江津,去鶴山坪憑吊和旅游,總是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