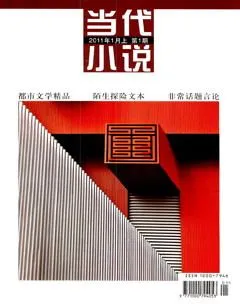弄堂風流
李家爸爸
兩條弄堂面街,窄窄長長。其實不長,只為窄,顯得長。弄堂里的大人,大多舊知識分子,都有一定背景。據說,上海四九年解放時,新政府不知該如何處理這批人,于是,統統收編進了同一大學。這兩條弄堂,其實也是這大學的宿舍。
除了夏天太熱,屋里實在呆不住,不得不出來乘片刻涼,平時,即使星期天,這些大人也是足不出門的。惟有例外的,是上下班時。那時的他們,開門出來,或由外面走進,總先探頭瞥上那么一瞥。這一瞥,只是道光,急促一閃,然后,快捷收回目光,俯首,縮起肩膀,腳步格外匆匆,弄堂里這段不得不經過的路,越快走完越好。
李家爸爸不同,進出弄堂,腳步也匆匆,卻跨得大,身板挺直,頭不下俯,黑得發亮的目光筆直視向前去。這目光,其實根本不看任何人,只是視前而已。
弄堂里誰都知道,李家爸爸進這家大學,是由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介紹,并用轎車親自陪送去的。大家都知道,李家爸爸當年,曾經當過孫中山秘書。
李家爸爸有個年輕的太太,小他一二十幾歲。其實也不年輕了,只是看上去年輕。她,白白的皮膚,清清瘦瘦,干干凈凈。細細的眉毛,細細的眼睛,細細的皺,偶然有的笑,也是細細的,細細的目光從細細的眼縫里甩出,眉頭稍稍皺一皺,被她看過的人,也就成了細細的了。這目光,那年代不少,只是,李家媽媽的相對顯明些。
李家有五個子女,三女二兒。三個女兒畢業于清華、北大、同濟,大兒在復旦,是數學系高材生。都是響當當的名牌大學,都是人材。惟小兒子,出生晚了,過了“好”年頭,只上了中專。按說,小兒子總是最受寵的,可李家爸爸最不寵的就是這個小兒子。
李家爸爸最喜歡的是大兒子。他的喜歡,因少有表情配合,看是看不出的,主要體現在對大兒的培養上。弄堂里的人,每到夜晚,習慣聽到小提琴的弦音,從他家傳出,在窄窄的弄堂里回來蕩去,撞到墻上,撞到玻璃窗上,然后,從各家各戶的門縫里滲入。琴聲時而悠揚委婉,時而急促亢奮,時而沉沉的,帶著人的心思一起旋轉、起伏、飄游,說不盡的纏綿。該說,精致委婉的傾訴,最能撥動人心中的那份溫情,那份美妙的柔意,卻那年頭,那樣的夜晚,聽來總讓人壓抑,雖說是享受,但卻是份重的享受。大兒子的提琴是李家爸爸親自教的。做父親的自己已不拉,只是教兒子。天熱,打開的窗口望進去,暗暗的底樓屋里,常見李家爸爸一旁站著,紋絲不動,看兒子拉琴,看得很專注。偶然,也見他動動嘴,動動指,指點一下,很偶然。他的動,不過動一動,不過吐兩個字。久久地,他就那樣手捏下巴,專注地聽,黑乎乎的目光一閃不閃地黑著,于虛無中遠了去。也只這樣的時刻,才讓人感到,這目光的盡頭,還無聲地活動著遙遠的記憶。大兒的琴拉得很出色,是復旦交響樂隊首席小提琴手。據說,上海交響樂團也曾邀請過他,但他沒去,想來還是名牌大學高材生更具魅力之故。
文革時,李家自然抄了家。抄家后的李家,原有的那份榮耀威嚴,不再那么榮耀威嚴了。其實,那份榮耀與威嚴,從四九年前遠遠拖來,已拖得很久很長,本也是衰弱了的。
李家大兒六五年大學畢業,七0年結婚。結婚時,老兩口讓出了光線最好的二樓,睡去了底層,小兒則搬去三層角。大兒媳是個護士。應該起碼是個醫生的。但那時,標準徹底變了,組合也都錯了位。兒媳出生較好。這“好”,已不是過去意義上的好。這樣的“好”,在過去,那是連進也進不到李家媽媽細細的目光中的。
婚后的大兒子,不再拉琴了。開始回家上樓,還常彎進底樓屋里,看看他的父母,卻最終,還是違不過媳婦的意愿。媳婦纖細的手指,在他袖管上輕輕一拉,輕輕一推,他的身體便失去了分量,即刻轉了向。天長日久,大兒子的腳步,走過底樓,也就沒了那份遲疑;天長日久,腳步一停不停地走上樓去,也成了大家習慣了的自然的事。
李家爸爸老了,那幾年,突然老了,老得非常快。天熱時,偶然,他也出來乘上片刻涼。弄堂里的人吃驚地發現,他的身體,已像只被曬過的蝦米,干干燥燥,萎縮不少,脊梁也彎了,像只弓,直直向前的目光,不再那么堅定、那么自信、自負,似也越發記不得曾經有過的氣派,開始游移,開始有了接觸其他目光的意愿。然而,沒人愿意接受這目光,沒人。大家根本不知,接受了,能和他說些什么。
李家爸爸臥床了,冬天、秋天、春天、甚至夏天,都臥躺在床。床邊茶幾上,大大小小、七歪八倒鋪滿了各種各樣藥瓶。底樓房里,沒有光線,黑洞洞的。上海的天氣又潮濕,總有那么多的水氣,地底、墻縫中滲出,帶一股陰、一股霉。一年四季,每到夜晚,人們總能聽到李家爸爸的咳嗽聲。這咳嗽聲十分蒼老、十分悲慘,碎了一般,翻動許多痰泡,每次都是響亮地開始,然后一點點微弱,直至沒聲,以為完了,可停一停,又更加急促、更加劇烈地開始。每次聽上去,都像是氣絕,那口氣斷了般,再也回不過來了……李家媽媽也突然老了,風濕性關節炎,腿不能走,心臟也不好,眼睛還得了不知什么病,老出水。那時候,照顧這對老夫婦倆的,就只有住在三層角里的不太喜歡的小兒子了。
小兒子在一家廠當科長,人緣很好,認識許多人。父親需什么藥,想吃什么,都由小兒子去買。父親進出醫院,也是小兒子去聯系,小兒子把他背上背下。李家爸爸退休工資算高,用什么錢,都他自己出。但他與小兒子很計較,找回的錢,一分一厘算清楚,時常還懷疑,懷疑小兒子貪污、報虛賬。人都躺在床上了,卻還捏緊錢,一張張數,數畢,深凹的眼抬起,惡狠狠地,皺癟的嘴,嘰里咕嚕不清不楚吐幾句。小兒子氣得幾次準備不再管他,可想怎么也是老子。已夠可憐,也就軟了心。李家爸爸有些積蓄,不多,但有些,全都塞在枕頭下。偶然,他的孫子——大兒子的兒子,去他房里轉一圈,他便直起身,用蚊蠅般的聲音,有氣無力喚過孫兒,被窩里抽出甘蔗渣似的手臂,指頭戳進枕頭,摸索一陣,扯出幾張錢,抖抖嗦嗦遞給孫兒,骷髏般的臉,跟著漾開老樹皮似的笑,很皺很皺,笑出僅剩的幾顆牙……
據說,李家爸爸曾給孫夫人寫過信,說他想寫一本孫中山先生的回憶錄。孫夫人辦公室倒是給了回信,謝謝他的好意,說已有人寫了。李家爸爸年青時喜歡寫詩,老了也寫一點,他讓他小兒子,找人幫他出了本詩集,他自己出的錢。都是些五言格律詩,還是用蠟紙、鋼筆刻的,油印機印的。沒幾個人看,看了,也沒幾個人懂。
李家爸爸的追悼會,出席的大多是小兒子的朋友,他自己早已與人沒了往來。幾個女兒在外地,趕不回家,就算趕得回,也覺意義不大。李家媽媽病身在床,腿不能走,眼老出水,自然去不了。大兒子是去了的,還有些傷感,掉了幾滴淚。大媳婦也去了,只不知是否因為悲傷,總繃著臉。小兒子胸前戴了朵白花,很忙,里里外外招待人……追悼會上,自然要念一念李家爸爸的生平。也就那一刻,大家才又重新想起他的不一般,想起曾經有過的輝煌,想起他讓人敬畏的不看人的目光。不過,這想起,也因遙遠,因時代顏色的關系,已是模模糊糊,遠不似當年那般影響人。
九十年代末回上海,我再進這條弄堂,去了李家。李家小兒子是我朋友,關系很好,以前老一起玩。弄堂似比記憶中窄很多,且舊不少,磚的墻壁也都剝落,像是又過了一個年代。黑洞洞的底樓屋里,李家小兒子與我聊了些往事,聊得我心思重重。他還放了音樂,仍是莫扎特、李斯特、貝多芬的。想起了他大哥,我問,他回說,一早已去美國。想起那兒時聽慣的靜悄悄的夜晚的優美凄婉的琴聲,問他大哥如今還拉不拉,他說他也不知道。似乎他們也沒多少往來。音樂聲中,打量一下四周墻壁,想觸摸些許記憶,卻不料,意外發覺,屋子盡處隔開一道墻,墻上有個小窗口,窗口中,一張皺得不能再皺的臉,眼已混濁不清了,正木愣愣看著我……李家小兒子對我說:“她在床上已躺了好多年了……”
胡老教授
五十年代胡老教授就已病休。那時他不老,不過五十八、九。
胡教授是在課堂講課時當場跌倒的,講著,一陣頭暈,眼一黑;失去了知覺。胡教授患高血壓已是多年的事,可那次醫生說,已到不能繼續講課的程度。
胡先生早年留學美國,讀的是會計學。想必曾是胸有抱負,埋頭小閣樓勤奮過一陣的。那年代,中國人的地位不怎么樣,在外難免受點歧視。有人說,自尊與自卑相輔相成,但胡先生身上卻只有自尊與自傲。在美時,一次路上,一洋人攔住他問:“你們中國人是否都吃老鼠。”胡先生當即拉大嗓門,手指人鼻:“我們從來不吃老鼠,只有你們才吃!”說完,輕蔑一瞥,放開嗓門,哈哈大笑,一聲一個音節,一聲響過一聲,而后,昂首闊步,燦燦爛爛揚長而去。這話雖談不上多少巧妙,可怎么說,也算以牙還牙了。胡先生有幾張美國時的留影,蕩秋千時照的,他身體魁梧,坐在秋千架上該說不怎么合,但照片上看,卻實在協調得很。他笑得開懷自如,旁若無人,身體、手腳放得開,瀟灑非常,完全不把身后過來往去的美國佬放在眼里。胡先生回國后成了胡教授,很吃香,名牌大學都來請他,門庭興旺,車水馬龍,其輝煌,想來沒多少人生能趕及。
胡教授開始退休幾年,常有學生、同事、領導來看他,過后稀少了,除每月一次,支部書記前來送上工資,順便坐他家沙發上,抽幾支配給教授的高級香煙,其他就沒什么人記得他了。開始,弄堂里的人走過他家門口,都會徒生幾分敬崇,久了,“胡老教授”也就僅僅成了個稱呼。
他有七個子女,都在外地,上海就他和太太倆。六零年一天,太太突然去世,他抱住太太,悲傷得哭出聲來。后來,他在家供了張太太的照片,放得很大,還叫照相館染了色,上面掛了黑帶,兩旁寫有一副他的親筆對聯:“老伴已去,我將何為?”很多年過去了,照片、黑帶與對聯還那樣供著。
據說老教授年輕時很驕橫,脾氣大極,滿滿一桌的菜,稍有不滿,他能暴怒大吼,掀翻整張桌子,嚇得他太太趕緊再燒一桌……為此,他后悔不已,常以此自責,怪太太在世時沒好好待她……
胡老教授家朝弄堂的門原先是用釘子釘死的,不開,不知哪年起,開了,且常開。每次經過他家,敞開的大門右側,總能見他坐寫字桌前的大半側面。每天,一張“解放日報”來,他匆匆翻閱一遍后,鋪在桌上,拿過一邊的紙牌,拆開,“噼噼啪啪”洗幾邊,便用那牌在報紙上接起龍來。“接龍”是種一人玩的游戲,接通接不通,都能無止境地一次次再接過。于是,老教授接得很少有停。接通該是很開心,卻他臉上從不見開心。“接龍”那刻,他是最無表情的一刻。
我小時候“康樂球”打得好,是附近一帶有名的“球王”。胡老教授知道后,哈哈大笑,說:“你是球王?哼,我才是球王!”我那個年紀怎么也不會“買他的賬”,說:比。他說:比。我家有康樂球盤,他家也有。我說:用我家的球盤。他說:看看,怕了吧,只敢用你家的。我說:好,就用你家的。于是,一老一小“怒目相視”地比起來。他畢竟老了,打不過我。于是便發急,急,就“賴”。他賴的方法是說我賴。我當然不懂該給他個“臺階”下,倆人便暴著青筋“吵”。吵久了,我說:“重比,算我讓你。”重比后我還是贏。老教授的趾高氣揚受到沉重打擊,臉憋彤紅,球棒一扔:“不打了。”跟著再補一句:“賴皮”。我便也球棒一扔,道:“打不過人家就賴,這么大年紀了!”說完忿忿離去。
老教授有這點好,下次再見,與我又是朋友,人前也坦言:“他打得好,我打不過他”。但即便如此,只要偶然他贏一盤,馬上不得了,“我贏了,我贏了,我是球王,我是球王”地大聲叫,跟著,又是“哈哈哈哈”洪亮得震得壞玻璃窗的笑,像是存心要氣死我。
老教授英文很好,尤其那時代,好的程度就顯更高。弄堂里有個張家爸爸,原國民黨中將的兒子,因打成右派,從原大學調去一家中專打雜。打了幾年雜后,忽又被任命當起英語教師。張家爸爸原先學的是經濟,英語不怎么樣,于是常去胡老教授處求教。也就這時,老教授的風度看得見一些了。對求學的,他一概慷慨無償幫助。然而,老教授留美的時代是不講語法的時代,他知道該這么用,卻不知為什么這么用。“右派”張爸爸偏偏執迷不悟,老釘住“為什么”問。被問急了,老教授大聲責問道:“中國人講話需要語法嗎?!”……老教授口語極好,輪到對話,次次打斷張家爸爸,糾正他發音,糾正他用詞,糾正多了,又不耐煩了,嘆口大氣,出口傷人道:“你這種英文怎么好去教學生?”——出口傷人,在他老年,算是做人做得最痛快的時候了。
老教授七個孩子中最喜歡的是“小七子”。小七子最小,也最聰明,口才也最好。其他孩子都怕爸爸,就小七子不怕。小七子的不怕,也就爸爸一發火,二聲“爹爹”叫,幾句好話一說,爹爹也就火氣全消。六十年代初,小七子到了娶媳婦時。小七子是不怕找不到媳婦的,只是他在東北一家大學教書,不想在那成家。
那年回滬探親,小七子認識了二醫大的畢業生,叫金蓮娜,名字就很洋派,長得白里透紅,如花似玉。金蓮娜是大資本家千金,上海的金家是有點名氣的。名門閨秀終是名門閨秀,那種高貴、矜持、與人保持的距離,換個人是學都學不像的。金蓮娜二次見過小七子后便喜歡得不得了,聲言即使跟他去東北也不動搖。這愛情,怎么也是感人的,卻那熱情,又有點不像名門閨秀。難說她喜歡小七子,與他有個教授爸爸有無關系——這種心理微妙得很,層次越高的人表現越微妙。
蓮娜的父母是在一家高級飯店與胡老教授見面的。那天,胡老教授乘了輛三輪車去,一向隨便的他,礙于兒子面子,穿了件呢制二用裝,魁梧的他,再提一根斯的克,氣派大得很。金老先生帶著十二分敬意,提前候在店門口。見到那刻,敬意又添三分,老教授的腿剛跨下三輪車,金先生便迎上前,笑容可掬,頭,格外文雅地點著,雙手齊伸過去,握住老教授,“您好,您好”連聲,“胡教授”更被當作名字叫起來。金先生年紀不大,五十多,保養很好,皮膚滋潤,手軟乎乎,又肉又暖。該說也是受慣仰慕的,但面對胡教授,卻一味謙卑,想要顯出些教養來。飯桌上,金家夫婦一次次提到美國,可老教授偏偏不接口。其實,退休后的這些年,只要有機會,他還是愿意提提美國,提提當年被名牌大學請來請去的事的,可對未來親家,他一點說的愿望都沒。
蓮娜來到胡家,使得我們這條安安靜靜的弄堂興奮了好一陣。一扇扇關起的門中,大人們都在議論:看看到底是有錢人家小姐,這種打扮,看就高檔;多好的皮膚,又白又亮;看看人家,說起話來輕聲輕氣,嘴巴抿住……知識分子的太太們,看資本家千金,又能看出許多味道。
蓮娜知道自己在眾人眼中的形象,也因此更想保持這形象。進出家門,腳步輕點,胸部微挺,目光垂地,不看人,偶然見了,淡淡一笑,若即若離,很有分寸。
有次去胡家,她剛買回一包熏青豆,說味道好極了,叫我張開嘴,讓我嘗嘗。她用食指與拇指捏上一粒,蘭花指翹很高,抿嘴笑遞過來,遞到唇邊,手指一松,一放抿嘴又一笑……熏青豆,讓人嘗一粒,感覺實在有點受辱,但當時,我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了她講究翹起的蘭花指上。
六六年的一天早晨,胡老教授的家門上出現一張白紙黑字的大字報。
老教授樓上原先有個鄉下女傭,后認了女主人為“媽”,又經媽作媒,嫁了位軍官,住在小閣樓里。因樓上樓下合用一廚房,想來受過點胡老教授的氣。文革開始后,軍屬的神氣可想象了,她穿起雙草綠色解放牌球鞋,也像軍人了,居委會里走進走出。大字報是請人寫的,她簽的名,罵胡老教授為“寄生蟲”、“吸血鬼”,說他“十多年無所事事,整日在家接龍,白拿社會主義工資”。
胡老先生血壓又升高了,面孔通紅,額敷冷毛巾,腳插盛有熱水的腳盆……
軍屬還不罷休,與他學校聯系,不能讓他逃過運動。于是來了抄家的。意外的是,抄不出什么。老教授家一張床,一張寫字臺,兩只沙發,幾把椅子,都是舊的,質地也很一般。書柜里,書也寥寥無幾,且都已發黃,落了厚厚的灰。想是該有些金銀財寶,結果也沒有,連存款都遠不及想象中多。沒人相信,便撬地板,撬了地板還是什么都沒,于是便把“寄生蟲”送去了“五七干校”。
胡老教授殘存的一點輝煌,那幾天,糊里糊涂就過去了。
老先生本就想得穿,這場運動后,想得就更穿了。他將補發工資看做“外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請幾個運動中幫過他的鄰居去飯店美餐一頓。“吃吧,吃吧,想吃什么自己點。”他揮著大手道。人家不好意思,他就自己動手點一大堆;人家還沒吃,他就自己帶頭先吃起來。胡家的門,從此也敞得更開了;凡有人去,男人,遞過罐頭香煙;女人,則拿出奶油話梅。吃過一根或一粒,他說再來。再來過了,又說自己再拿吧。有時,他與人聊一陣,開懷大笑幾聲;沒什么可聊了,也不客氣,繼續顧自“接龍”。他對自己,也越發不約束了,雞蛋、牛奶、特別是紅燒肉,該是不能多吃了,但他不管,照舊。
胡老教授與鄰居的往來越來越多,誰家有些什么事,他必解囊。隔壁劉家老先生去世,他送了個花圈,還叫了三輪車,前去參加追悼會。我插隊那陣,回滬探親,常去他家坐一陣。老先生對外面世界知道甚少,也不想知道。談起農村生活,幾句聽過,便擺手:“不要聽,不要聽,年紀大了,不想聽這些。”一次返鄉前,他敲開我家門,塞給我十元錢,說:“自己去買點東西吧。”說過轉身便走。我追上去,發現他的眼竟紅著,濕潤著。見我看他,他側過臉,寬大有勁的手,抓住我胳膊,使勁捏兩下,用力往后一甩。
老先生一點歸還的錢,沒過多久全用光了。每月工資,沒到月底,就已分文不剩。他不愁,活得很開心。實在沒錢時,會向他的鐘點女傭借。他家照樣傳出他中氣十足的笑聲。弄堂里的人,喜歡他,也越來越多地幫他,有上街的,都會問他一聲,要不要帶點東西,燒了好吃的,也總會端給他嘗嘗。那時候,胡老教授的稱呼已被大小鄰居一致改成了“胡家公公”。
那年寒天回上海,我帶了好些農產品,說要去看他,家人聽了,異口同聲勸我別去。我奇怪,問為何。家里人說,他兒媳不準他與任何人往來。他兒媳能管得住他?他會聽她?我感奇怪。
家里人說:“不同了,現在不同了……”
胡老教授從來看不慣他兒媳婦。“小氣”、“賊腔”、“虛心假意”,人前人后都這樣稱,并一概謂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作風”。文革開始,他與媳婦各管各,互不加照應。胃出血那次,也是鄰居送他上醫院,照顧他,幫他燒、買、洗。補發工資了,他沒太多想到兒媳。她生了孩子,吃住在家,老先生規定她,每月交十元生活費,其實只是意思意思,可媳婦的忍受已到極點。
“有這種人嗎?錢都用在別人身上,分不清自己人和人家人。”一場運動,蓮娜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該給人的距離感,大概也知輿論的重要,遇上人,她就這樣說。
一個月初,蓮娜去交那十元錢時,笑呼“爹爹”,鈔票拿在手,伸過去又縮回:“這錢,以后就算你給孫子買些東西吧?”老先生一聽,大聲道:“孫子歸孫子,該買什么我會買。這點錢,你都想不給?”說罷,仰靠椅背,放大聲,笑得十分鄙夷。笑得蓮娜惱羞成怒,面孔憋通紅:“恨死了,恨死了,真是恨死了……”聲音依舊輕細,卻咬牙切齒,提起那十元,一撕兩半,細尖的手指,點到公公的后腦勺:“老糊涂,老糊涂,你真是老糊涂了!”
“你你你,你竟敢打我。”胡老教授大叫起來。
里弄小組長來了,居民委員會也來人了。但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小七子從東北趕回,阿三、阿五、阿六也分別從北京、南京、無錫趕來。
“小七子總不能容忍他媳婦這樣對待他爹爹吧?”我說。
“別傻了,小七子還能幫他爸爸么?”
“那其他子女呢?”
“不還一樣。”
想不通,實在想不通。“他不是一直在子女中很有威信嗎?”
“八十歲的人了,還有什么威信;他的子女早已不是小孩。”
胡家的門還開,只是不常開;開也只開半扇,為的是透氣。
不知胡老先生后來的日子是怎么度過的。底樓房子,黑洞洞的,又潮濕。一個人不與任何人來往,沒人說話,沒人照顧,還有高血壓,雙腿又不靈便……
最后一次看見他,是傍晚,他正站開著的半扇門前,面朝外。他穿一套深色衣服,背后是沒光線的黑漆漆的屋。一片黑色中,臉成了白白一團。霎時間,許多記憶浮起,我叫了聲“胡家公公”,朝他走去。可他無動于衷,像在看我,又像沒在看。然后,呆板的目光,似有似無,隨著白白的臉一起,緩緩地呆板地移動,不知落在了哪;再后來,兩聲“踢橐”的腳掌拖地響,白白的臉退了回去,像一團漸去的光,消隱在一片漆黑中……
家里人說,胡家公公得了老年癡呆癥,已認不得人。
胡家公公去世那幾天,弄堂里特別靜。沒人被邀參加追悼會。我回滬知曉后,去龍華殯儀館祭拜了他。那時我很窮,只買了個簡單小花圈,放在他的骨灰盒上。欣慰的是,骨灰盒邊,我看見了劉家、李家,好幾家鄰居送的花籃,做得都很精致,還看到了右派張家爸爸的一只上好絲綢做的,兩條白帶上面寫著:哀悼胡老教授;學生張××。
司法部長
十八號這幢樓,先前住著教授一家,可沒過多久,搬去了十四號。許多年后,一個靜悄悄的夜晚,教授的兒子,大我十一歲的六四屆大學生,依然面帶懼色地說:“十八號有鬼。”有鬼?!我驟感一緊。教授的大兒子停了停,倒吸冷氣,壓低的聲音陰森不少:“這鬼是個清朝的官,總在黃昏將去未去時出現。我姐姐常這時樓下屋中練琴,多次聽到窸窸窣窣聲,以為是幻覺,偶然一次,一回頭,黑漆漆的樓梯上見走下個人來,戴一頂清朝官帽,夕光中,還看得到他官服上那個方形圖案……后來,我媽媽也見了這個鬼,一模一樣穿著,也出現這時辰。一次,這鬼還走到我媽身后,站著,聽她彈了好一陣琴……”
這故事完全符合十八號給我的印象,聽得我毛骨悚然。
十八號先后換過幾家人家,都沒住長,直至搬進楊守中一家,這幢樓才算安定下來。
楊守中,前某地司法部長,也有說是監察院院長。無法考證了。但大家一致清楚知道,他是殺害王孝和的兇手。
楊守中不高,矮矮,卻壯實;頭,大大圓圓;黑臉、黑胡、黑發、黑眼珠,尤其兩條眉毛,又黑又粗,眉角處還翹出兩簇半寸長的黑眉梢。他總繃一張臉,目不斜視,兇光畢露,拄一根斯的克,挺胸昂頭,步子跨很大。弄堂里的孩子,隔老遠,常沖他的背影叫:“反革命、殺人犯”,連本是反革命子女的也跟著叫。但只要他一回頭,兩條劍眉一緊,黑洞洞的眼珠里射出兩點刺亮的光,大大小小膽壯膽弱的孩子都會嚇得趕緊轉過身,有的甚至慘白著臉逃進弄堂。
楊守中家有兩扇門,一扇朝弄堂,一扇面街,他從來進出面街那扇。出門,這邊是住宅,多人;對面是火車線,少人,他從來走的是對馬路。出去,徑直過馬路,九十度轉彎;回來,行至對門,直角穿馬路去家。他家里,從不出一點聲,笑聲,說話聲都不出;也從不見朋友、親戚來往。他們也不想理任何人。也沒任何人敢理他們,一家老少六個人,像六個靈魂,生活在十八號這幢陰森森的樓里。
最老的靈魂是楊守中母親。她像只貓,老得在等死的貓。白色的皺皮,白色的眉毛,兩只眼睛是兩條拖得長長的線,往外蕩下;萎縮的身體,彎成一團;臉上沒表情,絲毫都沒有,完完全全像只已死去的老貓。
夏夜無風時,弄堂房子熱得難熬,人家都出來沿街路邊乘涼。楊守中有時會將母親放在藤椅上,連著椅子一起搬出。左右無人時,也會陪著坐一會兒;有人,搬出母親后,便折身進屋,喚太太出來陪。他太太坐一邊,便掌一把扇,替婆婆扇扇。婆媳倆也不說話,除了那把扇,一動不動,路燈下,像兩只影。可只要影子在,左右乘涼的,就算離得遠,都會感到她們的存在。
一天清晨,有人見一輛殯儀館的車從楊家面街門前開走。猜是楊守中母親死了,但無法證實。之后,楊家日日傳出一股香火味。有好奇的孩子,爬上屋頂,穿過厚厚的窗簾縫隙,望進他家去,見暗洞洞的屋里有香煙繚繞,見楊守中跪在地上,磕頭不止。
楊守中有兩兒一女。兩個兒子已工作,長得神氣,介書生樣。好一陣,弄堂里人奇怪地發現,倆人總是濕漉著頭發回家。后來有人說,游泳池老見他們,天天都見,他倆總是悶頭游泳,一游就是幾十圈。有人說,是身體不好,需要鍛煉。可這說法怎么都有點不通,于是更顯神秘。又一陣,兩個兒子忽然又都不見了。
—個冬日深夜,寒氣襲人,路上不見行人。弄堂小組長去敲楊家面街的門,身后跟兩便服男。門剛開,便服男搶先箭步竄入。不久,楊守中下來了,戴著手銬,被押進一輛飛駛而來的吉普車。據說,古普車黃昏時就在馬路對面不遠處停著。
楊守中被逮捕了。沒人知道為什么,又像無需知道,似乎是件早晚要發生的事。但弄堂里的孩子,還是神神秘秘地議論著,作各種猜想。消息終于傳來,不知有多少準確性,是小組長通過街道派出所那條線打聽來的:楊守中派他兩個兒子分別從廣東、海南偷渡去香港、臺灣,帶了兩封他的親筆信,裝在膠丸里。信是寫給蔣介石的,還有一份反攻大陸的具體計劃。但他失敗了,兩個兒子分別在邊境線上被捕。人人聽了噓吁不住,寒毛豎起。那個寒冬更寒了,寒得人不由縮頸扛肩,夾緊襖衣。等到大家緩過勁來,方才想起,楊家隔壁住一對神秘夫婦,不與人接近,沒人知道他們在哪工作。這對夫婦一定是公安局派來監視楊守中的,隔著墻壁一定裝有竊聽器……
楊家更靜了,只剩太太和女兒了。母女倆守住一幢陰森森的房,俯首垂目,無聲無息進出,臉上各添分剛毅,皺紋的更皺紋,光潔的更光潔。
六六年,狂風暴雨。一日,隔壁弄堂來幾個孩子,聚在我們弄堂,說他們附近一家花園洋房里,抄家抄出個地道,通很遠,里面藏有一沓沓的變天帳,還有刀劍等武器。有人問,有沒有槍支。回答不僅說有,更說還有發報機、手榴彈。人家聽呆了,驚慌中更覺黑洞洞的復辟陰謀。有人想到了楊家。那時弄堂里已有幾家被抄,楊家還未輪到,是因楊太太已退休,沒了專政單位。一位小將當即掏出袖章,臂上一套,揮手道:“走!抄家去!”一群孩子便跟著向楊家沖去,差不多踢開了門,蜂擁而入。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十八號這幢陰森森的樓。
家里不像想象中那么陰森,也沒什么貴重物品,原本質地不錯的床單、窗簾、被子,也已舊的舊,破的破。小孩們一個個忙著撕書,忙著將—張張唱片踩碎。一屋的亂糟糟。有人在扇楊守中太太耳光。她站著,一動不動,似乎耳光不是扇在她臉上。
抄家孩子走后,楊守中太太關門時,說了一句,她說:
“當年周總理還是我們救過的!”
一星期后,楊太太開煤氣自殺,但被女兒發現得早,沒死成。女兒跪在地,眼淚無聲地淌,求母親再別干這件事。母親合著眼“嗯”了聲,眼角處一滴濕。又過幾星期,一日清晨,女兒外出買菜回來,母親已吊死在門廊上,雙眼翻白,蕩下的舌頭,長長一條,已泛一層灰。女兒都沒哭,白著臉,找來把剪刀,扶起踢倒的凳,站上去,剪斷繩子,抱著母親一起摔下。等到好心腸的鄰居趕到,流著淚說:“你怎么這么大意,怎么不看住她。”女兒漠無表情,久了,答一句:“她想死,誰也看不住。”
楊守中的女兒不艷,但有冷峻的美,像母親。她原先是二醫大的高才生,五七年打成學生右派,去農村勞動教養,六四年才放回。母親死后,她一人守住一幢樓,獨進獨出,不與任何人往來。她也沒工作,不知靠什么生活。
不知又過多久,大概一年,大概二年,一日,楊家被封了,所有門窗都被貼上了公安局封條。楊家女兒不見了。面對那些縱橫交叉的白封條,人們不禁生出許多悲涼、許多恐慌。但漸漸地,卻又習慣了,似乎這幢樓天生就該貼上封條。
又是小組長那傳來消息,楊家女兒上交了房子,自愿去農村,嫁給一個鄉下人。嫁給鄉下人?大家都想不通了,連弄堂里的小孩都想不通,好像灰蒙蒙的天,氣壓很低,壓抑得很。后來,又有消息傳來,說她嫁的是一個勞改犯,是她早年勞動教養時在農場結識的。嫁給勞改犯,應該更慘,但人家卻都覺得可以理解了。
七十年代的一天,楊守中的女兒回來過,帶了個黑乎乎的男人,一副鄉下人樣,想必是她丈夫。她也黑了,頭添蒼發,也像鄉下人了。她原先很白,很像醫生。兩個黑乎乎的人,走到弄堂口,停了停,再走幾步,在她家面街的門前站住,朝窗里望了望,僅幾秒,顯然是怕人發現,即刻就又走了。她沒看見我。也許看見了,以為我認不出她;也許我長大了,她認不出了。望著倆人漸去漸遠的背影,直到望不見,想:她大概再不會回來了吧?
后來,十八號底層空了出來,東西堆去了樓上。二樓三樓依然上著封條。空出的底樓,搬進一戶新家,一位年輕的講師,和他年輕的太太。但不久,這位講師就瘋了,他說天天晚上聽到樓上有腳步聲和呼吸聲,像是有人在嘆息、在踱步……
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