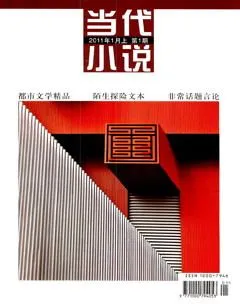償債
柳佳慧聽到一聲異常尖銳的剎車在村道上響起。
她不由得心跳加速,有點喘不過氣來。
她聽得出來,車是男人德貴的。
她在圍裙上揩揩手,慌慌張張跑出門。
刺耳的剎車聲,像用開水燙過的刀子,把村子像切皮蛋那樣切開了。馬上過年了,她特意買了德貴喜歡的皮蛋。那松花他總也看不夠,要她別切壞了它們。而她總把它們弄得一片模糊。后來她想了個辦法,用開水把刀口燙一下,就把皮蛋切得整齊漂亮了。但現在,發燙的刀子切錯了地方。村子頓時凝固下來。緊接著,有人大聲呼叫。
她預感到男人出事了。
自從男人開了車,她就常有這種不好的預感。她很害怕自己的預感。它一旦粘上來,就趕也趕不走。她頓腳。掐自己。捶自己的腦袋。都沒用。她越想越真切,最后她仿佛看到了事故現場一樣渾身發抖。她對自己說,你怎么這樣壞呢,你不是個好女人,總是想這些不好的事情。要等男人把車開進院子里,她才放下心來,給男人端上熱飯熱菜。她臉上笑著,心卻在不停地自責。
她說,你還是學門別的手藝吧,工業園那里,又開始招工了。
他說,你曉得他們為什么老是招工?就因為很多人不愿干了,工資太低。
她說,低就低一點。
他說,那幫外水佬,老欺負我們本地人,我才不去。
這一點,她當然也知道。那些廠,都是招商引資進來的,對本地人自然就歧視了,好工種、高工資本地人都沒份。即使本地人和外地人打架,公安局也幫著外地人。因為人家是老板嘛。他心高氣傲,肯定受不得這氣。這一帶村莊里的青壯年男人要么到外面打工去了,要么就是開車。只有那些沒闖勁的家伙才到廠里做事。
他早出晚歸,賺的錢都是自己的。他們很快蓋了一棟三層樓,修了院落,成了村里顯眼的人家。她又說,現在別開車了,要不,我們到村口開一家批發部吧?她看到鎮上有幾家批發部,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們村子在國道邊,開批發部肯定賺錢。他笑了,說,批發部?你以為那么容易啊,過幾年再說吧。
真的?
真的。
既然有了這么一個理想,她也就妥協下來了。
但他每次出車,她還是提心吊膽的。開車收入高,風險也高。辛苦更不用說。有時候車開到半路,壞了,哪怕是半夜哪怕是天上下刀子也走不了,還得鉆到車底下去鼓搗。她說讓我跟你去吧,半路上,你也有個伴。他說你現在的任務是要懷上孩子,別的不用管。不知怎么回事,他們結婚都三四年了,可她一直沒懷上孩子。有幾次,像是懷上了,但沒多久,身體又調整到了往常的軌道。她懷疑是自己太緊張的緣故。自從他開了車,她就常沒來由地緊張。男人半夜回來,要跟她親熱,她不讓,說你太累了。第二天一早,男人要跟她親熱,她又說,你要出車。
她后悔今天早上,就依了他。今天他不用跑遠路。畢竟馬上就過年了。今天他到幾個已經說好的客戶那里去拿錢。所以當她說你要出車的時候,他忽然變得執拗起來,他說我現在就出車。她一松勁,就沒擋住。但某種禁忌依然在事后鉗住了她。
所以那種不安全的感覺,今天特別強烈。每逢年節,她就更加緊張。好像它是一只快到手的鴿子,她怕一不小心,它就會撲啦啦飛走了。她一邊準備著過年的東西,一邊神不守舍地東張西望。從清早開始,天空就陰沉沉的,后來就下起了雪。
看到雪,她反而沉靜下來了。
男人曾跟她說過,天氣越惡劣,路面越難走,開車的人便越會小心的,你看,那些交通事故大多是在人沒有準備的時候發生的,對不對?她想了想,覺得有道理。幾時她擔心的事情變成了事實?說不定,她的擔心,可以暗中阻止那些壞事情的發生呢。這樣一想,她又有些高興起來了。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她有點等不及了。她盼著把這一天快點過完,好開始新的一年。她的心理負擔總是和季節的變化有著某種關系。真的,每開始新的一年,她都精神煥發的,不像大了(或者說是老了)一歲,反而像是年輕了一歲。因為她離自己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可就在這時,她聽到了災難的聲音。她遠遠看到他們家的車撞到了墻上。男人被村里人揪了出來,像個可憐蟲似的抱著腦袋。她心里安穩了些,但馬上意識到,可能更嚴重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事后想來,當時的情景就像一場惡夢。
男人喝了酒。他本來是不會喝酒的,但他在客戶那里拿到了錢,一時高興,就拉著對方到鎮上的酒館里喝了幾杯。后來她一直懷疑男人是早上累了,肚子里空。這個原因,男人當然不會講出來。啊,她真該死!男人把車開回村子里,車子忽然失去了控制,朝幾個正在踢毽子的小女孩沖了過去,國權的女兒小青當場就給軋死了。
就這樣,臘月廿九成了他們的末日。
男人被警察帶走了。什么都不用說。該坐牢就坐牢,該賠錢就賠錢。事情既然已經發生,她反而鎮靜下來。她暗暗吃驚了,心想這是怎么回事呢,難道她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好像一個人擔心天塌下來,等真的天塌下來了,他反而呼呼大睡?她狠狠給了男人一巴掌。那一刻,她恨他。把一切都毀了。但過后又后悔。她怎么能把責任都推到他身上去呢?所以她也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當然這是在家里,沒有別人看到。男人是在拘留所里過的年。她把該送的東西都送進去了,說,世上沒有后悔藥吃,所以你也不用后悔,外面的事我會盡量處理好。
就這樣,眼看著舊年就要過去,眼看著他們的船快要靠岸,可忽然一股猛力躥出來把她一推,重新把她推到了靠不著岸的地方。她一個人用力撐著竹篙。這時別人都是她羨慕的對象,除了國權家里人。國權只有小青這么一個獨生女兒。她到他們家去的時候,國權和他老婆蓮芝已經哭得沒有聲音,只有肩膀在抖。交警都已經處理過了,他們也不能把小青留在家里。他們剛從小青墳上回來。現在,小青在條臺上的相框里望著她。她不禁也哭了起來。其實兩家以前關系一直很好。有什么好吃的,互相通個有無。小青也經常到她家里來玩,嬸嬸嬸嬸叫得很親熱。她把條臺上的小青貼在自己胸口上,說,小青啊,嬸嬸我對不住你!下輩子我變牛變馬還你。小青好像在說,嬸嬸,你不知道,德貴叔叔在那一刻好可怕,像一頭發瘋的牛一樣瞪著又大又紅的眼睛。小青跟她說話時,總是仰著臉,像一朵向日葵。現在,成了冰冷的黑白。
她說,國權哥,蓮芝姐,馬上過年了,你們還是想開一點,有什么辦法呢,唉,我也不曉得說什么好了。
他們呆呆地望著她,好像不明白她在說什么。
她說,我曉得,你們恨我,恨德貴,如果我是你們,我也是一樣的,真的,如果我是你們,我心里還好受些。
他們嘴唇動了動。
她說,我對不住你們,現在,你們要對我說什么,盡管說,哪怕是罵我打我。雖然不管我怎么說怎么做,也救不回小青的命,但我要盡自己的力量彌補你們,這樣,小青在天上也會好受一些。
他們把頭轉過去,不理她。不過這也很正常,難道還要他們把她當親人當救星一樣看待么?她都死有余辜了。
她結結巴巴的,也不知道再說些什么好。安慰別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候讓別人也讓自己很尷尬,何況現在還跟自己有關,何止有關,她簡直就是罪魁禍首,她就更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們了。她和德貴是初中同學,在村子里也算是讀了一點書的人了,按道理,遇到這樣的事會表現得更好,可有一次,她在路上碰到了以前的一個老師,聽說他女兒在爆竹廠被炸死了,看到老師,她一下子不知道說什么好。因為她覺得自己的話一點力量都沒有,怕人家說她說假話。再說,事情剛過去不久,如果老師在盡力忘記這件事,那她不又把它提起來了嗎?可裝作不知道肯定也說不過去。結果,她只是對老師笑笑。等老師走過去了,她才大吃一驚,她怎么對老師笑呢?老師大概在想,他女兒被炸死了,她居然還對他笑!這件事讓她內心折磨了好久。她剛嫁給德貴那年,她爺爺死了。爺爺活了九十多歲,后來簡直是在活受罪,所以爺爺死了并不是什么壞事,但她做孫女的,總不能對爺爺的死興高采烈吧?在奔喪的路上,她一直很著急自己哭不出來。結果,當著那么多親戚和村里人的面,她真的沒哭出來。這件事又折磨了她好久。
記起晚上就是除夕夜,她腦子轉了一下,忽然知道該干什么了。她開始自作主張地忙活起來。她先把堂前打掃了一下。出了這么大的事,臟亂是不用說的。畢竟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不打掃怎么行呢?在彎腰做事時,她忽然意識到自己慢慢平靜下來,不那么尷尬了。她真的愿意當牛做馬,只要國權和蓮芝能重新高興起來。和國權他們相比,德貴不在家里過年算什么呢。哪怕是坐牢,也終究會被放出來。不管怎么說,她是不會再讓他開車了。她已經決定好,等把賠償的事情處理好,她就干脆和德貴出去打工。可他們欠國權家的心債,恐怕永遠也還不上。她開始給國權家做年夜飯。不管發生了什么事,年還是要過的,而且要過好。沒過好對第二年都有影響。她打了兩桶井水,把鍋碗都洗干凈了。她沒系圍裙,身上很快弄臟了。不過這樣也很好。她又燒了一壺熱水,用來發干菜。要用點燒酒,她到條臺上找,發現在小青的相框旁邊。她遲疑了一下,還是伸出了手,誰知身后忽然響起一身怒喝:你給我放下!她有些吃驚地回過頭來,見國權的臉比剛才更黑了。
蓮芝也說話了。她抬起頭,說,求求你,你走吧。
她已經差不多兩天沒聽到蓮芝說話了。還好,她聽得出來還是蓮芝的聲音。她有些驚喜地上前兩步,抓住蓮芝的手,說,蓮芝姐,我跟你們一塊兒過年吧,我當不了你們的女兒,就給你們當妹子吧,你以前不就把我當妹子嗎?
蓮芝說,現在說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她說,有,怎么沒有呢,我愿意給你們當牛做馬,來還欠下你們的債。
國權吼道:你滾吧,我們不稀罕!
她看到,蓮芝也用力剜了她一眼。于是她抹了把臉,從他們家跑出去了。
這個年,她是一個人過的。她還從未一個人過過年。別人家越是放爆竹,自己家越是冷清。
下午,從蓮芝家出來,她又去了縣里。本來不想去,但畢竟明天就過年了,今天是一個分水嶺。她還有希望,希望壞運氣快快過去,好迎接好運。一些商店已經在準備關門了。她擠了進去,給德貴買了條煙。德貴怎么離得了煙呢,現在更離不了。果然,他見了煙就撲了過來。才一天沒見,他像老了十歲,頭發是亂的,眼睛是紅的,臉又黑又青。他三兩口抽完一支煙(看樣子,恨不得把整根煙直接往肚子里吞),又抹起了眼睛。倒是她顯得鎮定。她說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你想得再多也無用,等你出來,我們一切從頭開始吧。待了一會兒,她就出來了。這時街上的行人少了,車輛也少了,到了車站,最后一輛客車已經開動了,她追了一陣,沒追上。那基本上是一輛空車。是啊,要回家的,都早已回家了。想想,她自己什么時候在大年三十這個時候還在外面?還好,她招停了一輛摩的。價格比平時貴十倍。她毫不猶豫地坐了上去。她對自己的奢侈暗暗吃驚。其實再等等,說不定還是有便宜車坐的。
回到村子里,許多人家已經在貼門神了。一片新鮮濕潤、喜氣洋洋的紅色。她也開始煮年夜飯,貼門神了。她把燈都打開了,頓時,新年的氣氛就撲擁過來了。德貴不在家,她也要跟德貴在家一樣過年。她不想不愉快的事。一切等新年過后再說。爆竹響起來了,先是稀稀落落的,漸漸成濃密的一片。她也把爆竹點燃了。她不害怕。她勇敢地用打火機去點燃了它。它疾速地炸響,有一顆彈到了她手上,很疼。但疼得很舒服。她故意離近了些。爆竹不停地彈到了她的手上,身上,還有臉上。真的,她打算今晚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不想。她狼吞虎咽地吃年夜飯。像小孩一樣放爆竹。自己給自己壓歲錢。放壓歲錢的時候,還說了幾句吉祥話。然后坐下來看電視。看趙本山。宋祖英。盡量讓自己看得津津有味。本來她很少看這類節目。往年這時候,她正在給爹娘還有兩個妹妹打電話,互相問好聊天。現在,她看了看電話機,沒理它。他們都已經知道她這里的事情了。她不想帶給他們不愉快的想法。她也不想接他們的電話,便把線拔了。爹娘叫她回娘家過年,她沒肯。她說你們老糊涂了嗎,出了嫁的女兒怎么能回娘家過年呢?看看,她多么深明大義。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看到外面的新鮮太陽,她長吁了一口氣。昨晚,她居然沒做夢。這很好。村里人認為除夕夜做夢不好。而去年除夕,她就做了一個很不好的夢,結果也就很不好。她骨碌爬起來。真的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了。她看了看新鮮的對聯,它們就像新年一樣充滿了希望。她剛把電話線插上,話筒就幾乎跳了起來。爹問,佳慧,還好吧,我和娘一直在打你的電話,你兩個妹妹也是一樣。她忽然說,昨晚,我在蓮芝家。
話一出口,她愣了。她怎么會這樣說話呢?大年初一,她怎么就跟爹爹撒謊呢?她在蓮芝家干什么?難道她能變一個小青給他們?爹又說了一些關心的話,才放下電話,她還在那里發愣。她終于意識到,不管她怎么努力,她還是沒法不想那件事的。它已經成了壓在她心上的一塊大石頭。
不行,她還是要去蓮芝家看看。她也不管是不是正月初一了。一想起這些,她耳朵里就是蓮芝的哭聲。昨晚,她把電視開得大大的,不然,蓮芝的哭聲就會從門縫和窗子里嗚嗚地鉆進來。她拿了兩包東西,還有一瓶燒酒,就往他們家去了。村里人開始互相拜年了。小孩子都穿起了花花綠綠的新衣服。然而男人們看到她,并沒跟她打招呼。幾個平時愛跟她開玩笑的,也故意裝作沒看到她。好像她是他們需要回避的。不過她也不在乎。因為本來,她也是這么想的。她和德貴,都已經成了村里的罪人和不吉祥的象征。她也就犯不著冒犯別人的忌諱。她走小路到了蓮芝家。
蓮芝顯然對她這么早登門感到意外。她看到蓮芝朝她點了點頭。她鼻子一酸,差點掉下淚來。她恨不得上前抱住蓮芝痛哭。他們家一點過年的樣子都沒有。依然穿著昨天穿的舊衣服。墻上沒貼一張新畫。甚至門神都沒貼。她把東西放在桌上,問,國權哥呢?按道理,要說幾句過年的話,可現在怎么說得出口呢?蓮芝說,還沒起來,從昨天一直躺到現在。她想到房里去探視一下,說幾句話,又覺得不方便,就猶豫著站在那里。誰知房間里忽然咚咚響起腳步聲,國權衣服也沒披,跨出房門對她破口大罵起來,說,你這個喪門星,這么早跑我家來干什么,你還嫌害我們家不夠啊!你別假惺惺的黃鼠狼給雞拜年,我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說完,又氣呼呼地回床上去了。
國權的怒罵并沒有讓她多么難堪。好像她正需要誰的一頓怒罵似的。蓮芝怕她尷尬,安慰她說,國權這兩天都這樣,你別怪,他也罵我,沒帶好小青。他把我什么都罵遍了。她對蓮芝笑了笑,說,我不怪他。
她還是堅持讓自己坐下來。不管忍受什么羞辱。她理解國權。她是個讀過書的人。她很羨慕電視里那些知書達理、深明大義的女人。她看她們總是看得熱淚盈眶。當然也有的女人文化并不高。比如有一個女人,男人遇到了不幸,欠下了一堆債,而這些債她根本不曉得也沒有任何憑證,但她還是答應還這些債。嫁給德貴的時候,他們就說好了,要做村里最好的夫妻,最好的人。他們是自己談的戀愛。當初她爹還不肯,嫌他窮。她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爹。果然,他們沒讓爹失望。他們成了村子里白手起家最先富起來的年輕夫妻。他們說,我們要做有理想的人,不跟村里素質差的人一般見識。不占小便宜。不搬弄是非。誰有困難就去幫忙。他們發現,做一個好人,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想到這里,她有些開朗起來。她拉著蓮芝的手。蓮芝的手割了她一下。她低頭一看,見上面有好幾個裂開的口子。她說蓮芝姐,國權哥的意思我懂。我沒有別的意思。到時候,交管部門怎么判,我都認。但我們不要因此成為仇家啊。
蓮芝嘆了口氣,說,你的心意我懂,但我滿眼滿腦子全是小青。我也曉得,你以前待小青比自己的孩子還親。你也不用為我們擔心,受這樣的打擊,也不是第一次了,小青那個姐姐,跌到池塘里才五歲。唉,這是老天跟我們家過不去。
她說,那天我看電視,說有個人被車撞了,司機跑了,(你不知道,一看到這樣的節目我就心驚肉跳)他斷了幾根肋骨,腎也被割掉了一個,兩年后,查出了尿毒癥,要換腎。可他們哪有錢買腎呢,就在親人里找合適的腎源。他兩個哥哥一個妹妹血型不配對,他爹倒是配得上,可年齡大了醫院里不敢做。他還有個弟弟也配得上,但腦子有問題,醫院里說這樣的人也不能。到縣里、省里開證明,可醫院還是堅持說法律有規定,不肯做。你說這不是命苦的人么?可惜我的血型不對,不然我就給他捐腎去。
蓮芝說,我知道,你是好心人,你家德貴也是好心人,不論上街下縣,每次在路上碰到我,他都要停下車子,捎我一程。好幾次幫我家拉東西都不肯收錢,說是順路,怪只怪我們命苦,也許我家小青就是這個壽數。
她說,也不能這么說,我家德貴什么都好,就是面子薄,有時候明明不能做的事情,或自己沒那個量做的,他也要充好漢。別人叫他喝酒,他就喝。有時候說不定人家是一句客氣話,可他都當了真。這次,他要是沒喝酒……我早就提醒過他。去年也是這樣,人家叫他去喝酒,他真去了,可他到那里,人家都已經動手了,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光叫他喝酒。這哪是叫他去喝酒,無非是看他開車,想讓他送那些客人回家,幫忙送送客我不反對,可不該勸他喝酒對不對?他回來還不敢跟我說,后來我曉得了,狠狠說了他一頓。
蓮芝說,唉,男人都這樣,愛這個東西,說起來,德貴比我家國權好,他喝醉了酒不是打人就是摔東西,不但打我還打小青,有一次,把小青打得好幾天走不了路。剛才,他還跟我念叨這些,可現在,他后悔也遲了。
這時,房間里傳來國權的哼哼聲。兩人沉默下來。過了一會兒,蓮芝說,佳慧,不談這些了。
過年后,交管部門的裁決書下來了。德貴犯交通肇事罪,后果嚴重,但主動打電話投案認罪態度較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同時附帶民事賠償十萬元給受害者家屬。這個結果在柳佳慧的預料之中。她把車賣了,加上存款,又向娘家人借了一些,都付給了國權和蓮芝。國權對那些錢看都不看一眼。蓮芝倒是推托了一下,說,既然小青已經沒了,要這些錢又有什么用呢?她說蓮芝姐,你要不收下我心里更難受。其實她已經聽說國權去縣里找了人。其實按道理,德貴判個緩刑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國權一心想要德貴坐牢。不過這也是她和德貴應得的下場,相對于小青一條命,十萬塊錢不多。所以她對國權也沒有一絲的不滿。她鼓勵德貴安心服刑。聽說監獄里很亂,她也花錢花東西去找了人,希望他在里面少受些皮肉之苦。
德貴始終眼淚汪汪的。
她還是那句話,對德貴說,錢是人賺的,等你出來,我們再重新開始。
開春了,她開始往田里播種。這些事以前都是德貴做,她頂多在田塍上幫幫忙。現在都只能靠自己了。種田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本來她打算到外面去打工。兩個妹妹叫她跟她們一起去,她想了想,還是沒答應。她不想離德貴太遠,要經常去探望他。她知道,德貴其實是個很脆弱的人,至少,沒有她堅強。她要不斷地鼓勵他。她要把田地弄得跟以前一樣生機勃勃,把家里弄得跟以前一樣熱氣騰騰。要是沒有熱氣,就不像個家了。德貴不在家也不要緊,就當他到外頭打工去了吧,村子里,這樣的人家也不少,男人在外面打工,女人在家里種田地照顧老人帶小孩。
一有空,她照樣去蓮芝家里。幫她做些事。她說到做到,要讓兩家關系更好,這樣才對得起小青。哎,那是個多么水靈靈的女孩子啊。蓮芝已經懷了孕。她差不多四十歲了,懷起孕來有些吃力。臉上又重新泛起了雀斑,像細小的蝴蝶一樣密密麻麻停歇在那里。蓮芝都有些不像蓮芝了。她陪蓮芝說話。做針線活。互相做好吃的。蓮芝想吃酸的,她就到野地里給她摘“酸瞇眼”。她們似乎又重新恢復了以前的那種親密無間。國權從地里回來,有時候也在那里坐坐。依然嚴肅而沉默。只在喝了幾口燒酒之后,臉色才有些松動。
這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不知是在自己家里還是在蓮芝家里,國權坐在硬木沙發上不停地摁電視機的遙控。看那沙發,更像在自己家里。奇怪,她怎么會夢見國權在她家里看電視?然后,她又跳到了另一個夢里。這個夢跟她白天看的一個電視節目有關。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渾身都是被指尖掐出的傷痕,孩子的媽媽斥責孩子不聽話,后來,她拎起女兒朝墻上摔去,只聽一聲悶響,孩子跌到地上。這個節目她看哭了。想不到世上還有這樣狠心的娘。然而晚上她在夢里重復了那做娘的虐待她女兒的過程。那小女孩像是她的大妹。小時候,大妹長了一頭的黃瘡,散發出陣陣難聞的氣味,娘要她抱大妹她總不愿意,作為報復,她把大妹頭上的黃瘡一片片剝下來。大妹疼得哇哇大哭。她呲牙咧嘴的,把妹妹剝得不成人樣,丟在什么地方,然而大妹又跟了過來,纏住她不放,而且還威脅她要告訴娘,她氣得上前拎起她的腳,大妹則伸出手來掐她的脖子。大妹的手忽然長成大人的手,骨節粗突,硌得她脖子很痛。想不到她居然有這么大的力氣……
實際上,還真有人掐住她脖子。她很快辨認出來,是國權。他怎么進來的?不知道。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她沒有叫喊。叫喊的反而是國權,他說,你男人軋死了我女兒,現在,你賠我!
她不怪國權。要怪就怪德貴。怪她自己。當國權看到她和蓮芝依然像什么也沒發生似的坐在一起,不禁大驚失色。他不再敢看她的眼睛。她想,或許,她已經把欠國權和蓮芝的債都還上了,她現在不欠別人,只欠小青的。是啊,小青的債,她怕是永遠也還不上了。她變得小心了。晚上,要仔細檢查門扣。她準備了一把剪刀。只是她還沒想好,如果真的再發生那樣的事,她是把剪刀對準對方還是自己。
后來的一天,再給蓮芝摘“酸瞇眼”的時候,她自己也忍不住大嚼起來。酸酸的、紅紅的汁液沿著嘴角不顧一切地漫出。她有些驚喜又有些麻木地想,說不定小青沒有死,她鉆到她肚子里來了。她說,小青小青,你的債我是能還清的。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