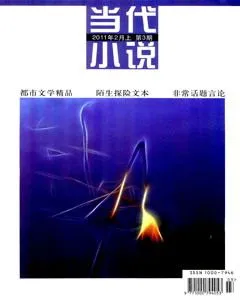曉看紅濕處
周五的黃昏,厲義氣走了米非。米菲走的時候,動靜很大,翻箱倒柜的,收拾了整整一箱子的衣服,像是準(zhǔn)備進(jìn)行一場長途旅行。厲義就猜想。米菲之所以把出走的前奏弄得這么大張旗鼓,無非是想給厲義挽留自己爭取點(diǎn)時間,厲義并不為所動,穩(wěn)穩(wěn)地坐在沙發(fā)里,頗有些冷漠地注視著米菲的一舉一動。米菲在最后扣箱包的鎖扣時顯得有些煩躁和不安,連扣了幾次都沒有扣好,手指都有些發(fā)抖了。抖了幾次,實(shí)在找不出再拖延下去的理由了,“啪”的一聲。終于扣好了箱包的鎖扣。拖著那只碩大的箱包,米菲頭也不回地就出了門。在門被米菲重重甩上的那一刻,厲義輕輕舒了口氣。
窗外。一支玉蘭花的枝椏斜在黃昏的暮靄里,白日里看著玉白的花骨朵此時呈現(xiàn)出好看的暖黃色,窗臺上一溜碼開的啤酒瓶齊齊敞了口,像是有無限的心事想要傾吐似的。卻是有口難辯的沉默和肅穆。電話就在這個時候響了。
電話是鮑十月打來的。鮑十月在電話里問厲義干嘛呢。厲義盯著玄關(guān)處鞋柜上的那雙木底拖鞋,告訴十月說,沒干啥,我還能干啥呢?發(fā)呆唄。鮑十月就說。那出來喝酒吧,西街新開張的湘菜館見。厲義有些懶懶地問,西街每天都有新開張的菜館,哪家啊?十月說,就上個月才倒掉的那家彩票站,現(xiàn)在改湘菜館了。名號叫魚米鄉(xiāng)。記得來啊?哥幾個可都等著你呢。放下電話,厲義還在猶豫去不去,晚飯是吃了的,不過只吃了一半,桌上還放著只動了幾筷子的“殘羹剩炙”,醋泡花生,宮保雞丁,還有米菲拿手的魚香肉絲。醋泡花生是每餐必有的下酒菜,魚香肉絲里的木耳不怎么好,米菲抱怨說小區(qū)里的木耳賣完了。在一個面生的婦人那里買的,經(jīng)水一發(fā),異常的發(fā)達(dá),水性太大,切成絲下了鍋,油星四濺,噼啵作響。驚得米菲在廚房里尖叫連連。想起米菲,厲義還是決定出去喝這場酒,有那么些類似青春期的叛逆意思在里頭。厲義去洗了把臉。又望了望鞋柜上那雙被米菲鄭重其事擺放在那里的木拖鞋,換了件襯衣就出門去了西街。
厲義喝完酒回來已經(jīng)是后半夜了。
進(jìn)了門,厲義把鑰匙呼啦扔在門廊的鞋柜上,碰倒了一只木拖鞋,拖鞋砸在鞋柜上發(fā)出“啪”的一聲脆響。換鞋的當(dāng)兒,厲義一偏臉就看見了那只旅行箱。厲義心底冷笑了一下。換上了拖鞋。厲義去了臥房,打開燈。只見米菲把自己裹在被子里裹得挺嚴(yán)實(shí),只一頭黃色的長發(fā)從被子里鋪散了出來,頭發(fā)是今天才染的,襯著銀灰色的被套那頭黃發(fā)給了厲義幾分陌生感,像外國電影里的某個鏡頭。被子下面一動不動,厲義盯著這幅帶著幾分陌生感的場景停滯了片刻就抬手按滅電燈,退了出來。
回到客廳,厲義坐在沙發(fā)里發(fā)呆。茶幾上,摔裂了的電視遙控器像個傷員似的被塑膠帶捆綁著。是米菲摔的。不止一次。在很多次的爭吵中,那只遙控器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yùn)。那塑膠帶就像是道魔咒。令那只遙控器逃脫不了自己被捆綁的命運(yùn)。厲義看那只可憐的遙控器時就看到了那張壓在遙控器下的便簽條。取了來看,米菲張揚(yáng)跋扈的幾個大字寫著:房子是我租的。要滾你滾!!!厲義不屑地冷笑了下,順手將便簽折成了一架紙飛機(jī)擲了出去。粉綠色的紙飛機(jī)在屋子里飛了一圈后穩(wěn)穩(wěn)地落在了那只被米菲拖了一圈后又最終拖了回來的旅行箱上。厲義伸手去衣兜里摸煙時才想起進(jìn)門前抽掉了最后的一支香煙。
厲義決定下樓去買包香煙。
在門廊處換鞋時,厲義又看了看鞋柜上的那雙木拖鞋,本想伸手去扶那只先前被碰倒的木拖鞋的,手伸出去了,卻在半路停了下來。今天和米菲的爭吵就和那雙木拖鞋有關(guān),干嘛要去扶起那只被米菲示威一樣地擺放在那里的東西呢?這么想著厲義就帶上房門下了樓。
樓下的小賣鋪已經(jīng)打了烊,厲義向小區(qū)外走去。月色很好。道路上空無一人。路燈早已熄了,這是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小區(qū),像厲義和米菲這樣的外來人口并不多見。小區(qū)里的人家該睡的都睡了,該醒的兀自醒著。醒著的也都醒在某扇亮燈的窗子后面,渾渾噩噩卻也與世無爭。出了小區(qū),往東就是厲義方才回來時的西街,西街在這座城市的西邊,在厲義和米菲住處的東邊。
西街上,各個店鋪前早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少數(shù)幾家亮著燈的館子也正張羅著收拾家什準(zhǔn)備打烊。一路尋去,竟沒有一家賣香煙的鋪?zhàn)印柫x卻已是越走越遠(yuǎn)。先前被香煙逼迫出來的那份焦灼竟?jié)u漸減弱了許多,厲義的步子慢了下來。
不覺就又走到了晚飯時和鮑十月幾人一同喝酒的那家湘菜館前。周邊的燈光雖然暗淡了許多,但“魚米鄉(xiāng)”的噴繪招牌依然顯得很招眼,網(wǎng)絡(luò)上下載的一幅盛裝土家族少女畫像被移花接木地和店里隆重推出的幾款主打菜組合在了一起,肆無忌憚地展示著屬于草根文化的審美趣味。
店堂里的一個伙計出來收拾門前幾把散落的椅子,站在明暗交界處的厲義顯得有些可疑,伙計看了他一眼,認(rèn)出了是晚餐時在湘菜館喝酒的食客,點(diǎn)頭打了個招呼。伙計嘴里叼了根煙,一點(diǎn)頭,長長的一截子煙灰就掉了下來。厲義叫住伙計問他附近哪里有香煙賣。伙計想了想,搖了搖頭。結(jié)果厲義其實(shí)是早就知道了,這條街道平日里沒少走,印象中的幾家香煙鋪?zhàn)舆@會兒都關(guān)了門。不過這一問自有它的妙處,伙計放下了手里的幾只長腳塑料椅子,從襯衣口袋里摸出煙盒癟下去很多的半包香煙來給了厲義。而后,伙計拾起塑料椅子回了湘菜館。
接過香煙的厲義開始往家走,嘴上已經(jīng)銜上了一支,手去衣兜里摸來打火機(jī),打火機(jī)是一次性的,打了幾次卻發(fā)現(xiàn)也已是彈盡糧絕。厲義一揚(yáng)手將打火機(jī)摔在路邊的馬路牙子上,“啪”的一聲卻砸出一簇火花來。厲義心里的火也被激了起來,感覺今天真正的是干啥啥不順。心情很糟糕的厲義走到樓下才又發(fā)現(xiàn)方才把鑰匙落屋里了,厲義狠狠地跺了一腳單元口那扇老舊的木門,樓道里的聲控電燈霍地就亮了。厲義的一張臉在那慘淡的燈光下卻沉沉地黑了下去。
沒錯,房子是米菲租的。在厲義還沒到來前就跟房東簽了合約的。每月的房租也是米菲交的。那是米菲的錢。厲義并不是吃軟飯的男人,在報社發(fā)行部打工雖沒啥大的出息,好歹也是月月有進(jìn)賬的。只是米非似乎更懂得算計和經(jīng)營。厲義的錢都用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米菲的錢卻用來交了房租。盡管兩人掙來的人民幣都混在了一起,那錢上又沒有寫上各自的名字,但按照米菲的說法,用來交房租的錢就是從她米菲那兒出的、此時的厲義就覺得自己很冤,比竇娥還冤。
日常的開銷是沒有什么計劃的,兩人的飲食,其實(shí)也就是晚餐都由米菲安排。早餐幾乎是不吃的,午餐都在各自的單位里吃。就只有晚餐,米非都盡可能地準(zhǔn)備得豐盛些,厲義晚餐有喝點(diǎn)酒的習(xí)慣。米菲在這點(diǎn)上很遷就他。在超市站化妝品柜臺的米菲是個熱愛生活的女人,雖是租住的房子,日常的生活用品包括床上用品外帶窗簾桌布甚至馬桶坐墊都要精心置辦,那只在厲義眼里幼稚愚蠢的木底拖鞋最能說明問題,買回來才穿上,大樓下的女人就頂著一頭的卷發(fā)夾子找上門來了。拖鞋被當(dāng)作裝飾品擺在了門廊的鞋柜上,看著鬧心。當(dāng)厲義看到米菲今天花了180塊錢染的那頭黃毛時終于忍不住絮叨了她幾句,連帶著就又說到了那雙拖鞋。米菲對厲義的不滿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失望,米菲咬牙切齒地說厲義。沒想到你墮落到這般田地,沒品位沒追求沒理想沒情趣,每天過這種除了吃飯就是喘氣的日子簡直就是一頭豬!厲義不知道一雙拖拉板怎么就被米菲上升到了這么一個高度。不可理喻!
貧賤夫妻百事哀。盡管兩人目前算不得夫妻,可要以法律來界定也算是事實(shí)婚姻。盡管兩人目前的狀態(tài)已是準(zhǔn)婚姻狀態(tài),可婚姻這個詞對兩人來說還是顯得那么遙遠(yuǎn)。大學(xué)畢業(yè)四年了,工作從一座城市換到又一座城市,居無定所,風(fēng)雨飄搖。
此時的厲義站在樓下的夜色里,感覺晚上的那場酒這會兒才上了頭。嘴里銜著的香煙離了火就啥也不是,銜在嘴里除了自慰就剩下了傻氣。啐出去會顯出幾分豪氣和灑脫,可這黑漆漆的夜里啐給誰看呢,厲義把煙重新裝回了那只癟塌塌的煙盒里。抬眼望了望三樓的那扇窗戶,里面還亮著自己出門時開著的燈,很忠實(shí)的燈光,
上了頭的酒精就讓這個時候的厲義想起了十月在酒桌上說的事來。十月是當(dāng)?shù)氐耐林苍僳E天涯了好一陣兒。最終回到了銅葵。和厲義一樣,十月也在銅葵的報社作發(fā)行。那家湘菜館招牌上的土家族女孩是十月的女朋友,女孩叫黃羚,有著羚羊一般修長的腿,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披戴著隆重的民族飾品游蕩在風(fēng)景區(qū)陪客人照相,女孩把自己叫做人肉布景板,一個人頭收取十塊錢的勞務(wù)費(fèi)。湘菜館的老板不知從哪個網(wǎng)站的貼圖板上搜羅到了黃羚的相片就拿來用了,被黃羚發(fā)現(xiàn)后不依不饒地找來理論,最后。在十月的調(diào)解下以老板請吃一桌飯告終。以十月的人緣很容易就湊夠了一桌子,不過話說回來,這年月,作飯局的應(yīng)邀嘉賓跑得都快。
酒桌上鮑十月很有些自豪,不斷地向座上的人勸酒,一有空就把黃羚攬?jiān)趹牙飺崤S羚的頭發(fā)。黃羚的頭發(fā)很好,長長的,黑亮。十月注意到了厲義的眼睛總往黃羚的頭發(fā)上瞅,就說,直板燙,就這一個頭三百多塊呢,黃羚驕傲地一擺頭,抬手打掉了鮑十月?lián)嵩谧约侯^上的手說,爪子拿遠(yuǎn)點(diǎn),油刺乎乎的!這時的厲義就感到自己真像米菲說的是墮落了,墮落得連當(dāng)今的頭發(fā)燙沒燙過都看不出來了,墮落得連直發(fā)也是可以燙出來的都不知道。那一刻他甚至對米菲花一百多塊錢染頭而給予的抱怨感到了一點(diǎn)小小的內(nèi)疚。
黃羚中途接了個電話就提前離席了,對黃羚的行色匆匆鮑十月似乎習(xí)以為常,繼續(xù)穩(wěn)坐席間。看著黃羚的背影從湘菜館消失后,酒桌上的氣氛一下松散了很多,厲義除外的七個男人都不約而同地將話題轉(zhuǎn)到了黃羚身上,轉(zhuǎn)到了女人身上。黃羚在時,席間也不乏對她的溢美之詞,但那都是包在餃子里的曖昧餡子,太多的中國含蓄包在其間,未下口之前只能透過不太明了的外觀去揣度其中味。現(xiàn)在則不同了,有如法式的漢堡,青凌凌的生菜融合了太多的奶油生猛地刺激著感官,每一句都顯得那么生猛和鮮活。鮑十月呵呵地笑著,很滿足地笑著。反倒是厲義的沉默更讓鮑十月覺得可疑。鮑十月說,厲義,你小子一貫心里作事,想嘛呢?厲義心里想著。嘴上就不覺地溜了出來,這女孩腦子缺筋。說完了,又冒出了半句,十月你啥時候整了這么一個……話沒說完,及時咽了回去。可畢竟晚了,鮑十月的臉一點(diǎn)點(diǎn)地黑了下去:酒桌上就有點(diǎn)沉默,鮑十月默了半晌,夾了筷子清蒸魚放進(jìn)嘴里,用手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抽出刺來說,管她缺筋不缺筋,也就隨便玩玩。說完這話,鮑十月的臉色就不那么黑了,仿佛不好的氣色都隨著那些魚刺被抽了出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就是就是,傻點(diǎn)好,十月又不指望和這丫頭齊家過日子白頭到老,缺筋不怕,丫頭挺好,該凸的凸該凹的凹,女人該有的打眼望去啥啥不缺。聽著眾人的話,厲義就在心底感嘆真是吃人的嘴短。
不知是出于補(bǔ)償?shù)男睦磉€是炫耀的心理,鮑十月開始講述他的情史。據(jù)鮑十月所言,截至目前他生命里經(jīng)歷了六個女人。聽了這個數(shù)字,席間一片艷羨的贊嘆聲。鮑十月繼續(xù)不緊不慢地進(jìn)行著他的講述,他說撇去黃羚不說,其余五個女人中給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數(shù)第一個名叫翁虹的女孩,那時的翁虹和鮑十月都還純情,該是看《在水一方》的年齡。可現(xiàn)實(shí)中的翁虹并不在水一方,現(xiàn)實(shí)中的翁虹就在鮑十月身邊,一個活生生的,有著溫度和美好的青春的肉體的女孩,就在年輕的、卻多少帶著點(diǎn)柏拉圖情結(jié)的鮑十月身邊。來自身體深處的聲音告訴少年鮑十月這個女孩唾手可得。
不厭其煩地吃著清蒸魚的鮑十月,帶著難得的,對往昔抱著一絲回望的神情說,他的這一份自信來自女孩翁虹和自己交往的一招一式中。說完。就又糾正自己說應(yīng)該是一顰一笑才對,一招一式對于那個年齡來說,太色情。太不純潔。
鮑十月最終聽從了身體的召喚。第一次對于兩人來說都顯得太過慌亂。那個炎炎的午后,在翁虹家那張狹窄的單人床上,面對第一個在自己面前衣衫褪盡的異性時,鮑十月積攢的所有對女性所持有的美好感覺都被摧毀了。他看著翁虹兩腿之間的那個地方不知所措,鮑十月說,他被那黑糊糊的一片嚇住了,那個地方和外國油畫里所描繪的是那么的不一樣,和自己臆想的也是那么的不一樣。當(dāng)他不能自禁地伏在女孩翁虹身上顫抖起來的時候,他看見了女孩翁虹眼里滾落的淚珠。鮑十月不明白,本該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怎么就會在尷尬甚至還有幾分齷齪感里結(jié)束。
鮑十月吐出了嘴里的一根魚刺,桌上的那條黃花魚已經(jīng)被他吃完了。停止了講述,酒桌上的氣氛忽然間就顯得有些肅穆。眾人仿佛被揭開了些什么似的,表情里不見齷齪,卻多少有幾分尷尬。坐在十月身邊的一江為著打破沉寂,賣乖地說道,不算不算,十月你小子謊報軍情,沒弄成的也拿來湊數(shù),明明四個硬說是五個,接著說另外幾個。一江的話并沒有得到響應(yīng)。大家還是顯得有些沉默。倒是十月打破了這稍顯異常的氣氛,如釋重負(fù)地說,操!說這些干嘛?都他媽打鳴叫破了嗓子的老公雞了,還擱這裝什么雛啊?來,喝酒。
大家碰了杯,喝了酒,卻發(fā)覺空氣里那股怪怪的氣氛依然沒有消失殆盡。仿佛還差那么一點(diǎn)什么才可以推動談話的繼續(xù)。
十月就說,知道那女孩現(xiàn)在人在哪嗎?就在東街的良友雜貨鋪。站攤呢。結(jié)婚了。應(yīng)該過得還不錯吧,多少年沒見過面了,聽別人說的。十月的這幾句話終于使空氣不再那么黏稠了,大家仿佛終于可以看到多年前那場被擱置下來的性事找到了突破口,像一部可以人庫了的老電影般完成了它的圓滿收場,
現(xiàn)在的厲義發(fā)覺自己不知不覺中就已經(jīng)來到了平日里極少走動的東街來了。做發(fā)行厲義跑的是南區(qū),作為一個外來的人,銅葵的東街對他來說是陌生的。此時厲義的一雙眼就不自覺地搜索起街邊的店面招牌起來。“良友”雜貨鋪的招牌就在這時跳進(jìn)了厲義的眼睛里,招牌下是扇窄小的門,店鋪里亮著黃暈溫暖的燈光。一個面容娟秀的女子懷抱著個孩子在柜臺里一邊搖晃一邊走動著。厲義推門走了進(jìn)去。
有火嗎?厲義盯著那女人的臉輕聲問道。有。建江,給客人拿個火機(jī)。女人沖著身后說了一句,厲義這才看到從女人身后站起的那個男人。男人給厲義取了只打火機(jī)放在柜臺上,厲義摸了送進(jìn)口袋,又看了女人一眼,轉(zhuǎn)身正要離去時,女人說,噯,您還沒給錢呢。厲義這才回過神來,連聲說著對不起就去口袋里摸錢包,卻糟糕地發(fā)現(xiàn),錢包竟放在那件白色的襯衣口袋里了。厲義一時愣在了那里,半天才艱難地說了句,不好意思,我,我這忘記帶錢了。明天給你送來好嗎?
女人有些遲疑,仔細(xì)地打量了一眼厲義,眼神里透著些狐疑。厲義就又說,你是翁虹吧?我一個朋友和你是中學(xué)同學(xué)。說完,看了一眼女人身邊的男人又補(bǔ)充道,女的,是一女朋友。
女人開了口。女人說,我不是翁虹,那女的不干了,這店是我盤她的。厲義就有些始料不及,僵在了那里。柜臺里的男人開了口,男人說,一塊錢的東西,拿上先用吧,改天路過送來就是了。女人看了男人一眼,男人又說,這么晚了,店鋪都關(guān)了門了,也難去別的地兒尋了。我們鋪?zhàn)娱_門開得早,關(guān)門關(guān)得晚,您以后多照顧就是了。女人這才對厲義露了個笑臉,懷里的孩子醒了,開始哇哇地亂哭,男人和女人就急急慌慌地哄孩子去了。
出了雜貨鋪,厲義點(diǎn)了掏出的煙狠狠地吸了一口,心里竟有些莫名的憂傷。
一根煙吸完,厲義正好回到了家門口。
抬眼望望,屋子里的燈依然亮著。上樓時,厲義擺弄著手里的那只一次性的打火機(jī),就想起那只存放在茶幾抽屜里的進(jìn)口火機(jī)來,鋼制的。說是防風(fēng)。去年生日時米菲買給他的,漂亮得像個工藝品,一直沒用。
厲義按響了門鈴。不一會兒就聽見米菲的腳步聲,走到門前停下了。門里,米菲嗓音有些沙啞地問,誰啊?
門外,厲義輕輕舒了口氣說,我,開門借個火。
責(zé)任編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