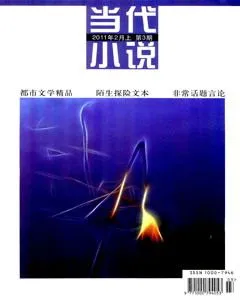狗吃剃的
1
王菲兒事后告訴老三,你老婆不是在你脫自己襯衫的時候打來電話的。
王菲兒的這句話說得有些拗口,但老三還是一下了就聽懂了,他試著平穩自己的呼吸,他說,哦,是嗎?
王菲兒使勁點了點頭,說:嗯,是的。
老三長噓了口氣,指代不明地小聲嘀咕了一句,媽的。
其實老三也知道,在他剝香蕉那樣把王菲兒從長裙中剝出來的時候,他包里的手機就震動了。那種不真切的嗡鳴,就像一蓬細碎又鋒利的沙子,讓他的好心情猛然打了七到八折。老三實在懶得去接電話,就接著脫自己的襯衫。一定是脫得太急,一枚扣子就崩掉了,彈到這家名叫北岸賓館的水粉色墻壁上,又折射到地磚上,骨碌碌劃了幾個不規則的圓圈,之后才很不情愿地在門口那兒靜止下來。老三接著脫褲子,這時候,他的手機已由震動轉成了樂曲,原本很抒情的《茶花女飲酒歌》,這會兒聽起來簡直轟隆隆的。
老三就皺著眉頭,從包里拿出手機。一看來電顯示,是老婆才思琦的手機號碼。與此同時,王菲兒白了老三一眼,隨手扯過被子,潦潦草草地蓋在身上。老三假裝沒有看見,眼睛看著手機屏幕,對王菲兒擺了擺手,既是表示歉意,也是示意王菲兒不要出聲。王菲兒偏偏用鼻子哼了一聲,老三忙將右手掌做了個下壓的動作。
接了電話,老三小聲又快速地說,我很忙,怎么了。什么事,快點說。他的這十二個字,事后被王菲兒稱為山寨版的三字經。
老三的老婆才思琦說。你爸丟了。
老三根本沒心思聽才思琦在說什么,他就隨口說,哦。
才思琦大聲喊,你爸離家出走了!
老三的心思仍舊沒放在通電話上,他說,行,我知道了,我馬上回家。
之后,老三就有些惡狠狠地將手機關機,接著脫自己的褲子。
王菲兒顯然聽見了才思琦說的話,她說,要不,要不你先去你爸家看看?
老三沒說什么,撲到了她的身上。
事后,老三剛剛點了根煙的時候,王菲兒就說了“你老婆不是在你脫自己襯衫的時候打來電話的”這句話。接著,她嘆了口氣,說,我爸前幾天心臟病又犯了,唉,現在他正在醫院躺著呢。
老三這才想起剛才老婆才思琦給他打電話,好像是說他爸怎么了。至于他爸到底怎么了,他卻一下子想不起來。
老三就問王菲兒,剛才我老婆在電話里說啥了?
王菲兒愣了一下,說,她說你爸離家出走。
老三急忙把煙熄滅,扔在地上,緊接著就開始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往衣服里面填裝。
王菲兒說,你說現在這醫院吧,得個小感冒,你沒有千八百塊都答對不了。怪不得人家都說,現在啊,你只要不得病,就是最大的收入。
老三沒說什么,但臉色開始向鐵青色過渡和靠攏。他從包里拿出一千元錢,扔在王菲兒的胸罩上。
王菲兒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知道你最近手頭也緊。
老三看也沒看王菲兒一眼,轉身就往外走。快要來到門前時,他停下腳步,哈腰撿起那枚襯衫紐扣。他站起身,轉過頭來,看到王菲兒正在低頭數錢。笑容已經從她身體的里面,一波一浪地泛到了她的臉上。
老三拉門走了出去,回手狠狠將門帶上,咣的一聲,把他自己也嚇得一哆嗦。
2
老三的爸爸今年六十三歲了,快要退休的前一年,混上了一個副處級。老爺子如今不缺吃又不缺喝。時不常摸幾把小麻將,每天早上起來還總去街心花園,跟那幾個老太太跳個交際舞什么的。在老三看來,老爺子的日子不說多姿多彩,起碼也是有聲有色。
而老三的老婆才思琦是中學老師,教英語。老三的大哥有個兒子,叫小慶,才思琦是小慶的班主任。小慶差不多每次考試的成績都是一百分,是三科分數加在一起。才思琦覺得臉面上實在過不去,今天上午她就去了小慶家,想跟老三的大哥商量一下,要不要讓小慶蹲級或者轉學,她也好撇掉這個爛包袱。可老三的爸爸、大哥、大嫂都沒在家。才思琦就問小慶,你爸你媽呢?小慶支支吾吾了半天,說,我,我不知道。才思琦一眼就看出小慶在撒謊,她想以嬸子和班主任的雙重身份訓斥小慶,但一轉念,她笑了,開始夸獎小慶是個誠實的孩子。才思琦還以魯迅、孔子、莎士比亞以及去年剛剛上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例,說明人之所以能夠成才和出名,就是因為年少時誠實。才思琦還想繼續這樣古今中外地旁征博引下去,小慶低著頭、噘著嘴巴,拿出了爺爺離家出走前留的一封短信。是一張A4幅面的白紙,內容很短,沒有抬頭和落款:我可能去澗河散散心,沒時候回來,誰也不用找我。才思琦認得這是老三爸爸的字跡,她這才知道老三的爸爸已經離家出走超過二十四小時了。老三的大哥、大嫂去找老爺子去了。才思琦就急忙打電話給老三,而老三正在跟王菲兒忙活。
現在,老三出了北岸賓館,將帕薩特開到河濱街的東盡頭。把車停靠在路旁,他拿出手機,開機。
有兩個未接來電,都是才思琦打來的。
老三就給才思琦打了電話。他說,老婆,剛才局長給我們開會,這頓發脾氣啊。我要是接你電話,就等于往局長槍口上撞。
才思琦就講了事情的經過,她說,你先別說這些沒用的,你趕緊把你爸找回來再說。
老三就氣不打一處來。你說你這老爺子老老實實地養老,多好!玩什么離家出走啊?你既然玩離家出走,那你就偷偷摸摸地進行,徹底一點,別留下什么線索啊。說什么可能要去澗河?去澗河就去澗河,還可能要去,拿誰不識數怎么的?老三就覺得,這老爺子真是閑出毛病來了。老三更生他大哥的氣。最近幾年,老三的爸爸一直跟老三的大哥住在一起,你當老大的怎么就好意思把老頭照看丟了呢?把老頭照看丟了其實也沒什么,畢竟人都長著兩條腿,想走就走,你總不能拿根麻繩給人家捆上。問題的關鍵是,老頭丟了,你倒告訴老三和老二一聲啊,偏偏悶著。老三一下子也想不出他大哥在打什么鬼算盤。
電話那頭,才思琦又說,你說別的都沒用,你快點去找你爸,
老三說,老大兩口子去找就行了,他們把老頭看丟了,哪輪到我去找?我眼眶子發青怎么的?
才思琦就罵老三,你腦袋進水了還是讓毛驢子踢了?你就不想想你大哥、大嫂為什么把你爸接他們家去?為什么你爸丟了,他們自己偷偷去找?
老三一拍大腿,說,操,我明白了。
3
按照才思琦的想法,她是想讓老三馬上開車去澗河。老三嘴上答應了,可剛要發動車子,他猛然覺得不對。老三知道,他爸如果真是去澗河了,無非是去見鐘紅娟,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可是,他爸要是沒去澗河,那他風風火火地趕去,除了浪費油錢和時間。他什么也撈不到啊。而更重要的是,這老爺子為什么要離家出走呢?老三甚至懷疑老婆才思琦是不是搞錯了。
老三正拿不準主意,大哥給他打來了電話。
老三啊,你說咱爸他多氣人,我天天好吃好喝伺候他,他倒好,連個招呼也不跟我打,走了。大哥說。
老三這才得以徹底確認,他爸真的是離家出走了。他就問大哥,你現在在哪?
大哥說,在家。
老三說,咱爸呢?
大哥說,我不剛跟你說完嘛,偷摸走了。
老三說,咱爸為啥走?是不是你又氣他了?
大哥說,我哪知道他為啥走?我天天好吃好喝伺候他,我啥時候氣他了?
老三說,那你咋不去找他?
大哥說,找了,我和你大嫂去鐘紅娟家找了。鐘紅娟說咱爸根本沒去她家。我和你大嫂忙活到現在,別說飯,連水都沒喝上一口。
老三就在心里決定要去澗河了。他覺得大哥真是死腦瓜骨,大老遠跑到澗河,就認準鐘紅娟一個人了。要知道,老三的爸爸當年在澗河下過鄉,那里可是有他很多知青朋友啊。這樣想著,老三說,老大,我把丑話說在前面。當初我想把咱爸接去,是你死活不讓。現在你把咱爸看丟了,你可真有才!咱爸要是平平安安、啥事沒有,那咱們什么都好說;萬一咱爸有個三長兩短,你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大哥說,我,我。
老三說,你我什么我?你怎么不駕駕呢?你趕驢呢?
大哥說,你尋思我不想找到咱爸啊?我是沒找著。小慶馬上就要中考了,我也不能把他一個人扔家里吧。
老三說,操,你照顧你兒子,你自己的爹就愛哪哪去了唄?
大哥嘿嘿干笑兩聲,說,老三啊,咱倆先別吵吵了。我看還是你先把咱爸找回來,送到我這兒。對了,咱爸這事,我看你還是先別告訴老二。老二,老二他,他也挺不容易的,老三啊,你可能不知道中考的重要性,小慶要是能考上重點高中,就等于一只腳邁進了大學門檻。
老三說,就你家小慶那樣吧,他要是能考上大學,我給豬買一件貂皮大衣。
大哥說,老三你這么說話就不對了,小慶……
老三搶著說,是,我說錯話了,瞎貓碰著死耗子的概率還是有的,馬糞蛋子說不上也有發燒那天。
大哥大喊一聲,老三!緊接著,大哥將語氣緩和了下來,說,老三哪,咱爸這事就勞你大駕了,我估計咱爸一定還在鐘紅娟家。再說你條件比我們好,有車。出來進去的,比我們方便。
老三說,你不說我還真忘這茬了。現在油價漲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不?咱爸我去找行,油錢得你和老二出,你倆一人拿五百塊錢。
大哥說,老三你要這么斤斤計較就沒意思了。咱爸這事,老三,你暫時別讓老二知道。老三,這些年咱爸一直住我這兒,人吃馬喂的,你和老二高興就送幾個養老費過來,不高興就半年見不到個人影,我。
老三打斷大哥的話,他說,那好,我不跟你斤斤計較,你不是大方嗎?好,我出五百塊,你去找吧。
大哥說,老三你。
老三說,我怎么?
大哥說,好好好,我出三百塊來回還不到五百里地。我出三百。
老三說,就五百。
大哥說,老三你,你,行,行,你過來拿吧。
4
車子向北行駛到橋旗路中段的香江小區,也不過是三四分鐘的光景。由香江小區的西側門,也就是鑫鑫五金商店和小讀者書屋之間的狹窄過道,老三將車子駛到了大哥家的單元門下。
大哥家住在三樓,九十多平方米,不是建筑面積,而是實用面積。
大哥家原來住在城鄉接合部,是棟平房,七米長,八米的跨度,日漸消瘦的嘟嚕河水就像一條濁黃的絲巾,在他家院門的正前方往東南拐了個急彎。老爸退休后,大哥就買了現在的這戶樓房,還把老爸接過來住。而老三的爸爸退休前是副處級啊,主管人事,心甘情愿或者不得不巴結他的人,少說也能編成一個連的雜牌軍。老三就覺得他爸的兜里,要是說有四五百萬元錢,可能不太現實,但四五十萬總還是靠譜的。老三就想,大哥這是把老爸一輩子的積蓄劃拉去了一大筆,否則就算把大哥的骨頭敲碎去賣,也不可能買得起這戶樓房。
老三騰騰騰上了三樓,大哥正在門口等他。
大哥手里拿著一個煙黃色的信封,說,老三,這是我的五百塊錢,還有咱爸l臨走寫的信。他邊說邊將一張信紙和一沓錢從信封抽出來。錢多是十元、二十元面額的,也有五十元、五元、一元面額的。他將錢和信一并遞給老三,說,數數,你數數。
老三突然覺得心坐有些過意不去,或者是臉面上過不去,想不要大哥的錢,但只是張了張嘴,沒說什么。
你不數就算了。大哥說著就將錢和信塞回信封,又說,辛苦你了,早去早回。之后大哥把信封塞到老三手里,就轉身進屋了,很重地帶上了門。門板和門框的撞擊聲簡直光芒萬丈,嚇得老三倒抽一口冷氣。
老三就下意識地握緊了拳頭,信封被握得不成了樣子,發出沙沙拉拉的細碎聲響。
操,連往屋里讓我一下也不讓啊。這樣想著。老三就清了清嗓子,將一口痰吐在大哥家的門上,轉身下了樓。
老三來到車子里,拿出老爸的信來看。之后老三仰頭嘆了口氣,心想老爸應該真的是去澗河看鐘紅娟了,只不過大哥去找他時,他沒好意思出來見兒子罷了。老三接著就埋怨大哥小題大做,你既然知道老爸這是去會老情人了,巴不得全世界都齊刷刷退到幕后,只剩下他們二人在臺前一個勁地夕陽紅,你還往前沖個什么?真是不知道仨多倆少、看不出眉高眼低。老三又想,就算他爸沒去會老情人,他也能從鐘紅娟那里打探出他爸的那些知青朋友。
老三就微笑著低下頭來,開始整理大哥給的又被他攥皺了的錢。老三把錢一張張捋順捋平了,隱約覺得數額好像不對。他就捏著信封的底部一倒,丁零零,滾出兩枚五角硬幣。老三就又數了一遍,果然不多不少,剛好是三百塊,其中一張二十面額的還缺了至少五分之一那么大的一個邊角,
老三就忍不住再去大哥家把那二百塊要來,可他隨即想,老爸不是去跟鐘紅娟過日子了吧?老爸偷偷會會鐘紅娟,這沒什么,要是真跟鐘紅娟結婚,這事可就麻煩大了。老三就急忙發動車子,駛出了香江小區。
5
老三的爸爸叫李狗剩。不是綽號,戶口簿的第一頁,黑亮黑亮的三個仿宋體,就這樣橫平豎直地打印著。
說到老三的爸爸的名字,也許有必要提一下老一輩東北人的講究。比如一個人磨刀的時候,你不要上前跟他打招呼,更不要沒話找話來說,否則的話,刀就磨不快,而且很有可能一直鈍下去,由此也就派生出了另一個說道,啞巴磨刀,刀才鋒利。再比如,嬰兒剛剛長牙的時候,姑媽要給他(她)送一雙鞋子,因為嬰兒長牙會妨姑媽的。這里說的“妨”,東北人讀成“方”,意思大致是妨礙,更確切一點說,是一個人給另一個人帶來了晦氣,讓這另一個人事事不順,甚至會有性命之憂。
李狗剩是家中的長子。他的前面,有三個姐姐。從大到小,她們的小名分別是改子、換子、滿桌子。父母給她們取這樣的名字,當然也有講究。改子和換子,含義不難理解,就是改成兒子和換成兒子。至于滿桌子的意思,其實仍是想要兒子,只是理解起來要拐上幾個彎。你想啊,女兒已經圍著一張桌子坐滿了,下一桌當然應該是兒子了,否則也太說不過去,簡直就是登鼻子上臉啊。很多時候,李狗剩就想。父親當初給他的三個姐姐取名的時候,準保是只差一點點,就把滿口被旱煙熏黃的牙齒咬碎。
毫無疑問,李狗剩的出生,讓他的父親猛然腰桿挺得筆直,睡覺時都嘿嘿嘿地笑出聲來。按說父親該給他取個好聽的,起碼是像那么回事的名字才對,可父親卻在憋到第三天的時候啪的一拍大腿,說,媽了個巴子的,叫李狗剩!
李狗剩長大后才知道,貴人理應賤名,這也是老一輩東北人的講究。父親給他取了這樣的名字,據說是為了好養活。理由如下,狗剩,就是狗吃剩的,不會有誰去招惹他的,自然也就好養活了。
六十多年來,老三的爸爸痛恨自己的名字,恨得瞪眼、咬牙、跺腳、扇自己的耳光、揪扯自己的頭發。因為這名字,他小時候被同學恥笑就不說了;因為這名字,他下鄉時又被知青不當一回事,也不說了。單說退休前吧,老三的爸爸本來是有可能直接提到正處的,就因為名字泡了湯。那個說了算的人,用老三他爸的話說,是個“身體長寬高一個尺寸的王八羔子”,這人點了一根煙,清了清嗓子,說,李狗剩,李狗剩,這名字不符合辯證法嘛。
可現在,老三的爸爸不覺得自己的名字可恨了。其中的原因,得從北岸醫院說起。
6
北岸醫院的那個醫生,蓄著連鬢絡腮的胡子。跟李狗剩說話的時候,他揚著腦袋,眼睛望著天棚。這讓李狗剩心里特別有氣。李狗剩心想,媽了個巴子的,長了連毛胡子你就以為你了不起啊?我來看病又不是不給你錢,你有什么資格這么傲慢?
醫生說,你是自己來的?
李狗剩說。對,我自己來的。
醫生嘆了口氣,
李狗剩說,這又不是什么龍潭虎穴,我有必要雇幾個保鏢嗎?
醫生笑了,露出夾在兩顆門牙間的一條菠菜葉或者韭菜葉。緊接著,他的口臭轟隆一下涌了出來,就像一個大麻袋一樣,黏膩膩地兜頭罩住了李狗剩。
醫生說,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應該讓你的家人跟你一起來,再做一下全面檢查,這樣做,是對你負責。
李狗剩說,這我可得謝謝你。可惜啊,我就老哥一個,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想在我身上榨出油水,怎么說呢,有點難。
李狗剩把話說得這么難聽,一來是他知道現在的醫院都是狠宰患者。明著暗著管患者要紅包。二來呢,是來醫院之前,李狗剩剛剛跟大兒子、大兒媳生過氣。老大這兩口子確實不像話,都四十好幾的人了,大白天的,明明知道李狗剩在家里。他們二人就明目張膽地過起了夫妻生活。老大媳婦的叫床聲,跟殺豬似的,十里地外的聾子都聽得見。要是老大兩口子只是偶爾來這么一次。也就算了。問題的關鍵是,這兩口子差不多天天這樣。李狗剩就想,媽了個巴子的,這明明就是往外攆我。我給你們買了樓,你們反過來攆我走。就算不是在攆我,也是想早早把我氣死。想到了大兒子的不像話,李狗剩接著就想到了二兒子和三兒子。媽了個巴子的,沒一個好東西。老二整天什么活也不干,就知道喝酒,就等房檐往下掉餡餅,活活把老婆孩子氣跑了。老三倒是有幾個糟錢。可是抖抖擻擻的,時不常就去找小姐,曾經有幾個老同事跟李狗剩見面時,都讓李狗剩勸勸老三,可別瞎扯淡,萬一得上什么埋汰病可怎么辦?李狗剩覺得真是把自己這張老臉丟盡了。李狗剩是想勸勸老三,可他能逮著老三的人影啊!李狗剩就在心里大罵,我怎么就養出了這么三個敗類?
醫生聽了李狗剩的話,攤了攤雙手,同時端了下肩膀。他說,既然你是老哥一個,我就把話直說了,肝癌,已經是晚期了。
李狗剩從椅子上出溜一下坐到了地上。他急忙爬起身來,渾身的汗滴就像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一樣。他磕磕巴巴地說,你,你,說,說說什么?你剛才說的,什么?
醫生又開始仰望天棚,說,你已經是肝癌晚期了。
李狗剩撒腿就跑了出去。撞翻了椅子,在走廊里還撞倒了一個孩子。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李狗剩自言自語。這半年多,李狗剩是經常覺得肚子右邊疼,他以為是三個孩子給氣的。有過一兩次,李狗剩也懷疑肝臟是不是出了毛病。但他絕沒想過會是肝癌。就算是肝癌,也不可能是晚期!李狗剩就想,準是醫生看我沒有給他送紅包的意思,話又說得很難聽,他就故意嚇唬我、詛咒我。
李狗剩就停下腳步,胡亂擦抹了幾把汗水。轉身回了醫院。他指著醫生的鼻子說,你給我聽好了,要是我不是肝癌晚期,你就想辦法吧,想辦法別讓我再看到你。
有關這一夜李狗剩的無眠和心焦、恐懼和感慨,這里就不細說了。第二天,李狗剩去了第三人民醫院,這家醫院也叫肝病專科醫院。
李狗剩仍舊說自己是個孤寡老人,讓醫生把他的病情如實告訴他。給他看病的醫生把滑到鼻尖的眼鏡往上推了推,之后長嘆了口氣。嘆得李狗剩的心噌的一下躥到了嗓子眼。
醫生的話說得很漫長也很委婉,但實質情況李狗剩還是聽出來了。李狗剩的確是肝癌晚期了,要是還能再活半年的話,就是奇跡。醫生拐彎抹角地勸李狗剩想吃點什么就抓緊吃吧,沒有治療的價值了,別說你只是個孤寡窮光蛋,就算有座金山,也是白扯淡。
就是在這么一種情況下,李狗剩最終決定了離家出走。一只腳都出了門了,李狗剩還是有些不放心,就給老大留了一張可能去澗河的字條。
7
老三路過二哥家時,突然決定去見見二哥。老三是這樣想的,就說爸爸去澗河看望朋友,結果病在了澗河,他去接爸爸回家,讓二哥出路費。
老三敲了足有五分鐘的門,二哥才拖拖拉拉地來開門。二哥的腳步踉踉蹌蹌的,左腳穿了襪子但沒穿拖鞋,右腳穿了拖鞋但沒穿襪子。
二哥看也沒看老三一眼。轉身斜躺在沙發上,他面前一瓶五十二度的北大荒白酒,只剩下一個底兒了。
老三咳嗽了一聲,二哥撲棱一聲站起身,碰倒了酒瓶子,酒瓶子砸壞了一個咸菜碗,咸菜碗彈飛了一雙筷子,稀里嘩啦、丁丁當當。嚇得老三緊忙后退了一步,以為二哥這是哪根神經發生了短路。
二哥身體晃晃悠悠的,他說,來了朋友,朋友,來,喝一口。我欠你那二百塊錢,月底,這月底你來,我保準還上。
老三知道二哥這是喝大了,把他當成了債主。他想轉身就走,但不甘心,就說,二哥,我去澗河接咱爸。
二哥挑了下眼皮,說,啊,啊,是老三來了。說完,眼皮卷簾門一樣啪嗒落下。
老三說,我去接咱爸,老大出了三百路費,你出二百五十就行。你要是看我可憐,多給個千八的,那更好。
咱爸,爸。二哥嘟噥了這么一句,抄過酒瓶子,把瓶口塞進嘴里,咕咚一聲,瓶子見了底。爸,咱爸。二哥放下酒瓶,又嘟噥了一句,接著就斜躺在沙發上,轟隆隆的鼾聲飛揚跋扈、說一不二,掀得房蓋都在呼扇。
操!就你這熊樣,分不著老頭錢,活該。老三這樣小聲罵了一句,離開了二哥家。
老三來到樓下,剛剛發動起來車子,二哥已經從沙發上爬了起來。趴在窗口,看著老三的車沒了影子,二哥嘿嘿一笑。
讓我出路費?有那錢,我買它兩箱北大荒。二哥自言自語。
隨即,二哥抬手使勁拍了下自己的額頭,心想,不對啊,去澗河接咱爸,分不到老頭錢,活該。壞了!二哥喊出這兩個字的同時,用右拳砸了下自己的左掌心。他似乎一下子都想明白了,老頭這是跟老鐘婆子搭伙去了吧?老頭的錢……
二哥就急忙從床頭柜中拿出一只又灰又黃的白襪子。又從襪子里面掏出四五張鍍了層腳氣和腳臭的錢來,五十、一百面額的都有。
二哥就直奔客運站去了。
8
李狗剩是帶著他最后的一筆積蓄離開家的。是一張兩萬塊的存單。另外,他的兜里還有差不多五百塊錢現金。
李狗剩在心里念叨,我最多只有半年的生命了。我最多只能再叫半年李狗剩了。狗剩,狗吃剩的,多好的名字,多符合辯證法的名字,我最多只能再叫半年了。
李狗剩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反正他是不想再聽老大媳婦的叫床了。至于二兒子那兒,李狗剩知道也不能去。他敢賭上他最后這兩萬塊,老二現在要是沒欠一屁股外債,他就管老二叫爹。老三那王八羔子,我能給他添麻煩嗎?李狗剩長嘆了口氣,他知道老三從小就跟他兩個哥哥爭吃爭穿,指望老三給他治病、給他養老送終,他還不如指望狗熊一覺醒來長出犄角和翅膀。
應該說。最初的幾天,李狗剩沒想過要放棄治療。好死不如賴活著,這道理傻子都懂。那些大喊什么腦袋掉了碗大個疤瘌的人。那是沒人真砍他的腦袋。事到臨頭的時候,誰腿肚子朝前、誰尿了褲子,他自己最清楚。
最近這幾天,李狗剩還看了一些醫學方面的資料,知道肝癌晚期這病,誰攤上都是只有等死這一條路可走。他還在一張娛樂報紙上看到,幾年以前,那個胖乎乎的演員,叫傅彪吧,得了肝癌,后來做了肝臟移植,但幾個月以后還是死了。那張娛樂報上說,傅彪當初出演一集電視劇的片酬是十萬塊。這么有錢的主兒,拿肝癌都沒有辦法。李狗剩就想,我一個狗吃剩的,還較什么勁啊。李狗剩就后悔,當初在位時,不少人羞答答或者直愣愣地行賄,可他全都回絕了。李狗剩就罵自己,當初你他媽的充哪門子大瓣蒜啊?
兩萬塊,能干什么呢?在一家宿費十元的小旅店住了一夜,李狗剩也沒弄清這個問題。李狗剩首先想到了去他一直想去的西藏,但這顯然是不可能了。接著,李狗剩想要捐給希望工程或者汶川災區,可他咬了咬牙、跺了跺腳,還是沒有這個狠心啊。
李狗剩就想先去看看鐘紅娟,之后再隨便走走吧,錢花光的時候,死哪算哪。
當年在澗河下鄉,鐘紅娟一家真是沒少照顧李狗剩。特別是鐘紅娟的媽媽,抽旱煙袋、裹小腳的老太太,差一點要認他做干兒子。要不是后來李狗剩返城了,光看這老太太的面子,說不準他真就能跟鐘紅娟結婚,當年鐘紅娟對他是很有好感的,他對鐘紅娟的印象也還不錯,起碼人品好,還能吃苦。得知李狗剩結婚之后,鐘紅娟哭了很多天,她媽媽也跟著唉聲嘆氣。鐘紅娟一直把自己拖到了將近三十歲才嫁了人,當時李狗剩家老三都快能打醬油了。要說鐘紅娟的命也真是差勁,婚后生了個兒子,卻是個腦癱。她的敗類丈夫呢,水稻、稗草分不清,但知道下河撈魚,結果被魚撈去了。鐘紅娟就再沒嫁人,靠著耕種三畝零幾分的田地,一個人拉扯著累贅兒子過日子。
鐘紅娟的這些個鬧心事,李狗剩是后來才知道的。當時李狗剩的老伴去世剛剛半年,老三和才思琦正在張羅結婚。用李狗剩自己的話來說,當時他真是“把我折騰得上炕都要拽貓尾巴”。連累帶上火,李狗剩就病倒了。他在醫院掛吊瓶時,趕上鐘紅娟也來給她兒子看病。再次相逢的驚訝、驚喜和驚恐加在一起,就等于物是人非啊。老三結婚時,鐘紅娟給老三買了一臺洗衣機。從這以后,李狗剩和鐘紅娟就有了聯絡,也不過是過年過節時通個電話。再就是鐘紅娟帶兒子來看病時,會到李狗剩這兒歇個腳,水倒是能喝上一杯。飯可是一口沒吃過。倒是李狗剩的三個兒子有什么事路過澗河時,會到鐘紅娟家吃喝住,臨走時,鐘紅娟還要給他們帶上自己在山上采來的榛蘑、木耳或者黃花菜。
9
老三離開二哥家,就去接來了王菲兒。
車子駛出市區的時候,王菲兒說,咱們這是去哪?老三說,去澗河。
王菲兒說,去那干什么?
老三說,接我爸。
王菲兒說。哦。
老三說,我爸有個相好的在澗河,我也不敢保證我爸一定去他相好家。反正我閑著也是閑著,咱們就出來溜達一趟。
王菲兒說,你爸都多大歲數了,還有相好,你保準是隨你爸。
老三就嘿嘿一笑,左手操控方向盤,右手從王菲兒的衣領伸進去,揉摸王菲兒的胸乳。
王菲兒把身子靠向老三,小聲說,你別摸了行嗎?我,我想要。
老三哈哈大笑,右手的力道就猛了一些,同時轉過頭來,去親王菲兒的臉頰。
王菲兒輕輕推開老三。指了下車窗外,說,好了,人家能看到。
老三就往外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就沒了跟王菲兒親昵的心情。因為看到一輛駛往澗河的長途客車超到了他的帕薩特前,右側第三排靠窗坐著的那人,正是他二哥。
老三一下子就想到了二哥這應該是去澗河找老爸。老三記得剛才在二哥家時說漏嘴了,原來二哥是在裝醉啊。
絕對不能讓老二趕在我前面!老三還在心里打定了主意,見到老爸,就把老爸接到自己家去住。這樣想著,老三就加快了車速。超過了這輛長途客車后,老三再次把車速提快。
王菲兒開始是歡呼過癮,接著就對老三叫喊。慢點,你慢點,開這么快,搶錢去啊怎么的?
對,你說對了!老三惡狠狠地說,就是去搶錢。接著又使勁踩了一腳油門。
慢點!你慢點!王菲兒帶著哭腔大喊。
你他媽的給我閉嘴!老三邊罵邊揚起右手,胡亂扇了一下王菲兒的臉。
車!王菲兒剛剛喊出這一個字。老三的車子已經撞在了迎面駛來的一輛紅巖大卡車上。轟隆一聲,濃煙四起。緊接著,就有火光和爆炸的巨響攜手沖出了濃煙的包圍。
那輛長途客車很快就駛到這個車禍現場i客車不得不減速,乘客紛紛離開座位,趴在窗玻璃上向外觀望。只有老三的二哥沒有這份閑心。
我說司機老弟,快開車啊,我到澗河有大事。二哥揮舞著拳頭大聲叫喊,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不在它們該在的位置上了。
10
要不是鐘紅娟拖拉著個腦癱兒子,我就會和她結婚嗎?李狗剩覺得還是不會。既然年輕的時候沒有緣分走到一塊兒,老了老了,還往一起湊合什么?李狗剩又想,再說我那三個敗類兒子也不可能同意。
鐘紅娟上一次來李狗剩家,正好是父親節那天。李狗剩的三個兒子都很給李狗剩面子,帶了點吃的喝的來看他。鐘紅娟肯定不知道這天是父親節,鄉下人不講究這個。那天,李狗剩真是覺得過意不去,他的三個兒子,沒有一個拿好眼色看鐘紅娟這娘倆。特別是老三,連聲鐘姨也沒叫。撂下東西就走了,氣得李狗剩真想上去扇他兩個大耳光。
回想這些事情的時候,李狗剩已經把那兩萬塊錢從銀行取出來了。
李狗剩打了一輛紅黃相間的千里馬出租車,來到火車站。在李狗剩的印象中,火車站是這樣一個地方,永遠亂哄哄。永遠有跟父母走散的孩子在嚎啕大哭。永遠有目光飄來飄去的半大小子,把手伸進別人的衣兜。
排隊買票的時候,李狗剩突然猶豫了起來。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去澗河看鐘紅娟,看了能怎么樣?不看又能怎么樣呢?是能讓我的生命延長半年,還是就看她一眼。做個了結?做什么了結呢?李狗剩甚至有些自作多情地想,萬一到了紅娟那里,我不小心說漏了,或者紅娟從我的神情和話語里看出苗頭不對,那她一定不會讓我走的。她的日子已經掉了底兒了,我還去給她添什么亂?這么多年我都沒幫她一把,臨到自己要死了,讓人家來照顧你?你的那臉皮都不是橡膠皮啊,是鑄鐵。
想到這么多年來都沒幫過鐘紅娟,李狗剩就轉身出了火車站。火車站的斜對過就是郵局,他想到那兒去給鐘紅娟匯錢。
往郵局走的時候,李狗剩是想把這兩萬塊都給鐘紅娟匯去。可來到郵局門前時,他又想,還是匯一萬吧,畢竟我還能活幾天,人們常說的過河錢還得備上幾個。而待到填寫匯款單,他又把數額降到了五千。剩下那一萬五,李狗剩想好了,三個兒子,一人五千,都分給他們算了。人生自古往下疼,誰讓我是他們的爹?他們怎么就不是我爹呢!這樣一想,李狗剩就忍不住笑了,比哭更難看的那種苦笑。
李狗剩能夠想像得到,他這三個爹要是知道他給鐘紅娟匯去了五千塊錢,他們百分之百都得炸廟。特別是老三,百分之二百會去把錢要回來。李狗剩也想像得到,鐘紅娟要是知道是他給她的錢,她一定不會接受,一定會再送回來,這就更加亂套了。這樣前后一想,填匯款單時。李狗剩就留了個心眼,沒寫自己的真名和真地址。
出了郵局,李狗剩心情敞亮了不少。
李狗剩來到了一家農用物資商店,買了一小瓶敵敵畏。李狗剩現在是徹底想好了,還是哪也別去了,就在家呆著,能活一天算一天。醫院是絕對不去了,多少錢也填不上這個無底洞,再說人家醫生都明說沒治療必要了。
我就在家呆著好了,哪天疼得我實在受不了,我就把這瓶敵敵畏喝了。李狗剩小聲嘀咕。
11
路過二兒子家的時候,李狗剩早已經把剩下的那一萬五千元錢分成了三等份兒。
李狗剩連敲帶喊了好半天。老二也沒給他開門。李狗剩認為二兒子一定是又跑到什么地方喝酒去了,
看看,你主動給人家送錢都送不出去。李狗剩閉上眼睛,將腦袋左右搖擺。
李狗剩回到大兒子家時,天色就稍稍有些黑下來了。
李狗剩一進屋,老大撲棱一下站起來,說,爸,你可回來了!你這是去哪了?
李狗剩張了張嘴,剛要說什么,就見大兒子一把操過手機,飛快地按了一串號碼。
哈哈哈。大兒子把手機貼在左耳旁,大笑說,老三你回來吧,我把咱爸接回來了,那五百塊錢你得還給我。嘁,咋不接我電話呢?
李狗剩說,老大,你也四十好幾的人了,你和你媳婦,算了,先不說這個。你先把老二、老三都給我喊來,我有話要跟你們幾個講。
李狗剩話音剛落,他身邊的座機來電話了。李狗剩伸出哆哆嗦嗦的右手,拿過話筒,就聽見一個男人風風火火的聲音。
這個男人先是說出了老三的名字,又問李狗剩是不是老三的家人。李狗剩說是。
這個男人說他是什么什么交警大隊的。這人接下來說的一句話,讓李狗剩倒在了地上。
除了人體和地面相撞發出的那聲沉悶的撲通,還有一聲啪,似乎清脆異常。
是李狗剩兜里的那個小瓶子,磕碎了。
責任編輯: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