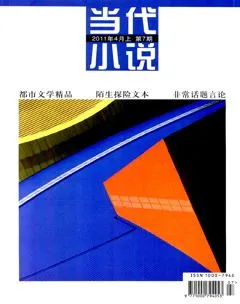在春天里傾聽生命的呼喊和細語
花初放,葉鵝黃,記憶中那些春天的抒情塵土飛揚。早春薄暮,一首大街小巷傳唱的《春天里》突然打動了這個冷漠的時代,想想,文學,真的也需要更多的真誠,來打動你的讀者。
穿越黑暗尋找光
讀陳應松的小說,有時候我們忍不住懷疑這個世界,我們忍不住要質問這個世界,一個普通人,對生活并沒有奢望,一點點愛與溫暖,一點點生存的自由空間,然而,也不能夠,這個世界不僅僅是黑暗的牢籠,禁閉心靈和夢想,而且充滿狂風暴雨,到處是生存的陷阱,就像端加榮,就像程大種,就像香兒……這個野貓嚎叫的湖,這個沖不破的長夜,這個漸漸荒蕪的家園,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是誰在用文字記錄我們的掙扎,痛苦,那些靈魂的孤獨、搏斗,還有無形的圍困,鐵網和冷漠的四壁,是誰在用心靈和生命記錄這一切?
陳應松的中篇小說《野貓湖》(《鐘山》2011年第1期),延續了陳應松一貫的底層關懷的文化立場,既寫出了鄉村世界痛苦艱辛的生存,也寫出了一個普通鄉村女子在感情和道義上的掙扎。由此把對底層的關注,從現實生存深入到精神和心理層面。這篇小說在敘事上,人物內在世界的探索,與日常生活的呈現,編織在一起,外在生活不乏刀光劍影,內心世界同樣電閃雷鳴。置身其中,黑暗世界里那顆備受折磨的心,給我們以長久的震撼。“野貓湖”顯然不是一個封閉式的生存空間,作為衰敗鄉村的縮影,作為生存淹沒理想的隱喻,這個野貓湖,是歷史的陰影,時代的創傷和鄉村的挽歌。香兒和莊姐,和丈夫,和村長,和無賴牛垃子,在這片土地上,掙扎和抗爭,堅守和慘敗。這是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喪失自我的明證。野貓的慘叫,毒狗偷牛的猖獗,弱女子四面楚歌的生活,在鄉村大地上發生的這一切,都不是故事,不是偶然,那個善良堅韌的女性,最終越過倫理底線,親手扼殺丈夫,無疑具有更深刻的悲劇意味。“野貓湖”,這個充滿暴力的世界,村長的暴力,無賴的暴力,偷牛賊的暴力……傳統意義上平靜自然純樸的鄉村生活,一去不返,家園的喪失,與終極歸宿的懸置,帶給我們無盡的憂思。小說借兩個女人的命運,寫出了個人的悲劇,時代的悲劇,生存的悲劇,愛和情感的悲劇,以及生存焦慮,心靈焦慮和有關存在的絕對孤獨。陳應松始終直面黑暗,和黑暗中的每一個人。那些暗和光,冷和暖,彼此交錯;那些沉默和吶喊,風雨和掙扎,縱橫交織;那些沉重的生和死,作為混亂時代的尖銳追問,質疑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張楚的中篇小說《七根孔雀羽毛》(《收獲》2011年第1期),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張楚有他獨一無二的審美品質和精神追求。日常生活很細碎,太多的人習慣了重復的,無意義的時間流,即使有些遭際超出了個人的忍耐力,多半也是漠然處之不會因為某種痛苦而反抗或者呼喊。張楚的文字,不僅在無意義的生活鏈條里找到了斷裂的那個最重要的環節,而且因斷裂而形成的傷害和痛苦,也被他逐一挖掘出來;他不僅關注存在本體,也關注存在自身的陰影。在詩意的悲傷里,不斷展開被時代、生活和命運折疊的人性。李云雷評價張楚是一個“黑暗中的舞者”,的確很形象;而另一方面,張楚又是一個“晨光中的歌者”,站在黑白交界處,冷靜描繪他眼中的世界,一半是悲涼,一半是熾熱。《七根孔雀羽毛》講述了一個人生的失敗者宗建明的生活。宗建明因為妻子曹書娟出軌而離婚,與開美容院的李紅同居。在朋友康捷家偶遇前妻,要回兒子小虎的念頭日漸強烈。曹書娟和小城首富丁盛關系曖昧。最終丁盛死于謀殺,宗建明因不知情的參與而進了看守所,小說結束于透過看守所鐵窗照進來的陽光灑滿宗建明失去自由的臉上。張楚的小說總有一種沉下去的力量,向生活的深處,精神的深處,向那沒有光的命運深處,追蹤那些對人生真正有意義的微芒。
余一鳴的中篇小說《入流》(《人民文學》2011年第2期),比起《不二》,《入流》顯然寫得更重。小說從拴錢兄弟運沙寫起,描述了白臉的江上王國和霸主地位,回憶了兄弟二人造船走上販沙之路的經過,穿插兄弟二人的愛情和婚姻,最終弟弟二寶和小小葬身江底,拴錢戰勝內心罪惡感步上白臉之路。小說整體上是一種象征,和一個寓言。現實批判和反思只是一個方面。就像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爾西。”《入流》所反映的漁民原始積累過程,同樣充滿了暴力和血腥。而且只有死亡,永遠沒有真相。就像羅金寶和老三的死,如一滴水落入滾滾長江,沒有任何回聲;或者就像白臉的發跡史,沒有人知道多少血腥和罪惡成就了這個呼風喚雨的江上霸主;或者,也沒有人能說清楚小白臉脅迫傷害了多少人才換來山里孩子的桌椅書本……“這個世界要是什么都能水落石出,長江的水早就載不下這許多船。”對照現實生活,我們不能不嘆服作者眼光和語言的犀利和深刻。小說寫出了金錢對人性的異化,寫出了私欲帶來的暴虐心理,沒有正義和邪惡的較量,每個人內心都有那么多深不見底的黑暗,這種人性的黑暗與社會的黑暗,互為因果彼此糾纏,讓我們看到了燦爛陽光之下的生活真相。
凌可新的中篇小說《紙村長》(《時代文學》2011年第1期),延續了凌可新一貫的尖銳的現實批判立場。鄉村權力對個人生活的踐踏,對個人命運的改變,對鄉村社會的禁錮,真的是觸目驚心。然而貌似強大的鐵權,真正遇到反抗,其實不過紙老虎一戳就破,村長最終因為自己的殘暴而葬身獒口。小說把土改和福貴父子兩代人的悲劇,與王老財和兒子現任村長王大寶兩代人的命運,對照來寫,是對20世紀中國鄉村變革和鄉村社會秩序的整體反思。鄉村極權是如何形成的?這篇小說有制度層面的思考,也有文化和民族性格心理層面的挖掘,魯迅說,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福貴父子的反抗中,父親是主導力量,而大眾的圍觀中,同樣隱約著反抗的焦灼。作者不僅寫出了一觸即發的矛盾沖突,還寫出了問題的本質,即在民眾中還看不到真正的精神自覺,大寶村長之死也不過是傳統善惡報應的多行不義必自斃,所以小說基調尤其壓抑和沉郁,小說所指出的問題也格外沉重和意義深遠。
凌可新的中篇小說《吃狗》(《星火》2011年第1期),則是一出日常生活的鬧劇。副局長老萬殺狗,是自身欲望的延伸。也是對漆黑一團的現實的消極對抗。作者以喜劇筆法寫出了老萬的家庭生活、單位場景和內心波瀾,對這個人物有所嘲諷也不無感嘆。小說的思想指向有兩個,一是借小官僚的人生狀態反觀整體社會現實,針砭時弊淋漓盡致;二是對民間和底層的反思含蓄深刻點到即止。老吳的訛詐看似荒謬,其實是底層的一種消極姿態,帶有自我毀滅的心理沖動。與同樣置身社會底層的那個女孩子的仗義,構成了民間的兩種形態。小說中兩次寫到殺狗都是隆冬。雪夜抓賭吃了村長的黑狗,雪天鍋爐房吊死了貌似市長家的黑狗。黑白對照隱喻了現實社會和蕓蕓眾生的黑白顛倒。小說以輕松幽默的筆調給這一群小人物畫像,在黑白布景上,人性的卑劣與現實的瘋狂交織,演繹著日復一日的庸常生活。
張全友的中篇小說《豌豆黑豆和扁豆》(《山西文學》2011年第2期),寫豌豆和黑豆兄弟二人做窯毀窯的故事,從人性和國民性入手,既有批判,更重反思。小說題目讓人想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詩句。其實這樣的故事在鄉村也許很尋常,裝腔作勢吃拿卡要的上級領導,帶頭先富裕的村干部,老實本分受苦受窮的農民,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的二流子單身,這些形象在新鄉土小說中基本已經定型化了,能夠寫出新意并不容易。這篇小說突出了扁豆八叔的表面仗義,對其內心陰暗點到即止,反而有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對大哥和劉麥穗的矛盾沖突也寫得生動鮮活,尤其最后一節大哥與那頭老黃牛的交鋒,豌豆沒有勇氣向舉報自己的劉麥穗揮刀,就把一腔仇恨發泄到無辜的老牛身上。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這個不可救藥的民族啊,歷經百年,悲劇依舊。小說中隱含的反思沉重而峻急。
透過生活尋找愛
王祥夫的短篇小說《雨夜》(《芒種》2011年第1期),小說寫一個小村,一個小飯店,和一個小煤窯。快要過新年的一個雨夜,小村里的一些沒事可做的年輕人,在周口店帶領下,去村頭攔路收取過路費,遇到了吉普車司機和來尋找自己男人的小婉。在小飯店里得知真相后,周口店等人掏出身上所有的錢留給了那個可憐的女子。小說不長,卻寫得跌宕起伏,小飯店是中鋒重墨,小村和小煤窯是側鋒淡墨。細密處微風不透,稀疏處大片留白。虛實相生,耐人尋味。小說渲染了雨夜的濕冷氣息,被大車軋壞的道路在雨夜格外泥濘坎坷,而那些一個接一個走在雨夜里的年輕人,現在他們要去劫道,他們沒事可做,盡管他們對生活充滿熱望,吃著素菜,喝著淡酒,說著葷話,聽著窗外,眼前是骯臟混亂的小店,不遠處是昏暗沉寂的家園,還有稍遠處田野的荒疏,被封閉的小煤窯和那個永遠也回不了家的人。這幅畫面隱含著呼之欲出的“悲劇”二字,小說卻沒有慘痛,只有隱忍的淚和沒有說出的疼。與凄冷壓抑的雨夜氣息相對照的,是溫潤動人的普通人的情感世界。這個短篇,無論從思想性,還是藝術性看,都相當成功。
《人民文學》2011年第1期的短篇小說有3個,總體感覺都不錯。哈金的《作曲家和他的鸚鵡》,石舒清的《浮世》,東君的《聽洪素手彈琴》。哈金和東君通過鸚鵡和古琴,寫出了一種比較稀缺的人生感覺。藝術和美和情感的統一。《作曲家和他的鸚鵡》中,作曲家和女友的情感隔閡,對盲人音樂家的深刻理解,與鸚鵡的內心交流,寫得很有韻味,也很感人。洪素手對古琴的執著,和顧先生的矛盾,靜夜里琴聲,最后的再次出走,同樣寫得很有韻味,也很感人。兩篇小說中,“蜘蛛俠”的死和鸚鵡的死之象征意味如出一轍。雖然有些情節不免刻意了,不過,那一聲嘆息還是讓我們感同身受,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呢?
說說石舒清的《浮世》。石舒清的小說和他的名字一樣,舒展清朗,細膩而又悠遠。《浮世》,落滿浮塵的世事和人生,那么沉重的日子,那么尖銳的傷痛,隱藏在夫婦二人的各自生活和日常對話里,作者寫得溫和甚至不乏溫暖。和以往的作品一樣,石舒清擅長浮世繪,對生活和情感都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和穩定立場。這篇小說的敘事很有生活質感,哈賽媳婦外表的粗糲和內心的細膩,婚前和婚后的變化,形成了一種綿延不絕的力量,對生活,還有自身的隱約的質疑。哈賽媳婦在家要帶三個孩子,還要喂羊,種地,丈夫在新疆煤窯打工,日子過得很辛苦。不過她認為自己還是滿意多一些。小說中的細節富于感染力,碾米,瞌睡,借錢,還錢,電話,家長里短的絮語里,飽含著溫潤的人生理解。后來哈賽煤礦出了事故,沒了一只眼睛,給了14萬賠償,哈賽特別興奮,打電話給媳婦,簡直稱得上報喜了,電話另一端的哈賽媳婦哭了。雖然對物質生活的改善也是抱有幻想的,可是,用一只眼睛作為代價,這種悲慘的出賣,在這個善良醇厚吃苦耐勞的女子心里,還是很難高興地接受。其實是個典型的悲劇,卻被主人公喜劇化了,這種情感反差的強烈震撼,比起一味的控訴顯然來得更有力量。
付秀瑩的短篇小說《錦繡年代》(《天涯》2011年第1期),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了“我”的表哥一個有些書卷氣的小男孩,成長為一個英俊倜儻的軍人,一個小城的父母官,然后漸漸地變了,有了別的女人,有了別的問題,最后被免了職。表哥的成長主線之外,是“我”對表哥,表哥對玉嫂朦朧的情感。小說還是同繞“舊院”往事展開,童年的美好與沉靜,成就了“我”心中那個揮之不去無限眷懷的錦繡年代。然而,如錦似繡的美好記憶與向往,終究在滔滔的世俗大浪中席卷而去,在無情的歲月中有太多的迷失和遺落。小說充滿了淡淡的感傷和濃濃的懷舊色彩。李云雷在評價付秀瑩的《舊院》時寫道:“《舊院》所要做的,就是挽留住童年的世界與夢想,這可以視為作者個人重返故鄉的一種方式,但其中也包蘊著所有人類共同的‘鄉愁’。”《錦繡年代》再次打開塵封的舊院和童年,在精神上復歸故鄉,在心理上回望童年,在愛的意義上思索人生,把那一份無處停泊的鄉愁幽幽婉婉呈現在我們面前。付秀瑩擅長以滿懷柔情包容那些尖銳的刺痛,在溫暖的春日,昔年重來,成長后的無盡鄉愁,都在童年光陰的深處,在那里長久棲落。付秀瑩飽含悲憫和同情之心,以輕盈圓潤的愛的筆觸,原諒了這個世界和這一路上的所有不完美。
張作民的中篇小說《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當代》2011年第1期),寫監獄生活的小說不多,因為題材敏感。看這篇小說題目,很容易想起普希金舉世聞名的同名詩作,普希金的詩是勸導人積極向上,張作民的小說也不乏此意。石方明因情場失意殺人,被判死緩,父母得此噩耗先后告別人世,石方明深感愧對父母,無限追悔,就此對生活失去信心,絕望之下一再試圖自殺。監獄警方派其他犯人嚴格看守,卻未能打消他輕生的念頭。警方無奈決定讓一個女監重犯給石方明寫信。于是,在無法相見只憑想象和書信往來的高墻之內,石方明和孫曉燕相愛了。石方明出獄后,終于找到真正寫信給他的孫小小,盡管孫小小身患絕癥,他仍然決定和她結婚。這篇小說為我們正面呈現了獄中犯人的生活,小社會大舞臺,爾虞我詐,心計,暴力,性壓抑,多重人格,主動改造和被迫活著,還有愛和自由的渴望等等。雖然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卻具有不言自明的現實意義。
曉蘇的短篇小說《花被窩》(《收獲》2011年第1期),寫的還是油菜坡的故事,是婆媳兩代人的感情世界和彼此由隔膜到理解的過程。秀水因為丈夫去外地打工了,就和修理電視接收器的李隨有了外遇。秀水和婆婆秦晚香關系緊張,丈夫走后,婆婆經常監視她。因猜測婆婆撞見了自己偷情,遂決定百般討好,后來得知婆婆年輕時也曾經出軌,震驚之下竟然惺惺相惜,二人終于有了發自內心的親情。這個小說抓住了人物的心理精雕細刻,秀水和李隨偷情時的聯想,洗被子曬被子時的聯想,擔心婆婆發現自己偷情時的緊張,請婆婆上樓同住的忐忑,和婆婆一起吃飯時的聯想,得知婆婆年輕時也曾出軌時的聯想,都寫得細膩鮮活,映照著特別耀眼的陽光,花被窩上的那點兒印記與花團錦簇就有了無盡的意蘊,或許作者希望生活還有人生中的微瑕,經愛的陽光一曬就了無痕跡,不僅一切復歸美好,還就此有了陽光的味道。
吳中心的中篇小說《獵豹》(《芙蓉》2011年第1期),我們一直都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探尋存在的邊界,對困擾自我的突破,對未知世界的向往,在中篇小說《獵豹》中,這種探索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小說講述了兩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從中學時代,到人近中年,成長的過程一波三折,每個人都經歷了欺騙和被騙。小說背景是煤窯,吳中心沒有以底層書寫的常見方式,展示財富的原罪,和井下黑暗的命運;一夜暴富更像是一個神話,給出個人面對世界的另外一個難題。從極度匱乏到物質充足,然而,還是不滿足,還是要彼此欺騙,打開每個人內心的善惡之鏡,這篇小說要拷問的可能不僅僅是師生五人,還有大千世界的蕓蕓眾生。
丁國祥的短篇小說《靈生》(《飛天》2011年第3期),寫出了無奈的生活深處那一種近乎絕望的愛。菊英的親生父母迫于生計將其送人,養父母含辛茹苦把她帶大,菊英無力醫治重病的養母,內心的愧疚最終埋葬了自己。長大后的靈生因對父母家園的愛戀,放棄了出國。小說中既有最現實的血淚,也有超現實的玄幻。民間的虛構和夢境的真實,作為小說的副文本,其實是另一種文化的綿延,從而把現實生活的艱辛,普世情感的緬懷,生死臨界的負罪和懺悔,完滿人生的渴求,與接通古今的宿命纏繞在一起。小說對人物內心情感的把握也恰到好處,光陰漸老,舊屋傾頹,而情懷依舊。
本欄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