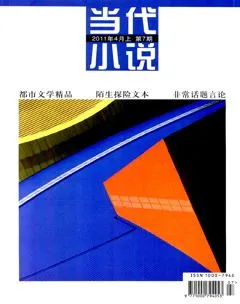心祭
依克拉姆大娘歸真的那天,達(dá)烏德在萬里之外的西藏日喀則就把消息知道了。是大娘的三兒子海順在電話里告訴他的。
那天,達(dá)烏德暈倒在昂仁縣抗震救災(zāi)的指揮崗位上,幾個(gè)藏族漢子強(qiáng)拉硬拽才把他塞進(jìn)汽車。剛剛送進(jìn)日喀則地區(qū)人民醫(yī)院,他就接到了海順的電話。
達(dá)烏德和海順兄弟三十年前是交換過口換的。那口換是只要大娘健在,他每年回老家時(shí)都要看望老人。一日老人身子不行了,不管達(dá)烏德在哪里,都必須告訴他。
大娘對(duì)達(dá)烏德有恩。
那恩,是一顆心,是一個(gè)人的一條命,也是一個(gè)人一生的一條路。
如今,大娘走了,是達(dá)烏德兌現(xiàn)承諾、應(yīng)承口換的時(shí)刻了。他卻遠(yuǎn)在萬里之外的西藏。
奔土如奔金。入土為安。這是等不得外地親人的回歸的。達(dá)烏德掐著指頭算了又算,就是能買上當(dāng)天的機(jī)票,也趕不上大娘的葬禮呀。
海順在電話的那頭說,達(dá)烏德哥哥,這些年你一時(shí)一刻也沒有忘記俺娘,每年探家都來俺家,你也替俺們兄弟盡孝了呢。再說你現(xiàn)在擔(dān)負(fù)的是國家的差事,一個(gè)省的援藏總帶隊(duì),由不得自己呀。
也是。達(dá)烏德沉思了一會(huì)兒。腦子里關(guān)于依克拉姆大娘記憶的沉淀就迅速地激活了。
當(dāng)然,最重要的是大娘的一飯之恩。
1961年春上。青黃不接的時(shí)令。
被秋旱、冬旱又接上春旱折磨了半年多的魯北平原,失去了它本應(yīng)姹紫嫣紅的春天本色,裸露在人們眼前的,除了白花花的鹽堿,就是漫天黃沙。干熱風(fēng)出奇得大,仿佛要和這片本來就貧瘠的土地較勁。小麥剛返青那會(huì)兒,原野上還能看出一點(diǎn)生命的跡象,及至清明節(jié)過后,那本來就有氣無力的小苗也慢慢地縮回去了,沙窩窩里能看得見的,也只有被埋在下面的麥苗那干枯的葉子。至于本應(yīng)蒼翠鮮亮的楊柳樹,早就被人們捋光了葉子,和野菜一起煮著吃了。最倒霉的榆樹們,榆錢剛打苞,被人們瘋搶一遍,葉子出來,又瘋搶一遍。榆錢和嫩葉都吃光了,人們又開始剝樹皮。榆樹們真可憐。遠(yuǎn)遠(yuǎn)望去,那被剝光了樹皮的榆樹們,像被剔光了血肉的人體架子,以其特有的白而赤裸,述說著天災(zāi)人禍強(qiáng)加給大自然的磔刑及其無道。
與大自然的蕭條相呼應(yīng)的,是人類的饑餓。
斷糧,威脅著所有的生命。
從春節(jié)到清明,村子里究竟死了多少人,誰也無心計(jì)算。但是,最近去世的幾個(gè),已經(jīng)很難找到人往墳上抬。都是親門近支為亡人做了祈禱之后,送到墳上草草地埋掉。甚至有的人在送亡人入土后回來的路上,眼一花,頭一暈,栽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死神一旦瞅準(zhǔn)誰家,總有人在親人們的哀嘆聲中無奈地上路。
達(dá)烏德也沒有逃過這場災(zāi)難。那一天,他和小他兩歲的妹妹索非亞像是約好了去赴一場災(zāi)難,一起躺在土炕上吐血。爹和娘眼看著一個(gè)九歲的兒子和一個(gè)七歲的姑娘已經(jīng)昏迷不醒,把所有能想的辦法都想了,能吃的東西都吃了,實(shí)在找不到能讓孩子活下去的門路了。兩個(gè)老人嗓子都哭啞了。一會(huì)兒抱起這個(gè)親親,一會(huì)兒又抱起那個(gè)親親,雖然孩子瘦得皮包著骨頭,可總是爹娘的連心肉呀。兩口子瞪著紅腫的眼對(duì)視良久,最后也只能是哀嘆一聲:咳,怕是留不住了,快去買克凡布①吧,省得孩子斷了氣來不及……
“那就快去扯布吧。”爹邁不動(dòng)兩條灌滿了鉛似的腿,瞪著絕望的眼對(duì)娘說。
娘眼睛里立刻浸滿了淚水。那一刻,她本來就黃得嚇人的臉,像是突然間又覆了一層黃表,慌汗珠子和渾濁的眼淚攪在一起,從她難堪的臉上滾落下來。
她知道,買白布對(duì)她意味著什么。作孽呀,我這不是替地獄里的小鬼拉纖么?走在去供銷社的路上,她緊緊地咬著牙關(guān),強(qiáng)撐著一步三晃的身子,像一個(gè)心無所依的孤魂。
這一切,被迎面走來的依克拉姆看在眼里。
妹子,看樣子遇上過不去的坎子了?
娘就照實(shí)說出了事情的原委。
唉,這年頭要是七老八十的大人遇上這種情況也就算了,孩子還小啊,他們是歲月的芽,是日子的根,咋能說埋就埋了呢。妹子,你先回去,讓我思謀思謀,想個(gè)把孩子留住的辦法。
像滿天烏云突然裂開一道縫,火石般的毫光立馬激活了娘那顆絕望的心。
一盞茶工夫,依克拉姆大娘真的來了。進(jìn)門把個(gè)背在肩上的口袋朝墻角一放:“他嬸子,家里也沒有什么好的,都是早些年開磨坊剩下的谷糠,趕緊給孩子兌活著弄點(diǎn)吃的,說不定這里面還能有點(diǎn)救命的東西呢。”說完,就一撅一撅地走了。
娘立刻把那口袋里的谷糠朝笸籮里一倒:呀,谷糠里居然還有兩個(gè)小米面餅子!
救命的仙丹呀!
爹順手抄起一個(gè)餅子在兩個(gè)孩子眼前一晃,那混濁的眼睛像突然開啟的電源,同時(shí)發(fā)出了光芒。接下來的狼吞虎咽,如果有如今的記錄手段,那肯定是動(dòng)物界人類這個(gè)分支求生欲望的最完美、最真實(shí)的體現(xiàn)。
半個(gè)小時(shí)前還是冥界備選的兩個(gè)孩子,一轉(zhuǎn)眼臉上就有了光澤,有了笑容。達(dá)烏德和索菲亞不約而同地看看爹,看看娘,兩個(gè)老人卻不約而同地哭了。
天不滅曹。就在那天夜里,上天落下了八個(gè)月來的第一場透地雨。那場雨下得不風(fēng)不火,不緊不慢,像一只溫柔的手,用多情的按摩把干透了的平原重新又給浸潤了。
這場雨為所有的生命注入了新的律動(dòng)。短短幾天,草綠了,鳥鳴了,青青菜、土露酸、苦苦菜、蒲公英……全都呼呼地旺長了。
達(dá)烏德和索菲亞又能到地里去挖野菜了。那天下午,達(dá)烏德早早地背回一大筐又鮮又嫩的野菜,高興地對(duì)娘說:地里的青棵棵長得真快呀。
娘說:小草和孩子一樣,有吃有喝就長得快。你能活過來,還不虧得你大娘給你送來的救命飯?記住,一輩子都不能忘了大娘的這頓飯。
娘的話,達(dá)烏德真的記住了。幾十年來,他念書升學(xué),當(dāng)兵提干,直到當(dāng)了縣委書記,當(dāng)了副廳長,時(shí)時(shí)刻刻都沒有忘記那頓飯,更沒有忘記給他那頓救命飯的依克拉姆大娘。每年回鄉(xiāng),他都去大娘家里坐坐。和大娘的親兒子一樣,嘮些居家過日子的大事小情。大娘知道這孩子厚道,很少提起當(dāng)年的那兩個(gè)餅子。只是有次論道起歉年度荒的話題,達(dá)烏德才知道了當(dāng)年那兩個(gè)小米面餅子,是大娘用兩簸箕谷糠從別人家換來的。說起這些,大娘心情很平靜。她說她見不得娃娃們受罪,如果能救活孩子的命,從她腚上拉塊肉都行。人活在世上,赤條條來,赤條條走,德行不能損。
這些話達(dá)烏德也記住了。
十五年前他在清和縣任縣委書記的時(shí)候,有一天早上起來散步,見一伙人在體育場附近的萬松園門口比劃著說什么。原來大家正在議論三官廟村一對(duì)農(nóng)民夫婦因意外事故閃下兩個(gè)孩子撒手人寰的事。他湊上去弄清了原委以后,問:這件事情村里的干部沒有報(bào)告嗎?就是那天晚上,他去了三官廟。在那里,他和村支部書記每人領(lǐng)養(yǎng)了一個(gè)孤兒。如今,那兩個(gè)孩子都大學(xué)畢業(yè)。達(dá)烏德領(lǐng)養(yǎng)的那個(gè)男孩已經(jīng)成家立業(yè)了。孩子參加工作以后,第一個(gè)月就把工資交給了他。不知為什么,達(dá)烏德沒有要孩子的工資,自己的眼睛卻濕潤了。
今天,在海順打來的電話里,聽到依克拉姆大娘歸真的消息,達(dá)烏德心里先是一震,接著對(duì)海順說了些安慰的話,自己卻一時(shí)間六神無主了。他的確想趕回去送大娘最后一程,他忘不了這個(gè)曾經(jīng)救過自己生命的老人。多么好的一個(gè)老人,善良、慈祥,雖說和自己的母親一樣,在莊稼地里苦累苦熬了一輩子,可她那金子般的心卻遠(yuǎn)在許多達(dá)官貴人之上。該去送老人一程呀,哪怕只是見上一面,也是對(duì)自己心靈的一種慰藉。他掐著指頭算來算去,除了眼前援藏工作正在抗震救災(zāi)的火候上,他怎么安排都趕不上老人的葬禮。西藏這地方離內(nèi)地太遠(yuǎn)飛機(jī)又不能直航。咳!
按照當(dāng)年的口換,他是應(yīng)當(dāng)回去的。憑著他對(duì)老人的那份敬仰與思念,他不能親自去送葬,至少也要大放悲聲地痛哭一場。
他沒有那么做。
他簡單地清理了一下辦公桌上文件,然后一個(gè)人心無所依地走進(jìn)辦公樓電梯,下意識(shí)地摁下了頂層的號(hào)碼。
到達(dá)頂層以后,他又一個(gè)人去了樓頂。
樓頂上擺放著一些機(jī)關(guān)干部業(yè)余時(shí)間養(yǎng)的花和盆景。在日喀則這個(gè)地方,能在樓頂上養(yǎng)花的日子不是很多。難得的季節(jié)啊。
達(dá)烏德站在一覽無余的樓頂。
目能所及,除了藏民的房子、藏傳佛教的寺廟、拴著哈達(dá)和彩帶的敖包,就是斑斑駁駁的高原。那高原逶迤著伸向遠(yuǎn)方,與雄偉的喜馬拉雅山連成一體,藍(lán)天白云之下,巍峨的西馬拉雅山雪峰,潔白無語而又肅穆莊嚴(yán),怎么看都像一位橫臥在祖國西南邊陲的老人,那老人慈祥善良敦厚豁達(dá)包容剛強(qiáng),像無數(shù)中國母親集體化身。那其中,誰敢斷定沒有依克拉姆老人的身影呢?
達(dá)烏德想著想著,腦海里的視像突然迅速地切換成故鄉(xiāng)一支充滿著人生終極關(guān)懷和哀婉情調(diào)的送葬隊(duì)伍。身著孝服的依克拉姆老人的親人們,哭著,走著,不時(shí)跪倒在地向前來送葬的人們叩頭謝孝……
突然,達(dá)烏德猛一轉(zhuǎn)身,從一盆正在盛開的菊花叢中,摘下一朵又大又白的菊花,朝著故鄉(xiāng)的方向,朝著喜馬拉雅山的冰川大阪,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又深深地跪下了。那一時(shí)刻,他覺得自己踏上了故鄉(xiāng)的黃土地,他融進(jìn)了滾滾的雅魯藏布江,融進(jìn)了用最純潔的母愛凝注起來的巍巍雪峰,融進(jìn)了西藏雪頓節(jié)的愉悅……
就在那一天,那一天的下午,達(dá)烏德帶著身邊的兩個(gè)工作人員,又一次返回遭受地震災(zāi)害的昂仁縣。
行前,他讓秘書把他剛發(fā)的一個(gè)月的工資全部帶上。他說,那里有他的爹娘,有他的親人,還有他的依克拉姆大娘。他說,他要去交納一份隨心的“乜貼②”。
注釋:
①可凡布:回族人死后用于裹尸體的布叫可凡布。
②乜貼:以非納稅方式周濟(jì)遭受災(zāi)難的人們所捐出的資金。
責(zé)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