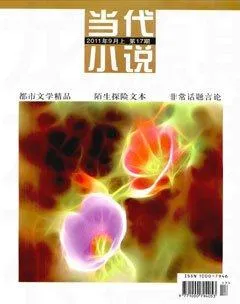清醒祭
1
南方的夏夜總是突如其來,出去的時候還尚存余溫的街道這會兒竟被潑了冷冰冰的黑墨,死氣沉沉的。星星累贅似的掛在夜空,時不時“嗖”地滑落一顆,劃得蘇小裸心煩。蘇小裸從廁所隔間的浴室走出,扒在宿舍走廊的護欄上,凝視著被他看了四年的街道、路燈、梧桐。在這四年的最后一晚,同樣的街道、路燈、梧桐卻倏然喪失了前一晚的勃勃活力,瞬間老去了。死的。是的。蘇小裸驚訝地發現,他看了四年的這些東西竟然是死的、沒有生命的,這使他失望透頂。他幾乎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于是他用架在護欄上的雙臂夾緊了自己的頭,像敲木魚樣的一下下敲打自己。酒精變成了一顆鋼針扎進了他的后腦,“啊”——他窩心地一聲粗吼,低頭,搭在肩膀上的白毛巾順勢滑下,剛好從馬葫蘆的巨大裂縫處鉆了進去。蘇小裸也不去理它,他異常清醒的思維開始游離、幻想,他想象著這條毛巾在地下道里面的歷程,或許它會永久地留在母校的地下,也算是他和黃島在這塊土地上存在過的證明。這塊毛巾,其實是他室友黃島的呢!
此刻,趴在床上的黃島像一只碩大的青蛙,他早已鼾聲四起,有一只大臭蚊子正在黃島的蚊帳外徘徊著找尋突破口。看著看著,蘇小裸的心窩泛起了漣漪。可他知道,為時已晚。他想起了剛才畢業酒會散場時于浩對他說的話,于浩說,蘇小裸,全班男生就你沒喝醉,你這人太有城府了,他們都說你不可交,讓人看不透。蘇小裸辯解說,誰說我沒喝醉?我喝醉了,我從沒喝過這么多,我頭都疼死了。于浩說,那你怎么沒哭?你看你走路都不晃的。四年啦!我們在一起四年了啊,怎么你都沒點留戀的嗎?我——,蘇小裸不知道該說什么了。他看了看周圍剛從包車里下來的同學們,確實都在哭。他們有的坐在馬路牙子上無聲地啜泣,有的相擁著把對方的脊背拍得咚咚響,有的一個人扶著梧桐樹干不停地嘔吐。他們的臉都變成了一面面反射月光的鏡子,蘇小裸能清晰地看到鏡面上的棱角、污痕。蘇小裸變成了一個被人遺棄的孤兒,除了于浩鄙夷地扔下那么一句外,再沒人理他。他孤零零地站在一群會哭的男人中間,他們的哭聲就像交響樂,而他,確乎是個不懂音樂的人。
蘇小裸確實喝多了,可他就是哭不出來也吐不出來,即便用食指去摳咽喉,也只是干嘔了幾聲,眼睛有點泛酸,倒是山崩地裂的頭疼折磨得他異常清醒。輔導員拍著蘇小裸的肩膀對大家說,互相攙扶著上樓去吧,已經很晚了,明天離校,都注意安全。蘇小裸二話沒說,拉著晃悠悠的黃島往樓梯口奔去。被失去重心的黃島拉扯著,他們倆像身負重傷的戰士,不停地撞著走廊的兩側,把一條一百米長的走廊足足走長了兩倍。
現在,所有的寢室都靜了下來。只有蘇小裸扒在走廊的護欄上,他開始像于浩質問他一樣的質問自己:為什么自己就是哭不出來呢?他確信自己已經醉了,他的沉重的腦袋正在被凌遲,眼中的景物也開始忽遠忽近,然而聽覺和思維卻異常清醒,似乎比平時還要清醒,清醒得涼絲絲的。他開始厭惡起自己的清醒,清醒使人失去很多東西,譬如勇氣。他告誡自己應該糊涂起來,在這四年的最后一晚,他必須糊涂起來,因為他喝醉了,喝醉的人不該這樣孤零零地在走廊里度過。于是,他大著膽子爬上了黃島的床。他想去給他脫衣服,想并排和他躺一會兒。因為過了今晚,他們可能再沒機會見面了。黃島猛地一翻身,把蘇小裸的手掌壓在了他后背下,壓得蘇小裸手背生疼,壓得他心怦怦直跳。蘇小裸停止了動作,就任他穿著衣服去睡吧。他坐在他的床上,定睛看著和他共處一室四年的黃島。他似乎看到他的額頭確乎多了四條抬頭紋,四年絲毫沒有改變他如嬰兒一樣的面容,卻平添了一股成熟英氣和一點狡黠的氣質。他們實在太熟了,熟得很多時候蘇小裸看黃島就像看到了另一個自己,熟得他發覺黃島在他面前就是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狡黠的氣質,這在別的同學面前是從未有過的。黃島的狡黠就像一只狐貍,嗖嗖地跑開來。無比清醒的蘇小裸的大腦變成了電影播放器,一幕一幕,像暴雨,瞬間紛至沓來。
2
夜愈發靜了。有一只黑貓站在走廊的護欄上向門里張望,它看到蘇小裸凝重的神情,竟竄到梧桐樹上逃掉了,梧桐發出稀稀落落的聲音。這時又剩下蘇小裸一個人了。他看著床上的黃島,又看了看另兩張空床上以及地上他和黃島各自的一堆行李,他們垂頭喪氣地躺在那。眼前的一切,沒法讓蘇小裸糊糊涂涂地過完今夜。蘇小裸開始回憶起許多個第一次。他想自己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如此關注、如此依賴黃島的呢?難道是第一次見面嗎?于是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倏地出現在他腦海里。他鬼使神差地抓起一個背包,退回到走廊上,重溫起了第一次走進這間宿舍的那一幕。
蘇小裸清楚地記得四年前父母陪伴他走進這間屋子時,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貼在門上的四個名字,他們按順序是這樣排列的:蘇律、黃島、宋科學、王占暉。后來王占暉因為轉專業,搬離了這間宿舍;宋科學因為交了女朋友,便借口跟學校打申請,租房去了校外;這間屋子里便只剩下了他和黃島,那時他還不叫蘇小裸,他叫蘇律。蘇小裸依稀記得他推門走進這間宿舍時首先看到的就是門左側黃島的床下一個撅著屁股在拾掇東西的南方婦女,然后就是直挺挺站在婦女身邊的黃島。黃島儼然一副南方農村高中生的模樣,他一米七的個頭,面容清秀,明顯搭配不當的衣著平添加倍了他淳樸的氣息,淳樸得很自然讓人想到一個詞——可憐。當時,黃島沖他笑了笑,示意了一下友好,接著便開始跟身旁的婦女喋喋不休。他們用蘇小裸完全聽不懂的南方方言在爭執一些在蘇小裸看來完全沒有爭執必要的問題,蘇小裸從他們的動作中判斷他們是在為一些物品的擺放位置這類的生活瑣碎各執一詞。看得出,黃島是一個無論任何事情都很有主見、不喜歡被人束縛的男孩,甚至,在他身上,蘇小裸嗅到一些似乎是初中生才該有的叛逆。
后來,黃島不無狡辯地對蘇小裸說,那不叫叛逆。黃島說他只是想堅持屬于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彼此熟識后,黃島在向蘇小裸喋喋不休地述說自己的母親是如何捆綁著他、像對待孩子一樣管轄著他的時候說道:我只想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外這兩年,我已經習慣了按自己的喜好生存,什么時間該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喜歡隨性,而不是整天被別人嘮叨,嘮叨著天冷了就一定得多穿衣服,嘮叨著每次吃飯都拼命給自己夾菜。黃島說,一家人還這樣子,我真是不習慣,這也是我為什么放長假都不愛回家的原因。后來,當黃島把他的“一家人”理論應用到蘇小裸身上也如是要求蘇小裸的時候,蘇小裸竟然倍感光榮。可對于黃島因此而很少回家的想法,蘇小裸是有些難以理解的。作為北方人的蘇小裸,每年只能回家一次,所以他斷不能理解黃島的想法。他對黃島說,你就是被慣壞了,你就是太叛逆了,你二十歲的人了還青春期,我鄙視你!黃島笑嘻嘻地辯解說,大哥,這不叫叛逆好啵?就算是叛逆,那也是“高級叛逆”。不過我確實知道自己是被慣壞了,慣出個性來了。在家我媽慣著我,出來后碰到你慣著我。對了裸裸,給我交五十元話費去哈!我身上沒零錢了。蘇小裸說,我要是你老爹,早就KO你了,敢跟長輩使橫。說著,蘇小裸一個拳頭砸在了鐵床扶欄上,疼得他哎呦哎呦叫了半天。黃島早已揚長而去。
自然,蘇小裸是喜歡這樣的聊天的。他知道黃島也是喜歡這樣的聊天的。只是他不知道黃島的喜歡究竟攙雜了多少習慣成自然的成分,蘇小裸會時不時地拿一個得失的天平來衡量他和黃島。黃島會不會在利用他的感情解決一些生活難題?比如手機話費或者洗衣服?他究竟給黃島交了多少次話費、洗了多少次衣服了呢?恐怕他自己也記不清。
以前黃島不回家的長假,蘇小裸一般是這樣度過的:白天陪黃島去逛街買衣服,偶爾買完衣服兩人便去街心公園和清水湖吹吹風。說買衣服倒是真的,說起逛街就有些牽強了,因為那根本不叫逛街。黃島不喜歡逛街,但他需要有人陪他去買衣服。他一般走進一家店,用雙眼快速將所有衣服秒殺一遍,有時候根本不需要走進店面,在門口一晃,黃島就可判斷出有沒有他想要的衣服。黃島往往是心里想好了衣服的樣子,直接去找;或者之前看好了某家店某個位置的某件衣服,直接去試穿。他偶爾征詢一下蘇小裸的意見,有時候根本不問,穿著合適就直接買下走人。所以,每次跟黃島逛街,蘇小裸都有些失落:打發時間的目的沒起到,從郊區跑到鬧市融入鬧市的目的沒達到,幾十分鐘甚至更短的時間里,逛街就結束了。偶爾在清水湖聊天倒是蘇小裸心里盼望已久的,按理說每天黏在一起的兩人話是早就說干了的。可是一到清水湖,黃島就變成了一只興奮的大雁,他躍上湖邊的長椅,迎著晚風張開雙臂,興奮得像一個詩人。這個時候,在蘇小裸眼中,黃島變成了一個騎士。他時而跳上跳下,時而順著臺階下到湖面上。總之,黃島是興奮的。興奮的黃島有時會說出一些蘇小裸不知道的事情。黃島給他講自己的小時候,黃島似乎能確信他講的都是對蘇小裸來說很感冒的事情。蘇小裸聽著黃島以前的事情,就像聽說書的在講故事。那些與蘇小裸所經歷的北方城市生活大相徑庭的南方鄉村開始像雨后的春筍在蘇小裸的心底冒尖,像沁人的甘露一滴滴淋在蘇小裸的每一寸汗毛上。然后蘇小裸就有些悵然若失,他發現自己并不能完全了解黃島,這在每次黃島的高中同學來看黃島,兩個人坐在走廊里叼著小煙的方言談吐中便可見端倪。那時,一向惜字如金也從來不見他抽煙的黃島變成了另一個黃島——一個從并不遙遠的附近一所鄉村高中走來的黃島。蘇小裸斷定,他和黃島之間有著近乎二十年的空白。這空白,時常讓蘇小裸心生恐慌。
蘇小裸恐慌的心卻在黃島的另一重敘述中變得陌生起來。黃島說,我在寫一部玄幻巨著,暫取名《狩妖》。蘇小裸沒多問,一下子沉默了下來。一個屋子里住著,蘇小裸竟然不知道黃島在寫小說。沉默沒有把氣氛變成冰山,甚至順理成章、不顯任何尷尬。他們吹著晚風,各自若有所思。突然,黃島問,蘇律,你不高興了?沒有,我挺高興。蘇小裸說。騙誰呀!你的情緒總是直觀地寫在臉上……黃島也不多問,默默地低下了頭。
3
小長假的晚上一般是這么度過的。一份螺螄、幾兩豆干、幾瓶啤酒,打包買回后擺在宿舍的某張桌子上。這似乎早已約定俗成。有一次,黃島喝醉了。那次黃島一邊喝酒一邊忙著給人發短信,蘇小裸不知道他是給誰發。蘇小裸的心里跟長了刺一般。他一股腦,灌了一瓶進肚。停下手里的短信,黃島沒說什么。他就拿起酒瓶,“女人都是賤貨!不搭理她就反倒這么勾引你!”黃島抹了一把嘴,“對不起兄弟了!”之后“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整瓶酒瞬間消失。那晚對蘇小裸來說也不知是盡興還是悲傷,總之他越喝越起勁,更像是在賭一口氣,賭黃島一味地發短信不理他的那口氣。他覺得黃島實在太沒勁了。黃島漸漸覺察到了蘇小裸的情緒變化,他放下手機,啟了瓶白酒。半杯白酒下肚,黃島的臉紅成了燈籠。他的那句來得莫名其妙的“女人就是賤貨!”卻反復在蘇小裸的腦海里盤旋。在黃島說完那句話之后,他就開始醉了。他突然用雙手捂著臉、一咧嘴埋著頭哭了起來。蘇小裸趕緊去撫摩著他的肩。他第一次看到一個二十幾歲的人在自己面前哭,并且哭得嗚嗚響。黃島的鼻涕蹭了蘇小裸一身。他站起來要撒尿,說著就沖蘇小裸的臉盆過去了,蘇小裸驚得手足無措,不知該不該拉住他。他想伸手,但內心里似乎又默許或期待著他的舉動,那更像是崇拜偶像所獲得的回贈,只是真要接受這樣的回贈多少讓蘇小裸厭惡起自己。蘇小裸的期待似乎夾雜著更多的好奇,好奇將要發生的一切。思忖繼續的同時,黃島早已泄洪完畢。泄完洪的黃島竟像個地痞無賴半提著褲子轉頭沖向蘇小裸,像個傻子般一邊玩弄著自己的陰莖一邊淫笑。蘇小裸頓時慌張起來,他不知道自己該以什么表情來面對眼前的一切。他心里應該是和悲傷相反的情緒,但是是高興嗎?他高興看著黃島在他面前衣不蔽體嗎?又好像不是,否則他何以主動制止了黃島的行為呢?他協助黃島提上了褲子,拉他坐了下來。蘇小裸沒理會他,他去倒臉盆,然后拿拖布。等蘇小裸收拾完回來時,黃島早又吐了一地,屋子里充斥著腐臭的味道。在這腐臭的味道沖擊下,蘇小裸卻異常清醒。蘇小裸百思不得其解,人真的會醉成這么個樣子嗎?吐完后的黃島似乎也清醒了一些,他罵了蘇小裸一句,蘇律,我操你媽!蘇小裸說,黃島你不能這么罵我!黃島推了他一把,怎么地?我還想打你呢!說著他“啪”一個巴掌扇在了蘇小裸的臉上。蘇小裸剛要回敬他,卻聽他低著頭的嘴里反復念叨著:蘇律,哥們。不,兄弟,你害苦我了,你害苦我了,你害苦我了……伴隨著這一聲聲的“你害苦我了”的是黃島接二連三的幾個巴掌,只是越來越輕,更像是對先前那一記重擊的撫慰。最后,黃島開始了第二撥的哭泣。蘇小裸收回了舉起的手,眼角也濕了一行。他不知道自己這是怎么了,究竟是一種釋放還是自責,他是看不得黃島傷心得這個樣子嗎?應該是,他不確定。
那天夜里的情況是這樣的:睡到半夜后,黃島突然高喊一聲把蘇小裸驚醒了。驚醒時,蘇小裸發現黃島已經爬上了他的床。那時黃島早已醒酒了,但他卻厚顏無恥地要求和蘇小裸睡一張床,并且在這個時候蘇小裸才有了除了蘇律以外的這個新名字。黃島是這么叫的,“裸裸、裸裸”我要跟你睡!他滿臉邪笑,直挺挺地壓在了蘇小裸的身邊。蘇律問他為什么叫他“裸裸”。黃島說因為你睡覺喜歡打赤膊。蘇律看了一眼黃島,整潔的睡衣穿在他身上很有暴發戶的味道。黃島說,你可是咱們學院的大詩人,應該有個筆名。咱就叫“裸裸”了,多個性。后來蘇律想了想,還是改成了小裸,蘇小裸。
那晚的蘇小裸體會到了失眠的痛苦。他從小到大從沒跟別人擠在一張床上睡過。而且宿舍的床實在是不夠寬綽,很多時候為了不擠到黃島,他都得側著身。黃島的鼻息像小熱風機一下下地從背后呼在他的耳根、脖子上,他的身體器官就不知不覺地開始了變化,那一晚,痛苦與焦灼、等待與期盼襲擊了蘇小裸的魂,他盯著電風扇,久久難以入睡。夢境就史無前例地奔放著,他夢見黃島騎摩托車載著自己去郊游,他從背后抱著黃島的腰,幸福得在夢里笑了起來。
那晚的情景竟然和現在尤為相似,不同的是,現在的蘇小裸是和黃島躺在拼起的兩張床上。蘇小裸時不時地翻身看看黃島。黃島早已鼾聲如雷。
4
蘇小裸開始仇恨起自己的清醒來。清醒,一切就都得按常理出牌。那么今晚,就將是個再平凡不過的夜晚了。可是今晚是自己能預見的時光里與黃島共處一室的最后一晚了,難道不該發生點什么嗎?“應該發生點什么”這個想法頓時讓蘇小裸既焦灼又羞愧。他不知道一直以來黃島是怎么看待他蘇小裸的。當然,在他面前,更多時候黃島都是樂觀并樂于開玩笑的。黃島會故意把兩個人的寢室制造出和其他任何寢室沒有差別的氛圍,很熱鬧,讓蘇小裸不覺得他們的寢室里少了兩個人。蘇小裸突然覺得黃島的這種氛圍制造或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回避,回避觸及一些令兩個人都尷尬的話題。蘇小裸想,黃島可能在骨子里是厭惡他的,因此在這四年的最后一晚他故意讓自己鼾聲如雷,過了今晚,他就熬到頭了吧?這樣想的時候,蘇小裸冒出個想法:要以畢業為界限,主動割斷和黃島的一切聯系。這難道不是一個好機會嗎?畢業了,以后換的新的聯系方式不告訴他,QQ也刪了他,那樣自己就可以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了。蘇小裸想,假使黃島主動聯系他呢?那就隨他去,如果黃島主動聯系他那就隨他去,否則自己絕不會主動再和黃島有任何瓜葛。那么,黃島真的會在畢業后主動聯系自己嗎?比如費盡心機地搞到他最新的聯系方式,或者強硬地對他吼:你膽敢不和老子聯系,老子滅了你!蘇小裸是期待這樣的怒吼的。他突然很想爬到黃島的床上,把那次挨他的幾個巴掌一股腦回敬給他。
思維在天馬行空一番過后,破曉前的疲憊把蘇小裸推進了夢鄉。他醒來時,黃島遞給他一瓶綠茶。黃島說,喝了它,醒酒的。你昨晚也肯定喝多了。蘇小裸心中有一絲小小的感動。他定睛看著黃島許久。黃島說,唉!打住!得,今天不適合煽情。今天就是普通的一天,過了今天,一切依舊。黃島轉身又笑嘻嘻地說,我昨晚真是喝多了……你扶我上的床?嗯。蘇小裸說,廢話,不是老子你還想是哪個美女怎么的?美女進不來咱宿舍。蘇小裸邊說邊覺得自己的話實在有點無聊,也有點虛偽了,這跟沒話找話差不多。難道他害怕尷尬在今天產生嗎?他不知道。黃島翻了個白眼,狐貍般地諂笑道,那你沒把我怎么地吧?蘇小裸揚了揚頭,看似若無其事地說,嘁!你一個男的,我能把你怎么的?沒興趣,再說你離帥哥實在有點差距。哈哈,那就好那就好。黃島像放了很大的心似的。
蘇小裸的思維總是會慢半拍。在說完這幾句的數秒后,他突然為黃島剛才的話有點來氣。再過數秒,他又有點小喜悅。他想,莫不是這小子渴望和我蘇小裸發生點什么嗎?哈哈!總之,他竟越想越高興。推開門,他看到太陽仍舊高高地懸在半空中,和每天并沒什么不同。
蘇小裸若有所失。他想,假使很多年后,他還會記得自己曾經住過的寢室、在墻上刻過的字嗎?自己的母校、母校上空的太陽會知道他來過這里嗎?或許,很多年后,連他自己都會忘了自己曾經來過,都會忘了這個和自己同一個屋檐下住了四年的兄弟。
蘇小裸說,黃島你幾點鐘走?黃島說,反正我東西都搬差不多了,我又是在本市工作,天黑之前背包走人不耽誤明天早上上班就行。蘇小裸說那咱們一起走吧!黃島說,好的。
氤氳中黃昏終于來了,黃島并沒有等蘇小裸。于浩幾個人要送蘇小裸。蘇小裸對黃島說,一起聚聚再走吧?黃島說不了,和于浩沒那么熟。我單位臨時有點事要早點回去。畢竟我試用期,身不由己啊!
就這樣黃島走了。
蘇小裸在宿舍樓底下捧著于浩買的半個西瓜,拉著行李箱打算往火車站趕的時候,接到了黃島的電話。他沒來得及接,黃島就掛斷了。蘇小裸迫不及待地跟于浩告別,然后拉著行李箱、捧著西瓜、像個要抓住時間的乘客一路小跑著往公交車站趕去。他一邊趕一邊撥通了黃島的手機。他停了停,竟有些緊張。
你剛才打電話有事?
噢,現在沒了。嘿嘿。我忘記帶硬幣了,想讓你送來一個。不過,我剛才碰見了同學要了一個。
噢。蘇小裸不知道說什么了,但沒掛電話。
黃島也沒掛斷電話。
他們隔著電話聽著彼此并不勻稱的呼吸。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這一次尤為漫長。
許久,黃島說,裸裸,我會想你的。以后你要常來找我玩,你知道的,我——很多生活上的事——我都弄得——亂七八糟的。
蘇小裸意識到自己在流淚了。在他光滑的臉頰上,他的兩行淚就像泉水涌了出來,一滴推搡著一滴,迫不及待地爭搶著,連成了兩條線。他第一次懂得悲傷。悲傷得徹底。此刻他哭著,卻并沒喝醉。他像重新活了一遭一樣,清醒地流著淚,它們像他多年前剛知道悲傷這件事的時候一樣地流出,純凈地滑落。
多年前?那是什么時候呢?四年前嗎?絕不是。因為四年前的這個時候,他,他和他的兄弟黃島,正在南北兩個方向、在各自糊里糊涂的生活中天真地沉睡。
責任編輯: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