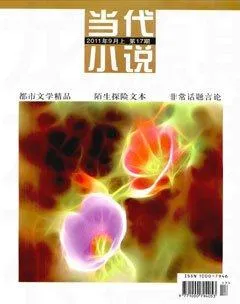被風吹走的夏天
張魚背著沉重的書包,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牲口欄里,娘正提著一桶稠稠的小米粥往牛槽里倒,旁邊一頭出生不久的小牛睜著清澈的眼睛望著張魚。
張魚埋怨道:“爹呢?不是說好去接我嗎?害我等了半小時才回來。”娘沒抬眼,還盯著牛欄,“你爹一大早就看活兒去了,人家催得緊,再說,你老大一個人了,這點兒路叫個啥?娘早些年……”
沒等娘說完,張魚的腳就邁出了牛欄,一邊向屋里走,一邊說,“我倒不如一頭牛了,哼哼。”
娘放了桶走到灶間,從鍋里拿出還有點熱氣的饅頭。鍋里還有蒸的白片魚,這種魚雖然刺多,但新鮮味美,放上蔥絲清蒸有一種特別的香味,是魯北一帶的家常魚。娘說,“你將就著吃幾口,中午咱包韭菜餡餃子吃。”
張魚搬了馬扎,坐在鍋臺前大口嚼起來。一會兒的工夫,半碗白片魚,兩個饅頭就進了肚。又去缸里舀了涼水咕咚咕咚地喝飽,抹抹嘴,走出了家門。
張魚是去找同班同學張旺。
到了張旺家,看到他家新漆過的大門緊鎖。門左邊的大槐樹下,張旺的老奶奶敞著衣襟扇著蒲扇,咧著沒牙的嘴沖著張魚嘿嘿直笑,“誰家的小子啊,長這么高了,找旺嗎?跟他爹打魚去了。”
張魚想去壩下看張旺跟他爹打魚,又瞧見日頭漸漸高起來,就悻悻地往家走。
回到家,張魚走到灶間,問娘有西瓜沒。娘說,沒買。張魚嘟囔,真是的,夏天哪有不吃西瓜的。娘說,你到小菜園摘根黃瓜將就著吃吧。張魚抬高了音兒,黃瓜是黃瓜,西瓜是西瓜!咋能一樣呢?他狠狠地走進自己屋,將門咣地關死。躺到炕上,翻了幾頁《意林》,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張魚夢見了好大一片地,枝藤蔓延,一個個圓圓溜溜的小腦袋探出葉間,烏黑的眼睛沖著張魚一眨一眨的。張魚拿一個在手里,小東西竟然張開嘴,紅通通得像個無底洞向張魚咬過來。張魚啊的一聲驚醒了。張魚抹抹頭上的汗,一邊下炕,一邊想著,那小東西摔到地上時,竟然變成了一個西瓜!
爹回來了,娘正把餃子往大鍋里面下。韭菜的香味彌漫著整個灶房,難怪人家說頭茬的韭菜香死人呢。
在飯桌上,張魚說,爹你買幾個西瓜吧!我想吃西瓜想得要命。爹說,咱家啥水果沒有,桃,杏,小甜瓜,脆瓜,就是沒有西瓜,你不吃不行啊。張魚說,爹,我真就想吃西瓜,特別想吃。爹說,你這孩子長饞病還是咋的?張魚說,爹,我真想吃,做夢都想。爹推了碗筷,哪來這么多熊毛病,愛吃不吃!娘也說,你這孩子。
爹到鄰村看承包工地的進度,張魚氣鼓鼓地又回了屋。娘要去河灘下的棉花地,問張魚去不去,張魚想想躺著睡不著也難受,就答應著起來。
張魚家的棉花地,就在家北,那條河叫幸福河,是德惠新河的一條分支。常年河水清澈,河兩邊是村民開墾的田地,有種棉花的,種菜的,間或還有一棵棵的桃樹。
棉花離地已經有一尺高了,開始分杈。娘放下水桶給棉花打杈,張魚則站在河邊看河里插的漁網。張魚想,那些網想必就是張旺家的吧,聽娘說運河里能出不少的魚呢,張旺家就靠這條河發了財。
“快幫我打桶水來,早干完早回家。”娘喊。張魚忙將目光從河里收回來,向棉花地跑過去。
張魚去河邊裝水時,發現河邊果然有好多魚。張魚用水桶去打,魚兒們就呼地一下散了,東游西蕩的一會兒又聚了起來,很有意思。張魚就順著河邊追那些魚兒,不知不覺追到了橋下。
張魚站住了,眼前一片好大的西瓜地,跟夢里一樣!他扔下水桶跑過去,西瓜蔓又長又粗,里面一個個或大或小的西瓜像玩捉迷藏的孩子在枝葉間似露不露。張魚向左邊的看瓜棚望去,沒聲息也沒人影。張魚咽了口唾沫,蹲下身搜索著眼之所及處的西瓜,他伸手摘下一個大點的抱在懷里跑向河邊,扔進水桶。張魚提著水桶鉆向一叢高高的蘆葦,蹲在里面用拳頭把西瓜一砸兩半。西瓜不熟,瓜籽還沒有成型,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直沖鼻間。張魚咬了一口,呸地吐到地上,接著站起來,狠狠地扔向河里。
張魚喪氣地站在橋下,他仰頭向上看,這時正好有一輛車從橋上開過。從車廂沒遮好的帆布看到,車上拉的是西瓜。
張魚的眼睛隨著那輛車走著,忽然,一陣刺耳的剎車聲,車猛然停住,接著后面跟的車瘋一樣頂了上去。
天上飛下好多好多的西瓜,鋪天蓋地的。
那個夏天,一輛貨車因司機打盹沖下幸福河橋,車掉下時,恰好砸到了高中生張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