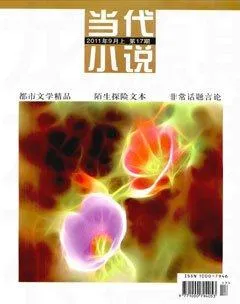冬天不覺得冷
一
零點,我去三八路的永和豆漿吃飯。我是那種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人。一到深夜肚子里必須進點東西。我所在的這座小城,24小時營業的餐館,除了永和豆漿,就是火車站附近的小店,那邊太臟我不愛去。
我哈著手推開永和豆漿的玻璃門,門上覆著層熱氣,我在上面留下一個清晰的掌印,將屋里的一些場景透露到大街上。這個點來吃飯的人不多,店里的燈沒有全開,光線有些暗。一個女人穿著白色的羽絨服,好像是艾格牌的,她正低著頭小口小口地喝豆漿,旁邊坐著一個健壯的男人,正在給她說什么,她不時笑笑。男人的嘴角沾著點東西,她拿起餐巾紙輕輕地給他拭去,那男人老老實實坐在那里一動不動。
點餐的時候,收銀員問了我好幾聲,我也沒想起吃什么。后來我點了份煮的牛肉沙河粉。找個角落坐下后,點上一支煙,才想起小票還沒交給服務員。我沒像以往高聲招呼服務員過來,而是走過去把小票遞給她,然后指指自己坐的位置。等餐的時間很漫長,我低頭翻看桌子上永和豆漿的企業文化報,報紙上有幾處油漬,估計是有人邊吃邊看落到上面的。我只揀上面的標題看,上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讓我很難看進去。我開始擺弄面前的筷子,先把兩根筷子對齊,在桌子上蹾蹾,然后再把它們放倒在桌子上擺齊。如此不知道擺弄了多少回,飯才上來。碗里冒出的熱氣,把眼鏡糊住了。我沒摘眼鏡,視線模糊著吃。才吃幾口,就覺得飽了。
平靜中突然發出“咣當”一聲,我趕忙把眼鏡摘下,用餐巾紙擦拭,戴上后掃掃屋里,她和那個男人剛才坐的位置空了,桌上只剩下兩只白色的碗。我愣了一下,然后起身出了永和豆漿。
外面很冷,身上的熱氣如同一下被偷跑了,身子不由自主地繃緊。一輛車后面的尾燈就像一對紅紅的眼睛,正慢慢駛去。我鉆進車里,把車啟動開,沒等預熱就掛檔起步。開到一個十字路口,正亮紅燈,那輛車沒有停,急馳而過。我把車剎住,突然意識到往這邊正是回家的相反方向。我趕忙掉轉車頭。心里問自己,這是怎么了?
大街上空蕩蕩的。路燈昏暗,仿佛就要沒電了。我清晰地聽到車輪胎和馬路摩擦發出嗚嗚的聲音。車燈像推土機一樣在路面上推過。我打開車內音響,是一個男人喑啞的聲音。這車自買了以后,這張CD塞進去就再也沒拿出來。他唱道:
愛曾經來到過的地方
依稀留著昨天的芬芳
地熟悉的溫暖
像天使的翅膀
劃過我無邊的思量
相信你還在這里
從不曾離去
……
車開yQwAfyfSoHFzLYvT0G2f2Q==到德興路,我發現路邊有個裹著厚厚冬裝腳步匆匆的行人。我想靠邊停下問問他要去何處,我可以把他送過去。這個念頭剛剛閃過,車已經跑出老遠。拐過彎,遠遠地就看見我家小區門口亮著的那盞燈,這時候我突然有一種感覺,這是行走在今夜?昨夜?還是前夜?
小區里的樓在黑暗里,像一個巨大的立方體。偶爾有扇窗戶露出微暗的燈光。我想,那是主人剛剛下班?還是有心事睡不著?
車庫的遙控電動門吱呀呀地打開,我在車里卻愣住神。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那個喑啞的嗓子已經啞住,我才清醒。把車停好,機械地拿包,摸索著打開單元的防盜門,一股溫暖潮濕的氣味撲面而來。在踢踢踏踏的腳步聲中,樓道里的燈亮了。開開房門,把客廳里所有的燈打開,屋子里的一切是那么凌亂,突然讓我說不出來的厭倦。脫掉夾著寒氣的外套,隨手掛在椅子上,那上面已經掛了好幾件衣服。沏一杯濃茶,然后打開電腦。電腦鍵盤上都是煙灰,低頭吹吹,煙灰飛到桌子上就像沙灘上的幾處鳥爪痕。我點上煙,這時候發現煙灰缸里滿滿的煙蒂。剛想倒到垃圾桶里,卻發現那里面更滿。用腳往下踩踩,騰出個空兒再倒進去。登陸QQ,上面有幾個發亮的動物像,我給他們逐一說了句,你好,吃了么?結果是沒有一個回話的。我只好上幾個門戶網站看看有什么新聞。看了一會兒,找出沒有寫完的小說,沒敲幾個字,腦子就空蕩蕩的,只好關上電腦。
沙發上凌亂不堪,皺皺巴巴的沙發罩上有一床沒疊的被子和一個癟了的枕頭。我躺到上面,開始擺弄手機。不自覺撥了一個號,電話那頭傳來的是一個女人冷冰冰的聲音,緊跟著是一串英語。我說,水費卡放在哪兒了?電話回復我的卻是嘟嘟的聲音。掛了電話,我用遙控器打開電視,一個臺一個臺地過,不是肥皂劇,就是電視購物的廣告。
我突然想起陽臺上的花,趕忙接水澆花。那花已經低頭耷腦,也不知道能不能緩過來。陽臺上還有一堆襪子,放在那兒估計已經很久,我又把襪子泡到盆里,才回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抽了會兒煙,喝了會兒茶。看看手機已經凌晨三點,卻沒有絲毫的睡意。
電視里一對男女正在吹噓某種品牌的表多么好,多么好。產自瑞士,鑲滿天然鉆石,但是價格有些可疑。屁股底下有些硌得慌,拿出來是本書,翻翻,看了幾行,就隨手扔向茶幾,可是沒扔好,書掉到沙發底下。我俯下身,摸了半天,沒找到書,卻摸出一把沾滿灰塵的紅色梳子,上面還沾著一根長長的頭發。我小心翼翼地把梳子和那根長發放進電視柜下面很少打開過的抽屜里。
這時候洗手間的下水道傳來一陣刺耳的嘩嘩排水聲。不早了,我提醒自己該休息了。我站起身推開臥室的門,打開燈,燈很亮,讓我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雙人床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
我嘆口氣,把燈關上,然后回到客廳躺在沙發上。
二
醒的時候也不知道幾點。根據我的起居習慣判斷,應該在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之間。外面時不時有行人和車輛經過的聲音。還有微小的聲音,似乎是舊報紙或者方便袋在風里翻舞。窗簾沒有拉嚴,陽光透過縫隙灑在屋里和我的臉上,讓我又有些迷糊。渾身疼,估計是長久一個姿勢造成的。我仰面朝天地躺著,揉揉腫脹的眼睛,盯著天花板的一個角落。那里有一只黃豆粒大小的蜘蛛趴在網里一動不動。前年的時候,它和米粒般大小。它和我一樣屬于夜里歡,白天沒精神的主兒。看情況它比我還要懶些。我的視線挪到天花板上掛著的圓形節能燈上,燈的周邊黑乎乎的,好像有三年多沒清掃過了。過去每逢春節家里都會做一次徹底的大掃除。我又閉上眼睛,昨天晚上夢里的一些片段跳躍出來,說來奇怪,這三年多我總是做同樣的夢。這讓我有些恐懼睡眠。我曾試圖用酒精改善我的睡眠質量,盡管我酒精過敏。可是除了增加癢得恨不得撓破的紅色斑塊,以及天旋地轉和嘔吐,睡著后那個夢還是無法擺脫。后來我只能放棄擺脫它,每天凌晨閉上眼睛以后,我在一邊看著它發生一遍,才沉沉睡去。
盡管不想起來,但我還是強迫自己起來,要不很快天就會黑了。我伸胳膊蹬腿鬧騰了幾下,掀起被子從沙發上爬起來。
刷牙的時候,在鏡子里我發現額頭上的皺紋比原來清晰。昨天好像是兩條深的,一條淺淺的。今天那條淺的,也非常明顯。我用手試圖撫平,松開手后,皺紋似乎更深了。我抹掉滿嘴的牙膏沫,無奈地沖鏡子里的那個開始衰老的男人笑笑。鏡子下方的置物架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我順手拿起一瓶看了看,是瓶女士潤膚霜,保質期已經過了一年,瓶身有些臟。我打開水龍頭,反復地清洗,直至光潔。然后我小心放回原處。
幾滴晶瑩剔透的水珠掛在瓶身上,我望著愣了會兒神。
我打開飲水機的開關,水稍微熱點,就沏了杯蜂蜜水。一起來喝杯蜂蜜水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之所以養成這個習慣是因為有個人曾對我說過,人經過一夜睡眠后,體內大部分水分已被排泄和吸收,這時空腹飲一杯蜂蜜水,既可補充水分,又可增加營養。
喝完蜂蜜水,我抽了根煙,然后開始準備早餐,確切地說是午餐——一桶康師傅方便面。由于水不是很熱,面沒完全泡開。打開紙蓋,飄出一股食品添加劑的味道,我的胃頓時有了反應,一股酸水從下往上直涌嗓子眼。我生生又給咽了下去。邊吃邊打開手機看未接電話,其中有好幾個是公司打來的,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情,他們是不會給我打這么多遍的。我一邊吐嚕吐嚕吃著面一邊回電話,是小謝接的。她說,合肥的張總今天晚上到。張總是我多年的客戶,和他的業務占了公司業務的三分之一,大家一直合作得很愉快。我說,晚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實在脫不開身,你們把張總陪好。就說我出差了。
方便面的湯味道很鮮。可是面和我的胃口沖突,一大半面沒吃下去,卻把湯喝完。桌子上已經堆了九個紙桶,還有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屋子里臟兮兮的,我有些發愁。從茶幾的抽屜里找出記事本,翻家政電話的時候,我看見記事本里夾著一張照片。端詳端詳,照片上的人既熟悉又陌生。我接著往下翻,翻到有幾行圓珠筆寫的文字的地方,那是個醋熘白菜的菜譜。我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完,然后把照片夾了回去。
沒過多久,家政公司的人就來了,是一男一女,看樣子像一對夫妻。我領著他們在屋里轉了一圈,交代他們什么地方需要清理,什么地方需要打掃。交代完,我才出門。
大街上和昨天一樣,車來人往,我想他們什么時候才能不再忙碌?
經過第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一段對話:
“明天上街咱們騎自行車。”
“為什么?”
“你看人家那一對,多幸福。”那雙眼睛里盛開著羨
慕的花朵。
“怎么了?”
“女的坐在后座,頭埋在男人的后背上,多暖和啊!”
我的耳邊響起自行車的車鏈子咯吱咯吱的響聲,后背上感覺到那張溫潤的臉。
三
下午的豪門茶莊安靜,茶煙裊裊。
我招呼經理,一個三十上下的女人,“哥們,下棋啊。”
我很早就認識她,因她性格像個男人,所以我稱呼她“哥們”。她說友誼長久,對此稱呼不反感,因此我就這么喊了下去。
邊擺棋子,她邊說,“昨天是九比十,今天一定扳回來。”
“憑你那智力,肯定是幻想。”我把煙、打火機掏出來放在桌子上。
棋下得很認真,兩個人基本上沒說話,只聽見落子啪啪的聲音。后來因為她要悔步棋,我不同意,兩個人爭執起來,旁邊的服務員抿著嘴偷樂。
這子還沒完全落下,怎么算悔棋呢?”她眼瞪得溜圓。
“怎么沒落下呢,明明是落下了。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是承認耍賴,就讓你悔。”我又點上一根煙。
她“呸”了一聲,“你少抽點煙吧,熏得我頭發、衣服上都是煙油子味,不知道的還以為我抽煙呢。你讓我怎么找男朋友。”
“抽完這根就不抽了。”我應付道。
豪門茶莊墻上掛得表好像不準。下了幾局棋,時針也沒轉一圈。我不由得有些焦躁,趁她思考的時候,起身看看擺在貨架上的茶葉。貨架上有一層灰塵,我抹了一下,看看變黑的手,心想,多久才能落這么厚的灰塵呢?
“你干什么呢?快過來下棋。”看她表情似乎是想到一步妙棋。
我慢吞吞走過去,先從抽紙盒里抽出一張紙,仔細擦手上的灰塵,擦完了,才看看棋盤,摸起棋子就放下去。她又開始思考。
我招呼服務員小靜,“妹妹,倒杯茶。”
小靜端上一杯日照綠,泡開的茶葉在杯底湛綠湛綠的,冒出的熱氣帶著清香。我吹吹飄在水面上的茶葉,抿了一口。然后問小靜,“你在這兒有兩年多了吧?”
“馬上三年了。”
“找對象了么?”
旁邊的小高插嘴說,“人家都結婚了。”
“怎么不通知我去喝喜酒?”我佯裝生氣。
正盯著棋盤的經理抬起頭,說,“通知你了,你說有事去不了,讓我代你隨禮。”
“是么?”我拍拍腦袋。
“下棋,下棋。”她催我。
我手里捏著棋子,并不放下去。“你們這兒的生意不如過去。要抓緊想想辦法。”
“這不是你操心的事,快點下棋。”她有些不耐煩。
時間就這么流淌過去,外面不知不覺暗下來。我掏出手機看看點,扔下手里的棋子,說,“到點了,該回家吃飯了。”
“把這盤下完,再走。”經理有些不甘心,今天她輸的局數比昨天還要多。
“明天接著下吧。”
“這盤你準輸了,不能走,下完再走。”
“那就算我輸了。”我笑笑,摸起桌子上的煙和打火機,就往外走。
她在后邊追著說,“一看不行就跑,賴皮。”
出了茶莊,我開著車在街上轉悠。前面路口左轉,新湖路;過兩個路口,左轉,青龍街;農業局路口,左轉,解放路。直行,過兩個紅綠燈,左轉,新一佳超市的停車場。怎么到了這兒?我問自己,天天傍晚來這兒你也不膩?
不行,今天要換個地方,我把車又啟動起來。這時候我聽見有人敲車窗,咚、咚、咚、咚,四聲有節奏的聲響。原來是停車場負責收費的大媽,她穿一件藍色羽絨服,外面套了件黃色馬甲,左臂上有個紅袖箍,一個淺綠色的書包掛在胸前。我推開車門下車,從褲兜里掏出兩塊錢給她,她接過來,“今天沒票了,明天給你吧。”她忙著整理書包里的零錢,看都沒看我一眼。她頭上有一縷白發被風吹起來,那樣子讓我想起房頂上孤零零的枯草。
“行,什么時候給都行。”我應著,快步向馬路對面走過去。
走到馬路中央,躲閃往來車輛的時候,我才想起來剛才打算換個吃晚餐的地方。看看近在咫尺的加州牛肉面館,算了,明天換地方。我想。
店里人不少,熱氣騰騰的,我看了一眼最里面墻角的那個位置,幸好還空著。剛坐下,那個右眼角有痣的女服務員就冒出來。還沒等我說話,她就說,“一共三十二元。”我笑了,她也笑了。我發現她今天打了藍色的眼
影,沒有過去好看。
今天牛肉面里的湯比往日少,紅油肚絲里的紅油放多了,辣得我直咧嘴。我發現也有如我一樣單身的食客,他們心不在焉地吃著,時不時左顧右盼。是不是在等身邊的座位不再空著?
吃完飯,我站在這座小城最繁華的街邊抽煙。霓虹燈、車燈閃爍,還有明明滅滅的煙頭,讓眼前的世界迷離、虛幻。我在想像那些坐在車里的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他們的心似乎飛到了家里。那里有暖心的問候,飯桌上熱氣騰騰的飯菜。當然最重要的是有那么一個能和自己說貼心話的人。想想自己,心情變得就像剛才桌子上只剩下點湯汁的空碗一樣。臉開始發木,跺腳,活動身子。去哪兒呢?我不停地問自己。
四
后來我萌生了個念頭,摸出手機給小呂打了個電話。小呂是我過去的一個同事,辭職后做酒水生意,賠了。現在在開夜班出租車。十多分鐘后小呂開著出租車到了。我把自己的車鑰匙遞給他,說,“你休息休息,我替你開會兒出租。”
轉了兩個街道,商業銀行門口上來一個戴棒球帽的男人。他坐在了后座,其實我是想讓他坐到前面。男人要去北園。
我說,“這天氣夠冷的。”
他說,“嗯。”
我說,“聽說北園要拆遷,有這回兒事么?”
他說,“嗯。”
我說,“解放路修路呢,要繞道走湖濱路。”
他說,“嗯。”
之后出租車里開始沉默,這讓我有些不舒服。透過后視鏡,我看見他正在擺弄手機,手機屏幕發出一閃一閃的藍色,他的臉被映襯得有些鬼魅。街上很清冷,路燈無精打采的。盡管對面沒有車駛過,我還是不時摁下喇叭。時速表上的針始終是在三十到四十之間。我突然覺得喉嚨有些癢,老想咳嗽,可就咳不出痰,我只好拼命地咽吐沫。打開車窗,風呼呼地鉆進車里,衣領子一下被吹起來,不時拍打著我的臉,一會兒半邊臉就木了。
那男人始終沒有抬頭,他的手機嘟嘟不停地來著短信。這個點,他怎么這么忙?和誰在聯系?朋友?這個點和朋友有什么事?老婆?不像。那是情人?直接打個電話多省事?現在我能給誰打個電話,聊聊呢?王胖子?這小子生活有規律,早睡覺了。李哥?不行。這時候給他電話會讓他生氣的。女的能打給誰呢?王萌?要是她對象接電話,明天準得出大事。
遠遠地看見了金碧輝煌的霓虹燈,馬上就到北園了。這時候我才發現空車燈還沒按下來,趕忙按下去。隨即車里響起一個有氣無力的女聲,她好像剛剛睡醒,“歡迎乘坐德州出租車,投訴熱線;xxxxxxx。”
下車前我對戴棒球帽的男人說,走好。回應的卻是一聲重重的關車門的聲音。我看著他消失在夜色中,心里空蕩蕩的。嗓子癢得越來越厲害,我用力咳嗽了一聲,終于咳出一口痰,我把頭探出車窗,使勁吐了出去,那口痰在空中滑行了幾秒鐘,便被遺棄在空蕩蕩的馬路上。
在錢柜門前我拉了個女孩。大冷的天她穿著裙子。一上車,她邊哈氣邊說,快點走。
我問她去哪兒。女孩不耐煩地說,“往前開就行。”邊說還邊回頭看。因為不知道目的地,車開得很慢。她呵斥道,“你快點!”
我問她,“有急事啊?”
“有人跟蹤我。”她這話讓我一緊張,掛錯了檔,車差點熄火。
我透過倒車鏡,看見后面有幾輛車,趕緊提速。快到路口的時候,我問她,“往哪兒拐?”
“隨便,快點就成。”她趴在座背上向后張望。
車開到東方紅路,剛才跟著的幾輛車都沒了蹤影,她才坐正位置。我問她,“誰跟蹤你啊?”
“我女朋友和她男朋友。”她抿了抿額前的頭發。
“你女朋友和她男朋友?”
“是的,他們想害我。”她從坤包里拿出一支煙,熟練地點上。
“你怎么確定他們要害你?”
“他們害了好多人。”她吐出一口煙。煙飄到前面,有點遮住視線,我趕忙用手扇扇。
“那你趕緊報案,這多危險。”
“沒用的,沒有證據報了也是白報。還會讓他們更加痛恨我。”女孩眉頭緊皺。
“這一切都是你的懷疑?”我扭頭看看女孩,她一本正經的。
“嗯,別看她表面對我好著呢。其實早就琢磨害我。
她還以為我看不出來。”
“她為什么要害你?”
“她就是這種人。有個女的可能已經被她害了。”女孩搖下車窗,把煙頭扔了出去。煙頭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落地后,濺起的點點火星,飄起來,又迅速消失。
“是么?”見我的口氣有些懷疑。她說,“那個女的臨消失前,我看見他們兩口子在背后嘀嘀咕咕。肯定是商量怎么害她。”
女孩說完指著前面路邊的一個網吧說,“就在網吧門口停。”
我看著女孩進了網吧的門,又看看旁邊的錢柜,里面依然燈火輝煌。
第三個乘客是一個五大三粗的醉漢。他坐在副駕駛的位置,立即把座位塞得滿滿的。他嘴里吐出一股酸臭的味道,讓我有些厭惡,趕忙把車窗的玻璃搖下來。他去國棉廠宿舍,有些遠。路上他跟我要煙抽。拿到煙,在打火機打著的一剎那,他轉動煙身看了看煙的牌子。點上深深地吸一口,然后緩緩地把煙吐出去。享受了半根煙后,他說,“小伙子,你怎么抽這么好的煙,掙的錢夠抽煙么?”我趕忙解釋,“這煙是一個乘客落下的。”“那好。”他說著把煙揣到兜里。
我瞥了他一眼,心中有些不快,心想,怎么還有這種人?
“中華煙就是好抽。”我沒確定他這是自言自語還是對我說,所以沒有搭腔。
“小伙子要會過日子,現在掙錢多不容易。”
我哼著哈著。
“我給你個信息,保證你晚上能多掙點。”他搖開車窗,吐出一口痰,我感覺有唾沫星子被風吹到右臉頰上,惡心得要命,趕緊用手擦擦。心里想,把他送到,得找個地方仔細洗下臉。
“我剛才從碧波浪沙出來,那可是個高檔的洗浴中心,那里的小姐啊,嫩得都能掐出水來。”他嗓子深處滾出低沉的笑聲。
“那地方我們出租車司機可去不起。”
“你肯定消費不起,我三天兩頭地去。”煙都抽到過濾嘴了,他還使勁在裹。
我沒吱聲,時速表上的指針迅速上升到六十。
“我的意思不是讓你去玩,而是讓你拉客去。碧波浪沙的老板講究,介紹一個客人去,給提成二十。”他盯著煙屁股看了得有十秒鐘,才把煙頭扔了,我看見他右膝蓋翹起來扭動了幾下。
到黑馬市場路口正趕上紅燈,我沒減速,沖了過去。
“小伙子,好好感謝我吧!”他拍了拍我肩膀。
“謝謝,謝謝。”我應付著。
說話間就到了國棉廠。我停住車,他問,“到了?”
我說,“到了。”
他開開車門剛邁下一條腿。我趕緊說,“大哥,還沒給錢呢。”
“錢?我沒錢。”他扭過身笑吟吟地說。
“大哥,一看你就是個有素質的人。我們開夜班出租的不容易。這趟你要不給,今天晚上就白干了。”我覺得自己的口氣可憐巴巴的。
“算你小子會說話,不用找了。”他扔下十塊錢滾蛋了。
計時器上顯示的是二十五塊四。
快零點的時候我把車交給小呂,還有皺巴巴的二十五塊錢。正打算走,小呂喊住我,“哥,請你到永和宵夜。”我回頭看看他,眼睛有些發澀,“咱們還是去火車站那邊吃燒烤吧。”
還是我開著出租車。車開到廣場天橋底下的時候,小呂說:“哥,上火車站你咋開到這里了?這不是去永和的路嗎?”我恍然大悟趕忙急剎車,頓時路面上響起刺耳的摩擦聲,我的身子也跟著晃了晃。小呂抓住車頂的扶手,關切地問我,“哥,你怎么了?”我趴在方向盤上片刻,抬起頭緊咬著嘴唇說,“沒什么。”
五
大前年的冬天,中心廣場的天橋下,我清楚地記得她穿著艾格牌的白色羽絨服,是我們在保龍倉買的。她緊緊摟著我的脖子,她的哈氣鉆進了我的衣領,癢癢的,又暖暖的。她伏在我耳邊說,“沒有你,我的生活會是什么樣?”
責任編輯:劉照如